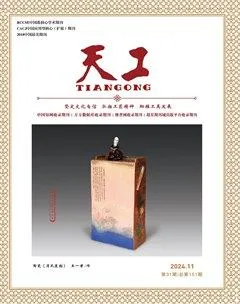埃尔·韦沙希雕塑的形式语言
[摘 要]埃及雕塑家埃尔·韦沙希以其作品大胆的人体结构变形、空间形式变化和几何节奏韵律而闻名。他的早期作品深受个人经历影响,常展现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迷茫,通过雕塑探索情感表达的新方式。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学习创作期间,韦沙希吸收了立体主义、布朗库西的理念以及亨利·摩尔的孔洞理论,促使他的作品从传统向抽象转变。他后来的创作不仅强调形象的延续与解构重组,还表现出对重力的抗争与克制以及强调女性形象的母性特质。韦沙希的雕塑语言独特,融合了本土艺术与国际现代雕塑理念,展现了个人情感与先进艺术理念的结合。他的作品不仅丰富了埃及雕塑艺术,也为世界现代雕塑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 键 词]埃尔·韦沙希;雕塑;形式语言;解构;空间变化
[中图分类号]J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556(2024)31-0024-03
文献著录格式:苏卓睿.埃尔·韦沙希雕塑的形式语言[J].天工,2024(31):24-26.
埃尔·韦沙希(El-Wechahi),埃及著名雕塑家,他继承了埃及丰富的雕塑遗产,在传统学院派风格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对西方当代雕塑大师风格的吸纳与学习,整合了古埃及的形式美感和现代雕塑的革新风格,不断探索新技术,大胆尝试结构处理与注重将物体从重力中解放出来等现代性创作路径,通过有意打破现成的旋律、节奏组合来建立自己的雕塑风格。对韦沙希雕塑风格的形成路径进行研究,可以为当代中国青年雕塑家在立足于本土形式风格的前提下,将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形式语言为己所用。
一、早期形式的探索
韦沙希整个艺术生涯的雕塑作品充满着对雕塑对象结构的大胆变形与处理,他的作品中透露出对空间形式变化和几何节奏韵律的迷恋,这正是其艺术天赋之所在。在早期的艺术与学习生涯中,他更多的是基于传统学院派在表现形式上的探索。
韦沙希早年母亲去世,母亲在韦沙希的童年成长环境中一直是缺失的。因此在早期缺少母爱的生活环境的影响下,韦沙希产生了对后果不确定性的恐惧。韦沙希的父亲反对他进入美术学院学习。父亲的不支持以及母爱的缺失,使他的艺术一开始充满了犹豫和担忧。在早期的艺术作品《寒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韦沙希的恐惧,压倒性的表现主义与超越灵魂痛苦的高昂的象征主义相协调。从形态和结构上看,一个人颤抖地拥抱着自己,瘦弱细长的双腿不安地弯曲,头部紧紧地贴在胸腔上,似乎不愿意面对寒冷,表现出一种脆弱和孤独的情绪。从内涵上看,韦沙希长期生活于埃及这个气候温暖的国家,寒潮并不常见且冬季短暂,在创作这件作品时,韦沙希只是一名大二学生,结合韦沙希之前的成长环境与经历,这件作品表达了他对自身前途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与迷茫,好像他拼命地拥抱自己是为了隐藏他此时的软弱和灵魂的空虚,不去面对质疑者的窥视和令人不安的锐利目光。
与《寒冷》相同的作品还有韦沙希创作于1963年的毕业设计《丹沙瓦的殉道者》,这件作品于同年获得了第五届埃及亚历山大双年展奖。韦沙希沿用了对人体结构的拉长处理,夸大了颈部的比例,表现出该结构因受绞刑的摇晃和拉长,双脚向下垂直拉长,二者共同成为悬挂的有力象征,但人物整体却有一种向上漂浮的感受,可以看到韦沙希在探索雕塑如何对抗重力。人物的手势表现出韦沙希早期关于信心与恐惧的二元性表现:人物右手做了一个投降的手势,像是对命运的认同,左手却坚持着它物理存在的最后迹象,徒劳地紧握着,试图抓住正在向上升通道漂浮的本体,一种矛盾的情感,即抗争与顺从的对立关系通过手掌的不同形态体现出来。雕塑底座被韦沙希处理成古埃及纪念性门道的建筑特色,建筑形式的底座与人体的量感对比无限放大了人物本体的精神力量,于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和悲剧的时刻被完美地描绘出来。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风格也影响着韦沙希的早期作品,他融合了表现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了最大限度的还原处理,以最少的细节呈现出来,没有任何次要元素和额外的补充。如韦沙希于1964年创作的雕塑《非洲》中,人物形象被压抑的反叛的神经所充斥,它穿过伸展的颈部的整个垂直轴向前倾斜成轻微的弯曲,保持踮起脚尖,以增加我们对挑战的感觉的影响,而这种感觉就在于头向后仰,下巴向前伸,嘴巴向前张,就像准备将他伸展的手臂向后伸展,形成一个既克制又横扫式的突袭。这座雕像特别让观者想起了贾科梅蒂著名的《行走的人》,尤其是向前弯曲的姿势。
韦沙希早期的作品可以看到来自如人体结构虽然变形但仍遵循客观规律的学院派风格和埃及传统造型着重于形式感与程式化的影响[1],此时期这种颇具悲伤的形式表现作品有1962年创作的《自由》《坐着的女孩》与1965年创作的《衰败》。韦沙希将迷茫和彷徨的心绪投射在自己的雕塑上,展现出哀伤与沉重的形式语言,同时这种激烈的情感冲突也促使韦沙希探寻更有力度的表达形式,来将雕塑的空间与结构形式作为情感宣泄的出口。当压抑的感情积累到在现有的雕塑形式上无法释放时,雕塑家或者艺术家自然会找到通道让它们从潜意识中流出,直到它们在雕塑的表面和尺寸上释放出来。韦沙希后续的雕塑形式变化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对于形式的转变
毕业后,韦沙希前往西班牙和意大利进行艺术创作与学习(西班牙1967—1971,意大利1971—1974,西班牙1975—1978)。在此期间,立体主义、布朗库西雕塑中的延展性、高度、灵活性、雕塑表面的光滑感和在空间上的流动形式以及亨利·摩尔的孔洞理论给予了韦沙希养分。
通过对同一主题的两件雕塑,即1967年创作的《鸽子 1》(见图1)、1972年创作的《鸽子 2》(见图2)的对比,可以明显分析出韦沙希对雕塑形式语言的转变过程。首先,在《鸽子 1》中,韦沙希更倾向于布朗库西对雕塑光滑表面以及形体流线型的概括处理方式[2],但理念却不尽相同,布朗库西1912年创作的雕塑《迈亚斯特拉》可以作为着力点进行分析。布朗库西在《迈亚斯特拉》中,尝试着冲破固定的外形结构去表现鸟的本质运动,为了突出飞翔,鸟身和脖颈被明显拉长,翅膀和身躯融为一体,成了一个完整的椭圆形,尾羽部分变成了半圆锥状,后肢拉伸成长方体,都是为了表现向冲破空间的限制发起冲锋的感受,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3]。而韦沙希的鸽子则截然相反,从鸽子胸腔的隆起与颈部的弯曲可以看到相近的提炼与表现手法,但却以翅膀作为两个支点,好像在避免坠落的危险,这只鸽子虽然表面上充满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却反映出一种压抑的痛苦。与布朗库西在空间无限向上延伸的鸟相比,韦沙希的鸽子更注重空间上的稳定,显然这两位艺术家所抗争的对象是截然不同的。因为韦沙希童年时期的迷茫、彷徨与对雕塑的热情追求继续在韦沙希的心中震荡碰撞。此时期,韦沙希的雕塑形式较埃及时期已经有了明显变化,虽然结构上仍旧没有脱离客观对象,但更加追求空间上的延伸感和对对象表面的提炼归纳,开始逐步脱离传统的形式。
到《鸽子 2》时,韦沙希已经将原有的封闭空间结构打破,整个形象上充满了几何化的孔洞与负空间关系,这种孔洞的叠套、穿插与薄厚变化直接让人联想到亨利·摩尔的形式语言。但亨利·摩尔的孔洞是与其流畅、自然的形体表现所配套的,是其从原始雕刻与自然景观中所汲取的灵感,并为了让自己的雕塑重新回归到自然。正如摩尔自己所说:“空洞的神秘性——与那些在山脊和悬崖上具有不可思议的力的岩洞是一样的。”[4]因此,摩尔多偏好巨大的尺度、流畅浑厚富有体量和质感的形体以呼应自然。而韦沙希不同,此时他仍保留传统的雕塑结构认知、从布朗库西那里得到的关于空间的延伸和表面光滑性的风格偏好以及与时代艺术发展的潮流相比立体主义稍显落后的多视角变化的空间观察方法。因此在这件雕塑上,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导致了结构的散乱、表面的封闭结构与孔洞形成的空间不相融使雕塑整体显得单薄以及观看节奏上的不连贯,但不可否认的是,韦沙希通过对布朗库西以及亨利·摩尔的形式语言的吸收,正在萌发解构意识。
三、形式语言的成熟
自韦沙希的雕塑语言转变后,在70年代及以后,他探索利用抽象形式,提炼解剖结构中固有的美学和结构关系,除了汲取布朗库西、亨利·摩尔的雕塑形式外,亦吸纳了奥西普·扎德金的“新立体主义”和贾科梅蒂满足于基本线条,其中以块为中心概念的空间几乎完全从这些雕塑的结构实体中消失的特点后,通过形象化和抽象化交替的方法,形成涵盖了多种形式表现语言的特点。

(一)对形象的延续与解构重组
韦沙希以客观形象的存在作为基础,减弱叙事和人物的塑造来激发表现力和象征性,以牺牲结构细节来维持本质的力量。然后将抽象用于探索空间的可能性,通过深入解构各体块之间存在的重叠关系,只投入最低限度的传统概念上的基本部件,让观者可以通过经验来识别雕塑的形象。接着将孔洞形式分别转换为空腔和凹槽,清空了大部分封闭空间,这样雕塑上的实体就成了依靠线条和角度存在的假定体积,这属于解构主义的形式[5][6]。因此当观者改变观看雕塑的位置时,雕塑的空间形状与边缘曲度会受到周围光线的影响而变化,使得雕塑的空间、方向和内部运动的延伸充满了想象上的可能性[7]。同时韦沙希延续了布朗库西的理念,在《思考中的女人》(1973)、《空间中的鸟》(1973)、《沉默》(1975)、《阿米拉》(1978)等雕塑上的体现非常明显。
(二)对重力的抗争与克制
这种抗争本身并不是传统观念上像贝尼尼一样单纯的形体对重力的脱离模式,而是在物质存在所施加的条件以及结构材料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从而创造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把雕塑的内在从物质需求中解放出来,把它变成透明的精神存在——在付出最大努力后,它即将实现救赎——但其形式依然平衡和均衡,这创造了一种普遍存在于韦沙希雕塑中的感觉,即让观者感受到一种被困住的奋斗能量。这种能量正在寻找从这些雕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那一刻,以显示被束缚的精神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精神往往倾向于反抗,寻找机会摆脱固体材料的束缚。例如,1975年创作的《不可能的跳跃》,其特殊的形成即将在努力和努力的压力下爆发,在雕塑保持平衡的空间中飞翔,而没有离开我们正在寻找其运动终点的物质存在。因此他的雕塑作品的平衡建立在一个小的支点底座上,通过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雕塑体块以此为发射脉冲,并在其上方进行空间穿透,以平衡雕塑各部分相互施加的力矩,实现雕塑整体块体稳定性与设计动力学和扭曲线条灵活性之间的复杂兼容性。明显表现出此特点的雕塑作品有《展望》(1986)、《尝试寻找平衡》(1987)和《20世纪人类》(1990)。
(三)女性形象中的母性
通过对韦沙希成熟时期的作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女性在主题和形式层面上具有的特殊地位,尤其是以母亲身份出现的女性形象,如1987年创作的《女人和马》,韦沙希基于研究块体空间的形式和结构可能性,使表面从彼此的内部连续出现,以某种方式出现和消失,导致视觉循环的出现,观者的眼睛来回、上下、进出,连续不停地试图控制这些持续的旋转关系,马匹姿态稳定而高昂,从环抱马匹脖颈的女性形象和马匹的脊柱间形成的圆弧空间可以说是属于母亲的保护的凝聚点,一种温和而不容置疑的力量孕育其中。此外,还有《第一步》(1978)、《女人与海》(1992)、《家庭》(1992)、《十七岁》(2006)等雕塑,可以明确看到韦沙希对女性形象的诠释更偏向于他对母爱缺失所带来的遗憾下的潜意识投射。
四、结论
通过对韦沙希雕塑形式风格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对先进的雕塑理念充满着好奇心与学习动力,并且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这些雕塑理念,结合自身的经历与情感偏好,将自己的雕塑形式语言独特化。其中在如何处理当代雕塑理念的本土化上,主要依托于对自己情感的仔细分析,在大量实践后,选取其中可用的部分进行深入创造,因此实现了两者的完美融合。
参考文献:
[1]刘建华,钱显毅.古埃及雕塑的艺术特征及其影响[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2):324-326.
[2]张耀.20世纪初西方雕塑艺术的重构与简约:以布朗库西为例[J].美术观察,2016(4):124-125.
[3]杜义盛.布郎库西和他的“鸟”[J].雕塑,1999(S1):58-59.
[4]陆军.摩尔艺论[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5]周越.走出来的语言:浅析解构主义[J].美苑,2003(3):42-43.
[6]何忠.难解的结:“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J].装饰,2003(2):47-48.
[7]刘玉庭.论雕塑的空间表现模式[J].艺术设计研究,1999(2):15-18.
(编辑: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