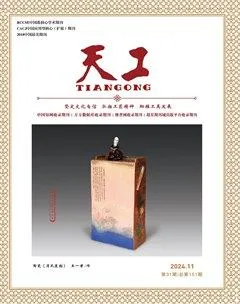商代豕磬相关问题探讨
[摘 要]铜磬是商代打击乐器的一种,主要集中出现在长江流域,从已发现的商代豕形铜磬来看,其遵循了石磬的形制和音乐性能设计,有着越文物的典型特点,器身上的乳钉纹饰非单纯记音符号,器身整体造型与纹饰反映了商周时期南方地区人们的图腾崇拜。铜磬是适应南方环境而生,跟南方大铙一样,有着祭祀娱神功能,充实了南方音乐文物发展脉络,而因自身局限,最终消失在向乐器发展的道路上。
[关 键 词]音乐文物;娱神礼器;图腾崇拜;豕磬;音乐性能
[中图分类号]J5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556(2024)31-0012-03
文献著录格式:袁鑫,尹衡炎.商代豕磬相关问题探讨[J].天工,2024(31):12-14.
一、类型学分析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2件铜磬(简称上博磬,见图1),传为1989年湖南湘阴县城关镇出土。两件铜磬的形制、纹饰基本相同。一件长56.3厘米,高28.5厘米,重17千克。另一件长50厘米,高26厘米,重13.55千克。整体造型为野猪形象,口微张,吻部上卷,腹下部有两曲踞状足,弧背上饰鸟状脊,脊下有一长方形穿孔。磬身饰乳钉10个,臣字眼部位饰1个乳钉,磬身中部的乳钉外饰火纹,乳钉之间有阴线云雷纹,磬身两面乳钉个数相同、纹饰相同。
现藏于湖北长阳博物馆的铜磬(简称长阳磬,见图2),1992年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磨市镇官家冲村白庙山坡下土层中出土。通长46.4厘米、高25.3厘米、上部厚2.8厘米、颈厚2.2厘米、下部厚1.5厘米,重9.1千克。整体作板状,呈野猪造型,嘴微张,唇上翘,尾短,弧背饰一组似猪鬃的凤鸟扉棱。磬身两面各有10个乳钉,臣字眼部位饰1个乳钉,中间1个较大乳钉周围饰火纹,其余9个略小,两面乳钉数量一致、位置不对称。弧背上部有一长方形穿孔,下饰呈卷云纹的足,后足断缺,器身满饰阴线云雷纹。
湖南博物院收藏的铜磬(简称汨罗磬,见图3),2012年于汨罗市白塘乡曹家村出土。通长52厘米,高28厘米,厚1.5厘米,重13.05千克。通体呈匍匐状,嘴微张,上吻部上卷,弧背上饰一组似猪鬃的凤鸟扉棱,背脊下有一供穿绳的圆形穿孔,短尾下弧。腹部饰9个乳钉,中间乳钉外饰一周火纹,腹中部饰鱼鳞纹,吻部及肩、下腹环饰回纹、云雷纹。腹下中间有巨大的三角形生殖器室,两侧置卷云状扉棱的屈足。
除了已发现的实物,文献另有记载同类型铜磬,如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王黼编写的《宣和博古图》,记录了宋王宫宣和殿珍藏的4件铜磬:“周雷磬”2件、“周琥磬”1件、“周云雷磬”1件。马今洪在其《青铜磬琐论》一文中对这4件铜磬的形制、纹饰有具体介绍,并将尺寸换算,进行了对比,这里不再赘述。
二、音乐性能分析

磬是我国古老的打击乐器。早期石磬多为特磬,即单件的大型磬。1950年,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虎纹特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该器制作精致,纹饰精美,是商王朝重要的礼乐器。出土于安阳殷墟的一套石编磬,尚存3件,其上皆有铭文,分别为“永启”“永余”“天余”,每件可出一音,3件的音阶结构相当于今天bE调的sol、la、do。
同样作为乐器,铜磬的音乐性能如何?以汨罗磬测音数据为例,以倨孔下方即磬身正中所刻火纹处的乳钉为起点,以逆时针的方向审视豕磬各乳钉的音高数据,可见整个音高呈由低到高的排布(见图4)。该磬的最低音为倨孔下方,即磬身正中所刻火纹处的乳钉,音高为“#G3+3音分”,最高音为磬的下半部分,从左往右数第1个乳钉,音高为“#C5-4音分”。从各个乳钉处所测音高来看,各个重复音的音高具有很大的统一性,同一八度内的重复音之间的音高差值最大为5音分,而5音分的差值人耳很难分辨,故可忽略不计。由此看来,豕磬的音高在铸造时有主观布局的可能性。
以豕磬倨孔的位置为中线,将其分为前后两部分,左侧(即头部一侧)的面积相较于右侧(即尾部一侧)较小。故此,其悬挂演奏时应该是尾部一侧下垂,头部上扬。按照石磬的演奏习惯来看,应是敲击下垂一侧(即豕磬尾部一侧)。尾部一侧的乳钉数量较多且排布较之于头部一侧更为分散,音响效果应好于较密集的排布,也更方便敲击。再从其各部分音高数据来看,其下垂一侧的乳钉的音高多为小字组和小字一组,在实际的演奏中也更加实用,磬身正中所刻火纹中心处的乳钉也与尾部一侧几个乳钉的音高一致。如果按照磬身比例将豕磬和石磬的比例进行比较的话,其身子到尾部应对应“鼓部”,最右侧的两个乳钉也对应鼓上角和鼓下角,而从一般石磬的测音结果来看,也是鼓上角和鼓下角的音最高。故此可以推测豕磬虽形制特殊,但其整体形制比例和音高设计仍遵循着石磬的设计思路。
从五个乳钉的频谱来看,能看出敲击同一个乳钉会有两个相对较强的音高先后出现,听起来也很杂,音高不明确,故可以确认下面的乳钉应该是没有作为一个记音符号使用。目前来看,乳钉的目的可能更多还是用于消除杂音,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它可以作为不同敲击点的标记,因为不同位置音响的变化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

商代的磬还没有完全定型,并没有形成我们今天所认知的设计和布局。磬上的乳钉是否和钟上的枚一样起到消除高频振动的作用是有待商榷的,因为从石磬的声学分析实验来看,更为平滑的表面更适合板块的振动,具体可参见《编磬音时程特性的分析》①②。
在马今洪的文章中,上博磬的测音数据相较于汨罗磬和长阳磬较为独特,其文中的测音数据均为音乐学记法,即#c1 = #C4,其音域为:e2-c4。汨罗磬和长阳磬的测音数据均采用的是物理学记法,笔者尝试将上博磬的数据转写为物理学记法,并将三者一起比较,结果如下表。

从表1可以发现,上博磬的音域比汨罗磬和长阳磬至少高了一个八度,而从马今洪文中给出的形制数据(青铜磬形制数据)来看,上博磬无论是长、高、厚还是重量,都是三者中最大的一件,其音高应该也是三者中最低的。从这一角度看,其形制数据与测音数据并不匹配。此外,从汨罗磬和长阳磬的形制数据与测音数据的比较来看,两者都遵循了板块状振动体音高变化的基本原理,即通过调整磬体的长度、厚度来调整其音高,简单来说就是长度越长,音高越低;厚度越薄,音高越低。
三、造型与功能
湖南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商周时期的动物造型青铜器,最有名的如豕尊、象尊、牛尊等,这些动物造型的青铜器反映出商周时期湖南先民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对比湖南湘潭出土的豕尊,以及器身上的鸟纹和鱼鳞纹,汨罗磬的造型恰如湘潭出土的豕尊的“侧面照”。毋庸置疑,豕磬虽非旋律乐器,仍具有一定的乐用功能,是用于某种特殊祭祀场合的礼乐器。观察铜磬上的乳钉纹饰,很难将其定位为记音符号,其所发音高是不能构成音阶的。那么,这类型铜磬上的乳钉既与音频无关,其如此规律的布局,又有何寓意?
据《史记》《尚书》等文献记载,后羿射日的故事发生在夏商之际,与豕形磬所属年代相近。豕磬上有10个乳钉,中间的乳钉居中,外一周的火纹即代表着太阳光芒,另外9个乳钉围绕其排列,与后羿射日的故事有着相似性。
甲骨文中有关于殷商时期养豕的记载:“陈豕于室,合家而祀。”豕很早就被家庭饲养,同时是祭祀的主要物品。与铜铙通过敲击发出声音沟通天地一样,动物造型(豕)的青铜乐器,同样可以达到沟通天地的作用。
越人视鸟为保护神,越地有鸟田的传说,《越绝书·记地传》记载:“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小大有差,进退有行。”越人对鸟的崇拜,表现为越地铜器上的鸟饰扉棱、豕尊上的立鸟纹饰,以及肩部的鸟饰等。
近年来,在汨罗地区出土的一件觥形器,其造型之精美,显示出拥有者地位的不一般,显然是适用于较为重要的场合。其与豕形铜磬发现地相距不远,说明汨罗地区在商周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豕磬和觥形器显然同样用于重要祭祀场合。
总之,铜磬的整体造型和乳钉纹饰,以及器身上的鸟饰扉棱与越文化的太阳崇拜、鸟崇拜和豕崇拜似有联系,是越地独有的太阳、鸟、猪图腾崇拜的三位一体。
四、源与流
铜磬的年代为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其形制受到了中原石磬的影响,纹饰上又有着南方青铜器的典型特征。两种质地的磬是否有联系?
出土资料显示,早期石磬多分布于黄河流域,造型扁长,通体打制,整体难以看出具体为何种动物。石磬多在大墓中发现,且还出土有其他类型的乐器;同时期的南方,石磬发现数量很少,仅在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址、四川巫山大昌镇双堰塘遗址出土了石磬。与此同时,既具有殷墟文化特点又有本地元素的铜磬在长江流域多有发现,且无一例显示有具体的出土环境与共存器物。出现这种不同,或许跟两者的功能有关,北方石磬更多是承担祭祀功能,是权力的象征,南方铜磬则更多的是祭祀、娱神功能。
晚商时期,石磬仍占多数,同时出现了成组的编磬,石磬的功能逐渐由仅承担打击任务的节奏形乐器向可以演奏的旋律性乐器发展,其音乐表现力进一步增强。铜磬从目前出土实物和文献资料来看,似乎很难成编。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铜磬算不上旋律乐器,其音质较为嘈杂,延音也很短,从整体测音数据来看也不足以构成音阶。从汨罗磬的测音数据来看,其音高有一定的规律性,结合其他豕磬的数据来看,这种规律也不具有普遍性。商朝出现的铜磬,也用于祭祀,可能是与其他乐器共同使用,承担伴奏的作用,非主旋律乐器,且以往的金石乐器也多是起这样的作用。
石磬材质多为石灰岩,而石灰岩又微溶于水,因此石磬在南方无法长期保存。且早期石磬可能无法兼顾音高、纹饰和耐用度这些因素。此时铜磬就应运而生,其更适应于南方环境。从音乐学角度看,其音域和音色过于短,更适合室内祭祀。它与铙同用时,音高一致,使得两者可以轮替或同时敲击。此外,铜磬虽同铜铙一样,多单独发现,但发现地点并不是在山河湖畔,可能与铜铙置于天地间祭祀自然神灵有关,铜磬较铜铙轻便,能适应不同祭祀场合所需。
值得注意的是,汨罗磬上只有9个乳钉,另一个靠肩部的穿孔,非常规整,所见为圆角方形而不是圆形,穿孔的直径和乳钉的直径大小接近。有可能是当时工匠忘了铸造器身的穿孔,临时将其中一个乳钉改制成了穿孔,与早期的石磬的圆形穿孔形制似有联系。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铜磬跟不上音乐实践的发展,单面的敲击不能发出和声和双音,音色、音高、音长都满足不了需要,进一步乐器化难度较大,因此最终消失在向乐器发展的道路上。
参考文献:
[1]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2]李纯一,方建军.考古发现先商磬初研[J].中国音乐学,1989(1):82-89.
[3]王子初.石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J].中国音乐学,2004(2):5-18,2.
[4]方建军.西周磬与《考工记·磬氏》磬制[J].乐器,1989(2):2-4.
[5]王子初.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钟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之二[J].中国音乐学,2007(1):5-36.
[6]高蕾.中国早期石磬述论[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2.
[7]王安潮.石磬形态通考[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03.
[8]王秀萍.乐器学视域下的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研究[J].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4.
[9]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98.
[10]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462.
[11]马今洪.青铜磬琐论[J].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6(00):16-26.
(编辑:王旭平)
注 释:① 徐雪仙、冯光生、褚梅娟:《编磬音时程特性的分析》,《乐器》1984年第3期,第1-3页。
② 徐雪仙、冯光生、褚梅娟:《编磬音时程特性的分析(续)》,《乐器》1984年第4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