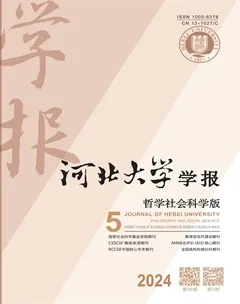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何以困难重重?
摘"要:产教融合是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能力的关键所在,也是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主题。与顶层设计相比,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在实践层面却陷入落实困境。作为典型的产教融合政策,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执行关涉产教系统的多个部门与主体。以教师企业实践政策为研究对象,展开案例研究,可以发现,由于受到层级性治理与多属性治理机制的双重约束,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可能会出现失真执行、象征执行的现象。究其根源,受限于“条块分割”体制,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容易走样,偏离政策预期目标,这也是制约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顽疾所在。解决顽疾的关键在于,发挥各级党委的统筹作用,尝试建立临时性领导小组,通过高位推动,在短时期内将处于高度分化状态的“条块分割”体制重新“粘合”,并通过经费保障、信息交流等方式辅助提高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效率。
关键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层级性治理;多属性治理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24)05-0152-09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24.05.014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后,我国一直在竭力探索适合国情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虽然不同类别和发展阶段的制度条款、基础设施、社会态度会影响一个国家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成功,但是一些欧洲国家成功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仍然被频繁介绍与应用到亚洲和非洲国家[1]。在发展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我国也曾试图引进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但“水土不服”的现象比比皆是,往往只是更多地借鉴了该国办学模式的要素框架,却很难真正达到实际的育人效果。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不只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应该跳出教育视域寻找其逻辑起点[2]。任何一个国家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形成都有其经济社会基础,盲目照搬他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只会陷入歧途,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方为可取之道。
深化产教融合,始终与产业、行业、企业等保持密切联系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应有之义,也是职业教育办学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任何一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形成都离不开产教融合这一逻辑主线。产教融合是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能力的关键所在,不断提高产教融合效益也是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工作。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我国对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019年以来,职业教育领域连续出台4份高规格文件,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均将产教融合列为重点改革工作。
然而,与政策层面的大力推动相比,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在实践层面却遭遇落实困境。有研究认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现实困境表现为,产教融合的内外部支持环境并不成熟,产教融合的运作平台没有真正建成,产教融合的实施要素欠缺[3]。也有研究认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经过多年的规模化仍面临制度规划的空泛化、市场合作的盲目化与特定组织合作的松散化困境[4]。但长期以来,产教“融而不合”、校企“跨而不实”的现实困境始终难以破题[5]。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困境展开了解释。如有学者运用博弈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分析框架发现,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合作结果不确定、法律制度支撑不足等造成了产教融合困境[6]。也有学者借助组织边界理论视域指出,高校、企业、政府的有形物理空间、身份意识、规章制度以及组织内部成员的特殊认知等属性,限制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深度[7]。还有学者基于系统理论、生态学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等多学科视角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践壁垒进行审视,将产教融合困境归结为产教融合系统内外部缺乏科学设计、未能形成产教融合生态圈、缺乏利益相关者支持等原因[8]。
已有研究对于解释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虽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但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已有研究多从西方经典理论学科视角出发审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困境,未能关注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问题的中国情境。如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一样,中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不可忽略中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独特的政治、文化、经济与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多从宏观上探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困境,缺乏经验研究抓手。实际上,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在落实过程中,是以具体的政策工具为载体的,通过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某一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可起到“以小见大”的效果,为洞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问题的本质提供经验依据。
本文将以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为研究对象,在批判性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探讨职业教育治理方式如何对产教融合带来深刻影响。为避免泛泛而谈,将结合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理论视角,建立一个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以期将学界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问题的研究推进一步。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分析框架
作为一项国家制度安排,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方针的落实往往要依托特定的政策工具。其中,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即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政策之一,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执行涉及产教系统内多个相关主体,包括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与大多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相似,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是一项公共政策。立足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执行视角,有助于提出具有适切性的分析框架。
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情境下,政府在其中具有独特地位,形成中国特色的强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由此,中国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具有显著的高位推动特征。从纵向来看,中国公共政策执行往往表现出层级性特点,涉及复杂的科层关系,上下级之间的博弈行为颇为常见;从横向来看,中国公共政策执行往往表现出多属性特点,涉及多个不同部门,不同部门之间可能会存在分歧。层级性反映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网络中的“条条”特征,即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上下贯通的职能部门或机构,也包括部门、机构与直属的事业单位;多属性反映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网络中的“块块”特征,即各级地方政府内部按照管理内容划分的不同部门或机构[9]。大多数地方部门都要接受“条条”和“块块”的双重领导,通常情况下,“条条”关系是业务关系,“块块”关系才是领导关系,因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决定人事任免[10]14。
基于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理论视角,本文将尝试构建一个“层级性治理—多属性治理—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探讨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治理机制,并致力于回答:(1)由于政策的层级性特点,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在纵向上下级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博弈?(2)由于政策的多属性特点,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所涉及的教育、人社、财政等不同部门存在什么样的合作可能?(3)针对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的上述特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理策略?在上述分析框架下,本文试图将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置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的议题之下,从而展现出更加接近中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的实然状态,进而为解释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何以困难重重这一重大问题提供切入点。
(二)研究方法
针对拟要解决的研究问题,本文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展开研究。在国内外公共政策执行相关研究中,案例分析方法得到广泛应用,被认为是分析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方法。甚至有公共政策学者指出,政策分析中的案例分析比量化研究更为有效[11]。同样,在对中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相关政策的研究中,要特别关注典型政策的挖掘,唯有如此,才能挖掘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困境的本质原因。
本文所选用的案例研究对象是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通过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层级性治理、多属性治理难题,进而提出可能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策略。在展开后续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对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背景由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正式确立始于21世纪初。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职业教育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专业教师每两年必须有两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2016年,教育部等六部门正式发布了《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文件规定,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含实习指导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5年必须累计不少于6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回溯过往,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逐渐趋于完善的形成过程。然而,与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相比,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同样遇到困境。如有调查研究表明,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存在动力不足、配套条件不成熟、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12]。
由于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是一项涉及不同层级部门、不同利益主体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公共政策,在政府的高位推动之下,不同层级部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该政策执行过程中来。同时,还牵涉教育、人社、财政、税务、发改委等多个部门的利益,不同部门之间指向集体行动的合作颇为关键。由此,以教师企业实践政策为案例分析对象,透视中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的独特机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总之,选择教师企业实践政策作为本文的案例分析对象,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
为科学把握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落实情况,并为案例分析提供数据支撑,笔者带领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研,基于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层抽样,最终共回收问卷1912份,其中有效问卷1692份,有效回收率为88.49%。尤其是通过对调查问卷在背景变量部分所设置相关问题回收数据的分析,为进一步了解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层次性治理与多属性治理状况提供了实证依据。
三、层级性治理与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失真执行
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场域中,与地方层面制定的职业教育公共政策相比,国家层面制定的职业教育公共政策通常表现出宏观性的特征。原因在于,国家层面职业教育公共政策在正式出台之前,往往要与多个相关部门进行会签,相关政策要点的表述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做出调整,进而可能导致正式出台的政策文本往往采用宏观指导性表述。同时,在职业教育公共政策通过行政力量高位推动的过程中,往往要落实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职业院校、教师等不同层面。在此过程中,不同层面落实主体可能会根据特定发展需求,对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公共政策采取具体化处理,进而形成具有一定层级性特征的形态各异的职业教育公共政策。地方在执行国家层面职业教育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会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政策进行再规划,并倾向于制定既能完成上级任务又能适应地方需求的职业教育公共政策。在从中宏观场域向职业院校这一微观场域转移过程中,职业教育公共政策还会再次经历规划落实的过程,并衍生出便于职业院校、教师执行的政策方案。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理想目标是得到从上到下一致真实地执行,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失真执行则是一种更为常见的现象。对于国家层面专门出台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文件,地方层面普遍并未出台可落实的教师企业实践政策配套执行办法,仅仅是在地方相关的职业教育改革文件中略有提及,甚至在表述角度与方式上与国家层面文件并无显著差异,无法对职业院校有效执行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带来具体指导。而且,教师所参与的企业实践项目多是校级层次,国家及地方层次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参与机会较少。笔者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1 692名高职院校教师的调研发现,样本教师参与校级、县(区,县级市)级、地级市(州,旗)级、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级、国家级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比例分别为51.89%、11.17%、25.06%、10.22%、1.65%。此外,地方相关部门对于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在职业院校层面的考核并不严格,大多只是一些形式上的考核,其主要依据为教师在参与企业实践后所盖的公章,真实性无从考证。
在地方层面无文件可依的情况下,职业院校层面往往会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对政策进行执行,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失真现象的发生。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大部分职业院校往往只是停留在表面宣传倡导的层面,未能根据本校教师职业发展情况制定出可操作的执行办法,相当一部分职业院校教师未能有组织地参与企业实践。调研发现,通过自主联系渠道参与企业实践的教师超过一半,占到51.83%。而且,对于参与企业实践的教师,职业院校并未给予特别的支持,教师往往面临“工学结合”矛盾,教学工作量无法得到有效减免,甚至要牺牲寒暑假休息时间参与企业实践。调研发现,从脱产情况来看,全脱产实践(无教学任务)的教师仅占到25.47%,半/不脱产实践(挂职锻炼有教学任务)的教师则占到74.53%,大部分教师在参与企业实践的同时还要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量要求;从时间安排来看,整个学期或学年、寒/暑假、每月/周抽出零散时间参与企业实践的教师比例分别为14.72%、69.33%、15.96%,教师企业实践占据了教师大量假期休息时间。
以上种种,往往导致教师对参与企业实践缺乏足够动力,教师企业实践的真实参与率并不高,达不到政策目标要求。调研发现,年均企业实践时间为15天以下、15天-1个月、1-2个月、2个月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7.73%、30.61%、39.01%、12.65%,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达不到“专业课教师每年至少一个月以多种形式参与企业实践或实训基地实训”的国家标准。即便到了企业实践,教师也会出现“人在心不在”的情况。从现实情况来看,“走马观花”的现象仍旧比较普遍,教师很难从中积累相应的经验与获得隐性知识[13]。
从职业教育层级性治理的角度来看,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在地方、职业院校、教师层面的失真执行,其背后反映的是“条条”分割的问题,源于不同层级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主体利益的不一致性,甚至是冲突性。国家层面制订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初衷是弥补教师普遍企业工作经历不足的短板,旨在通过企业实践帮助教师了解行业前沿知识,提高实践教学能力,并将企业实践成果转化到课堂中来,这显然是国家基于职业教育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全局作出的重要决策。但面对国家层面的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地方层面往往会根据政策执行的难度、紧迫度、重要性等对政策进行再规划。由于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真实执行,往往需要地方层面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在上级缺乏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对该政策执行往往表现出敷衍塞责的态度,更多的是在形式上完成任务。而到了职业院校、教师层面,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又会得到进一步的“过滤”,基层执行者往往将自身利益的损益值作为是否真实执行政策的对照参量,受益越多越乐于执行,反之则会出现抵制、应付政策的现象。对不少职业院校而言,由于过高生师比的存在,长期以来面临教师短缺的矛盾,教师参与企业实践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矛盾。而且,不少职业院校没有专项经费用于支付教师企业实践所产生的成本。对教师而言,企业实践会占据个人正常教学工作之外的大量休息时间,且在交通、餐饮等相关支出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自然不愿参与企业实践。由此,在多方“共谋”的默契之下,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很难取得实际效果,也很难起到有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
四、多属性治理与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象征执行
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场域中,由于职业教育公共政策所涉及的问题具有较强的跨界性质,往往牵涉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表现出较强的多属性特点。从横向上看,职业教育公共政策的执行往往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方能达到政策预期目标。当不同部门之间政策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时,职业教育公共政策往往能得到较好的执行。但是,由于部门职责分工与功能定位的差异,上述理想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仍较低。更为常见的情况是,职业教育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协调不同部门力量的情形。如果不同部门之间在对政策的认知上存在分歧,则有可能出现,某部门在执行某个政策时,无法得到相关部门的配合与支持,从而出现职业教育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孤岛现象”。
作为一种典型的具有产教融合特征的职业教育公共政策,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执行同样牵涉教育、人社、财政、税务、发改委等不同的部门,需要多部门的共同参与。通常情况下,上述部门是相对独立的主体,拥有各自的职责以及政策执行时的考虑与出发点。缺少任何一个部门的支持,教师企业实践政策都可能会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阻力,而无法达到理想的政策目标。近年来,出台的教师企业实践相关政策文件主要出自教育部门,在教育部门上下级之间的传达与落实上尚且通畅,但涉及财政、税收等配套要求往往要依赖地方相关部门的支持。然而,地方相关部门往往只认垂直管辖部门的文件,执行教育部门文件的积极性并不高。
如《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五条特别强调,各级财政、税务部门要把深化产教融合作为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推进降成本、补短板的重要举措,落实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有关财税政策,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和企业参与办学。调研发现,由于各地财政力量悬殊与重视程度不同,上述政策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再如,《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及《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中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中仅对企业应当接纳教师到企业实践及教师接受培训的经费来源做了规定,但并没有对企业能够获得的相应经济鼓励,如国家直接经济奖励、减免税收、退税等做出明确且可操作的规定[14]。
以上种种,导致企业在核算完接收教师企业实践的各项成本后,往往会发现,如果没有相应的成本补偿,很可能入不敷出,自然难以有足够的动力与积极性接收教师参与企业实践。即便是接收教师实践的企业,也更多的是对政策进行象征执行,往往要求教师企业实践过程不要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调研发现,在教师企业实践的主要形式中,观摩交流式、顶岗实操式、企业顾问式、技术培训式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1.25%、37.88%、12.12%、8.75%。可见,观摩交流仍然是教师企业实践的主要形式,该种形式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影响较小,教师参与顶岗实操的机会要少于观摩交流。而由于能力的有限性,企业较为欢迎的企业顾问式、技术培训式等企业实践形式仍然较少,这也间接影响到企业接收教师实践的积极性。
从职业教育多属性治理的角度来看,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在地方相关部门以及企业的象征执行,其背后反映的是“块块”分割的问题,源于不同类别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主体职责的差异性与诉求的不一致。在“块块”体制下,下级部门往往听命于上级主管部门,与同级其他部门之间更多的是配合关系,而非服从关系。这也就不难理解,从地方层面来看,教育部门调动其他部门力量的能力相对有限,在缺乏明确上级同类部门文件指示的情况下,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体推动的教师企业实践政策,难以得到其他相关部门的有效支持。对于这种跨部门事务,往往需要上级分管领导甚至领导小组来协调推进,甚至需要列入联席工作会议议程之中。但在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过程中,该政策普遍未得到相关领导的支持,也普遍未被列入联席工作会议议程,导致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无法得到各部门的通力配合,自然容易流于形式。对企业而言,由于其经济属性所在,更多受到人社、财政、税务、发改委等部门的约束,受教育部门的约束则较少。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在缺少其他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企业并不具有接收教师参与实践的义务,对于教育部门出台的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更多的是象征性配合。而且,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如果接收教师企业实践会带来“入不敷出”的情况,企业自然不会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来执行该项政策。
五、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我国加快了职业教育改革的步伐。其中,产教融合即为其中的改革重点,并出台了一系列与产教融合密切相关的政策文件。然而,从实践层面来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仍然遭遇了一系列落实困境,未能达到政策预期效果。
现有对于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困境的解释,多局限在西方学科理论视角,存在用西方学科理论视角“剪裁”中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践的嫌疑,从而造成“问题在域内、解释在域外”的现象,无法洞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困境的根源所在。更重要的是,上述解释方式忽略了产教融合的中国情境,未能关注到中国产教融合问题的独特性。要避免把舶来的理论化成先入为主的判断——看到现实与理论不符,便直斥现实之非,进而把了解的现象变成了讥讽的对象——否则就丧失了“同情的理解”的机会[10]1。同样,我们不可一味地斥责中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所面临的困境,而是需要回到“事件现场”,分析该困境产生的来龙去脉。显然,从纯学理意义上将该问题解释清楚并不容易,容易陷入大而无当的空洞分析之中,这也是已有研究普遍存在的不足。实际上,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作为一项国家顶层设计,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是以具体的政策工具为载体的,对某一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可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以经验研究为抓手实现“以小见大”,有助于洞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困境的本质根源。本文在贡献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借助搭建的分析框架,将职业教育治理方式对产教融合的影响引向更为细致深入的讨论,这在一定意义上构成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的中国经验。
作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重要缩影,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揭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困境的根源。以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为案例研究对象,借助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理论视角,构建出一个“层级性治理—多属性治理—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的过程展开分析。研究发现,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执行受到层级性治理与多属性治理两大机制的约束。由于“条块分割”体制的影响,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容易陷入走样,导致政策失真执行与象征执行现象的发生。
从纵向上看,在层级性治理机制下,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在从上到下的执行过程中,会经历科层组织下不同层级主体的“过滤”。在中国,庞大的科层组织几乎影响到国家各个方面,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经过科层体系的“检验”与“磨炼”,如果不能顺应或者驾驭科层组织,那么政策或可能走样,或可能终止[15]。在这个冗长的政策执行链条中,每经历一个层级,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目标取向都会发生新的变化。但遗憾的是,这种变化更多地表现为“钝化效应”,地方层面普遍并未将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列为重点执行工作,提供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较少,考核也不甚严格,职业院校层面普遍未在教师企业实践方面给予教师时间、工作量、经费等方面的充分保障,教师层面参与的积极性与动力也普遍不高。在多方主体的“共谋”之下,教师企业实践的形式已经大于实质,长期处于失真状态,从而偏离了政策预期目标。
从横向上看,在多属性治理机制下,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执行涉及教育、人社、财政、税务、发改委等不同部门,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支持对于政策的顺利执行至关重要。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具有典型的多属性特征,当该政策落到地方层面时,需要其他部门给予政策配套。但由于相关部门往往只认垂直管理部门的文件,导致配套政策的落实效果并不理想,由此带来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的“孤岛现象”,教育部门在执行该政策过程中普遍无法得到其他部门的有效支持。同样,企业与产业系统的人社、财政、税务、发改委等部门联系更为密切,在缺乏政策约束与利益激励的情况下,也普遍未给予教师企业实践政策足够的支持。以上种种,导致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在产业系统相关主体方面只能得到象征执行,从而也偏离了政策预期目标。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所面临的困境,本质上反映的仍然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这一“老大难”问题。产教融合及其制度设计的实质在于“产”“教”间关系的构建[16]。由于产业系统与教育系统在组织性质上天然的差异性,以政策的方式推进产教融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条块分割”问题。已有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的“块块”问题,即产教之所以难以融合,很大程度上源自不同部门之间的不配合,以及缺乏企业的应有支持。如相关研究指出,教师企业实践“一头热”之现况依然普遍,激发企业积极性依然任重而道远[17]。但相关研究仍然多是对表面现象的探讨,未能关注到产教融合政策本身的多属性特征,不可过多苛责产业系统相关主体在产教融合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行为。同时,已有相关研究并未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的“条条”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实际上,对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顺利推进而言,“条条”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不亚于“块块”问题。本研究创新性的发现在于“条条”问题的本质是产教融合政策的层级性治理,政策在自上而下执行过程中,会经历层层“过滤”,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某一主体的不配合,而更多表现出一种“共谋”行为状态,这是中国情境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困境的独特之处。
为破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所面临的困境,也为以教师企业实践为代表的诸多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提供助力,仍需提出针对性的破解之策。层级性治理与多属性治理所存在的问题,更多地需要依赖高位推动的方式来解决,这是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典型特征。高位推动对于应付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真执行、象征执行等无组织化问题极为有效,可以在短时期内将处于高度分化状态的“条块分割”体制重新“粘合”。而且,面对原子化式存在的职业院校与教师群体,作为外源力量的高位推动是凝聚基层中心意识与思想、规范基层集体行动的有效方式。对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顺利推进而言,各级党委的态度和角色至关重要。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的政策,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采用建立各种临时性领导小组的方式,针对产教融合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采用集中研讨、会商分析等方式解决,发挥临时性领导小组的协调沟通、下情上达、监督考核作用,减少可能存在的制度损耗与摩擦成本。
当然,破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难题,还需要强化经费保障、畅通信息交流渠道。不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执行需要以资金为保障,但各地财政禀赋不同,需要上级部门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让各地政策执行者都能得到基本的经费保障。倘若如此,将更有利于解决产教融合过程中的“块块”问题,促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顺利推进。信息的有效交流,无论对于破解“条条”问题,还是对于破解“块块”问题,都有重要帮助。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可以让条块体制下的产教融合不同行动主体对政策的目标与细节更为清楚,减少彼此之间的距离感与陌生感,通过建立信息通报制度、联合评估制度等保证信息的“上传下达”,从而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从一种外在强制的政策设计转化为内在自愿的集体行动。
在上述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还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的市场化改革,引导行业、企业等以项目的形式提供产教融合服务,由政府、职业院校等根据服务内容与质量等支付相关成本,建立多方主体共同促进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利益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1]
BILLETT S.Vocational Education:Purposes,Traditions and Prospects[M].New York:Springer,2011:4.
[2]郝天聪,石伟平.产业结构转型与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基于对美国、德国、日本、中国的比较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20(8):122-128.
[3]罗汝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价值判断、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J].职业技术教育,2017(25):49-53.
[4]宾恩林.凭什么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规划、市场匹配与组织结对[J].职教论坛,2024(5):27-35.
[5]匡瑛,朱正茹.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关键是实现跨界组织实体化运作[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81-92.
[6]万伟平.产教融合的运行困境及其突破机制研究——基于博弈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24(2):30-37.
[7]甘宜涛.组织边界理论视域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现实困境与突破[J].江苏高教,2024(5):111-117.
[8]朱喜祥,程兰诗,王荣辉.系统共生和对接融合:多学科视角下的产教融合困境与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22):65-71.
[9]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5):61-79.
[10]兰小欢.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11]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政策制定[M].谢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0-32.
[12]董仁忠,季敏,刘新学.江苏省中职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情况调查[J].职业技术教育,2015(33):38-45.
[13]郝天聪.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政策落实困境的质化研究[J].教师教育研究,2021(1):93-98.
[14]涂三广.职业院校教师到企业实践:问题与对策[J].职教论坛,2014(27):23-27.
[15]陈家建,边慧敏,邓湘树.科层结构与政策执行[J].社会学研究,2013(6):1-20.
[16]朱德全,熊晴.共享式发展: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四维统筹制度设计与实施路径[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147-158.
[17]黄茂勇,胡俊杰.企业实践系统何以提升高职教师教学科研效能——基于广东省14所高职院校的实证调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15):89-96.
(责任编辑"侯翠环,王丽婉)
Why is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so Difficult to Govern?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terprise Practice Policie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HAO Tianco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7,China)
Abstract: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the key to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them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Compared with top-level design,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encountere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ation.As a typical policy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the implementation of enterprise practice policie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involves multiple departments and entities of th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ystem.Taking teacher enterprise practice polic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ing case studies,it can be found that due to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hierarchical governance and multi-attribute governance mechanisms,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 enterprise practice policies may exhibit distorted and symbolic execution.At its root,limited by the “segmented” system,teacher enterprise practice policies are prone to deviate from policy expectation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which is also a persistent problem to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The key to solving this problem lies in leveraging the coordinating role of party committees at all levels,attempting to establish temporary leadership groups,through high-level promotion,re-bonding the highly differentiated “segmented” system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and assisting i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tegration governa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through funding guarantees,information exchange,and other means.
Key words:vocational education;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teacher enterprise practice policy;hierarchical governance;multi-attribute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