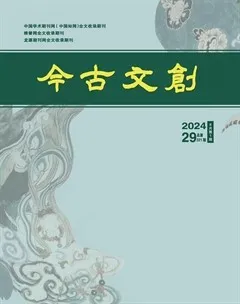困境与突围
【摘要】加缪在《鼠疫》中深刻洞悉了瘟疫爆发下个体和群体生活以及心理的巨大变化。他用隐喻的形式深化了疾病书写的内涵,指出疾病在引发恐惧和死亡的同时也能催唤起新生的精神力量,并促成个体及群体的认知转变,包括对人本身、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多重关系的再思考和重新界定,集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由此萌生。
【关键词】加缪;《鼠疫》;疾病书写;文学隐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9-003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9.009
基金项目:巢湖学院校级科研一般项目“新冠疫情背景下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瘟疫书写研究——以《鼠疫》为例”(项目编号:XWY-202208);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2022年安徽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类重点项目“族裔散居下毛翔青早期作品中的文化身份构建”(项目编号:2022AH051690);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多模态语料库的外宣英文网站中‘中国故事’话语研究”(项目编号:23YJA740037)。
与萨特并称为“战后法国的良心”的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是法国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重要代表作《鼠疫》是描绘20世纪40年代阿尔及利亚奥兰城鼠疫肆虐的文学巨著。在这部小说中,加缪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笔触,揭示了疾病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如何塑造他们的命运,以及如何促使人们形成命运共同体。
小说自出版以来便广受关注和褒扬。国内外学者对于《鼠疫》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存在主义、荒诞哲学、人本主义和叙事学等角度,对作品中的疾病现象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聚焦于小说中的疾病书写,探索瘟疫下个体和群体的创伤和认知转变,以及集体意识和共同体意识的萌生。
一、文学隐喻下的疾病书写
疾病书写在文学作品中较为普遍,尤其是在大规模瘟疫爆发的背景下,作家会以疾病隐喻其对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如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黑死病横扫欧洲时的凄惨和绝望,笛福《瘟疫年纪事》中1665年大瘟疫爆发时的恐慌和无助。其中,加缪的《鼠疫》更是从正面描写了鼠疫这一烈性传染病给个体和社会带来的创伤。
在加缪笔下,疾病使特定时期的生活方式、心理机制和认知结构等发生变化,因而又被赋予多重隐喻意义。加缪在小说中描绘了瘟疫爆发时的惨烈状况,并以瘟疫书写建构了灾难、宗教和道德的三重隐喻。
(一)疾病的灾难隐喻
在瘟疫背景下,人们一旦沾染疾病,就会与未感染者区分开来。疾病不仅打破了身体的平衡,更是打破了患者生存空间的平衡。在小说中,当鼠疫疫情发展到近乎难以控制的态势时,官方下令实施封城举措。医生配合警察的工作,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一经发现,便会立即带往隔离点。无论是病人还是病人家属,从被带出去的那一刻,基本就意味着就此永别;而尚未感染的人也会在悲伤和恐惧的夹击中惶惶不可终日。当疫情褪去,城市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但是人们似乎无法正视这场来势汹汹的浩劫。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只要他们还未找出科学有效的抗疫方法,鼠疫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并再次把人类拉入可怖的人间炼狱。
(二)疾病的宗教隐喻
随着古代几次瘟疫的大爆发,医疗知识和医疗手段的滞后性与瘟疫扩散蔓延的爆发性形成了强烈反差,医学在疫情面前似乎失去了原有效力。因而,身处困境中的人们甚至放弃了对医学的期待并转而诉诸宗教,渴望借用宗教的力量寻得生命的救赎和心灵的疗愈。
在小说中,由于愈发失控的疫情态势和民众难以遏制的恐慌,教会决定举行为期一周的祈祷仪式。帕纳鲁神甫在教堂的第一场布道中就为此次疫情的发生进行了归因: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奥兰城市民都是罪有应得。他认为这场灾难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并劝诫人们只有完全信任上帝并真诚祷告,才会幸免于难。即使在后期自己也感染瘟疫,他也坚信自己真诚的祷告就是唯一药方而拒绝接收医学治疗。然而,这位坚定的信仰者最终也因身染恶疾而撒手人寰。信奉上帝的神甫也未能被救赎,这一事实又再一次加剧了群众的恐惧。通过神甫这一人物命运安排,加缪表明了自己对瘟疫宗教隐喻的立场——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宗教只存在于人们的情感寄托中,永远无法帮助人们战胜客观存在的瘟疫。
(三)疾病的道德隐喻
作为烈性传染病,瘟疫会在短时间爆发蔓延,进而引发大范围社会恐慌和秩序混乱。官方往往会通过多种渠道来宣扬在特殊时期勇于奉献、不畏牺牲的英雄事迹,给民众以情感渲染和道德感化。
在小说中,塔鲁就是这样的“时事英雄”。虽是一名外来人口,在鼠疫横扫奥兰城时,塔鲁毅然将个人安危抛之脑后,主动要求加入感染风险极大的卫生医疗队伍。然而,加缪却否认其为一名可歌可颂的“英雄”,他在文中借用里厄医生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1]403事实上,塔鲁是把鼠疫视作可以轻易将个体置于死地的疾病,他给予患者充分的同情和理解,并企图用满腔热情和必胜的决心与之抗衡。然而这又无外乎在无形中认同、接受并内化了鼠疫的道德隐喻意义,且将其作为道德的对立面加以反抗,尚未真正认识到鼠疫的客观存在性。此外,作为一个满身道德污点的罪人,鼠疫并未对科塔尔这种缺乏道德的恶人施以惩罚或宣判死刑。
勇敢无私的塔鲁因感染鼠疫而亡,阴暗自私的柯塔尔却能在鼠疫中苟活,这样的人物结局安排是加缪对疾病的道德隐喻的一种驳斥。作为客观存在的瘟疫,鼠疫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个体,既不会因个体高尚的品德而授予“免死金牌”,也不会因个体道德瑕疵而对其宣判死亡。
二、亦灭亦生——疾病的双重影响
瘟疫的爆发必然引发个体生命的萎靡和死亡以及精神的迷失和异化,但是同时也会催生出强烈的新生力量,激发人类的求生意志和情感需求。
(一)疾病引发的生命死亡和精神异化
疾病会致使人的生理性死亡,即个体生命的终结。在小说“无辜的病孩”这一章节,加缪具体描述了因感染鼠疫而死亡的孩子形象:“他小小的躯体已经完全被瘟神的魔爪控制,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瘦骨嶙峋,离开人世时脸上还残留着泪痕。”[1]267感染鼠疫的患者在经受了漫长剧烈的痛苦后咽下最后一口气,而后被蒙上白布送往坟场。随着死亡人数的不断攀升,奥兰城已经没有空闲土地用以尸体埋葬了,后期甚至出现尸体随意丢弃的现象。
同时,疾病会致使人的社会性死亡,即个体之间关系的疏离。当被确诊以后,患者会处于严格的封闭隔离中而无法与他人交流;为了防止传染,在社会空间中,每个人都与他人保持距离。更糟糕的是,健康人会无意识地将患者的感染症状投射于自身,这一心理投射多会引发严重的心理危机。为避免引发个体恐慌的自我投射及可能的疾病传染,人们会避免与他人近距离接触。小说描绘了人们彼此刻意疏远的场景:大家都戴起了薄纱口罩,即使交谈也保持一定距离。这种在与外界和他人的持续疏离中,个体自我生命力也会不断减弱并陷于难以调和的身心矛盾中。
社会将疾病人格化,并把患者钉在“耻辱柱”上,患者的自我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会随之受到损害。疾病给个体带来的不仅仅是痛苦的创伤体验,更有创伤后难以释怀的负面情绪和消极情感。随着瘟疫的持续扩散,恐惧和怀疑在个体内心疯狂滋生,人性的自私和无助在瘟疫面前凸显得更为淋漓尽致。这不仅对社会的相互关系和秩序造成了冲击,还可能引发经济困境和地区冲突。
(二)疾病催生的新生力量
疾病在导致以上困境的同时也催发了新生力量,包括生命主体的求救意识和情感补偿需求。人类对于疾病的探索过程就是生命主体的自救过程,只有找到正确科学医治方法,个体才有可能保全自我,社会才有可能稳定发展。在小说中,面对瘟疫的无情袭击,个体生命显得尤为脆弱。奥兰城的人们祈求逃过此劫,求生欲望达到顶峰。父母在面对可能会被感染或者已经感染的孩子更是惊恐万分。有人抱着孩子不停地祈祷,恳求上帝放过他们;有人哀求医生给出特效药方,以缓解巨大伤痛。
同时,在瘟疫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节奏、社交方式乃至心理状态都可能发生深刻的变化。面对这样的挑战,情感补偿成了一种重要的心理支持机制,有助于缓解焦虑、孤独等负面情绪,增强个体的心理韧性。在他者关联理论中,弗洛姆强调了与有生命的他者建立关联的必要性,并指出个体的健康有赖于他者关联情感的满足。小说中描写了纯粹至深的情感,有深沉的亲情,如里厄母亲对里厄的关心和爱护;有深厚动人的友情,如里厄与塔鲁的心心相惜和相互扶持;还有陌生人之间的鼓励和善意。这些美好的情感都给人以温暖和慰藉,以及继续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三、疾病影响下的认知转变
如同自然灾害一般,疾病自始至终贯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对于人类来说,瘟疫这种大型烈性传染病是一项复杂而棘手的挑战,涉及众多复杂的因素和层面,每一场瘟疫的爆发都不是个体可以轻率解读和简单剖析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会对自我以及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多重认知关系产生转变,试图去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等。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
在瘟疫这一特殊背景下,个体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再思考,并对自我身份进行了重新定位。
小说开头便指出,奥兰城市民工作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发财。这实际上是病态的“金钱社会”,看似物质财富已经帮助人们摆脱了贫穷并走向文明新阶段,但有时对于物质的过度崇拜恰恰是一种极端化的野蛮。鼠疫的突然爆发,打破了城市的宁静与秩序,使得人们陷入了恐慌与绝望之中。这种无力感,反映了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时的脆弱性。
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束手无策和惊慌失措表明了人类并非是整体自然界的主宰和中心。加缪以一贯的冷静自持,犀利地指出事态的真相—— “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在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催祸患,重新吸取教训。”[1]288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恒话题。在瘟疫肆虐后,人类重新审视自我位置,并重拾对自然界的敬畏之情。
(二)集体意识与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萌发
17世纪英国著名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在《丧钟为谁而鸣:生死边缘的沉思录》中写道:“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钟声为谁鸣响,它为你鸣响。”[3]2这种“丧钟为你我敲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小说中同样有所体现。
在鼠疫的肆虐下,个体的生存变得异常艰难,人们不得不放弃部分个人自由,转而寻求集体的保护与帮助。这种集体意识的萌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地恐慌、绝望与挣扎中逐渐形成的。人们逐渐意识到,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应对灾难,才能有可能战胜鼠疫并重获新生。在集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命运共同体意识也随之萌生。人们逐渐认识到,在这场灾难面前,每个人都是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每个人的命运都与他人紧密相连。这种命运共同体意识不仅体现在人们之间的互相帮助与支持上,更体现在对共同目标的追求与坚守上。人们开始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为了整个社区的安宁而奋斗。
新闻记者朗贝尔原本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但随着疫情的扩散,他逐渐意识到抗疫是一场需要人人参与的持久战,利他即利己,他人命运即为自我命运;科塔尔曾因抑郁悲观而差点自杀,但当他投入抗疫的洪流中,想要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时,他逐渐找到了自我价值感和归属感。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个体的命运已融入以鼠疫和全体市民共有的情感和记忆构成的群体命运中。小说中的主人公以及众多普通市民,都在这场灾难中展现出了强烈的集体意识与命运共同体意识。他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生死与共的集体。他们共同面对灾难,共同承担责任,共同追求希望。这种集体意识与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萌生,不仅让他们在灾难中找到了力量与勇气,也让他们在困境中找到了人性的光辉与希望。
四、结语
不可否认,疾病与人类共生共存。它不仅仅局限于医学领域,还深入涉及历史和文化等多个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疾病的困扰,而文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疾病在个体生命中的深刻意义,并引导我们正确看待疾病。通过疾病的书写,《鼠疫》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观念。这部小说不仅揭示了人类在面对灾难时的种种反应,也展现了人类在面对困境时的团结与互助。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认识到,无论面对何种灾难,人类都需要构建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才能最终战胜困境,实现自我救赎。
正如王晓路所指出:“实际上,疾病和医学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学表征不仅是在主题上,当然也不仅仅只有关于鼠疫的创伤记忆和书写。”[4]《鼠疫》以其深刻的疾病书写和独特的命运共同体建构,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人类社会的独特视角。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人性、社会以及人类未来的深刻洞察。因此,对这部小说的解读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加缪的文学思想,以及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参考文献:
[1]加缪.鼠疫[M].刘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3]欧内斯特·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M].李尧,温小钰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3.
[4]王晓路.疾病文化与文学表征——以欧洲中世纪鼠疫为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27-33.
[5]王予霞.西方文学中的疾病与恐惧[J].外国文学研究,2003,(6):141-146.
[6]麦克尼尔.瘟疫与人[M].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作者简介:
马曼华,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