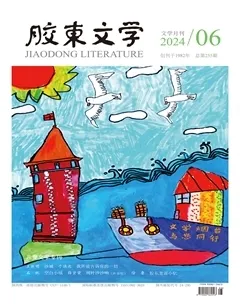源于常识又超越常识
写作是写作者通过文字,用自己的经验、知识或者灵魂,与读者和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内心什么样,为写作而做的准备什么样,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写作者的造化和命运。
在思考儿童文学的时候,成人是“他者”,是站在成人立场审视、打量、思考儿童文学的所有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对儿童文学有一种独特的感动?我想是跟童年的生命有关。童年的生命对于成人来说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思想史、文化史、文学艺术史上常常有童年崇拜的理念。从提出“以儿童为中心”的卢梭,到提出“儿童是成人之父”的英国湖畔派诗人,再到中国“五四”以后以丰子恺、冰心为代表的多位作家,都有一种特别的童年崇拜观。
彼岸性和神秘性
儿童文学是有神性的,它跟童年的生命和美学结合在一起。儿童文学和童年的神性主要表现为彼岸性和神秘性。
相对成人的生命和艺术美学,童年的美学是一种彼岸的美学。为什么湖畔派诗人和启蒙主义时代的人们要从童年寻找救赎的力量?因为在儿童的身心世界里,可能保留某种世俗社会所不具备的纯真和天然力量。《大海的尽头在哪里?》这部童话的标题就是一个对彼岸的追问,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会把读者的眼光引向遥远的彼岸和远方。
儿童世界所展示的生命奥秘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信息和艺术体温等,带有一种神秘性。这种神秘性在成人的思维里可能是荒诞的甚至不存在的。儿童文学具有彼岸的经验和神秘的特质,常常表现在生命、哲学、艺术美学的终极意义上皆具超越性,这也是很多人对以《安徒生童话》为代表的卓越美好的儿童文学写作怀有喜爱和敬意的原因。
《大海的尽头在哪里?》文本的形象设置是幼儿熟悉的蚂蚁和大象,二者形象反差很大,带来了故事内在的叙事趣味和张力:
一只蚂蚁爬到海岸边,望着一个接一个的海浪涌到岸上,不禁忧愁起来:“海这么大,而我这么小,我一辈子也不能看见大海的尽头……我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呢?”
蚂蚁在一棵棕榈树下坐下,哭了起来,他感到这般委屈。
这时,一只大象来到岸边,问道:“蚂蚁,你哭什么?”
“大海的尽头看不见。”蚂蚁呜呜哽咽道,“大象,你个子大,或许能看得见吧?”
大象开始张望。他看啊,看啊,甚至踮起脚,但除了海水,仍然什么也看不见。大象在蚂蚁旁边坐下来,也哭了起来。
他们哭呀,哭呀……突然,蚂蚁说:
“听着,大象,你爬上棕榈树,我爬到你身上,我们再看看!”
蚂蚁爬到大象身上,大象则爬到棕榈树上。
他们看啊,看啊,除了海水,照样什么也没看见。于是,他们坐在棕榈树上又哭了。
这时一条金枪鱼游到岸边。
“喂,”他喊道,“在岸上好好待着,哭什么啊?”
“大海的尽头看不见。”蚂蚁和大象异口同声。
“怎么?”金枪鱼感到奇怪,“这里难道不是大海的尽头吗?”
“对呀!”蚂蚁兴高采烈地叫着,“呵呵,大象!我们见到海的尽头啦!”
“呵呵!”大象高兴地欢呼起来,并开始从树上下来。但他突然顺便考虑了一下,问:“那么大海的开头又在哪里呢?”
在这篇幼儿童话里,蚂蚁和大象都是孩子,他们都有哭的情节,幼儿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会产生代入感。在这三四百字的故事里,情节却一波三折,很巧妙。蚂蚁和大象都看不见大海的尽头,这是第一处转折。对于从海中游到岸边的金枪鱼来说,这里是大海的尽头,也是他们想探究的彼岸,第二折结束。结尾出现第三节,大象顺便想了想:“大海的开头又在哪里呢?”故事涉及此岸和彼岸、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带有一种哲学气息。
《西绪福斯神话》中提过西绪福斯反复将一块巨石从山下往山顶推的情节。这个神话之所以深刻且影响深远,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是人类处境和命运的一种象征。而《大海的尽头在哪里?》这篇小童话的厉害之处在于结尾点出了人类的某种精神处境或者精神责任:追问是永远的命运。
幼儿能读懂这些吗?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是把人类文化的、文明的、艺术的、哲学的重要问题,以简约的图式潜藏在故事框架的底层,等待孩子们阅读,也等待孩子们成人以后的反刍。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什么可以影响孩子一辈子?因为站得很高的作品都有一套完整的寓言结构和值得思考的内在深度。
“简洁”和“准确”
写作儿童文学的常识,就是书写童年的艺术常识,“简洁”与“准确”是尤其需要注意的两个方面。
“她是一个瘦削而精明的女人。”
“尽管使坏吧!”汤姆勇敢地叫道。
“我父亲帮我解了方程式。”汤姆谦逊地说。
这类文字喜欢运用形容词,不是简洁的语言。简洁不是简单,而是单纯,富有趣味和表现力。
当代美国通俗文学领域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家在《写作这回事》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写作真正最糟糕的做法之一就是粉饰词汇。”他十分反对滥用副词,认为副词就像门前草坪上的蒲公英,不清理,一朵十朵几十朵很快就会把草坪弄得一团糟。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通俗文学,也适用于儿童文学。斯蒂芬·金特别说到对话:
界定对话最好的方式就是“某某说”,比如“他说”“她说”“比尔说”“莫妮卡说”……也许你的故事已经讲得不错,相信用“他说”,读者就会知道他讲话的语气动作——是慢是快,是愉快还是伤心。
我相信通往地狱的路是副词铺就的,我要站在房顶上大声疾呼我的观点。
斯蒂芬·金的说法听起来有点儿极端,但若对于叙事而言是个重要的提醒。如果对话中人的情绪、情感、性格等都需要用副词来说明,是否就意味着叙述和交代是不充分、有问题的?换个角度,如果前后的交代已经清楚,语气也把人物的性格、此刻的情绪情感充分表达出来,再在对话里加上相同意思的副词来强调就没有必要。所以斯蒂芬·金看似极端的说法其实无关用词本身,而是关于叙事的完整性、统合性和充分性。语词是否足够简洁,可以提示和检验叙事是否足够充分完整,前后是否统一清楚,是否传递了想要传递的相关信息。而副词、形容词滥用的词句,有时候却被贴以“好词好句”标签。这不仅造成儿童文学里粉饰词语泛滥的文艺腔,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中小学生作文重语词、轻真情实感的歪路。
刘海栖《有鸽子的夏天》中有一段对话:
我问赵理践这两只鸽子是从哪里来的。
“取水巷知道吗?”赵理践说,“有家养鸽子的……”
“知道知道!”我说,“是不是胡卫华?”难道是胡卫华的鸽子?
“没错!”赵理践说,“就是胡卫华,是他的鸽子,我老给他家送蜂窝煤。”
我差点没叫出声来。
这部小说显而易见的特点就是语言简洁。加副词很容易,许多作者可能随手就会加上去,比如:“取水巷知道吗?”赵理践“有点儿神秘地”说,或者赵理践“微笑着”说。虽然这两个词语表达的意味不同,但是不管用哪一个都不如不用。“‘知道知道!’我说”,可能很容易就被加成“我连忙说”。而“连忙”的意思在“知道知道”里已经表达出来,所以“我说”二字足矣。“‘没错!’赵理践说”,作者没有加上“得意地说”或“高兴地说”之类。此处没加副词,但传递的意思已经清楚,甚至还给我们留下可以琢磨回味的空间。
简洁并不意味着表意不充分。反之,正因表意已经充分,作者才选用最简洁的语言来呈现。简洁,看起来是语言的表层问题和形式问题,但它不仅关乎形式和技术,还关乎表意和人物塑造、情感和灵魂的表达。
《有鸽子的夏天》中“杏核大王”一章的结尾是这样的:
“我们家善明真不赖!弄回来这么多杏核,”鸭子他妈正在刷腌咸菜用的粗瓷坛子,她指指那堆杏核山,“去年腌好了给他爸捎去,他爸说他们队上的人都爱吃,叫今年多腌点,我还发愁到哪里去弄这么多杏仁呢!他爸那伙人有口福啦!”
鸭子的爸爸是开卡车的司机,过去给铁路货场运货,现在支援大三线建设去了陕西,很难得见他回来。
啪!啪!啪!……
“鸭子”妈妈的话不过是生活场景的简洁叙说,但其中却蕴含丰富的感情。这一章的前面讲到“鸭子”徐善明跟另外一个伙伴儿赌杏核的情节。虽然他赢了很多,但后来他不肯赌,也不愿意把杏核借给这个对手继续赌。边上的人觉得有点儿扫兴,说他“真奸”,意思就是小气,连他的对手也拽他装杏核的书包。结果书包被拉断,最后还是赵理践替他解了围。其实“鸭子”徐善明在前文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有点儿不讨人喜爱的。他小气、抠门,没有那种敢甩出去的男子汉气,不大可爱。但是从这一段简洁的叙说里,我们一下子知道他小气、抠门、拿不出勇气的原因——这些杏核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做成杏仁咸菜捎给他“支援大三线建设”的爸爸和同事们一起吃。
作品和人物的意蕴和内涵在这里丰富起来。作者没有用额外的话说明“鸭子”为什么要赌那么多杏核,为什么不愿意再赌下去,为什么小气,而是通过“鸭子”妈妈的一段日常语,对“鸭子”爸爸的介绍,以及最后的三声“啪!啪!啪!”,间接说明原来他要把这些杏核送给他的爸爸。内涵和情感都在背后,人物的形象立起来,小说要表达的感情也丰满起来。
而所谓语言的准确,是指语词形式和表意之间有一个准确的对应关系,作品叙事与人物性格、生活逻辑、历史逻辑等是自洽的、统一的。说到底,与生活常识、写作常识有关。
“准确”几乎是文学最基本、最重要、最考验作家写作才能的一项要求。对文学来说,准确是一个重要的前提,生活的准确、事理逻辑的合理都很重要。如果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断产生疑问,那么作品的自洽性、完整性、可信性就会受到影响。
我曾读过一部作品的初稿,里面有个情节是在火箭试验场发生意外事故时,一位战士大声喊道:“别管我了,快去保护液氢车。基地里眼下只有这一台液氢车,如果它被烧掉了,东方二号火箭就无法加注燃料,准备好的试射,就无法如期进行了。你们一定要让东方二号按时完成试射,一定要让它飞上天。”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战士居然还能说出这么大段、理性、非口语的语言,这显然是不成功、不准确的描写。
近年出版了一系列谍战题材的儿童小说,故事完整,可读性较强。但是作为此类题材的尝试之作,作者在故事编织上往往用力过猛,过度使用巧合导致漏洞较多,人物形象矛盾,可信度降低。巧合是文学创作的常用手法,但是过度使用,一定会弄巧成拙。
谍战题材作品讲究悬念呼应、情节惊悚起伏,但是如何把握它在叙事方面的“度”,如何在表现谍战故事惊险、人物大智大勇的同时,保持对过往岁月的尊重和敬畏之心,保持艰险、残酷历史再现的准确性,避免把谍战题材写作变成“谍战神剧”写作,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美”和“善”
“简洁”“准确”的背后绝不仅是语词形式与意义简单对接的问题,一定蕴含着重要的观念、情感和灵魂,如朝向美和善的表现力。
善有多种,首先是英雄之善与日常之善,两者存在不同,又有所关联。英雄之善是我们对一部作品中英雄角色代表善的力量、善的立场的一个基本认识,可能更多的是英雄在面对恶势力时善恶分明,毫不留情,并且所向披靡,代表的是善的正义和力量,是一种符号性的“善”。如奥特曼跟怪兽之间的对决,永远都是以奥特曼胜利、怪兽的死亡告结,这是我们把善与恶、英雄与恶魔之间的对决上升到符号性的表现层面,是我们接受的一种文学语法。
如果放到日常生活语境中,善到底是怎样的?该如何理解?《长袜子皮皮》中,林格伦很好地把握和调适了孩子的天真逻辑与学校的教育逻辑之间的冲突。在日常的学校对话场景里,皮皮代表的是永远没有缰绳可以圈住的狂野和自由,而老师代表的则是用成人社会体制化教育规则来约束她的一种力量。虽然皮皮很努力地想要遵从学校的规则,可她的天性实在不能被这些规则约束。在她努力想要跟上规则可总打破规则的矛盾中,可以看到天性无可约束的自由状态。她对待世界的善意让读者能够接受她身上童年野性的合理性及其独一无二的价值。
在很多作品里,老师很容易被塑造成一个有着“刻板印象”的角色,来代表教育主义的戒律和符号,但林格伦笔下的老师并非如此。虽然她的问题被一再打断,自己又被皮皮古灵精怪的回答弄得很尴尬,但她一直保持老师对待孩子的基本方式:提醒皮皮要遵守学校规则,并告诉她这些规则是什么。当这位老师发现皮皮完全不在她的掌控范围之内,她没有恼羞成怒,而是不再问皮皮任何问题。作为老师,她代表规则,也努力引导孩子尊重规则,但这种代表和引导没有把她带入教育暴力的状态,没有让她做出损害和侮辱童年的行为,是一位值得信任尊重、具有良善之心的老师。
儿童文学创作要避免两极化:觉得一方代表善,另一方就必然代表恶。生活很复杂,个体身上常常善恶交织,难以界定。这时我们该怎么表现?《长袜子皮皮》里,孩子自由、狂野、不受约束的天性,童年的天真跟社会既有的教育文化体制相对峙的矛盾,都呈现在日常之善的情境里。在皮皮和老师的人物刻画上,在童年的天性和成人世界的规则意识的表现上,都能看出日常生活里微小质朴却又很珍贵的美好和良善。对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和阅读来说,发掘、表现和认识、体味这种日常生活中微妙但又很重要的善的内容,与仅仅去认同英雄们所代表的善的立场、符号相比,也许更加重要。
善还有观念之善与文学之善,两种亦有很大区别。所谓观念之善,就是作为观念的善,是儿童故事写作的出发点。儿童文学是真善美的文学,但绝对不是用故事来解释善的观念这么简单。与观念之善相比,文学以其特有的表现力表达善的内容,揭示善的美学,这就是文学之善。很多时候观念的善是抽象的、概念化的,文学会让我们看到更具体的、更肉身的善,善会穿过观念进入我们生命体验的深处。
在洛贝尔“青蛙和蟾蜍”系列中的《惊喜》中,青蛙和蟾蜍是好朋友,一天刮大风,他们的庭院都落满了树叶,他们不约而同地为对方扫庭院。按照故事想象的惯性,这个作品可能想表达互相帮助的主题。很多故事都会遵从观念之善,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个逻辑来实现一定的结果——感情上、行为上或思想上的结果。但这个故事的结尾打破了两个生命之间善意关怀的习惯模式,青蛙和蟾蜍善的行为没有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实质性的改变——青蛙和蟾蜍都心怀对方看到干净院子而高兴的心情和想象回到家里,可一阵秋风过后,他们的院子再次落满树叶。正因为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改变,青蛙和蟾蜍对彼此的爱和关切的感情才尤为赤诚和可爱,这个小故事表达的友情、生活和生命的主题才更加深邃动人。
从观念之善到文学之善,重要的认识转变是善的行为价值不在于结果,而在于生命体验。我们在写故事的时候,不知不觉会怀有一种意图:善的行为最后往往指向功利性的结果,比如获得奖赏。其实,善的正义性和珍贵性、行善的合理性,不是由它带来的可见的功利性结果来证明——善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善也有扶弱之善和普遍之善。传统儿童故事的基本文学“语法”是除暴扶弱。代表暴力和暴政的压迫者处于善的对立面,似乎理所应当被驱逐和清除,从《大林和小林》《神笔马良》到《闪闪的红星》都是如此。承认除暴扶弱的善固然重要,然而在此基础上再来写这类主题,还能往前走到哪里去?
《假话国历险记》是一部主旨非常鲜明的寓言体童话,假话国里发生的是对暴力和暴虐压迫的反抗。小茉莉来到假话国,发现这里不让说真话只让说假话,国王也一心要掩饰其虚假身份。在经历了一番冒险后,小茉莉用无与伦比的高亢歌声摧垮了虚伪的假话国,国王贾科蒙内也灰溜溜地出逃了。写到这里,扶弱之善的意图已经完成,故事可以结尾了,但是作品给国王安排的结局让人意想不到:他拎着一提包假发遇到一个人,这个人不但赞美他的秃脑袋,还告诉他这个城里有一个秃头俱乐部,昨天它还是秘密的,现在终于公开了,他有这么棒的秃脑袋,肯定能够当选俱乐部的会长。贾科蒙内听完心里五味杂陈。这个处理非常有幽默感,当真理在最后实现的刹那,当正义在最后一刻被扶正的瞬间,得到解放的不仅仅是一部分人,而是所有人,包括贾科蒙内国王这个暴力和暴虐的施行者。当普遍的真理被揭晓时,当善的力量获得胜利时,每个人都是善和正义的受惠者。真正的善和正义常常会“解放”所有生命,具有一种更通达、更普遍的伦理力量和价值。
在儿童文学写作中,怎样思考此类问题,怎样写出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善,而不是以牺牲传统观念中代表恶的力量为代价的有限的善,可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