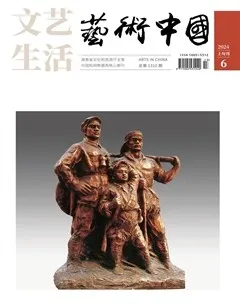书法家李宪文 雕虫小集弁言
李宪文,生于上世纪80年代,山东曲阜人,现居烟台,别署更生、甦斋。现为鲁东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师、山东省当代艺术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烟台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山东省书协会员,主要从事书法、篆刻和文房刻铜研究与创作。
扬雄在《法言》中曾以“雕虫篆刻”喻之辞赋创作,并认为“壮夫不为也”。在其眼中,作为“立言”的文学创作地位已然如此之低,更不用说“雕虫篆刻”本身了!说到篆刻,“鸟虫印”在篆刻艺术中的地位或许也正是“壮夫不为”的小门类。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对鸟虫印一直存在偏见,特别是一些装饰感较强、文字辨识度太低的鸟虫篆,我认为于篆刻诸门类聊备一格,偶一为之虽无不可,终难登大雅之堂。事实上,基于对篆刻史的观察,“鸟虫印”的地位也确实如此,特别是在明清流派印大放异彩的篆刻黄金时代,“鸟虫印”并不被看好,甚至一度被斥为“缪印”。
单从“鸟虫篆”的历史来看,传世文献中,许慎在《说文》中有“秦书八体”“新莽六书”之说,其中均有所谓“虫书”和“鸟虫书”,并明确提出“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自东汉以降,对其名称历代不一,除“虫书”“鸟虫书”外还有“鸟书”一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总归是一类用于特殊场景的装饰性文字。
以目前传世和考古材料所见,鸟虫篆在先秦时期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且多见于南方地区的兵器铭文,于印章则多见于汉代玉印,而且主要是私印。至于《说文》提到的所书“幡信”则至今未见到让人信服的材料。
对鸟虫篆这一文字类别,学术界研究成果则首推容庚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先后发表的《鸟书考》《鸟书考补正》《鸟书三考》、新《鸟书考》(1964)。近代则有曹锦炎先生的《鸟虫书通考》《鸟虫书通考(增订版)》,相对集中的出版物资料则以曹锦炎在其原《东周鸟篆文字编》基础上增订改进而成的《鸟虫书字汇》和韩天衡《古玉印集存》《秦汉鸟虫篆印选》为最优。当然,以我拙见,拣选出的字和印章总量虽不算少,但严格意义上的“鸟虫篆”和“鸟虫印”还是极为有限,作为直接参考资料的字形、印例严重不足,也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篆刻创作中“鸟虫印”难以成长壮大。
再将视野缩回到篆刻中的“鸟虫印”创作,自明清以来,鸟虫印创作相对于篆刻艺术整体发展而言,可谓全面式微。直到民国时期,以方介堪先生为代表的大量优质仿古鸟虫篆印创作出现,称得上鸟虫印“中兴”。新中国以后,海上韩天衡、吴子建一出,又极大拓宽、丰富了鸟虫印的创作边界和思路,将鸟虫印创作领进了一个新的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韩、吴二人之于鸟虫印之功不啻邓石如、吴熙载之于清代流派印。而近十年来,以鲁大东、黄文斌为代表的新印人则大量地将先秦至两汉时期装饰感较强的青铜器、玉器、漆器纹饰引入鸟虫书印章创作,又为鸟虫印创作开一新门户,或可拟之赵之谦、黄牧甫之于晚清印史。
癸卯夏月,我蒐集整理了一些互联网所见吴子建先生的鸟虫印资料,整理之余,出于好奇,试着临仿了几方,不知为何竟然开始对鸟虫篆有了好感。趁热打铁,我集中临刻、仿刻了一些,受师友委托刻印时也刻意地采用鸟虫印风格创作,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癸卯岁尾汇总了一下,奇懒如我,在这半年时间,仅鸟虫印竟也刻了六十多方,剔除一些不太成型的和没留下印花或照片的,尚有五十多方。其中印文上占比最大的是闲章吉语,另外还有少量姓名章、斋馆印等。当然,限于眼界和腕力,风格并不统一,还是以模仿为主,配篆、用刀也明显稚嫩,甚至偶有硬伤。即使如此,于我也是难得的历练过程。年假期间,我把手头相对完整和清晰的印蜕重新归类、整理,以影像定格下这些“一日之迹”就当存档,略有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印章均已散出,却仅有印花而并未拓下边款。
思来想去,这一印章小辑暂且直白地名之曰“雕虫小集”,恳请诸师友多多指正批评,有以教我,也希望新的一年能再多刻一些,回头看看是否会略有寸进。
2024年2月18日夜草于甦斋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