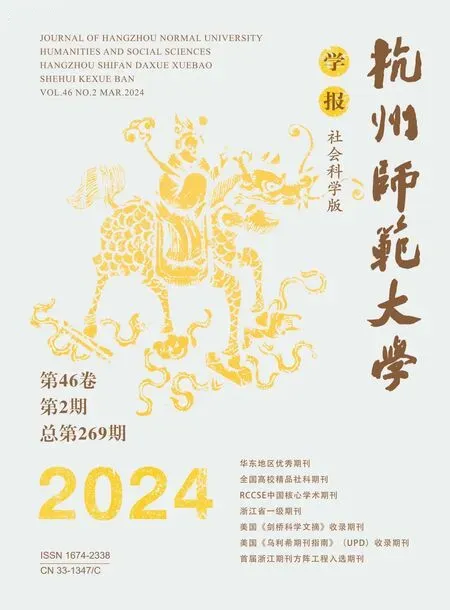重树经学典范:曹元弼“郑注配经”的思想要义
邓国光
(澳门大学 中文系,澳门 999078)
“经学”是中国哲学或学术思想之重要基础,但自20世纪初以来备受冲击与否定。物极必反。近30年来,学术思想主体性之关切与研究日渐深入与具体,于观念移植所引致问题更为深切反思,文化本位属性日趋明确,而“经学”探索明显受到普遍重视,经学思想与文献等方面之研究成果超迈前人。但未可就此满足,很多基础观念与问题所形成的种种成说,仍然需不断反思、实事求是、深入探索,其客观面貌方始得以呈现,而能够成为来日学术发展的重要参考。本文循此而进,尝试透过20世纪现代学校体制之外的重要经学人物曹元弼先生(1867—1953),揭示其以50年人生光景重树经学灵魂人物郑玄之地位的事实,以明学术典范重建之客观缘由,并超越方法论上返本之实例,以为再殖学术思想主体性之参借。
一、会通大义
“会通”本来是经学术语,是传统学术的重要观念。清末出现以“会通”为治学大原则的追求,存在特殊的历史机缘。此下专以曹元弼为个案进行研究,从而说明在此历史背景之中彰显“会通”的特殊意义。
曹元弼江阴南菁书院出身,师从黄以周,因学行纯笃,罗振玉推荐予张之洞[1](P.25),遂得起用为“学堂经科”总教习,奋力建设经科课程。其于20世纪30年代刊出《复礼堂述学诗》自注云: “光绪庚子辛丑后,……张文襄师既于《奏定学堂章程》注重读经,又奏立湖北存古学堂,以保国粹,正人心,塞乱源。”(1)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卷十五“述群经总义”第十五首自注,苏州吴县家刻,1938年,第16页。循此端正人心职志,自是其经学关怀,经学典范之重建,以此为端倪。
民国后,曹元弼完全退出体制。其布衣治经,无复体制依靠,然学术关怀未坠,因蔡元培提倡“伦理学”,遂更端视“礼教”,引出根本之伦理大义。其《复礼堂述学诗》序云:
弱冠前后出入十年,博观群经注疏各家之说,专力尤在礼。……以为圣人生养保全天下生民之道在爱敬。自天子至于庶人,各推爱亲敬亲之心,以爱人敬人,则和睦无怨,礼达分定,上下相安,天下国家永治无乱。本父子定君臣,人伦明,王道浃,此天地之经纬,民之所由生。[2](PP.14-15)
倡言圣贤经世本衷之爱敬为伦理根源,博而反约,总汇礼教,所以安天下,此其返本之学,乃中国学术精神之旨归也。故其归宗,心术为要。人格之高俊,于焉为尚,非关门户或中外之别也。
王欣夫于1920年从学于曹元弼门下凡35年,于师门了解至深,所撰《吴县曹先生行状》尝谓:“先生说经,一以高密郑氏为宗,而亦兼采程、朱二子,平质通达,与番禺陈氏为近。”[3](PP.522-526)其后更详言曰:
吾师年十九问学于定海黄元同先生,言治学当以家法为主,先生正之曰治经当以经为主,师由是不敢以株守旧说为遵家法,务由注以通经,不强经以就传。深推诸家离合异同之故,归于(而)案之经而合,问之心而安,久之乃益知郑义之不可轻议。说字宗许,说经宗郑,说理宗朱,非徒沿袭旧说,必求实而得于心。元同先生以“力挽时失”,李越缦以“高密干城”许之师。[4](P.1498)
所言“由注以通经,不强经以就传”,“说字宗许,说经宗郑,说理宗朱”之经学会通门径,乃曹氏于《复礼堂述学诗》之自述(2)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卷九《述礼总义》第六首自注,第5页。,特点在“案之经而合,问之心而安”,承孔子责言“于女安乎”之意,治经而有得于心,方为根本,非关门法,而诉之以学术主体责任感之自觉与实践。故此会通之道,乃经学自身之适时调整,体现学术主体生命力之充盈,以对治时代学术之逶颓情态。
详考曹元弼标举会通重旨,其来有自,原非闭户自倡。王欣夫撰提要存录曹元弼《毛诗学》,通盘综述其治经原则及贡献云:
吾师曹叔彦先生,于光绪丁酉(1897)掌教湖北两湖书院,张之洞举所著《輶轩语》中治经法、“明例、要旨、图示、会通、解纷、阙疑、流别七目”,属撰《十四经学》。继又掌教湖北存古学堂,而家居编撰时多,先后逾十年,诸经以次毕事。……至辛亥年止,已刊成全书者三:曰《周易学》,曰《礼经学》,曰《孝经学》。已刊而未成者三:曰《毛诗学》,曰《周礼学》,曰《孟子学》。于是以刊成三书,序而行世;未成三书,尚待续刊。其时忧患学《易》,注力于《周易郑氏注笺释》《周易集解补正》二书;继又撰《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均巍然巨帙。……吾师经传洽熟,所疏释有左右逢源之乐,且兼通群经,尤为自来儒林所罕有。(3)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庚辛稿卷一“《毛诗学》存四卷 一册”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19页。庚辛即庚子、辛丑,乃1960年至翌年。
“兼通群经”一语,定调曹元弼造诣。所谓“七目”,具见于张之洞《劝学篇》中,是为“明例、要旨、图示、会通、解纷、阙疑、流别”,此晚清戊戌年后极具影响力之主张。曹元弼晚年述张之洞《劝学篇》宗旨,于《复礼堂述学诗》云:
《劝学·内篇》皆致治之本,《外篇》皆救时之要。(4)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卷十五《述群经总义》第二十二首自注,第18页。
曹元弼自陈,秉承张之洞嘱托以学堂经科之建设原则,于《复礼堂述学诗》序云:
公既为《劝学篇》,又属元弼编《十四经学》,先为《原道》《述学》《守约》三篇,以提其纲。又与执友梁文忠公同编《经学文钞》,所录皆发挥大义、通贯源流之文。[2](P.15)
曹元弼又于《复礼堂述学诗》自注此事云:
光绪戊戌,……属余编《经学文钞》。余因博采众家,与节盫商榷去取,积年成书,务在阐明先圣作经垂教之旨,精别经师授受源流。二书盖亦《经郛》之意。(5)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卷十五“述群经总义”第二十一首自注,第17页。
“二书”盖指《十四经学》《经学文钞》,拟延续阮元未成之《经郛》。其《十四经学》乃循《劝学篇》“七目”为叙述纲领。此《经学文钞》十五卷,原拟为“存古学堂”之经科课本,乃庞大经义学工程,初与张之洞幕下梁鼎芬共襄其事。唯梁氏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引退,故独力处理。盖张氏以学堂取代书院,时间甚短促。然数年之间,曹氏完成《十四经学》之《周易》《礼经》《孝经》三学,并补成《经学文钞》十五卷,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江苏存古学堂刊出,故艰难可知。后胡玉缙撰讲义《周礼学》,亦只成遗稿六卷,足见学堂讲义之困难,非可一蹴而就,若非意志坚定,不足成事。
《经学文钞》卷首“经学大义”选录《劝学篇·内篇》五篇,张氏“会通”大义,曹氏所拳拳服膺,更为撰《礼经》《周易》《孝经会通大义论略》三篇讲义,彰显此大义,收入《经学文钞》之中,于其中所收录之《礼经会通大义论略》云:
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诗》之美刺、《春秋》之褒贬,于礼得失之迹也。《周官》,礼之纲领,而《礼记》则其义疏也。《孝经》,礼之始,而《论语》则其微言大义也。……盖圣人之道,一礼而已。(6)曹元弼、梁鼎芬《经学文钞》卷十二《〈孝经〉大义》,苏州:江苏存古学堂刻本,1908年。原刊未刻页码。
以礼统摄诸经之会通原则,具见曹元弼所撰《原道》《述学》《守约》三篇,亦置于《经学文钞》卷首“经学大义”,乃经世礼学之要领。曹氏于《复礼堂述学诗》自注云:
凡各经师发挥大义之文,皆分类采入此书,然如顾亭林、戴东原、段茂堂、阮芸台、孙渊如、汪容甫、张皋文、陈功甫、凌次仲、胡竹村、陈兰甫诸先生文集,说经居太半,考据精确,指示后学津途。(7)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卷末《复礼堂授群经总义书目》,第31—32页。又见《经学文钞》题下自注。
类聚清儒述说经义文章,盖此类文章,每见独到心得,与解经专书互补长短。末篇《守约》专述“归约”大义云:
治经之法,约之以《劝学篇》所举七事。……善乎南皮张相国之《劝学篇》,设治经简易之法,为“守约”之说。……郑君曰:“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总会之者,约之也。赵邠卿曰:“《论语》者,五经之馆辖,六艺之喉衿也。”馆辖、喉衿者,约之也。(8)曹元弼《经学文钞》卷首《经学大义》。
追源礼义本源,开出王道治平实践愿力。郑玄本此旨以通孔子成德理想,曹氏遂贞定“郑注配经”为典范,对治清中叶以来瓦解之潜流,树立礼教主体精神,非标榜汉宋门户,则是其卓识。
二、重建郑玄经义大统之要义
曹元弼身处易代之际,废经政策推行之后,依然闭门治经,坚守志节,身行忠义,严绝袁世凯招手。其于《复礼堂述学诗》直述其事云:
余伏处海滨,以待天下之清。不意袁世凯僭设礼制馆,以书币来浼,余矢死力拒之。呜呼!礼所以明人伦。乱臣贼子,礼于何有?其所谓礼制,不过粉饰僭伪而已。(9)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卷九《述礼总义》第七首自注,第6页。
盖对治当道巧借“礼制”以掩饰恶行,故高扬郑玄注《礼》之真实价值与意义于人世,践行郑玄立身行事为榜样,深意自存,于《复礼堂述学诗》自表云:
郑君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元弼学郑学,谨奉以为法。“礼是郑学”,六经同归,其指在此。修身之要,为政之本。国耻能兴,乱生能止。(10)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卷七《述〈礼记〉》第六十六首自注,第65页。“礼是郑学”乃孔颖达语,李云光师就“学”之高度阐明其“虽有语病,终非诐辞”,见《三礼郑氏学发凡》,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6年,第5页。
郑玄风骨高俊,志节有在。时代以掊击郑玄为风尚,则人心与学风偏颇失本,诋毁经学,同时毁弃良知而不自知。曹氏维护郑玄,所以端正人心,坚定不移。
然清末瓦解郑学之风气,因新学与今文学普流而弥烈。其时梁启超昭察当时今文学之成就云:
庄、刘别兴,魏、邵继踵,谓晚出学说非真,而必溯源于西京博士之所传,于是标今文以自别于古,与乾、嘉极盛之学挑战。抑不徒今文家也,陈硕甫作《诗》疏,亦申毛黜郑。同为古学,而必右远古,郑学日见掊击。[5](P.130)
颂扬今文学有功于掊击,所以挑战乾、嘉权威,故齿集于毁灭郑玄经义为要务,可见攻击力度之强度与方向,不复正视古来学人自身之风骨道义;此就其身份角度言之,故颂扬新变,破而非立,属趋新态度之一偏之见。
唯百年后,于世界文化之认识更为深刻周至,则通儒如徐复观者俯瞰全局,按察思想之发展义脉,反省世纪变幻之历程,出以重建文化主体气轴之长远考虑,则更深刻反省到集体偏趋一途之深层祸害,故云:
及清代今文家出,他们因除《公羊传》外,更无完整之典籍可承,为伸张门户,争取学术上之独占地位,遂对传统中之所谓“古文”及“古学”,诋诬剽剥,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已。……遂使此文化大统纠葛纷扰,引发全面加以否定之局,我常引以为恨。[6](PP.1-2)
此洞察排击古学之反面作用,以故徐氏云“我常引以为恨”,此现代学人临终前之心事。
然百年前,曹氏身处其时,早见及此,所陈袁世凯“僭设礼制馆”乃其一端。其非无的放矢或偏执一端,盖目击时艰,故其本“正统派之为经学”,推尊郑玄,所以长远考虑民族文化与生民休戚与共之发展,而非标榜个人喜好而已。曹元弼晚年于《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深省云:
盖自道、咸间,矜奇立异之徒,厌读书而喜盗名,恶郑学之平正通贯、不易穿凿。……而乐“今文”说之零文碎句所存无几,可借以驰骋胸臆,浸淫不已;遂至离经畔道,非圣无法。[7](PP.14-15)
背离此道而苟事矜奇立异,衍而为意气横生者,若尊郑之实效,验证以唐史,可知“唐人《诗》《礼》正义皆郑学”(11)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卷十五《述群经总义》第四首自注,第5页。,则学术端庄之实效可见。1933年曹元弼刊《中庸通义》,序曰:
昔孔子集前圣之大成,修定古大学教人六艺之文,作《孝经》以立其大本,因兼综道之全体大用,举纲统目,明示万世。[8](P.1)
周照前史,则“立其大本”为要义,乃确立郑注“总会”宗旨(12)《经学通论》云:“郑玄的注释大都不拘于一家之说、一派之言,而是旁征博引、融会贯通。”见马宗霍、马巨《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6页。,统摄道之“全体大用”,归本孔子集大成之精神,以“明示万世”,非徒局促于当下。
曹元弼维护郑玄经说,不遗余力,非出一时意气,乃基于学术造诣。曹氏年十五治《仪礼》,“耗十年精力”,光绪十八年(1892)刊出《礼经校释》二十二卷,其所据顾千里校、张敦仁刊《仪礼注》《仪礼疏》,乃称善本:其称引前修,“先师称郑君”,其他称君;“宋朱子称朱文公”,余称某氏某,是其尊郑玄而并重朱子,意非偏袒汉宋。郑玄称先师者,以其“依经立注,述先圣之元意,天秩人纲,不坠于地”[9](P.3),乃以郑氏据经文为本谊。(13)郑玄《三礼》注,自存完整义理,见李云光师《三礼郑氏学发凡》第四章第三十一节“申其义以释之”,第245—267页。所以先圣之元意,正是“王道”精神,此其推天德以立人道之保民大义,孔子身处天下大乱之时而作《春秋》,护持者端在于是。郑玄注经,宣述孔子精义,故举以为“先师”,深意存焉。
曹元弼所言“依经立注”为郑玄注经之原则,乃谓“郑君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故依经立注,为学者宗”[10](P.47),以况郑玄注经原则。溯其词所出,王逸《离骚章句叙》云:“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杜预《春秋左传序》以“先、后、依、错”说《春秋》与《左传》关系。下衍至清,则见凌曙《春秋公羊礼疏》称何休“依经立注,厥功伟矣”[11](P.2),曹元弼初有取于此。然此语毕竟以赞何休,以拟郑注,依然存依托之意,未足标举高明。
自民国以后,曹元弼经学更进新境,乃提炼出“郑注配经”以代之,郑玄之为先师地位,方得彰显。1938年刻《复礼堂述学诗》,首标“郑注配经”一词,自注云:
大抵士非坚苦卓绝,不能砥节砺行,任重道远。……郑君守死善道,其学与圣经并重,此千古儒者法戒也。元弻拟撰《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以郑注配经,而采马注与诸家说并入笺中,用示区别。[2](P.65)
身处神州陆沉之际,表出郑玄传经,守死善道,则文化大统斯得长存。1951年,《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四十卷成,其自序云:
我生不辰,……闭门避世,治《易》十有七年,……又竭十年力,潜研《尚书》。据郑注为本,集合《大传》《史记》《说文》(偁《书古文》)、马氏佚注,及《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周秦诸子、两《汉书》等所载《书》说为之笺;而博观约取,近师胡、江、王、段、孙、陈诸先生义,反复深思,弥缝变易释之。……寻绎其语脉,发皇其精神,务使文从字顺,一览而悟。[7](PP.15-16)
“据郑注为本”,乃视郑注如同经文之不刊,此“郑注配经”精神所在,乃千锤百炼之贞定,然至今不显。
若以此疑曹氏胶滞“汉学”,盖张之洞《輶轩语》标榜“宜讲汉学”,囿限于乾隆以来所谓汉宋门户之争持。(14)王欣夫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刚编纂颁行,由于总纂纪昀提倡‘汉学’而诋斥宋儒,因而‘汉学’与‘宋学’两派门户之见非常顽固。”见王欣夫《顾千里集·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页。然曹氏之说“会通”,归之于“守约”,重建道统,其“寻绎其语脉,发皇其精神,务使文从字顺”之治经大旨,乃其心得,超越刻意张皇今文、古文学之争持(15)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云:“晚清言两汉经学,每好分别今古家法,张皇过甚,流衍多矣。”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83页。家法、师法义无大别,见叶国良《师法家法与守法改法》,《经学侧论》,台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9—236页。,曾未专守一隅。其于朱子尊崇有加。1925年刻出《圣学挽狂录》,其“条例”二云:
《论语》旧有包氏章句、郑氏注;……朱子沈潜古训,会通先儒,发抒心得,作为《四书集注章句》,纯粹以精,至当不易。[12](P.1)
其正视朱子会通之精神,不曾游移,乃云:
朱子博极群书,含英咀华,融会贯通,《四书》注中语语有来历,字字有体验,好学深思博观有得者自知之。(16)曹元弼《圣学挽狂录》卷一“贫而无谄”节按语,苏州:苏城隐贫会养正堂,1925年,第53页。
曹元弼谓“郑君、朱子,集经学理学之成。理学从经学出,政治从圣经义理出”,其尊朱子之事实,显然可见。
曹元弼集大成之精义,会通之道,更有进焉,非止于郑君与朱子。此义于《复礼堂述学诗》压卷,以向所未显,故征述如下:“孟子而来及董生,儒宗许郑起东京。昌黎正学开朱子,卓尔亭林大义明。”自注云:“历代儒林,国朝先正,行谊著述,大矣美矣盛矣。而继往开来,学派统归于江都、召陵、高密、昌黎、紫阳、昆山六贤,此圣门之宗子,人伦之师表也。”(17)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卷十五《述群经总义》第三十一,第27页。确立董仲舒、许慎、郑玄、韩愈、朱熹、顾炎武为“圣门宗子”,一脉相传,继往开来,统宗归极,经学大统之所以立,修齐治平之典范具在,不容时人任意否定者也。
三、王道重建之保民要义
然则郑玄之为先师,其遍注群经,标示三《礼》,其《周礼》《仪礼》《小戴礼记》三注完整流传,“礼是郑学”就此而言,乃其精义所在。三《礼》之中,“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13](P.11),《周礼》因“致太平”之设计而特为所重,所以为天下谋求长远之福祉,“王道”以之彰显与实现。郑玄注《周礼》,汇汉礼精粹,曹氏《复礼堂述学诗》总结郑君《周礼注》为“极轨”云:
郑君因二郑之义,贯通群经,阐扬大典,先王经世宏纲细目,灿然分明。其所变易,则晦者无不明;其所弥缝,则歧者无不合。义据通深,斯为极轨矣。(18)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卷四《周礼》第四十四首自注,第58页。
经郑玄提倡,宋元以来托古改制,依《周礼》重整国体,更革国政,逮至晚清,此风蔚然大盛。与此同时,汉代以来以春秋公羊学为核心之今文之学,亦至清中叶后张衍发煌。《周礼》学与《公羊》学均在现实政治运作中起作用。张之洞为抗衡康有为,刻意标榜《周礼》古学。故晚清经世之学空前澎湃,实质在《周礼》《公羊》二学互持。(19)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汝纶)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9页)己丑(1889)后日记尝言:“近读王荆公《周官新义》,爱其文。……汉以来……独汉董仲舒《繁露》中所说《春秋》为最善。”曹氏亲历其时,谓:“安石假《周礼》,有为毁《周礼》,而皆以私智矜言变法。”(20)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卷四《周礼》第六十首自注,第73页。此乃为张之洞说法,表明张之洞之倡明《周礼》,本立心之公,本质大异乎北宋之王安石。
曹元弼《周礼》学师承黄以周,其所以重树“郑注配经”透出之人格典范,乃在千古不磨而挺立之圣贤精神,体现于至诚开出之礼学,以安天下而保苍生。礼学自存崇高人格之本质,并存崇高之“王道”实践。曹氏自陈研治《周礼》之历程云:
元弼少肄业南菁书院,从院长黄元同先生问故。先生承太夫子敬民先生式三家学,博通群经,尤邃于礼。……元弼撰《周礼学》,于封建、军制、庙祧等,皆因先生说而推详之,不揣固陋,间有弥缝,亦先生赞辨前贤之义。虽下已意,实本师法。(21)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卷九《述礼总义》第六首自注,第4—5页。
盖《周礼》之本在“王道”,曹氏于《礼经学》早有体会云:“《周礼》者,圣人本人伦以立王道之实事度礼。”(22)曹元弼《礼经学》卷四“会通第四:《礼经》”,宣统元年(1909)刻本。又言“三代之学所以明人伦”,礼为人伦(23)曹元弼《礼经学》卷四“会通第四:《书》”云:“孔子曰:‘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者,人伦也。”,是曹氏经义之本调,则“古今政教不易之道”乃具指王道人伦。故论政教,必本由衷关怀民瘼、心存救民水火之至诚,王道斯立。《周礼》王制之法,王道之纲领。礼在实行,条例清晰乃基本要求,故曹氏本“凡经文立言皆有法度”(24)曹元弼《礼经学》卷一“明例第一:礼经”。是《周礼》之学,本此以“立王道之实事度礼”,所言“实事度礼”指官联之类安排与管理,乃治体所在。
“王道”乃儒家经论核心,意义显见于周初箕子之向周武王说“九畴”,具载于《尚书·洪范》,乃以建立长治久安之经世大策。郑玄建立《周礼》为主轴之三礼系统,以《周礼》六官正文皆强调“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此《周礼》全书之基本前提与原则,而其意义原型出自《尚书·洪范》“九畴”之五“皇极”,云“皇建其有极”,乃所以“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此王道之根本大义。东汉晚年朝臣弄权,天下惟艰,王政不复,郑玄此际退身官场,坚持布衣身份终身治经,统理有汉四百年经学成果,死守善道,寄存王道大义于经注之中,以传后世而期盼“致太平”。此曹元弼之所以视为经学“极轨”者,存乎“经世”之关怀。经学之所以“经世”,乃建基于“保民”之淑世精神。此精神犹如父母爱护子女之真实感情,王道乃出自爱护天下苍生之衷款。
曹元弼身历时代巨变,四夷交侵,治体巨变,士人学术精神毁颓于日本传入之西方学术与体制,老百姓身陷水火,更苦不堪言,为古来所未有。时代之悲哀,岂能无视!其在20世纪初20年代讲述《论语》,于此难耐胸中悲痛云:
烽火蹂躏,甚者数百里无人烟。其次城邑残破,死亡枕藉。其最轻者,亦颠沛流离,辛苦垫隘,无所控告。士则十儒九丐,农则苛敛无艺,商则竭泽而渔,工则失业待毙,兵则积血暴骨,非杀人即为人所杀。穷民迫于饥寒,强者为盗为匪,弱者投缳饮药以死。四海之内,凡我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其疾痛惨怛之状,虽木偶铁人,犹将下泪;仁人君子,蒿目伤心,流涕呜咽,直泣尽而继之以血。呜呼!人之生也难矣!造物之不仁甚矣
处不仁之世以行仁政善道,此儒家经学之经世,方为真精神所在,原非学术门户或方法之所可范限。故自清代以来“帝王经学”窒压此“保民”之学术大义,而斤斤汉、宋之门户与方法,遂致逐末失本,徒以文字功夫夸誉,衍至西方学术体制之全面侵蚀,而中国文化主体之经学及其经世保民大义完全失落,凡此皆为通经之士如曹元弼者所大声疾呼以对治者,又岂在学术研究方式之细枝末节之类之倡导也。其忧世忧民之心至切,故身体力行,以东汉郑玄为立身治学之典范,同时正视两千年来经学承传之大统,而非独尊一家门户,故而讲求“会通”,于此透露悲天悯人之经学,代代相承,展示正面之建设力量,方为华夏学术精义所在。曹元弼身处风雨飘摇之时代,体会更为深刻,然亦处于教育体制排斥经学之世代,以故其“郑注配经”之深刻意义,此至道之失落于教育体制之中,至今依然不为世所知。然大统精神绵绵若存,复苏之机如历代经学承传之根本、忠诚之爱护心与使命感,亦必贞下起元者也。
四、结论
对待先贤与其学术,坚持遵守客观持平与知人论世两大原则,摆脱意气,在历史情景中理解人物与思想,是为关键,若刻意拔高或矮化,比无知更伤害学术。此所以本文正视民国以来长期受到轻视与刻意遮蔽之正统经学人物,及其为保存民族文化元气而奋斗终生之事实,以彰显中国生命学术之本质。专举曹元弼先生为例,以其于经学成就之卓越所提炼之学术典范意义。本文考述曹元弼以郑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为立身榜样,正视天下苍生于连年不息之战祸所受之伤痛,重树文化之主体精神,而思长远药治之方。其在清末参与学堂经科建设,成绩斐然。民国后曹元弼以布衣身份坚持治经,贯彻“由注以通经”之原则(25)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卷一五《述群经总义》第三十一。,致力复兴郑玄注地位,重建经学体统,确定《周礼》建极以致太平之宗旨,贞定“郑注配经”,以礼学自存高尚情操之本质,“保民”以建极之至德体现于生活世界,则其学术与生命实践统合为一,无疑是“虽无文王犹兴”之布衣经学典范。曹元弼“生命学术”之奋斗方向与事实,已经远远超越当时中学与西学孰为优劣的表象问题,应当为今后中国学术思想研究所珍惜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