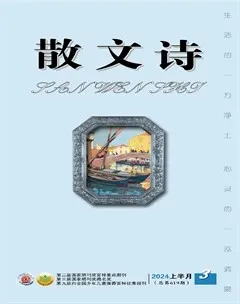乡音符号(外五章)
◎陈亚男
怀念, 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顽疾。 一个格外轻的脚步, 落入尘埃, 老旧的留声机吱呀作响。 回忆的线索, 缠绕过路的风。
一垄一垄的庄稼, 无规律地晃动着沉甸甸的穗子。 蕨类植物在山间静默生长, 将一场大雨的潮湿尽数吞下。 草籽与鸟雀的契约, 被新的泥土悉心照料。
故乡每一处珍贵的土地, 都令我珍重地一读再读。
稻穗流动的往事, 在骨骼里来来回回。 月光如水, 轻柔地淹过我的头顶。 在枯草掩埋的旧土里, 藏匿了岁月往复的秘密。 稻花漫香、 秋风乍起的年月, 故乡温软的风便吹拂过祖母的慈眉。
旧 忆
田间下过了一场雨水, 也许有蝌蚪。 倚声而歌, 原已是十年前的故事。 老旧收音机里的戏曲早已不再清晰, 田野的风声, 遗忘日光的曲线。
采茶的母亲, 做蒿子粑粑的祖母, 将童年的味道放入我掌心的纹路。
拉着老牛去春耕的祖父, 在田间地头用足印刻下一行行诗,稻子与玉米的灵性, 在自然之风里摇曳不息。
在钟声的迁徙里, 我听见, 稚子时代脱落的旧牙, 落在屋瓦上发出的一声“叮当”。
生命里的炊烟, 被时间赋予一切意义, 包括怀念。
祖母阖眼前未说出口的那句话, 终于, 我已不再耿耿于怀。
母 亲
归鸟记得时间, 从远处飞回筑巢的树。 傍晚的细风, 一趟一趟吹温心底的涟漪。 树木的叶片于一场风里婆娑不息, 细小的声响隐入流动的空气, 轻叩时间的虚无。
在母亲面前, 我不必将自己剪裁、 修整, 蒙上某一种不透光的砂纸。
母亲不图回报地爱着一个全部的我, 爱我最真实纯粹的面孔,如同宁静的土地接受一株花, 爱着其或完整或残缺的每一片花瓣。
爱可以抵御一切冷色, 在任何平常的时刻, 消解我语无伦次的悲伤。
而母亲, 是我心底长长久久的温度, 是时间最深的刻痕。 沉静如大海, 裹挟着爱的海浪, 一次又一次地浸润我的心魂。
我们之间
湿润的气味在风里漂泊, 你朝风摊开手掌, 掌心密密匝匝的纹路里, 生长出半截未宣之于口的诗篇。
在细碎的斑驳里, 观察一整个春天的来去, 尝试了解, 一株草的枯败与重生。
无数个悲欢的瞬间里, 我们成为彼此的另一双眼睛, 拨开荆棘, 拥起丛林里那朵不朽的蔷薇。
叶脉和日光交织不息, 季节的风缓慢流动, 你最爱的青提将要过季。 存在的永恒, 如同叶脉之上的隐喻。
但在无数月色泛滥的时刻, 我永久而深切地爱着你。
空气的流动悄无声息, 我们谈论起幻想中的世界。 也许是在山间, 远离人烟的地方, 眼中流连的湖泊, 倒映着水中月。
遥远之地
清晨的湖泊, 如同玻璃一般晶莹。 涟漪眷恋树的摇曳, 虔诚地临摹影印。 麋鹿张眼, 波澜不惊地凝望云雾花园, 开满外墙的蔷薇如同一个朦胧的梦。 这里沙漏缓慢, 岁月温和。
在午后, 将思索想象为一次旅行, 把一个完整的朝夕, 送给一本书, 以及耳机里的音乐。 被写上字句后夹在书本里的落叶,不再凋零。
羊群和花朵, 身上披着暖阳。 树影是干燥的河流, 依然荡漾。每一件好事都活着, 系上崭新的花结。
直到天色已晚, 我的夜空有最大密度的深蓝, 星子弥漫, 月亮比任何地方都要明确。 在月光的轻纱下, 我心甘情愿地, 被一首遥远的歌谣变成一个孩子。
寻 觅
过期的胶卷, 搅拌曾经的月光。 一片陈旧的芦苇, 在回忆里摇摆, 怀念着生命里每一场孤寂的大雪。
当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 穿过漆黑的隧道, 耳机里流淌的音乐影影绰绰, 来自星星与远方的箫笛。 一块裸石的纹理, 在阖眼的想象里变得具体。
凝视着蘸上倦意的灯光, 一口气许下十个毫不相干的愿望。
一个惊人的幻觉, 击碎虚无主义, 在一次尤为漫长的呼吸里,昨夜的琴音下落不明。
叶脉透过光, 折射整个世纪。 使人想起, 月色下一种奇特的芬芳。 不管走到哪里, 仍辨乡音。 不止一次地怀疑, 世间没有答案。 但寻觅本身, 也是一种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