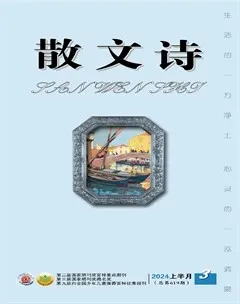我内心低矮的岛屿
◎席南凇
除了抵达
为了抵达, 你掏出湖心的一点白。
像往事浮在水面上, 有船经过时, 水就碎了。 那不满足于成为一滴水的水, 还在夜晚继续叫嚣。
我问你: “过了这么多年, 你的疆土是否还能种出海棠花?”眼看着, 疆土越分裂越小, 压在你名字上的眼泪, 已是禁忌。
总有人等待着被原谅。
脱下厚重的皮囊, 露出骨骼, 并无差异的, 在深秋, 凝视着一只麻雀。 你说: “看, 那只麻雀要降落了, 与海棠花的种子一起降落在腐朽里。 万物的忧伤沉积在这儿, 内心干涸, 无论怎样催促, 都发不出声响。”
你说: “为了抵达结果, 我重新编排了开始, 但依然无法跨越黑与白的鸿沟。 是的, 我该坚贞地走上这条路, 使用自己的躯体、 承诺、 本我的定义, 来重新衡量生的价值。”
为了抵达真实, 你开始虚构。
“至今, 我没有见过那扇只进不出的门。”
暴露在高原与高原的交汇地带
静静地, 回望遥远的光, 日复一日地照在故乡的房檐上。
不断重复的, 所谓的命运, 就这样呈现了。
当我同朋友谈起一种怀旧感, 仿佛是在高原与高原的交汇地带灌满回忆。 我突然记起, 火车站旁的一家面馆被聒噪的喊叫声笼罩着, 一如送别时内心的咆哮。
我牵过许多人的手, 也牵过河流的手, 往事零碎, 堆在废旧的草场上。 微风吹过, 记忆里摇曳的身姿再次摇曳起来。
我暴露了。
我的故乡被三大高原兜着, 摇晃, 我身处其间, 说不出来它具体的模样。 一张看惯了的面孔, 如今是夏天的颜色, 也远远地望着千里之外的我。
而关于一个村庄的诗句, 一个女人注定要在村头和村尾徘徊很久、 很久……
黑玛丽鱼
你不再是那条黑玛丽鱼。 那方寸之地, 数得尽的水草, 看得尽的陆地。
你不再用鱼鳞来遮挡昆仑山北坡的雨。
一次次, 它们落在湖泊的眼睛——湖泊中的湖泊, 柔和而浩渺, 仿佛世界的终点就是这里。 悠扬的琴声落在水中央, 将寂寥推得更远……
之后, 水, 打开了你的鳃。
之后, 没有谁可以阻止你长出腿来, 在水的利刃上直立行走。疲乏的时候, 你就坐在桑树的果实上, 跟着一起红, 或者白。
仅仅是一条黑玛丽鱼, 却拥有了比梦还要寥廓的内心。
此时此刻, 另一条黑玛丽鱼从你身旁游过, 高喊, “褪去一身鳞片, 从繁琐的秩序中跳脱出来的, 终将自由。”
你说, “在繁琐的秩序中得以宁静的, 终将自由。”
一只鸟的自白书
你叼着玉佛寺门前的枝条, 一路飞向深邃的黎明。 同时, 也将你狭隘的欲念隐藏在佛的慈悲里。
“佛说众生, 我便是众生。”
万千生命浓缩在你的双翼上, 振翅, 飞翔, 于油菜花地里诞下孩子。
死生之间, 这个巨大的黑洞常常枪声四起。 子弹掠过你的羽毛, 擦出明亮的火焰, 最终把巢穴烧毁。 不仅仅你一个人的巢穴, 等到大海水涨时, 潮汐也睡在这里。
从丰盈到嶙峋, 漫长的流年间, 储藏在你子宫里的风, 越来越小。 在人间这个没有边界的鸟笼里, 你持续地飞。 那些躲在红色砖瓦背后的人们也持续地飞。
但是, 只要一想到在田地里耕种的妇人, 你的鸣叫突然有了意义。
年轻的槐树
活着的年岁不足十年。
在门前站立的年岁同样不足十年。 如今, 已经将大半的枝条搭在屋檐上了。
一棵槐树, 也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才肯坦诚。 裸露, 无需缘由,在母亲那间房子进进出出时, 它毫不犹豫地拦下呼啸的北风。
母亲挺直腰, 又弯下去, 把生命之水引到槐树的表皮。
这就足够了, 善与恶、 奉献与索取, 在同一个女人的命运里不停地流转, 为远方的我埋下浅显的伏笔。
雨来, 就长在喧闹里;
雪来, 就长在沉默里。
而无论怎样, 都用自己挺拔的身躯挡住了灾祸。 正值夏季,我年轻的槐树已然繁茂成阴, 与微风有了另一种神秘的誓约。
——“无法倒回去的, 我的体魄, 还未萎靡。”
——“我长居于人们的悲欢里, 即便常淋雨, 对生活, 还是一无所知。”
黑 犬
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窝。
唯一一件垫在身体下的衣服, 还是去年冬天我从衣柜里翻出来的。
雪未消融的时候, 就堆在锁住它的铁链上。 铁链横躺在雪中,异常醒目, 而最醒目的, 还是它轻微的叫声, 落在结冰的玉米秆上, 掷地有声。
白的雪, 白的天空, 白的来路, 白的归处。
黑的犬, 黑的枷锁, 黑的瓷碗, 黑的洞口。
只是用手抚摸着它的背, 它便把前半生的秘密说了出来。 关于贞洁, 它说它梦见一只蝴蝶在稻田里留下印迹, 随后就跟随喜鹊奔向黄昏。
广袤的红色压在蝴蝶和喜鹊的额头上, 沉重, 却坚毅, 于炽热中获得安宁。
我们的灵魂在相互触碰的过程中有了停靠的位置, 或是墙壁的阳面, 抑或是羊群的玄关处。
从无到有, 水声潺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