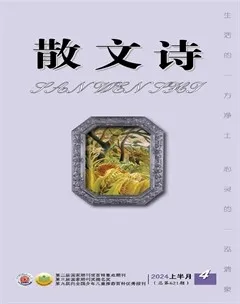于菲菲叙事
◎青 晨
序 曲
当雨落下, 你获得了某种宽恕。
于菲菲走在街上, 看到一只猫, 穿着人的衣服, 蹲在树阴下的墙角看着自己。 眼神格外清澈, 闪着光。 一只猫以人的姿态伸展身体, 低声说: 亲爱的, 你的身体里住着魔鬼。
那只猫跟着于菲菲走了很久, 消失在另一条街的树阴里。
雨还在下, 树上的叶子也在一片片落下, 雨水包裹在每一片叶子上, 让人莫名想起一首老歌, 名字忘记了。
于菲菲走出这座她生活了很多年的小城。
有关早餐
“天空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看到这句诗, 特别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于菲菲在日记中写道。 阴暗是一种空白。
否则, 天空中的白云就会浮现。
有时候, 她会面对一个魔鬼, 把自己蜷缩起来, 装作威武的样子, 没有比那个时刻更让人恐怖。 面对一块块褪去的衣皮, 多么神奇, 现在是春天, 她仍然走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 容貌鲜妍,她怀疑自己不存在。
早晨起来, 喝了一杯酸奶, 吃小块的曲奇。 之前不是这样的。
听到一个名字, 久远而恍惚。
于菲菲寻找那只猫, 有着青柠味道的语言。
它说, 我们都是碎片, 裁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他能让你进入下一个世界。
人样的
她住在一只笼子里, 密不透风。
不愿出去, 是我见过最执拗的人。
于菲菲对我的评价, 我不太同意。 首先我喜欢去流浪, 当然,这句话说了有很多年, 我现在还住在这样一间狭小的房间里, 足不出户。
早晨起来, 吃了小块的曲奇, 一杯酸奶。
临写王羲之的《圣教序》, 停不下来。 像在写一个人的一生,粗细变化, 歪斜横竖, 停顿快慢。 没有想到太多, 但却感受到大的悲伤, 然后是大的喜悦。 每一个字都在呼吸, 都在一万遍中不同。 我知道我每次临写都不一样, 都有不一样的气息与感受。
当感觉要停下来之前, 我清洗了毛笔, 大半个早晨已经过去了。 天空还是一片空白, 没有要下雨的意思。
木心说尼采重要的不是他的哲学, 而是他的思想。 他是属于诗的,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尼采的原因。
看, 这个人。 常常臆想, 人样, 太人样的。
我不太喜欢于菲菲, 她有时过于矫情。 比如不喜欢唱歌, 但喜欢听, 听一整天; 不喜欢买衣服, 喜欢逛一天街; 不喜欢吃早餐, 却每天都在吃。
她, 太人样。 她追随一只猫。
得路镇
她追随一只猫。 琥珀色的眼睛, 玻璃弹珠。
我见过的样子, 不会转动。
和所有的情节一样, 火车缓慢行走。 适合一个人的旅行。
或者说适合漫无目的前行, 它会经过麦田, 经过那粒糜子,经过一条河一条小溪, 经过一个又一个小镇。 其中一个停留了三分钟, 于菲菲站在小镇上, 看到了那只猫。 那个小镇的名字叫得路镇。 很远的山顶上有一座塔, 猫朝着那个方向去了。
她有一对玻璃弹珠, 放在衣服兜里。 走路时, 就会发出奇诡的声音, 她从来不把手伸进里面。
一个肥胖的男人坐在旁边, 裹着一身兔毛, 长着红眼睛。
于菲菲看见他在兔毛里面奇瘦的骨架, 与眼睛很是相称。
佝偻着壳内的躯干。 大家都躲开他庞大的身体。
有个孩子拔了一撮兔毛, 他没有喊疼。
一下子缩小了, 像个漏了气的气球, 瘫在地上。
火车上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小孩开心地大笑。
于菲菲把手伸进口袋, 玻璃珠冰凉寒冷。 她触摸到一个人的眼神, 噩梦般的哀怜。
火车进入黑暗, 驶入下一个隧道。
那个男人叫鹿
她走了, 很庆幸。 似乎平静了, 再没有风波。
街上有新人结婚, 车子过不去, 只好停下来。 平日里, 我绝不去凑热闹看这些, 今天索性就多看几眼。 看到了新娘子, 没有那么漂亮, 穿着红色喜服, 和新郎走在一起。 高跟鞋很细,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 新郎后面跟着彩车队, 一字摆开。 回家后, 我忽然看到了新娘的微笑, 一整天都挥之不去, 低头莞尔的那种笑,特别美。
于菲菲和我说, 她路过一个叫“得路镇” 的小镇, 她想住下来。 那里可能有白鹿这种动物, 她说, 这是直觉, 会给人带来美好的事物。
我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买了一大堆书, 越看越无知。查了得路镇, 没有查到。
以前看过的书忽然间觉得好无聊, 以前喜欢的一部分作家诗人, 现在都不喜欢了。 我现在喜欢一些小人物, 觉得能离自己近一点, 比如得路镇有一个与鹿为伴的男子, 于菲菲告诉我, 她猜想那个男人就叫鹿。
她没有拍照片给我, 我有些不太相信她说的话。 我甚至怀疑她不存在, 就像我怀疑那个新娘今天并没有笑。 她低头时看了自己的裙摆, 有没有被路上的尘土弄脏。 新郎的样子完全不记得了, 他有没有跟在新娘的旁边, 很模糊。 书里写了好多奇怪的话, 蒙头大睡时, 那些话全部出现在梦里。
那个叫鹿的男子与那个低头看裙子的新娘。
他们在空中飞, 在敦煌的壁画里。
陌生的城市
他们在敦煌的壁画里飞。
没有衣带飘飘, 没有丰腴的体态。
飞得很笨拙。
笨拙是一种智慧, 于菲菲不喜欢说话。
不喜欢和熟悉的人说话, 在陌生的城市, 她喜欢用另一种语气声调和人交谈。
这个城市的第一天也在下雨, 感觉世界就像连成一片的样子,雨从那边延伸了过来。 路边的梧桐树有大片的叶子落下来, 比雨的声音还大, 似乎安静了许多, 从另一个城市里区分出来。 渐渐地, 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踩在陌生的地砖上。 于菲菲买了一顶帽子, 咖啡色。
之前, 她从不戴帽子, 现在戴着, 觉得很好看。
他从不关心她的衣着。 这里的人, 都没有看到她。 没有看到一个戴着咖啡色帽子的女人。
在街上走了一天, 没有看到穿着白色风衣的人, 腰带上绣着几个字。 这里的人没有看到另一个人。 她也没有看到。
只有一些树的影子, 他们躲在屋子里, 躲在雨伞下面。
于菲菲喜欢这样, 她不会微笑。
她一笑, 就消失了。
忧郁的苹果
会凭空消失的人, 我知道有一人。
她不会笑。
准确地说, 你不知道她笑了没, 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定是经历过许多苦难的。
中午, 去干洗店洗衣服, 门上着锁。 但我听到里面有声音,很大声地吵架, 一个人的声音, 两个人的吵架内容。 有些绘声绘色的感觉, 一声比一声高, 忽然就安静了。
还记得店主的样子, 微胖, 眼睛很大。 长睫毛扑闪扑闪的,我把她比作“苹果”。 店里挂满洗干净的衣服, 散发茉莉洗衣液的味道, 店里还有一台老式缝纫机, 苹果有时会在上面安静地做衣服, 光线从玻璃窗打进来, 像一幅美妙的西方油画。 苹果有时在房子里移动, 没有见过她的男人, 刚才听到过他吵架时的言语很糟糕。 一颗苹果的移动, 很可爱, 也很忧郁。
我喜欢用水果去代替人, 比如于菲菲, 我把她称作柠檬。
喝柠檬水, 临写《圣教序》, 听音乐。 那个“之” 字像天鹅般飞起来。 “降” 字的一长点变成了一把横笛, 真是美妙。 独有“生” 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着诸位, 却也姿态飘逸。
柠檬水喝到一半更酸了, 音乐早就停了。
早上什么也没有, 连馒头也没有, 昨天下午也什么都没有。
哈哈镜
心不在焉, 则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走不完的路, 没有找到一间屋子可以为她停下来。
雨水浇透咖啡色的帽子, 贴在脸上。
于菲菲怀念那只流浪的猫。
怀念它紫色的蝴蝶结, 它曾经收留了她。
夜色浸在雨中, 浓厚粘稠。
一面哈哈镜重新收留了于菲菲。
她的脸在里面变得异常庞大, 眉骨更加突出。
露出大大的牙齿, 好似大大的微笑。
于菲菲第一次看到了于菲菲的模样。 很满意。
镜子里, 她的身后有一群小丑在跳舞, 场面非常欢乐, 她也加入进去。
她看到了小城所有的人都舞动着胳膊, 脸上涂着厚厚的油彩,慢慢地, 油彩被雨水冲刷干净, 他们, 不见了。
她用她的哈哈镜看街上的人, 有一次, 不小心看到了一个大鼻子, 鼻息特别大, 像刮大风般吵人, 但他不是那个人。
他是一个路人。
这里的人都像长着小眼睛的老鼠, 双手着地, 窸窸窣窣地走路。
买橘子水的老女人是巫婆, 脸上长了千百层褶皱, 每一层里都藏着秘术, 于菲菲从不敢喝她的橘子水。 她就住在小区旁边低矮的房子里, 每次见面, 于菲菲都会微笑着打招呼: 妞子, 来一瓶橘子水吧。
那个人也曾给她买过好多次橘子水, 她最喜欢喝。 那时的他,眼睛里都是星星, 于菲菲最喜欢。
每次看着他的眼睛, 就像望着一整片星空。
苹果的反义词
也许只有终结生命, 才会得到一个人的谅解, 得到世间所有的宽恕。
雅尔洛死后, 杜拉斯原谅了他所有的过错。
这样的结局也许是最好的。
曾经也有人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也许她死了, 大家便都可以释然了。
一些琐碎的小事更是可以原谅的了, 比如一位老伯在你不留意间, 把旧的扫把放在你车头前, 当你开车压在上面时, 他要你赔他一把崭新的。
好吧, 幸亏没有压倒小猫小狗, 花花草草, 赔他。
看看黄宾虹的画吧, 他的画宏厚华滋, 气势磅礴, 能容纳万物万事。 道法自然, 墨色变化多端, 每个人都能寻找到不同的内心声息。
傅雷曾评价黄宾虹: “初看艰涩, 格格不入, 久而渐领, 愈久愈爱, 是神品、 逸品。”
他的画, 我也临摹了, 气象万千啊, 自己的笔太拙, 心境也太拙, 拍了个背面, 大家都说墨色很好。
我不敢把正面拍出来看。
又去了干洗店, 换了老板, 是个瘦高的女人, 和之前的苹果可以组成一对反义词。
我没有询问苹果的事情, 把衣服放下, 走了出来, 门上的风铃照样一串叮当作响, 在闭上之后关在了屋子里。
碰到了放置扫把的老伯, 他乜斜着看了我一眼, 我赶紧把车子一周仔细检查了一遍, 什么也没有, 直到开走了好一会儿, 我还是觉得好像压过了什么东西。
回到家后, 我确定那是他的那个眼神。
看花人
越过山丘。 更多的人扑面而来, 于菲菲, 你好啊!
最先碰到的是她的眉骨, 她一一回击, 算是问候了那些人。一曲英文歌结束后, 进入到无人区。
这是一片秘密基地, 山顶的墓地, 有木桥连接着两个世界。不是祭奠的日子, 一般没有人来到这里。 木桥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 表示它的节奏很是欢快, 于菲菲也很欢快。
山顶还有一座小凉亭, 用来让风吹过它的身体, 四围便是散落的坟墓, 于菲菲坐在亭子里, 有一种俯瞰天下的感觉, 真好,她唱起了歌, 一片鸟鸣帮衬着, 声音越来越浓密。
山上的树木浓密茂盛, 遮盖住了于菲菲。 先是盖住了她的脚,接着是身体, 然后是她的嘴巴, 还留着眼睛看狭小的天空, 看天空中的白云, 一整天。 那云变幻多端, 来回穿梭, 走了又回来。有时它们会透露于菲菲的心情, 所以, 不必装作欢乐, 或者悲伤。
在这高山之巅, 竟然从来都没有想要流泪的感觉, 看见任何东西都觉得喜悦,
每次回去的时候, 于菲菲都会折几枝树枝, 插在花瓶里。 装一瓶山上的空气, 放在桌子上。
曾听闻一位寻花者, 去山里的寺庙求签, 最后留在了寺庙。他去的那天, 寺院内一株老梅树, 刚刚开了几朵。
还没有落上灰尘, 他每日都要在树下诵经念佛。
躺在一株桂花树下, 看桂花落下, 于菲菲想画这样一幅画。
那人穿着长袍, 戴一顶草帽, 半睡半醒。 亦梦亦幻, 不知是他梦花, 抑或花梦他。 他不是庄子, 桂树也不是蝴蝶, 是有人在看着他们。
也许只有古人有这样的情怀, 现代的人没有长袍, 也不戴草帽, 亦不会躺在树下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