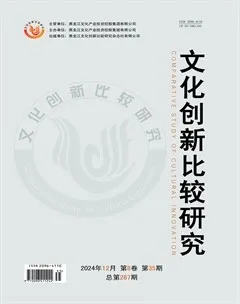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翻译要素浅析
摘要:中医典籍翻译是一种较为复杂的语言转换过程,触及医学思想、哲学认知(包括生命观、疾病观)等多维度、多层次的解读。在翻译过程中,有一些基本要素对翻译有着关键影响和制约作用。在此,笔者拟就术语化(路径)、理据性(语境)、能动性(译者)等方面对《黄帝内经》翻译进行解读,剥开其语言概念外壳,基于目标语重新诠释其语言内涵和文化思想,从语词、语句的本体范畴、文化属性、文本特征等角度明晰译语与中西医语境的契合与糅杂,建构源语和目标语的最佳匹配形式与意义延展,从而在翻译中将文本诠释与文化诠释有机结合,为中医典籍翻译的规范化研究提供素材与借鉴。
关键词:《黄帝内经》;翻译;要素;术语化;理据性;能动性
中图分类号:H315.9;R2-03"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12(b)-0011-04
Analysis of the Element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Inner Canon of Huangdi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lassics is a complex process of language conversion, involving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s of medical ideas and philosophical cognition on life and diseas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ere are some basic elements with a crucial impact. Now the translation of The Inner Canon of Huangdi is to b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rminology (path), reasoning (context) and initiative (translator), and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target language with the medical context based on the ontological, cultural and textual features of the words and sentences is also clarified. We aim to construct the optimal forms and meanings to combine text with culture in translation,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The Inner Canon of Huangdi; Translation; Elements; Terminology; Reasoning; Initiative
翻译是一种信息形式和意义转换的工具。在翻译过程中,作者提供源语信息,译者进行信息选择、策略运用并根据受众需要将源语信息传递给目标语读者。在中医典籍翻译过程中,一些因素对其译语形式与意义的构建有着影响和制约作用,主要包括形式与意义赖以存在的语境,即源语语境和译语语境、译者的构筑与赋予、文本语言构建路径及受众的接受等。中医西渐的历史经验表明,鉴于语词特异性、西方认知难以同中医学说的表达对接等障碍,中医翻译呈现出“思想和文化上不可逾越的沟壑”(陈可冀,2015),而单一的语言学、翻译学理论支撑下的研究显然不能解决当前呈现的各种问题,中医翻译尤其是中医典籍翻译应基于何种角度、采取何种方法,一直是学界思考的问题。
以成书于先秦两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为例,其行文风格凝练简洁,语词错简深奥,文化内涵丰富,以《黄帝内经》为首的中医典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极大影响了中医临床和中医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其兼具多样化和特殊化的词义引申、表层结构与深层内涵之间的歧义冲突、大量深奥的修辞手法等都成为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最大障碍。近年来,学界将研究重心转向文本本体研究。李照国(2018)、王银泉(2017)、詹菊红(2021)等人相继提出应最大限度地发掘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典籍在英语译介中的医文转换与文化落地效应。在此,笔者拟就术语化(路径)、理据性(语境)、能动性(译者)三个方面对《黄帝内经》的翻译进行简要解读和示例,以为学界提供一个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本文所有例词和例句的英译形式皆参考了Ilza Veith、吴氏和李照国译本并根据本文观点做了适当改写。
1 术语化(路径)
术语(terminology)是在特定学科领域用来表示概念称谓的专门用语,具有专业性、单义性、科学性等基本特征。术语化主要有两种形成方式:一种是原有词语的直接借用,另一种是作为术语元素或成分构成术语[1]。以《黄帝内经》为例,其术语大都属于中医通用词,如气、阴阳、五行、经络、六淫、五轮八廓、火为阳、九窍、阴虚、金水相生、急则治标、君臣佐使等,不胜枚举。不过,历经古今词义的演变,其“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矛盾日趋复杂”(李照国,2000)。这些术语在目标语中几乎完全没有对等语,从而翻译就成为目标语中术语形成的强大支撑和有力依据。换言之,翻译是否成功决定了其在译语中是否能真正实现“二次术语化”,即从某一范畴的术语转变为另一范畴的术语。于译者而言,首先可以基于术语标准化原则对《黄帝内经》的核心概念做出具有主控性、主导性的翻译阐释,以避免语义混乱,其间基于严格阐释意义的标准化翻译路径至关重要。
比如,术语“细脉”,用来指代“在指下感觉细小,脉细如丝”的脉象,据此可以找到thin、thready、small、fine等不同对应词。事实上,对于目标语受众来说,如以上4个词语,隶属同一语义范畴的不同的翻译形式或许承载了不同的意义内涵,从而造成语义模糊或歧义。又如,“学说”“理论”一词,最早有theory、norm、doctrine等译法,李照国教授对译语进行了探源并提出theory一词无论是从词典释义explanat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an art or science,还是从实际运用来看,都有更广泛的语用学基础[2]。因此,目前学界大都采用theory,如essential qi theory(精气学说)、yin-yang theory(阴阳学说)、visceral manifestation theory(藏象学说)、meridian and collateral theory(经络学说)、the theory of five circuits and six qi(五运六气理论)等。再如,“玄府”一词,由于西方人大都无法理解中医通过观物取象、援物比类等方式来推论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及施治方法,所以,形式逻辑指导下的译语mysterious house并不能被受众以特定方式接受和理解。“玄府”,正如王冰所注,“汗液色玄,从空而出,以汗聚於里,故谓之玄府。府,聚也”。汗孔以其细微幽玄不可见,或汗液色玄从孔而出,因而译为sweat pore(汗孔)最为清晰明理。有一点是肯定的,《黄帝内经》中大部分语词处于中西医学和中西文化的非共核部分,所以追求完全静态的形式对等并不可行,合理构建基于意义对等的译语似乎可以为中医典籍翻译提供理据性和术语化路径。当然,也可以考虑兼顾形式与意义。比如,以中医病名“顿咳”一词为例,典型的顿咳虽与西医学的百日咳相符,但世界中医药学联合会在《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中将其译为whooping cough,也有少数学者译为chin cough、kink cough,都没有采用西医对照语pertussis、bronchocephalitis,而是保留了cough一词,兼具用来表示其形、音特点的whooping、chin、kink之意。如此,既呈现中医语言符号特征(阵发性、痉挛性),又揭示出其实际内涵。
不同学者和学派对如何实现“二次术语化”的观点和研究角度有所不同,特别是针对同义词和近义词的翻译。比如:“亏”和“不足”是统一为insufficiency还是分别对应于consumption、loss、insufficiency?“脾气不舒”和“脾气壅滞”都用来指肝失疏泄或食伤脾胃导致的消化机能障碍,是统一为constrained spleen qi还是对应于spleen qi stasis,抑或spleen qi jamming?对此,笔者主张除特殊情况外,应采取相同的译语形式以保证意义统一,从而为实现译语的“术语化”和“规范化”提供保障,同时也在不损耗信息的前提下降低了阅读和理解的复杂性。
可以说,西方思维认知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重视语言的逻辑性,而翻译的逻辑性离不开译语的规范性,中医典籍中的术语如何通过译语实现二次术语化,使其在译语中呈现科学性的翻译理据至关重要。
2 理据性(语境)
理据(motivation)是事物获得名称的依据,用来说明名称、语义和表象的相互关系。《黄帝内经》语言多源于其自身的医源系统、文化内涵和哲学思维等母体,是人们对传统医学体系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认知的结果,具有良好的理据性。对此,译者可以通过分析语词的构词方式和语义结构来充分考量其理据性,从而使译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其命名理据,增强译本的信息生产力与传播力[3]。试看以下示例。
例1: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素问·阴阳离合论》)
《黄帝内经》语言的深奥晦涩与它善用比喻等修辞形式有很大关系,本句形象而具体地勾勒出原文喻义,“开”“阖”“枢”三字理据充分清晰,翻译时可以据此考量语词的本源意义和理据性从而给出译语形式。不过,理据相同,译者不同,译语输出也有区别。
吴连胜译:The Taiyang controls the superfice and spreads the yang energy to guard the exterior, so it is open; Yangming controls the interior and receives the yang energy to support the viscera, so it is close; the Shaoyang situates at the location of half superfices and half interior to transport between the exterior and the interior, so it is the pivot.
Veith译:This then is the parting and the meeting of the three Yang. The Great Yang acts as opening factor, the 'sunlight' acts as covering factor, and the lesser Yang acts as axis or central point.
从译文来看,吴氏父子基于考据路径,清楚解释了“开”“阖”“枢”的基本内涵和功能,通过superfice、exterior、open 来观照“开”,interior、viscera、close来观照“阖”,half superfice、half interior、pivot 来观照“枢”,对“三阳之离合”提供了依循语义理据范畴的形式构建,读者可以循到其词义的表征来源,从而追溯到其理据词,即“门”。 而Veith版译文仅使用了opening factor、covering factor、axis or central point,没有过多的显性解释,虽具有相当程度的“回译性”,但如果放到更为晦涩﹑更为复杂的句子背景中,恐怕读者在短时间内会由于不明所以而拒绝参与思想和文本的交流过程。
事实上,符号意义的清晰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目标语读者的理解程度和沟通效率。同时,信息量的充分程度决定了读者的参与程度和理解程度,而信息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符号意义的清晰度来决定的[4]。由此,注重研究并观照源语的理据,包括词源理据和语义理据,并且通过译文合理恰当地表达出其理据性内涵,从而通过语篇形成一定规模的译文理据,对中医典籍翻译是十分有意义的。
3 能动性(译者)
从宏观来看,《黄帝内经》翻译是一种知识信息与文化信息传播的手段,不仅指向文本,而且与译者和读者相关。从文化传播角度看,翻译过程是两种文化协商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是两种文化的中介和翻译活动的第一主体,拥有对文本信息转换的决定权。对于译者来说,这种决定权可称为翻译动机,即“译者能动性”,即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的主体控制性,包括翻译动机、观念等各个方面,贯穿翻译的始终,这些主体性因素对翻译过程和译文产生了深刻的隐性影响[5]。
比如,Veith在《素问》译本序中指出,“这部典籍的翻译代表了医史学家的方法,而非汉语言学家的方法,希望这一初步研究能成为对该书原文进行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尤其是对众多的语言学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可见,Veith是从医史学家的角度来介绍一部中医古籍的概貌,那她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诠释手法就不足为奇了[6]。不可否认,译者的文化身份、文化取向及译者身处的外部大环境对其自身产生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他(她)的语言选择或翻译方式上。仍以Veith为例,她所处的20世纪中期,中医学在西方医疗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影响甚至决定着Veith的文化取向和翻译策略,所以她很重视译文在读者中的可接受性,多采用归化法来阐释,同时也大量借用西医术语表达中医学概念,如例2。
例2:
黄帝问曰:天有八风,经有五风,何谓?岐伯对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素问·金匮真言论》)
Veith译:Huang Ti asked: \"There are eight winds in Heaven and there are five different kinds of winds in the arteries (veins 经); how can this be explained?\" Ch'i Po answered: \"When there is evil which arises from the eight winds, the evil becomes the wind of the veins and affects the five viscera; this evil will cause sickness.
Veith将“经、 经脉”译为arteries(veins),将“邪”译为evil,并在其他篇章中将“经络系统”译为the vascular system(血管系统),将“天癸”译为menstruation(月经),将“肾”译为testes(睾丸),如例3。
例3: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素问·上古天真论》)
Veith译:\"When a boy is eight years old the emanations of his testes (kidneys) are fully developed; his hair grows longer and he begins to change his teeth. When he is sixteen years of age the emanations of his testicles become abundant and he begins to secrete semen. He has an abundance of semen which he seeks to dispel; and if at this point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element unite in harmony, a child can be conceived.
Veith凭借自己的理解和其他译本来进行《黄帝内经》翻译,出发点就是她在序言中所说的,“出于从医学史角度对《内经》译介,使得西方人了解中医学”,从上文就可以看出她大量使用了诸如emanations、testes、testicles、semen等语词。这种“只翻译内容大意,而不去深究字义”(Veith,1951)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西方学者的翻译风格。她英译的《素问》(1—34章),虽然被菲利克斯·曼(Felix Mann)等学者认为晦涩难懂,但这种诠释风格为之后很多国内学者,如罗希文等人提供了借鉴,也受到部分学者的推崇。这种“集体性”诠释风格,即对医理或文化范畴的概括性译介,虽然部分掩盖了语词的符号色彩和词义特征,但在当时确实对中医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7]。
在中医典籍翻译中,译者对文本意义及其符号形式、意义的阐释、构想、创造,最终都要通过读者对译本的阅读、解读或解码,在传与受的互动空间中,使文本中的形式内涵或潜在意义转化为译文中的现实意义,从而完成翻译的“意义建构”到“意义生成”的完整生产过程[8]。所以,发挥“译者能动性”,通过对信息进行鉴定、解读甚至取舍、变换、调整信息结构和语义达到交流传递的最优目标,从而构建出一个融合译者和读者的“传”与“受”的互动空间非常有意义。当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是能动的、积极的,译者赋予文本的意义在读者阅读过程中得以确认、检验,并有可能被再创造。这是一种互动的过程,尤其需要译者把握中医典籍中丰富的意义内涵,使读者能够很好地融入译本意义构建中,如此,译者和读者才能在中医文本建立的联系中获得“共通”[9]。总体而言,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特殊内涵,彰显了“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的哲学思想、“援物比类”的隐喻结构、“内外相合”的整体理念。中医典籍语言具有强烈的“语言张力”,不仅传递了信息形式,还以中医特有的思维形态或隐或现地展示了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和内涵[10]。因此,把阴阳、五行、精、气、神、性味、归经、脏腑、经络、六淫等玄远幽深的概念和范畴翻译得言之成理,向全球推介一套能够折射出中医意象的译介语言,此乃荦荦大者。
4 结束语
本文基于术语化、理据性、能动性三要素对《内经》翻译现象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基于其翻译传播路径,重点探讨了如何在翻译中关注源语与目标语所传递的意义内涵,进而实现语言形式与意义的有效重构,这对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梁镛.术语化和术语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1986,1(3):20-23.
[2] 朱翔,何高大.哲学诠释学视角下的中医典籍翻译[J].中国电力教育,2012,25(28): 156-157.
[3]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 马翾昂.“形式”与“内容”的符号学重审:一种基于理据性的循环形式论[J].符号与传媒,2024,2(9):59-73.
[5] 程颜.论中西“场域观”视角下中医翻译的意义建构[J].医学与哲学,2017,38(4):78-81.
[6] 邱肋.中医古籍英译史实研究综述[J].中西医结合学报,2011,9(4):459-462.
[7] 程颜.传播学视阈下中医典籍翻译研究[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8] 潘源.影视艺术传播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
[9] 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10]唐韧.中医跨文化传播[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