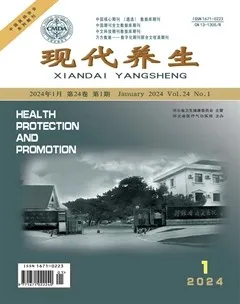神经内科疾病坏消息告知技巧
曾慧鈃 崔立谦 李金标
【摘要】 神经内科危重病、慢性病患者较多,疾病确诊后的坏消息会对患者和家属造成一定的心理应激,对治疗和预后产生不良影响。目前国内关于神经内科医生坏消息告知的报道很少,通过总结坏消息告知的模式、告知策略和告知方式,探讨神经内科医生坏消息告知的技巧,有助于提高神经内科医生的医患沟通能力。
【关键词】 坏消息告知;神经内科;沟通模式;告知技巧
中图分类号 R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223(2024)01--05
Breaking Bad News: Application in Neurology Zeng Huixing, Cui Liqian, Li Jinbiao.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ajor Neurological Diseases, National Key Clinical Department and Key Discipline of Neurology, Guangzhou 510080, China
【Abstract】 Critical illnesses and chronic diseases are common in neurology departments, which seriously affect the physical function of patients and even endanger their lives. Bad news of disease diagnosis will cause certain psychological stress to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t present, doctors are generally anxious about whether they can properly inform bad news. There are few reports in China about bad news being communicated by neurologis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communication modes of bad news notification procedure: SPIKES, SHARE, ABCDE, NURSE, and three types of communication modes: direct, pre-announced,paused, as well a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strategies of notification, aiming to discuss how neurologists inform bad news to patients and families skillfully.
【Key words】 Breaking bad news; Neurology; Communication mode; Notification skills
神經内科危重病、慢性病患者较多,如脑卒中、脑炎等,发病急、病情重,对患者的躯体功能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危及生命;或者如帕金森、痴呆等,病程迁延、逐步进展、预后不良,严重影响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这些疾病确诊时患者及家属往往心理准备不足,导致焦虑抑郁情绪发生率高、影响治疗依从性。因此,采用恰当方式告知相关病情的坏消息、及时安抚患者和家属的情绪并使其配合治疗,对神经内科医生来说是一项有挑战的医患沟通任务。大多数医生对于如何告知坏消息会感到焦虑,一方面是来自家属希望隐瞒病情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医生本身的心理压力:缺乏告知坏消息的知识和技能,不知如何合适的表达;担心患者听到坏消息后的反应无法应对;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患者和家属会谈;担心患者或家属提出的问题无法回答;受传统文化提倡的“报喜不报忧”所影响等[1]。不恰当的告知方式会加重患者及家属的焦虑程度,增加其对医生的不满情绪、对治疗计划的抵触,不利于患者身心健康的恢复。良好的告知方式有利于患者正确对待病情,增加患者的医疗满意度和治疗依从性。大多数关于坏消息传递的研究都集中在癌症患者身上,应用于非肿瘤环境中传递坏消息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国内关于神经内科医生坏消息告知的报道更少。通过总结坏消息告知的模式、告知策略和告知方式,探讨神经内科医生坏消息告知的技巧,有助于提高神经内科医生的医患沟通能力。
1 坏消息概念及其告知模式
医疗中的坏消息[2],一般是指患者病情恶化或者预后差的消息。但在实际医疗工作中,可能会改变患者对未来看法的信息都属于坏消息[3]。所以,确定什么是坏消息不在于医生,而在于接收消息的人,它取决于患者和家属的理解、接受程度及受教育程度[4],当患者不能理解或不能接受自己所患疾病的情况,对其而言都是坏消息。如何把事关生死的消息有技巧地告诉患者及其家属,是对医生沟通能力的巨大考验。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固定的程序来进行坏消息的告知,但国外研究报道的几种模式,描述了有效传递坏消息的程序和步骤,用以帮助临床医生向患者及家属恰当得体地告知坏消息,减轻医生的心理负担,这些模式均强调四个重要目的:收集信息,传递信息,人文关怀,提供帮助[5]。
1.1 SPIKES模式
该模式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告知模式,由美国学者Baile[6]针对癌症病情告知设计的,整个过程约60min。该模式包括6个步骤:①设置沟通场景(S-Setting up);②评估患者对病情的认知(P-Patient's perception);③引导患者参与协商(I-Invitation);④医学专业信息告知(K-Knowledge);⑤移情稳定患者情绪(E-Exploring);⑥总结病情,提出治疗对策(S-Strategy and Summary),具体内容如下。
(1)设置沟通场景:医务人员选择一个安静、不易被外界打扰的场所。可能有些患者或家属被告知坏消息后情绪会表现得比较强烈,故可以准备一些面巾纸,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得以体现医务人员的人文关怀。
(2)评估患者对病情的认知:有的患者在谈话前就已经对自己的病情有些了解,医务人员应首先确定患者对自己病情的了解情况,如用开放式提问如“您对自己的情况有什么了解呢?”“您担不担心您的病情呢?”来评估患者对自身疾病的了解情况。应知道以下3点:一是患者对病情的看法?二是患者已被告知了哪些信息?三是患者对病情的理解程度?这样医务人员才能了解患者对自己病情的了解情况和实际病情之间的差距,从而大概估计真实病情告知后患者的反应。
(3)引导患者参与协商:医务人员可以问一些问题如“你想了解有关的问题吗”,让患者有更多的参与感,同时试探患者是否做好接受信息的准备,以及他希望获取的信息需求。
(4)医学专业信息告知:告知坏消息前一般需要给出暗示,如“抱歉,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要告诉您”,让患者有心理缓冲时间;醫务人员将病情和治疗的信息如实、简洁、通俗易懂地告知患者,提供基本的正面信息,给出切合实际的希望。
(5)移情稳定患者情绪:正常人对坏消息的心理反应有一个过程:震惊否认—痛苦内疚—愤怒怀疑—消沉—平静—重建恢复。当患者在发泄情绪时,医务人员要临阵不乱,安静陪伴,不要打断他们发泄,认真倾听并严密观察他们的反应,鼓励他们表达目前感受,对其感受作出合理的回应(移情),尽全力减轻其疑虑和担心,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6)总结病情,提出治疗对策:医务人员用简单、可被理解的语言总结患者的病情并提出治疗方案,即使预后差,大多数患者还是希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参与接下来治疗的选择与决定[7]。医生应该避免说“恐怕我们不能再为你做什么了”,这让患者感到无助和被抛弃;相反,在没有治愈可能的情况下,重点应该是帮助患者重新定义希望,例如更少的痛苦,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
1.2 SHARE模式
是由日本学者Fujimori[8]等设计的模式,整个过程约10~15min。 包括四个步骤:①支持的环境(S-supportive environment);②如何告知坏消息(H-how to deliver the bad news);③提供进一步的咨询(A-additional information);④同理心及提供情绪支持(RE-reassurance and emotional support)。具体内容如下。
(1)支持的环境:医务人员应该在时间和地点上有充分的准备,目的是方便和患者共同面对及处理这个艰难的问题。或许医务人员时间有限,但为了告知效果佳,医务人员应该留出15~30min,找一个不被人打扰的环境,让手机处于静音状态,耐心告知,以免患者感觉医务人员敷衍了事。
(2)如何告知坏消息:医务人员先思考并排练一下应怎样来告知坏消息,比如说话方式是开门见山还是委婉一些,有哪些可以使用和避免使用的语句,需要家属在场与否等等,但是不管使用怎么样的告知方式,都要求诚恳而准确的告知,不能有所隐瞒,尊重患者的知情权。
(3)提供进一步的咨询:在告知坏消息前,要询问患者或家属对病情的了解程度和患者想了解哪些方面的信息。如果患者对病情已有一些了解,那就要完善其所了解的。还要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出回应。
(4)同理心及提供情绪支持:患者听到坏消息后的反应尽管有所不同,可能是悲伤、恐惧或愤怒,但是医务人员需要认同他们的情感,理解他们的处境并尊重他们的表达方式,从心理上、精神上体谅并支持他们,如温柔注视、轻柔拍打肩部或上肢。同时鼓励患者释放自己的情感,并进一步了解坏消息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样做有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6]。
SPIKES模式和SHARE模式的区别在于:SPIKES模式强调患者的自主权、告知顺序的严格以及所提供信息的详尽,而 SHARE模式则强调告知时家属的陪伴、告知时要婉转、要给患者及家属提供情绪上的支持[4]。SHARE模式告知时间短,基于我国医疗环境和家属参与决策的现状,有学者认为该病情告知模式相对更适用于我国[7]。
1.3 ABCDE模式[9-10]
该模式内容和SHARE模式相仿,整个过程15~30 min,内容清晰,告知时间适中,但在实际临床工作中还应结合具体的情景和家庭及文化的差异[7]。主要包括五个步骤:①事先准备(A-advance preparation):②建立治疗环境/关系(B-B-build a therapeutic environment/relationship);③充分沟通(C-communicate well);④处理患者及家属的反应(D-deal with patient and family reactions);⑤鼓励患者表达情绪并认可(E-encourage and validate emotions)。具体内容如下:
(1)事先准备:回顾患者的病史,进行心理排练,并做好情绪准备。如果患者愿意,请安排一名支持人员。确定患者对其疾病的了解程度。
(2)建立治疗环境/关系: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隐私,为每个人提供座位。如果合适,保持目光接触并坐得足够近以接触患者。
(3)充分沟通:避免使用医学术语,并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允许沉默,并按照患者的节奏移动。
(4)处理患者及家属的反应:处理出现的情绪,积极倾听,探索患者的感受,表达同理心。
(5)鼓励患者表达情绪并认可:纠正错误信息, 探索坏消息对患者意味着什么。
1.4 NURSE模式[11]
这是一种接收并回应患者情绪的五步法,目的是提高医务人员的移情反应。NURSE模式是对告知过程中患者情绪支持的一种好方法[7],具体内容如下。
(1)命名(naming):医务人员说出患者的情绪,如“您一定很害怕”“不知道您是不是……”。
(2)理解(understanding):医务人员在作出回应前,要理解患者的恐惧和担忧,向患者重复自己的想法以示理解,如“这对您来说一定是艰难时刻。”
(3)尊重,同理心(respecting):尊重患者的情绪表达,通过肢体语言或将陈述强度与患者情绪强度相匹配来实现,比如轻拍安慰患者,当然有些患者或家属不喜欢医务人员这么做。医务人员要对患者充分了解,根据文化和个人喜好的不同,做出适当的举动。
(4)支持(supporting):不仅要提供情感支持,鼓励他们积极应对疾病,还要提供接下来的治疗措施,将治疗方案的内容、步骤及预后告知患者,并给予建议。
(5)探索(exploring):直接询问患者的想法,如直接问“可以看出这个消息对你来说很沉重,你现在是怎么想的?”,这样有助于告知者更加了解患者,并增强告知者的同理心[6]。
尽管有不同的告知模式,但由于文化的差异,直接照搬引用并不合适。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文化更具差异性,对于坏消息告知模式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告知模式制定本土化的坏消息告知模式[7]。
2 坏消息告知方式与策略
2.1 坏消息告知方式
医生的告知方式有3种[12]:①直率式,在交谈的开始就直截了当告知病情;②预告式,交谈的前2min内分段传达病情;③停顿式,医务人员对病情描述非常详细,特别着重描述导致病情恶化的缘由,但是会拖延至少 2min的时间告知真实病情或者避免确切描述病情的本质。
坏消息告知方式的选择会因文化差异而不同,西方更偏向直率式和预告式的告知方式,更直接地完成告知;相反,东方患者对恶性病情的接受程度较低,故更偏向停顿式的告知方式,循序渐进告知病情[13]。
另外,在疾病的不同阶段,采取告知方式也不同。对于危及生命的病情,要直截了当告知家属病情危重程度,以免耽误治疗[2]。对于病情不是特别急但预后相对不好的疾病:①告知疾病诊断时,采取预告式或停顿式告知,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内容;②诊疗方案的决策阶段,采取预告和直接告知的结合,既给了坏消息来临的警告又明确告知各种利弊,有助于患者或家属做出最后的决定;③确定诊疗方案后,采取直接告知可以简明扼要地让患者或家属知道其情况;④若患者不幸死亡,采用预告与直接告知的方式,能充分考虑到家属的感受,给予其人文的关怀[14]。
2.2 坏消息告知策略
在被告知对象的选择上有两种策略:①直接策略是指直接向患者如实告知疾病的诊断。②间接策略则是指向患者家属告知患者的病情。直接策略保证了患者的知情权,为患者留出更多自主选择、决定后续治疗方案的空间。间接策略可防止患者在听到坏消息后情绪激动,产生过激的言语和行为,进而影响后续的治疗进程[15]。
在国内,对于不太严重的疾病,医生通常会直接告知患者,而对于相对严重的疾病,医生则通常会先与家属进行沟通[16],由家属决定是否告知患者,即所谓的间接策略。如果家属出于保护主义选择隐瞒,那么患者本人的知情权就会受到侵犯;但如果家屬选择告知,可能会由于专业知识的不足,导致告知的信息有误。国内一项研究表明,尽管很多家属不愿意向患者告以实情,然而患者本身意愿较强烈,要求自己承担,并且不同意医生对实际病情有所隐瞒[17-18]。
中国的知情同意法律法规随着患者偏好的变化而变化。法律法规的重点从保护患者逐渐转向告知患者[19]。1994年《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62条允许医生在医生认为合适的时刻替患者通知家属以“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章第11条规定,医生只应如实告知患者,同时应避免不良后果。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章第55条规定,当病情“不宜向患者解释”时,应向家属提供信息。2018年《医疗纠纷防治条例》第2章第13条规定,只有在“昏迷或其他无法自主做出决定或病情不适合向患者解释的情况下”,才应告知家属。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9条规定,医务人员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对于不能或不宜向患者说明的情况,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20]。
因此,理论上应选择直接告知策略,对病情是否如实相告应当取决于患者的诉求,问其是否想知道疾病诊断及治疗细节,而并非取决于家属的意愿。但是现实情况需要结合多方面综合考虑,由于每个患者教育背景和家庭经济环境不同,医生在日常工作中要注意仔细观察患者,初步判断其心理承受能力,对病情难以接受或者是一旦得知会导致病情加重的患者,可以优先考虑告知家属。
3 神经内科疾病坏消息告知技巧
神经内科疾病可根据病程及病情分成3类:一是起病急且重、可能遗留严重后遗症的疾病,如大面积脑梗死或大量脑出血或脑炎导致昏迷,短期意识无法恢复,如横贯性脊髓炎导致截瘫及二便失禁;二是慢性进展、可药物控制的疾病,这类疾病可能随时间延长或发作次数增加而逐渐进展,但具备药物控制症状出现,如帕金森综合征、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癫痫等;三是慢性进展、缺乏特效药治疗的,这类疾病相当于绝症,药物只能延缓其进展。如肌萎缩侧索硬化、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内科不同疾病坏消息的告知技巧应结合神经科疾病的特点和患者的需求进行告知。
(1)应根据不同的疾病种类采取不同的告知技巧:对于诊疗困难的疾病(如帕金森综合征、肌萎缩侧索硬化等),首先诊断就要谨慎,因为一经诊断就意味着病情不可逆、预后差,对患者和家属都是重大的打击。对确诊的患者的告知可参考SPIKES模式进行,采用预告式和停顿式告知,根据患者文化程度选择直接或间接告知。对于诊断容易的疾病或发病初期病情就严重的疾病(如脑卒中、脑出血等),告知前无需作过多铺垫,因为大部分患者及家属本来就有心理准备,告知时应更倾向于鼓励支持。对于病情突然变化的疾病(如意识变化),应尽早、直接告知预后不佳,希望家属有思想准备。避免花过多时间在告知过程上,否则会耽误治疗。
(2)告知时应根据患者的理解程度进行解释:比如大部分患者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神经脱髓鞘,此时就可以简单解释为保护神经的表皮脱落引发的神经传导异常,也可以运用类比的方式:像电线一样,表皮破损里面的电线出现异常放电现象,引发的接触不良进而失去工作动力。另一种方式是“俗话说”,将“癫痫”解释为老百姓所说的“羊癫疯”[16]。就是把专业的医学术语具体化、形象化、通俗化, 使患者对疾病有清晰的了解[21]。
(3)要回应患者及家属针对疾病提出的疑惑和问题,也要回应及安抚他们的情绪:神经科疾病常常对身体功能影响较大,病程长、花费多。有的患者得知诊断后往往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相比治疗方案的选择,更多想了解“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如果什么也不做会怎么样?”之类的问题,而医生经常对这类问题不做解释说明;或当患者意识不清时,家属希望了解是“患者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出现后遗症?”等。因此医生要了解患者及其家属的关注点,针对性给出妥当的解释。当患者或家属出现担心、恐惧等负性情绪时,要及时的安抚。如利用移情陈述(如“似乎您现在感觉……”或“这对您来说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有助于患者意识到他们的感受很重要,甚至会觉得被理解;支持性陈述(如“我是来帮助你的。”或“我们一起努力”)防止患者产生被遗弃的感觉;探索性问题(如“您说您很担心,能告诉我更多吗?”)有助于患者找到倾诉的渠道。
(4)注意在坏消息传递中适当加入好消息,给予“希望”,会令患者或家属在经受坏消息的打击后获得安慰。3类疾病坏消息告知时在传递“希望”时有所不同:第1类疾病的“希望”可以是稳定病情,康复锻炼,并适当降低生活期望值;第2类疾病的“希望”可以是正常生活,并预防发作;第3类疾病的“希望”则可以是尽量延长寿命。要让患者明白,尽管医学有了显著的进步,但不是所有疾病都可治愈;如果疾病无法治愈,至少我们可以练习与他们相处,享受当下的生活。
4 总结
对于神经内科医生来说,告知关于疾病的坏消息始终是一件有难度的工作任务,但只要做好充分细致的准备,注意“充分铺垫、循序渐进、语言通俗、人文关怀”这几个要点,多站在患者及其家属的角度考虑问题,就一定能取得对方的信任和理解,共同找到解决办法,这个困难的任务也就能迎刃而解。
5 参考文献
[1] Johnston DL, Appleby W. Pediatric oncologists opinions on breaking bad news[J]. Pediatr Blood Cancer, 2011,56(3):506.
[2] 闫柏刚. 如何将“坏消息”妥善告知患者[N]. 健康报,2021-01-27(005).
[3] Berkey FJ, Wiedemer JP, Vithalani ND. Delivering Bad or Life-Altering News[J]. Am Fam Physician, 2018 ,98(2):99-104.
[4] 王貴荣.外科医师告知病情坏消息的方法和技巧[J].中国医药指南,2012,10(34):384-385.
[5] 张俊平. SPIKES沟通模型在年轻乳腺癌患者病情告知中的应用[J]. 泰山医学院学报, 2015, 36(4):3.
[6] Baile W F,Buckman R,Lenzi R,et al.SPIKES-a six- step protocol for delivering bad news:application to the patient with cancer[J].Oncologist,2000,5(4):302-311.
[7] 周英华,庄严,张伟.提高医生告知坏消息的技能——两种常用沟通模式[J].医学与哲学(A),2017,38(3):81-85.
[8] Fujimori M, Akechi T, Morita T, et al. Preferences of cancer patients regarding the disclosure of bad news[J]. Psychooncology, 2007,16(6):573-81.
[9] Rabow MW, McPhee SJ. Beyond breaking bad news: How to help patients who suffer[J]. West J Med, 1999,171(4):260-263.
[10] VandeKieft GK. Breaking bad news[J]. Am Fam Physician. 2001,15;64(12):1975-1978.
[11] Back AL, Arnold RM, Baile WF, et al. Approaching difficult communication tasks in oncology[J]. CA Cancer J Clin,2005,55(3):164-177.
[12] Shaw J, Dunn S, Heinrich P. Managing the delivery of bad new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doctors' delivery style[J]. Patient Educ Couns, 2012,87(2):186-192.
[13] 杨雪松, Jonathan Silverman, Suzanne Kurtz,等.医患沟通技巧——如何告知坏消息[J].中国医学人文,2018,4(7):56-57.
[14] 孟玲.坏消息告知的交际策略及其有效性个案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2(4):42-51.
[15] 陈越,苏新春. 医生告知“坏消息”策略观察[J].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1):153-158.
[16] 陈越.中国医生的话语策略:坏消息传递的案例分析[J].中国医疗管理科学,2019,9(2):14-20.
[17] Jiang Y, Liu C, Li JY, et al. Different attitudes of Chines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oward truth telling of different stages of cancer[J]. Psychooncology, 2007,16(10):928-936.
[18] Wuensch A, Tang L, Goelz T, et al. Breaking bad news in China--the dilemma of patients' autonomy and traditional norms[J]. Psychooncology, 2013,22(5):1192-11955.
[19] Hahne J, Liang T, Khoshnood K, et al. Breaking bad news about cancer in China: Concerns and conflicts faced by doctors deciding whether to inform patients[J]. Patient Educ Couns, 2020,103(2):286-291.
[20] 鐘瑜琼,王晓敏,刘星.癌症坏消息告知中的伦理困境及其对策探讨[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1,34(9):1182-1187.
[21] 吴会娟,龙艺.医患沟通中的协商策略探析[J].医学与哲学,2018,39(5):36-40.
[2023-08-14收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