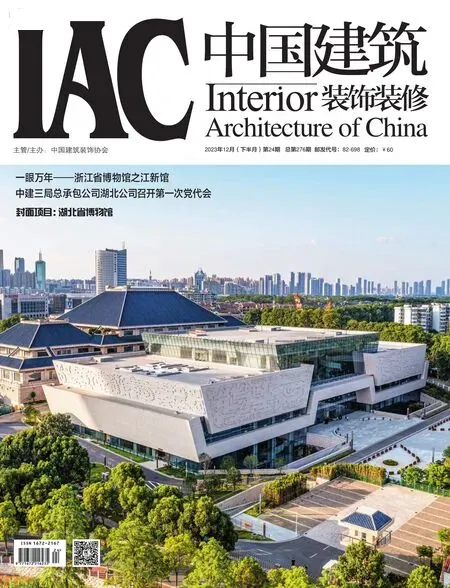基于共生理论的广州市城市更新研究
张 颖 梁景怡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至2022 年末,广州市常住人口为1873.41 万人,城镇化率为86.48%,已达到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1]。“十四五”期间,广州市提出将“城市更新”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表明后续城市建设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外延式的“增量”发展,向重视城市核心区集约型内涵式的“存量”发展转变。本文探讨了基于共生理论的广州城市更新,聚焦“城村共生”背景下的更新发展策略。
1 广州市城市更新研究
1.1 城市更新概述
城市更新是对城市中的旧工业区、城中村等已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进行更新,旨在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人居环境,推进土地、能源、资源的节约利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2023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继续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市更新,深入推进“三旧”改造。“三旧”改造主要面向旧城镇、旧厂房和旧村庄[2]。其中,旧村改造是三旧改造的重中之重。旧村改造是对城乡建成不久的农村村内部分年代较久的危旧房屋、设施等按照标准进行改造和修缮。
旧村改造常见方式有3 种:第1,由政府主导,进行土地整理和征收储备;第2,由村民主导,进行自主改造;第3,引进合作企业,由开发商和村集体共同主导进行合作改造。20 世纪90 年代以前,广州市主要实行“政府出资、政府建设”[3]。目前,广州市城市更新一般遵循“政府主导,鼓励市场参与”的原则,即在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的情况下,由市场主体制订改造实施方案和补偿方案,根据要求推进改造全过程。
1.2 广州市旧村改造现状及问题研判
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是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广州市虽然是国家级中心城市,但是仍有大规模连片的城中村,从土地产权、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上看,它们保留着传统村落的形态特征,但同时也具备城市的空间形态并承担一定的城市功能。
目前,广州市约有272 个城中村,其中中心城区有137 个[4]。下面从功能空间布局、道路系统、文化、产业4 个方面分析城中村的特征。
1.2.1 功能空间布局
目前,广州市城中村的用地以居住功能和商业功能为主,部分公共服务设施功能用地被占用,造成空间秩序混乱。另外,部分村民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断占据城中村的内部公共空间,造成自建房建筑群体过度密集等问题。因此,城市更新需要平衡多元利益,重视公共空间建设和功能重塑,协调多方利益,杜绝大拆大建。
1.2.2 道路系统
城中村内部不同等级路网交叉,人车秩序混乱。另外,城中村道路在建设时尺度相对狭窄,已难以承担机动车主干道的交通职能。城中村内部道路的有效衔接成为道路交通改造的首要任务。
1.2.3 文化
广州市的很多城中村在历史沉淀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记忆,存续着宗亲、血缘、典型白话、民俗等文化传统。但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很多城中村缺乏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加速了文化遗产的损坏与丢失[5]。因此,在城市更新中要注重保护与延续它的历史记忆及记忆空间,探求历史记忆与乡村发展共生,避免在城市化进程中丢失文化底蕴。
1.2.4 产业
城中村为广州市提供了接近13%的产业用地,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城中村的产业门类主要以小微型商业及附加值较低的初级制造业为主,产业门类多但产出效益较低,导致带来的土地附加价值较低[6]。
2 共生理论概述
“共生”是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提出的一个生物学概念,主要指2个不相同的有机体生存在一起[7]。而建筑领域的“共生”思想则是由日本建筑大师黑川纪章首先提出,强调异质文化的共生、人与技术的共生、内部与外部的共生、部分与整体的共生、历史与未来的共生、理性与感性的共生、宗教与科学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生[8]。黑川纪章的共生思想,涵盖了时间、地点、人、物质、形式及意识形态等可能存在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并通过消解各事物之间的对峙状态,达到相互共存的平衡状态。另外,从哲学思想角度进行思考,“共生”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别同时存在,而不是像达尔文“优胜劣汰”理论中的单一的互相竞争关系。
“共生理论”作为一种已有的成熟理念,为城市更新改造提供了新思路。城中村与城市作为2 个不同的异质体,分别代表了混乱与秩序、停滞与发展、流动与创造。城中村改造除了涉及城市建筑学科的问题,同时也包含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问题,属于多学科合作协调的复杂问题。
3 基于共生理论的广州市城市更新策略研究
城市更新不仅是我国转变城市发展的方式,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9]。本文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研究对象,提出通过空间共生、文化共生、产业共生、利益平衡4 大路径助力实现城市更新。
3.1 空间共生
空间共生策略,指尊重城市与城中村差异的空间形态与空间特色,拆除村民为追求房屋租金而建设大量破坏古村落原有建筑肌理文脉且质量较差的自建房建筑,新建适宜的商业空间予以补充,保留村内现存完整的祠堂、庙宇以及风貌完好的传统民居建筑。同时,空间共生策略还强调城市空间与村落空间共融,避免集中改造行为将城中村空间“格式化”。
广州市海珠区沥滘村作为目前广州市中心城区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在其更新方案中提出要继续保留沥滘古村中的典型古建筑,并结合沥滘古村打造湿地粤生活体验街区,开放社区的首层空间,融入休闲、社交功能,构建慢行区域,释放街区活力,营造更多公共空间,让林荫大道两侧成为生活聚集的场所。同时,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满足城中村居民的日常需求。沥滘文化体验街区示意图如图1 所示。

图1 沥滘文化体验街区示意图(来源:网络)
3.2 文化共生
文化共生策略强调传统文化与城市精神共生,注重城中村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城中村的传统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地打造创意文化产业,培育创意文化产业园。结合传统习俗建设社区文化艺术中心,以促进社区文化传承。
为更好地提高城市竞争力,广州市应将属地文化元素注入传统物理空间,用科技展现新功能与新形式,实现文化与消费、产业的深度融合。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文冲村已有800 年历史。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冲村作为广绣的重要代表地区,有大量的家庭刺绣作坊。为更好地保护广绣文化,文冲村的城市更新项目“广州幸福里”经过原址修缮等改造方式,完整保留了文冲陆氏大宗祠并将其建设为广绣非遗传承基地,达到在保护中创新、在继承中活化的目的。
3.3 产业共生
产业共生策略是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打造优质的产业空间,同步推进产业的引进和培育,达到产业空间结构的升级转型。广州市以城市更新为契机,提出要“产业先行”,吸引更多高端产业向中心城区聚集。
上境村是广州增城区面积最大的村镇工业集聚区,改造前整个园区村集体物业面积不到20 万m2,当时企业仅有26 家,主要以物流仓储、建筑材料制造等低端产业为主,总产值约1.4 亿元,年纳税总额不到600 万元。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上镜村改造后成为以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汽车电子等高端产业为主导的智慧型产业园区,预计2025 年投产后年产值可达83.4 亿元,年纳税总额可实现3.34 亿元。上镜村改造前后对比如图2 所示。

图2 上镜村改造前后对比图(来源:网络)
3.4 利益平衡
由于城中村改造在市场层面上涉及多方利益,因此利益平衡的策略重点在于协调城中村更新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即平衡政府、村民、开发商三者之间的利益[10]。从政府角度来看,城市更新是促进城市发展、落实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应多关注开发商的利益需求和村民的居住需求。从开发商角度来看,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存量市场更新是未来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开发商应当全面考虑,避免“一杆子买卖”,考虑置入更多的公共空间,在规划设计时考虑政府的城市发展需求和居民的传统文化保留需求。从村民角度来看,在保证自身居住权益的同时,也需要顺应城市发展的需求,不应幻想通过拆迁实现“一夜暴富”。
4 未来发展趋势
结合社会、城市、产业等理念,未来城市更新发展的趋势主要包括以下4 个方面:
1)多方参与模式兴起。目前,广州市城市更新主要由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城市更新能够带来巨大的内需空间,预计未来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
2)精细化更新不断推行。在严控大拆大建的新要求下,城市更新将更加追求精细化和品质化。城市更新精细化的改造要素不仅包括建筑、公共空间和公用设施等空间环境,还包括文化遗产保护、功能性属性、产权关系以及技术方式等组成环境,现阶段的微改造可以称为城市更新精细化的第一步。未来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将更多地表现为通过小尺度改造,使城市功能不断优化和城市空间品质不断提升。
3)加强与产业结合的发展。城市的现代化要依靠产业,产业的能级决定城市的能级。在更加注重产业内涵的发展趋势下,随着我国扩大内需战略的推进,城市更新不仅对于补短板、扩内需、增投资意义重大,同时也将有助于畅通循环,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4)低碳发展可持续。在“双碳”目标下,更要注重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绿色引领,实现城市更新的技术体系新突破。随着绿色低碳技术的加快创新与推广,将为城市未来实现“低碳城市”目标奠定基础。城市更新作为城市发展重要的规划手段,也将充分结合低碳发展理念、以低碳规划设计为引领,使改造后的城市更具可持续性。
5 结语
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品质的重要环节。本文以广州市城市更新为例,通过研究城市与城中村共生共融的更新路径,结合共生理论,探讨了广州市城市更新策略,以期为城中村更新改造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