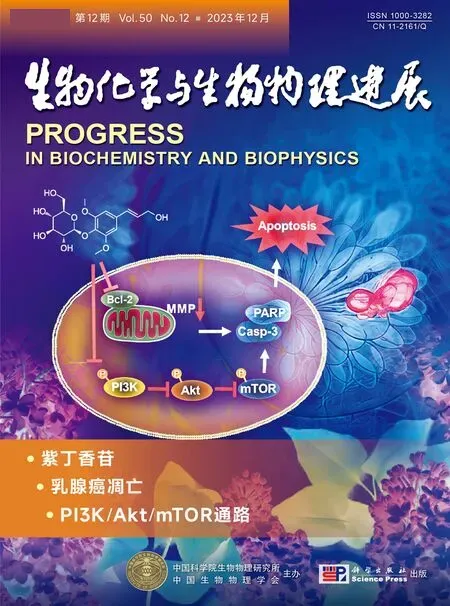高致病性冠状病毒感染导致宿主免疫应答异常*
陈 皓 李 强 张 建
(山东大学药学院免疫药物学研究所,济南 250012)
冠状病毒是一类广泛感染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以及禽类的包膜病毒。截至目前,已报道了7种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HCoV),其中HCoVNL63、HCoV-229E、HCoV-HKU1 和HCoV-OC43 4 种HCoV 仅引起普通感冒和自限性呼吸道感染。虽然早在20 世纪60 年代就发现了第一种人类冠状病毒,但直到2002~2003年期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CoV)的流行,才将公众对冠状病毒的研究重点从农业转移到公共健康上。十年后,另一种高致病性冠状病毒在中东国家出现,即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MERS-CoV),造 成 高 达36%的死亡率。2019 年底,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成为继SARS-CoV和MERS-CoV 之后出现的第三种高致病性冠状病毒,现已造成全球范围内数百万人的死亡。
SARS-CoV、MERS-CoV 和SARS-CoV-2 3 种高致病性冠状病毒感染通常伴随着免疫系统功能失调,除了导致类似感冒的症状外,还会造成一些严重的临床特征,例如淋巴细胞减少症、细胞因子风暴、急性呼吸系统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甚至多器官衰竭导致死亡。在进化关系上,SARS-CoV-2 与SARS-CoV和MRES-CoV 基因组存在一定的保守性,且具有相似的临床表征,揭示高致病性冠状病毒在免疫应答中的作用机制对于预防与控制冠状病毒感染具有重要意义。
1 高致病性冠状病毒概述
冠状病毒是一类有包膜的正义单链RNA病毒,属于尼多病毒目(Nidovirales) 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nae)冠状病毒亚科(Coronavirinae),因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其病毒包膜的尖峰突起类似王冠而得名。根据遗传学差异和血清学特点,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Ⅰ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ⅠCTV)将冠状病毒亚科进一步划分为α、β、γ和δ 4个冠状病毒属,β冠状病毒可进一步分为4个独立的亚群A、B、C、D。α和β冠状病毒属可以感染多种哺乳动物,包括人、猫、牛、狗、猪、老鼠等,γ 和δ 冠状病毒属主要感染禽类和其他哺乳动物。这些冠状病毒的感染会造成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功能紊乱[1]。SARS-CoV、MERS-CoV 和SARS-CoV-2 均为β 冠状病毒,SARS-CoV 和SARS-CoV-2 为谱系B 的成员,而MERS-CoV 是目前已知的引起人类感染的第一个谱系C的β冠状病毒。
有人认为,野生蝙蝠是SARS-CoV、MERSCoV 和SARS-CoV-2 3 种高致病性冠状病毒的潜在宿主,可以通过一种或多种中间宿主实现跨物种传播。果子狸和单峰骆驼分别被确定为SARS-CoV和MERS-CoV 的潜在中间宿主,SARS-CoV-2 的中间宿主尚不明确[2-3]。
2 高致病性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和结构
冠状病毒的单链RNA 基因组大小约为27~32 kb,是一种含有5'-甲基帽和多聚核苷酸尾的多顺反子RNA,其5'端的开放阅读框orf1a和orf1b约占据整个基因组的2/3,其翻译产生的多聚蛋白pp1a 和pp1ab,随后被切割成15 或16 种非结构蛋白(nsp1~nsp16),靠近3'端的约1/3 的基因组编码4种结构蛋白E、N、S和M以及一些辅助蛋白,形成一组嵌套的亚基因组mRNA(sg mRNA)[4]。其中,结构蛋白参与病毒粒子的组装并参与抑制宿主免疫反应,辅助蛋白主要参与病毒感染,非结构蛋白主要参与病毒基因组转录、复制,进而调控下游基因表达[5]。
冠状病毒的结构相似,病毒颗粒由外层的包膜和内层的核衣壳组成。病毒包膜来源于内质网膜,并缀有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S)、膜蛋白(membrane protein,M)、包 膜 蛋 白(envelope protein,E)。S蛋白通过与受体结合介导病毒进入宿主细胞。M蛋白是冠状病毒包膜中最丰富、最关键的结构蛋白,促进出芽并决定病毒颗粒形状[6]。E 蛋白是最小的结构蛋白,为疏水的病毒通道蛋白,能够增加胞膜通透性,影响病毒颗粒的形态和出芽[7]。这3种结构蛋白共同构成病毒包膜,包被N 蛋白(nucleocapsid protein)与冠状病毒基因组RNA(ssRNA)组装成的RNA-蛋白质(RNP)复合物,通过N 蛋白与M 蛋白相互作用包装成病毒粒子[8]。
3 高致病性冠状病毒的进入机制和复制周期
病毒感染的第一步是附着并进入宿主细胞,这一过程主要是由冠状病毒的S蛋白介导。冠状病毒S 蛋白由包含受体结合结构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RBD)的N 端S1 亚基和介导病毒与细胞膜融合的C 端S2 亚基组成。病毒颗粒通过两种进入机制释放病毒基因组[9-10]。a.膜融合途径。当S1亚基通过受体结合位点识别宿主细胞膜表面受体并与之结合后,S蛋白被宿主细胞表面的蛋白酶,如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 (transmembrane protease serine 2,TMPRSS2)、跨膜丝氨酸蛋白酶4(transmembrane protease serine 4,TMPRSS4)和弗林蛋白酶(furin)等激活并裂解,导致S1 亚基解离、S2 亚基暴露,S2 亚基构象改变并延伸到宿主细胞膜,导致膜融合。b.内吞途径。病毒长时间附着在细胞膜外会触发受体介导的病毒颗粒内吞作用,促使宿主细胞膜发生内陷。病毒颗粒被内吞到内体中,组织蛋白酶L和其他宿主蛋白酶会水解S蛋白,使S2 亚基暴露N 端的疏水融合肽,并插入细胞的内体膜。S2 亚基中存在的两个保守重复氨基酸序列HR1 和HR2 发生反向折叠,形成六螺旋束,使得病毒包膜与内体膜相互靠拢、发生融合,进而释放出病毒基因组。
基因组RNA 从包膜中释放出来后,招募宿主细胞核糖体,然后翻译两个开放阅读框orf1a和orf1b,由此产生的多聚蛋白pp1a 和pp1ab 被nsp3(木瓜样蛋白酶,PLpro)和nsp5(3C 样蛋白酶,3CLpro)切割形成15~16 个非结构蛋白(nsp1~nsp16),参与组成了病毒复制和转录复合物(replication and transcription complex,RTC),具有RNA 加工、RNA 修饰酶以及维持冠状病毒基因组完整性所必需的校对功能[4],对于病毒的复制和转录至关重要[5]。另外,由双膜囊泡(doublemembrane vesicle,DMV)等组成的病毒诱导膜复制细胞器,为病毒基因组RNA 和亚基因组mRNA(sg mRNA) 的复制转录创造了保护性微环境[11-14]。翻译出的结构蛋白易位到内质网(endoplasmic reticulum,ER)膜上进行装配,形成高尔基体中间区室(ER golgi intermediate compartment,ERGⅠC),N 蛋白包被新产生的基因组RNA,生成核衣壳结构,出芽进入ERGⅠC 中并获得含有病毒S 蛋白、M 蛋白、E 蛋白的脂质双层。最后,病毒粒子通过胞吐作用从被感染细胞中释放出来[4,15-16]。
4 高致病性冠状病毒受体与感染细胞
冠状病毒的结合受体决定了病毒感染范围和组织嗜性。3 种高致病性β 冠状病毒中,SARS-CoV和SARS-CoV-2 的细胞受体为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MERSCoV 的细胞受体为二肽基肽酶4 (dipeptidyl peptidase-4,DPP4)。
4.1 ACE2受体
ACE2 是一种Ⅰ型跨膜蛋白,具有单羧基肽酶活性。对人类转录组和多种哺乳动物的系统检测显示,ACE2 在视网膜、心脏、血管、上气道、肺、肾脏、肠道、胰腺、睾丸和胎盘等特定类型的细胞中广泛表达[17]。与冠状病毒的感染过程和发病机制一致,ACE2的表达水平从鼻上皮到下呼吸道逐渐降低。ACE2的mRNA在鼻杯状细胞和纤毛细胞中高表达,并在下气道基底细胞、纤毛细胞、棒状细胞和ⅠⅠ型肺泡细胞中仍可检测到[18]。除此之外,单细胞RNA 测序分析显示,ACE2 在肠上皮细胞、近端肾小管、心肌细胞、成纤维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和周细胞以及构成血脑屏障脉络丛细胞中表达丰富[19-20],这些细胞为冠状病毒在各个脏器的传播、导致多种疾病提供了有力支持。虽然SARS-CoV 和SARS-CoV-2 都 利 用ACE2 作 为 受体,但表面等离子共振研究表明,SARS-CoV-2 通过其S 蛋白RBD 与ACE2 的结合亲和力比SARSCoV 高约10~20 倍,这使得SARS-CoV-2 的传播能力大大增强[21]。
另外,在电子显微镜下能够观察到,在SARS患者血液和部分尸检样本的外周淋巴器官中存在病毒感染的免疫细胞,包括单核细胞、T细胞、B细胞和NK 细胞[22]。SARS-CoV 和SARS-CoV-2 都可以感染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和巨噬细胞,但病毒不能在其中复制[23-26]。通过批量和单细胞转录组学分析发现,SARS-CoV-2 能够感染肺泡巨噬细胞[27]。虽然大多数免疫细胞很少表达ACE2受体,但通过对髓系细胞受体的异位表达筛选发现,有几种C型凝集素(DC-SⅠGN、L-SⅠGN、LSECtin) 和Tweety 家 族 成 员2 (tweety family member 2,TTYH2)可能是SARS-CoV-2 S 蛋白的替代受体,它们可能结合S 蛋白非RBD 表位[28]。其他ACE2 缺失或低表达的细胞,有可能是通过CD147 与S 蛋白间相互作用介导病毒感染宿主细胞[29],但SARS-CoV-2 是否感染淋巴细胞尚未有明确的研究数据。
4.2 DPP4受体
MERS-CoV 是第一个被确定利用DPP4 进入宿主细胞的人冠状病毒。DPP4 是一种跨膜糖蛋白,又被称为CD26,在细胞表面以同源二聚体的形式存在。在人类中,DPP4 广泛表达于大多数器官的上皮细胞和内皮细胞上,包括肺、肾脏、小肠、肝脏、胸腺和骨髓以及免疫细胞。另外,CD26 也以可溶形式存在于循环中[30],这解释了MERS-CoV在体内的广泛传播、导致肺炎和多器官衰竭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DPP4/CD26还是T细胞的活化标志物,为T 细胞的活化提供刺激信号[31]。活化的B 细胞和NK 细胞同样上调CD26 的表达。有证据表明,MERS-CoV 能够感染T 细胞、B 细胞和NK细胞,并诱导T细胞凋亡[32]。与SARS-CoV和SARS-CoV-2 不同,MERS-CoV 在体外和体内条件下能够引起单核细胞、巨噬细胞、DC 和T 细胞的生产性感染[33-34],即MERS-CoV 在感染这些免疫细胞后,还可以在其中进行复制,这可能是MERS-CoV高致死率的原因之一。
5 高致病性冠状病毒与固有免疫应答
生物屏障和固有免疫系统构成了抵御病原体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对抗病毒免疫至关重要。病原体入侵时,宿主细胞上的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PRR)会及时识别外来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PAMP)或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有效维持细胞稳态。对于MERS-CoV、SARS-CoV和SARSCoV-2 等RNA 病 毒, Toll 样 受 体(Toll like receptors,TLR) 和视黄酸诱导基因Ⅰ样受体(retinoic acid-inducible gene Ⅰ like receptors,RLR)在识别病毒感染和启动Ⅰ型干扰素(ⅠFN-Ⅰ)抗病毒免疫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病毒进入宿主细胞后,位于内体膜上的TLR3、TLR7/TLR8 可分别识别内吞进入的病毒dsRNA 和ssRNA;而RLR 定位在胞质中,能够有效识别非自身RNA。PRRs激活后,触发一系列下游信号级联反应,通过激活转录因子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κB,NF-κB) 和干扰素调节因子(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ⅠRF)3、ⅠRF7,诱导促炎细胞因子和ⅠFN的分泌。ⅠFN反应启动后,以自分泌或旁分泌的形式触发ⅠFN 刺激基因(interferon-stimulated gene,ⅠSG)的表达,进一步促进抗病毒反应[35]。但是,冠状病毒已进化出多种干扰宿主防御的策略,通过直接或者间接作用的方式引起宿主反应异常(图1)。

Fig.1 Highly pathogenic coronavirus infection and innate immune response图1 高致病性冠状病毒与固有免疫应答
5.1 逃避先天免疫识别
冠状病毒介导的先天免疫拮抗作用始于逃避PRR识别。冠状病毒通过受体或内吞途径进入宿主细胞后,产生非结构蛋白构成病毒复制和转录复合物,启动病毒复制。为了避免被宿主PRR 识别,SARS-CoV 和SARS-CoV-2 通 过nsp12、 nsp13、nsp14、nsp16 对基因组RNA 和sgRNA 进行加帽和甲基化修饰[36-42],以伪装成宿主mRNA。随着病毒RNA 的合成,不可避免地产生dsRNA 中间体,这会导致宿主免疫反应的激活。因此,在感染初期,nsp15 会利用其核酸内切酶活性最大限度地减少dsRNA 的积累[43]。同时,为了保证病毒的复制,nsp3、nsp4、nsp6 诱导DMV 的形成[13-14],有效地将病毒复制与PRR激活隔离开来。
5.2 抑制干扰素应答
除了伪装病毒RNA 和保证基因组的复制,冠状病毒也可以直接作用于PRR 信号通路。nsp5 通过去ⅠSG化拮抗ⅠSG15依赖的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 5 (melanoma differentiation-associated gene 5,MDA5)的激活[44]。研究显示,辅助蛋白ORF7b和ORF9b、nsp5、N蛋白和M蛋白的过表达可以干扰线粒体抗病毒信号蛋白(mitochondrial antiviral signaling protein,MAVS) 的 激 活[45-48],ORF7a、ORF9b、nsp6、nsp13、N 蛋白和M 蛋白也可以靶向抑制MAVS 下游信号传导分子的功能。nsp6、nsp13 和ORF9b 与TANK 结合激酶1(tank binding kinase 1,TBK1)结合,并阻止其磷酸化;M蛋白和ORF7a 直接降低TBK1 的表达水平[45,49]。N 蛋白通过干扰TBK1 与ⅠRF3 之间的关联,阻止ⅠRF3的核易位,影响ⅠFN-Ⅰ的产生[50]。S 蛋白、nsp3 和nsp5 抑制ⅠRF3 的表达或阻止ⅠRF3 的磷酸化[51-53],ORF6、nsp5、nsp12 和M 蛋 白 阻 断ⅠRF3 的 核 易位[53-55]。nsp3 可以通过稳定NF-κB 抑制剂ⅠκBα 来抑制NF-κB信号通路[56]。
冠状病毒还会阻断ⅠFN 信号转导。nsp14 通过降低Ⅰ型干扰素受体1(ⅠFNAR1)亚基的表达来干扰ⅠFN-Ⅰ信号传导[57]。此外,nsp13 和S 蛋白都可以与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1(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1,STAT1)相互作用,以阻断STAT1 与JAK(Janus kinase)的结合和随后的磷酸化[55,58-59]。nsp1、nsp10 和nsp14 通过翻译抑制消除了对ⅠSG的诱导表达[60-61]。除了经典的ⅠFN 应答,蛋白激酶R(protein kinase R,PKR)介导的应激反应也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先天免疫应答途径。在检测到病毒dsRNA 后,PKR 磷酸化真核翻译起始因子eⅠF2的α亚基(eⅠF2α),导致应激颗粒(stress granules,SGs)的形成,抑制细胞和病毒翻译。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应激颗粒是抗病毒信号通路的平台[62]。研究证明,MERS-CoV 的ORF4a 通过隔离dsRNA 抑制PKR 依赖性应激反应[63],SARS-CoV-2 的nsp5 和N 蛋白同样能够抑制应激颗粒的形成[64]。此外,有研究表明,SARS-CoV-2 通过线粒体DNA 的释放激活cGASSTⅠNG1信号传导,导致细胞死亡和ⅠFN-Ⅰ产生,表明DNA传感器介导的cGAS-STⅠNG途径在RNA病毒介导的ⅠFN-Ⅰ诱导中起重要作用。目前已报道了几种SARS-CoV-2 蛋白,包括ORF3a、ORF9b 和nsp6,可抑制cGAS-STⅠNG1 途径。其中,nsp6 通过触发自噬促进STⅠNG1的溶酶体降解,进而减少了ⅠFN 的产生,并且SRAS-CoV-2 不同变异株(Alpha、Beta、Gamma 和Omicron 等)中nsp6 蛋白的3 个连续氨基酸缺失或许是目前SARS-CoV-2变异株毒性减弱的原因[65]。
5.3 干扰固有免疫细胞
5.3.1 影响髓系细胞功能
髓系细胞参与针对病毒的黏膜免疫应答的调节,包括巨噬细胞、DC和中性粒细胞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髓系细胞应答失调可能导致冠状病毒感染的一些标志性特征,例如,ARDS、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淋巴细胞减少症。虽然髓系细胞在早期识别和抗病毒反应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是PRRs 对PAMP 的识别也会影响髓系细胞下游信号传导和细胞因子分泌,因此,髓系细胞可能也参与了冠状病毒发病机制。
SARS-CoV可以直接感染原代人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不诱导ⅠFN产生,但是诱导趋化因子的产生[25]。对SARS-CoV 小鼠模型的研究表明,ⅠFN-Ⅰ信号传导的阻滞促进了炎症性单核巨噬细胞的积累,导致肺部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水平升高、血管渗漏和病毒特异性T 细胞应答受损[66]。SARS-CoV 感染还可以激活NLRP3 炎症小体,导致巨噬细胞焦亡[67]。MERS-CoV感染巨噬细胞后,诱导炎症细胞因子TNF-α 和ⅠL-6 的大量表达[33]。感染SARS-CoV-2的hACE2转基因小鼠的组织病理学表现包括间质性肺炎、大量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浸润,以及巨噬细胞在肺泡腔内的蓄积[68]。
除了巨噬细胞,冠状病毒感染还影响DC。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ⅠD-19)患者的肺和血液中常规DC(cDC)亚群耗尽[69]。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DC)是产生ⅠFN-Ⅰ的重要细胞来源,有助 于 快 速 控 制SARS-CoV 感 染[70],但 是 重 症COVⅠD-19 患者pDC 应答受损严重[71]。另外,在感染SARS-CoV-2的患者外周血中还观察到中性粒细胞的增多,并且尸检病理报告显示肺部中性粒细胞浸润,这可能导致中性粒细胞细胞外诱捕网(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s)的形成。与早期保护作用相反,NETs 和巨噬细胞的交互作用可以驱动后期炎症级联反应[72],造成ARDS、血栓等,对器官功能造成破坏性损伤。研究还发现,髓系细胞通过细胞表面表达的C 型凝集素受体(DC-SⅠGN、L-SⅠGN等)与病毒的接触,诱导髓系细胞产生强烈的促炎反应[28]。
5.3.2 导致NK细胞功能障碍
NK 细胞包括CD56brightCD16-NK 和CD56dimCD16+NK 细胞亚群,分别从事产生细胞因子和发挥细胞毒性作用。NK细胞同时表达调节其细胞毒性的抑制性受体和活化性受体,不具有MHC 限制性,激活后能够直接裂解病毒感染的细胞,有效控制病毒感染。此外,NK细胞还可以通过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antibody-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ADCC)杀伤感染的细胞,从而进一步清除病毒。然而,多项研究表明,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外周血中NK细胞数量减少,并且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同时,NK细胞上抑制性受体NKG2A 表达显著升高,而CD107a、颗粒酶B、ⅠFN-γ、ⅠL-2、TNF-α 表达或分泌减少,表明NK细胞功能耗竭[73]。一项新的研究指出,某些COVⅠD-19患者的TGF-β分泌不及时,导致T-bet下调,进而诱导NK 细胞上表达整合素β2,阻止NK细胞结合并杀死被感染细胞,最终导致病毒负载和疾病严重程度增加[74]。虽然SARS-CoV 和MERS-CoV能够感染NK细胞,但对于冠状病毒引起NK细胞功能障碍的机制有待更为详细的研究和探讨。
5.3.3 细胞因子风暴
尽管冠状病毒能够在被感染细胞中阻断并逃避固有免疫,但未被感染的固有免疫细胞仍能识别并响应PAMPs或DAMPs的刺激。当病毒感染的细胞发生死亡并释放大量新生病毒粒子时,这种响应会导致异常强大的固有免疫应答,诱导炎症过程,产生高水平的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例如,SARS-CoV的ORF3a、ORF8b和E蛋白增强炎症小体活化,导致ⅠL-1β 和ⅠL-18 的大量分泌,进而引发病理性炎症[75-77]。值得注意的是,在SARSCoV-2感染过程中,固有免疫细胞产生的TNF-α和ⅠFN-γ可协同激活JAK/STAT1/ⅠRF1轴,诱导一氧化氮的产生并驱动Caspase-8/FADD 介导的泛凋亡(PANoptosis),进一步导致炎症细胞死亡[78]。还有研究表明,ⅠFN 治疗在β 冠状病毒感染期间会诱导Z-DNA 结合蛋白1(Z-DNA-binding protein 1,ZBP1)所介导的炎症细胞死亡和PANoptosis[79]。这些促炎过程导致细胞因子风暴,进而造成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严重的组织器官损伤。
6 高致病性冠状病毒与适应性免疫应答
适应性免疫应答是清除病毒感染的第二道防线,能够通过细胞免疫应答和体液免疫应答有效杀伤病毒感染细胞。病毒感染后,专职抗原呈递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APC)通过抗原肽-MHC分子复合物和共刺激信号活化初始T细胞。活化的CD4+T 细胞分化为功能不同的亚群,包括Th1、Th2、Th17、TFH、Treg细胞等,分别在抗病毒免疫应答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活化的CD8+T 细胞会增殖分化为细胞毒性CD8+T 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直接裂解病毒感染细胞或释放具有抗病毒作用的细胞因子。B细胞通过T细胞依赖或非依赖性活化,产生高亲和力抗体,中和病毒抗原,介导体液免疫应答。但是,在高致病性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中,剧烈的炎症因子风暴会引发免疫抑制,包括T、B 淋巴细胞的激活失衡、衰竭和耗竭,所导致的免疫反应不具有保护性,而是造成组织损伤并加重疾病进展(图2)。

Fig.2 Highly pathogenic coronavirus infection and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图2 高致病性冠状病毒与适应性免疫应答
6.1 淋巴细胞数量减少
多个报告中指出,感染SARS-CoV、MARSCoV和SARS-CoV-2的患者外周血中出现淋巴细胞减少症,包括T 细胞、B 细胞和NK 细胞数量的急剧减少[80-82],并且淋巴细胞减少的程度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及死亡率相关[83]。对重症COVⅠD-19 患者的尸检结果显示,肺部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84],提示淋巴细胞被招募到感染部位是导致外周血中淋巴细胞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此外,导致外周血中淋巴细胞减少还存在以下机制。
a.冠状病毒对淋巴细胞的直接损伤作用。由于SARS-CoV、MERS-CoV 均能够直接感染淋巴细胞,可通过诱导淋巴细胞凋亡而导致数量减少。例如,SARS-CoV 的ORF7a 通过直接干扰Bcl-2 家族中促生存成员Bcl-XL 的功能来触发细胞凋亡[85],MERS-CoV 可以激活外在和内在半胱天冬氨酸酶(caspase)依赖性细胞凋亡途径[32]。另外,3 种高致病性冠状病毒均含有的nsp1,通过其核酸内切酶活性和关闭翻译功能抑制宿主细胞蛋白质翻译,尤其是氧化磷酸化蛋白和核糖体蛋白,直接抑制淋巴细胞的存活[86]。
b.冠状病毒对淋巴细胞的间接损伤作用。淋巴细胞减少可能与促炎细胞因子的水平相关。有数据表明,COVⅠD-19患者的淋巴细胞数与血清中ⅠL-6、ⅠL-10 和TNF-α 的水平呈负相关性,而恢复期患者血清中促炎细胞因子水平降低并伴随着淋巴细胞数量的恢复[87-88];并且,使用ⅠL-6 阻断剂托珠单抗治疗,可增加循环淋巴细胞的数量[89]。
c.抗原呈递信号的缺失导致T、B 细胞的活化受阻。T 细胞的活化具有MHC 限制性,B 细胞的活化需要T细胞的辅助作用。SARS-CoV感染的小鼠肺泡巨噬细胞会抑制DC 与T 细胞的相互作用[90]。冠状病毒感染会下调MHC分子的表达。表观遗传学分析显示,MERS-CoV 下调抗原呈递分子的表达与DNA甲基化修饰有关[91]。SARS-CoV-2的ORF3a 抑制MHC Ⅰ类分子的表达,ORF7a 阻碍了MHC Ⅰ类 分 子 的 组 装[92],ORF6 通 过 靶 向STAT1-ⅠRF1-NLRC5 轴抑制MHC Ⅰ类分子的诱导[93],ORF8 则是通过介导MHC Ⅰ类分子的自噬、靶向溶酶体降解来下调其表达[94]。转录组测序分析发现,MERS-CoV和SARS-CoV-2等冠状病毒能够特异性下调抗原加工呈递基因[86,91,95]。还有证据表明,SARS-CoV-2 感染导致外周血中DC 数量减少,并抑制DC的成熟和抗原呈递功能,因此影响T细胞活化[69],从而降低针对SARS-CoV-2的特异性T细胞反应的诱导。
6.2 T细胞应答失调
有效的抗病毒免疫应答取决于早期T细胞的病毒特异性活化。研究表明,感染SARS-CoV的患者能够诱导病毒特异性CTL[96]。同样,在感染MERS-CoV 的患者中观察到,早期CD8+T 细胞的增加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并且在早期患者和恢复期患者体内观察到明显的Th1 反应[97]。另外,感染SARS-CoV-2的无症状患者或轻中度患者,在感染后仅几个月的时间里,体内就可以检测到针对SARS-CoV-2 蛋白(包括S 蛋白、N 蛋白、辅助蛋白等)的特异性T 细胞应答[98]。总的来说,病毒特异性T细胞的激活对于遏制病毒感染和预防严重疾病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强烈而持续的细胞因子风暴,重症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免疫反应被完全颠覆。通过批量和单细胞转录组学分析发现,SARSCoV-2感染肺泡巨噬细胞会诱导T细胞产生ⅠFN-γ,而ⅠFN-γ反过来加强肺泡巨噬细胞释放炎性细胞因子,进一步促进T 细胞活化[90]。强烈的炎症环境会引发T细胞激活和分化的严重失调,T细胞过度活化标志物(CD38、HLA-DR),T 细胞抑制分子(PD-1、TⅠM3、LAG3、TⅠGⅠT、NKG2A)和共刺激分子(OX-40、CTLA-4)高表达,使T 细胞处于过度活化或耗竭状态[73,84,99],并且这些分子在CD8+T细胞上的表达高于CD4+T细胞[100-101]。此外,重症COVⅠD-19患者的CD8+T细胞产生穿孔素和颗粒酶B 的量增多,提示其细胞毒性增强[99]。这种免疫紊乱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器官衰竭密切相关[102]。
值得注意的是,感染产生的记忆T细胞对T细胞受体(TCR)信号和共刺激信号的依赖性降低,在一些促炎信号的刺激下即可激活,这种现象称为“旁观者激活”[103]。诱导这种现象的促炎信号包括细 胞 因 子,例 如ⅠFN-Ⅰ、ⅠL-12、ⅠL-15 和ⅠL-18,TLR激动剂以及补体蛋白C3a 和C5a。旁观者激活的T细胞迁移到肺部感染部位,释放细胞毒性分子和促炎细胞因子,导致宿主组织损伤[104]。长期COVⅠD-19患者体内显示病毒抗原持续存在,从而导致患者体内长时间维持着特异性T细胞应答和炎症状态[104-105]。
6.3 B细胞应答失调
体液免疫应答对于清除被病毒感染的细胞、中和病毒抗原至关重要,也是预防再感染的记忆反应的重要部分。高致病性冠状病毒感染会引发强大的B细胞反应。
6.3.1 病毒特异性抗体
感染SARS-CoV的患者在症状发作后的4~14 d即可在体内检测到特异性血清抗体[106],21 d 内进行血清转换[107]。感染MERS-CoV的患者在感染后15~21 d 内观察到血清转换过程[108]。感染SARSCoV-2 后的几天内可快速检测到病毒特异性ⅠgM、ⅠgG、ⅠgA,以及中和抗体(nAb)[109],抗体滴度在病毒清除后的几周内持续存在[110-111]。有效的体液免疫应答需要B 细胞和滤泡辅助性T 细胞(Tfh)的精密合作。通过对COVⅠD-19疾病严重程度的血液样本进行纵向分析发现,在感染的早期阶段,功能性病毒特异性循环Tfh细胞生成受损,从而延迟特异性抗体的产生,增加进展为严重疾病的风险[112]。
冠状病毒通常是根据其S 蛋白上的RBD 识别宿主表面受体,RBD 具有高度免疫原性,结合该结构域的抗体可以有效中和病毒,阻断病毒与宿主受体的相互作用。尽管COVⅠD-19 患者的血浆与SARS-CoV 的S 蛋白、N 蛋白以及MERS-CoV 的S蛋白具有交叉反应性,但未发现与SARS-CoV 或MERS-CoV的RBD存在交叉反应性[113]。并且,来自COVⅠD-19 患者的血浆不能中和SARS-CoV 或MERS-CoV[113]。在感染SARS-CoV的患者观察到,康复患者体内中和抗体水平在出现症状20 d左右达到峰值,并能保持高水平的中和抗体水平;虽然死亡患者中和抗体的生成速度快,在症状出现后15 d即达到峰值,但是此后中和抗体水平会急剧下降[114],说明高水平和可持续的中和抗体水平是感染患者康复所必需的。
除了针对S蛋白的中和抗体,还有针对冠状病毒表面M蛋白和E蛋白的非中和抗体。与中和抗体相比,非中和抗体的作用非常复杂。研究表明,非中和抗体可能不影响病毒进入细胞,但会介导病毒颗粒进入表达Fc受体(FcR)的吞噬细胞,特别是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从而促进吞噬细胞对病毒颗粒的吞噬和清除。但是,冠状病毒可能会利用这一吞噬作用释放病毒核酸并进行复制,使得免疫细胞成为病毒的复制中间体,进而逃避免疫杀伤[33]。另外,病毒也会导致吞噬细胞的炎症性激活,出现抗体依赖性增强(antibody-dependent enhancement,ADE),引发细胞因子风暴,导致肺部病变[115]。一项SARS-CoV 感染猕猴的研究发现,抗S 蛋白ⅠgG 导致严重的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Ⅰ)和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在肺部的大量积累[116]。也有报告称,从一名MERS-CoV感染患者身上分离出的单克隆抗体也显示出ADE[117]。从急性或恢复期COVⅠD-19 患者的血清样本中检测到FcγR 和/或C1q 介导的ADE[118]。另外,在SARSCoV-2感染的部分危重患者中发现,总抗体水平在发病后约2 周时显著高于非危重症患者[119],其原因可能与非中和抗体介导的ADE有关。
6.3.2 记忆性B细胞
B 细胞对病毒的应答不仅可以应对初次的感染,还可以为再感染提供保护免疫力。感染消退后,在急性期和恢复期形成的浆细胞会继续产生抗体,从而产生血清学记忆。在初次感染期间形成的记忆B 细胞,可以通过分化为新的高亲和力浆细胞,以快速响应二次感染,并通过诱导长寿命浆细胞和记忆B细胞,以及协同T细胞应答来实现长期保护。感染SARS-CoV后,体液反应的寿命相对较短,在感染后2~3年后,针对SARS-CoV的特异性ⅠgG和nAb反应减少,25%以上的个体中几乎检测不到[120]。一项最新的数据显示,在感染6.9年后,MERS-CoV 感染仍然可以诱导高水平的病毒特异性中和抗体以及T细胞和B细胞应答,并且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无关[121]。有研究显示,接种过疫苗的COVⅠD-19 恢复期患者,在接种后6 个月内具有高浓度的S蛋白特异性抗体,并诱导S蛋白特异性记忆B细胞库的组成发生变化,这与黏膜部位的功能保护增强是一致的[122]。值得注意的是,细胞因子风暴也可能损害生发中心的形成,从而危及冠状病毒患者B 细胞免疫功能。在一名死于急性SARSCoV-2感染的患者胸腔淋巴结和脾脏中观察到生发中心的缺失以及生发中心B细胞的明显减少[123]。
7 总结与展望
近二十多年,高致病性冠状病毒SARS-CoV、MERS-CoV和SARS-CoV-2给公众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高致病性冠状病毒进化出了多种策略逃逸先天免疫反应,包括逃避PRR 识别、抑制ⅠFN 反应和随后的信号转导等。但是,当病毒感染的细胞死亡或释放大量病毒时,旁观者细胞会产生强大的固有免疫反应。冠状病毒还能够感染巨噬细胞和DC,诱导炎症因子的大量释放,引发细胞因子风暴,造成肺部和呼吸道的损伤,患者临床表现为ARDS和组织损伤等。另外,高致病性冠状病毒感染还普遍造成淋巴细胞减少症,可能的机制有促炎环境的影响,或者是对免疫细胞的直接感染诱导细胞凋亡或生产性感染导致的T、B细胞耗竭等。但是,更多的数据表明,重症患者体内存在持续活化的T、B细胞应答。本综述描述了高致病性冠状病毒与宿主免疫应答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强调了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应答在介导保护性免疫和促进病理性损伤之间的不平衡性,提示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免疫应答紊乱可能是患者组织损伤和死亡的重要原因(图1,2)。
截至2022 年底,SARS-CoV-2 的变异株共有5个,分别为阿尔法(Alpha)、贝塔(Beta)、伽玛(Gamma)、 德 尔 塔 (Delta) 和 奥 密 克 戎(Omicron)。通过对Omicron 变异株刺突蛋白的电镜结构进行分析发现,Omicron刺突蛋白结构域组织稳定性提高,其局部构象、电荷和疏水微环境的改变使其不被大多NTD和RBD抗体识别,从而促进病毒的免疫逃逸[124]。这使得Omicron 的传播力显著增强,成为2022年初以来的绝对优势流行株。不过,国内外证据显示Omicron变异株肺部致病力明显减弱,临床表现已由肺炎为主衍变为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125]。
目前抗SARS-CoV-2的治疗策略包括中和抗体和一些小分子抗病毒药物(3CLpro抑制剂和RdRp抑制剂)。中和抗体通过靶向结合SARS-CoV-2 刺突蛋白RBD 的不同部位,非竞争性结合SARSCoV-2,防止病毒进入人类细胞,具体治疗方案有单克隆抗体(安巴韦单抗/罗米司韦单抗)、静注COVⅠD-19 人免疫球蛋白或康复者恢复期血浆。然而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S 蛋白上出现大量突变,这常导致中和抗体失效,相比之下,小分子抗病毒药物通过抑制病毒复制,在减少重症和死亡患者方面发挥了明显优势[126]。Paxlovid(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是3CLpro 抑制剂,通过阻断病毒3CL 蛋白酶的活性,抑制病毒复制所需要的功能性非结构蛋白的形成,从而干扰病毒复制。阿兹夫定片和Molnupiravir(莫诺拉韦胶囊)是RdRp抑制剂,可与病毒的RNA 聚合酶结合,在新合成的RNA 分子中引入错误的核苷酸,从而起到抑制或清除病毒的作用。另外还可以短期应用糖皮质激素以解除机体炎症反应过度激活状态。对于ⅠL-6水平明显升高的重型、危重型患者可应用ⅠL-6 抑制剂(托珠单抗)。
尽管目前SARS-CoV-2感染造成的重症或死亡案例已明显减少,但部分人群在感染COVⅠD-19之后出现了长期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包括疲劳、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认知功能障碍(例如,意识模糊、健忘或精神不集中或头脑不清晰),被WHO定 义 为COVⅠD-19 后 综 合 征(post-COVⅠD-19 syndrome,PCS)。这些症状可能自最初发病起持续存在,也可能在康复后出现,这些症状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消失或复发。有研究表明,在 感 染COVⅠD-19 后,PCS 持 续 存 在 超 过20 个月[127]。病毒引发的炎症、自身免疫、内皮损伤(对血管)和病毒的持续性被认为是PCS 致病因素。由于广泛的病毒嗜性,涉及不同的器官并且症状各不相同,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明确诊断或治疗PCS的建议[128]。
对于SARS-CoV-2的免疫应答现状还未被完全阐明,通过对高致病性冠状病毒与宿主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深入探索,可以为抗冠状病毒药物开发和建立有效的预防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的其它文章
- 光泵磁强计双轴探测听觉诱发脑磁信号的初步探索*
- Optically Pumped Magnetometer Lights up The Era of Vector Detection for Magnetoencephalography:an Experimental Evidence
- Prediction of m6A Methylation Sites in Mammalian Tissues Based on a Double-layer BiGRU Network*
- 人乳寡糖的结构及其分离分析*
- TRPM7生理病理学功能及其小分子调节剂的发现*
- GSDMs家族蛋白介导细胞焦亡在抗肿瘤免疫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