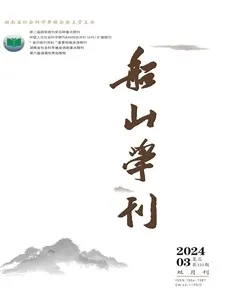董仲舒与王船山人性论之异同
摘"要:董仲舒与王船山虽所处时代背景不同,但在人性论的建构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从天道阴阳的角度阐明人性的来源,主张天道有阴阳而人性有善恶;都肯定人性的差异性,区分了先天人性与后天人性,并在修养论上提出以心养性。他们的人性论也存在差异:董仲舒区分了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旨在强调圣王之教;而船山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性,否定了中民之性与圣王之教的说法,提出“日生日成,习与性成”的动态人性论,更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其思想更具有现代性。通过对董仲舒与王船山人性论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儒家人性论从帝国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思想嬗变。
关键词:董仲舒"王船山"人性论
作者李慧子,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成都"610066)。
自唐代韩愈撰写《原道》以来,孟子性善论作为儒家道统的核心地位被不断强化,宋明理学更是推崇孟子性善论而贬抑荀子性恶论。汉代大儒董仲舒因其“性未善”论与荀子相近而被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其人性论思想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在儒学思想史中有一条隐而未显的人性论线索,那就是荀子的性恶论和以董仲舒、王充为代表的人性有善有恶论,直到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那里才得以凸显。董仲舒与王船山作为汉代与清代的两位大儒,所处的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都有所不同。汉代最突出的时代课题是建构一套为大一统帝国服务的国家意识形态。汉武帝的三次策问旨在思考国家如何根据天道明晰人心、人性,在天人关系的基础上建构伦理和政治秩序。董仲舒把汉武帝的“大哉问”总结为“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 [1]2498,“董仲舒开创性三品说,目的是为汉武帝君主专制的社会等级制提供人性论的根据,他的性三品说也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2]52而王船山身处天崩地裂的时代,其人性论在学理上建构在批判程朱理气二分人性论的基础之上,在现实中则表现为对君主专制的反抗,因而具有现代性。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与王船山的人性论建构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对两者人性论的比较,可以看出儒家人性论从帝国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思想变迁。
一、人性的善恶及其天道来源
(一)人性有善有恶论
董仲舒认为,孟子的性善论不完备。当与动物性相较时,人性是善的;但当普通人性与圣人之性相较时,则会发现人性并非全善。阴阳相参而生化天地,天创生万物,“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3]410。董仲舒从天道阴阳角度解释人性中的善恶,指出天道有阴阳,人性有善恶。“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穷论者,无时受也。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3]299-300如果人的性情有善而无恶,就像天有阳而无阴。如果性是善的,那人怎会有七情六欲呢?“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3]294-296
王船山认为,“夫性者生理也”[4]55,二气五行之理就是人性的内容。“乃其所取者与所用者,非他取别用,而于二殊五实之外亦无所取用。”[4]56“二殊五实之妙,翕合分剂于一阴一阳者,举凡口得之成味,目得之成色,耳得之成声,心得之成理者皆是也。是人之自幼讫老,无一日而非此以生者也,而可不谓之性哉?”[4]55性是气之理,性必在气中。船山主张气既是宇宙之本也是万物之源,性则是气化流行中所显现的纲纪条理。宇宙万物之所以有条理秩序,乃是由于气本身具有健顺、生生之性。“气日生,故性亦日生。性本气之理而即存乎气,故言性必言气而始得其所藏。”[5]468-469性源自于天而顺应天道下贯凝聚于人的形气之中。“原于天而顺乎道,凝于形气。”[6]33气是天之气,气禀秉受于天,气质中的善与不善也来自于天,因此不能说天命中没有恶。“使性而有不义,则善与不善,性皆实有之;有善与不善而皆性气禀之有,不可谓天命之无。气者天气,禀者禀于天也。”[4]54-55如果人性是全善的,就不会接受不义:“使性而无弗义,则不受不义。” [4]54但人性需要以气之形质为体,而气之形质是有善有不善的,因此人性也有善有不善,需要人在后天的道德实践(习)中去成就善性。如果说义理之性是“不受不义”的纯善之性,那么习的作用不仅无效,而且性也无法成就和实现。这就是所谓“不受不义,则习成而性终不成也” [4]54。由此可见,船山并非完全的性善论者。
(二)善恶的天道来源
董仲舒提出天人同类、天人相副。天是万物之祖,天创生万物与人,天人是父子关系。“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无天而生,未之有也。”[3]410由于天人是父子关系,因而人的形体和情感与天数是相副的。“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3]354-355
董仲舒肯定仁义礼智的先天性。为了确证这种先天善性,他说明了仁德来自于天。“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3]329因为人是天所生,“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3]318,所以人性具有仁德。董仲舒延续孟子的论证思路,通过肯定人有天赋的善质来高扬人区别于动物的卓越性,强调人要意识到自身的仁义之性而自觉行使天赋的使命,从而成就仁义礼智,以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3]466
王船山批判张载、程朱义理之性的说法,提出本然之性之外别无义理之性,因为义理之性“是气质中之性,依然一本来之性也”[5]466。善不是先在于气而存在的抽象理念,而是体现于二气之中。“阴阳之相继也善,其未相继也不可谓之善。故成之而后性存焉,继之而后善著焉。”[7]1006这里所谓“相继”的意思是阴阳二气互相配合、促进发展,如果阴阳未相继,那么善就不会产生。换句话说,在船山看来善是在阴阳相继之后成就的,不能离开阴阳二气而存在,所以善并非如朱子所说的是一种可以超越气而存在的至纯至善的理念。当阴阳二气相继并体现在气之形质上时,人性就是善的。“《易》曰‘继之者善也’,言命也;命者,天人之相继者也。‘成之者性也’,言质也;既成乎质,而性斯凝也。质中之命谓之性,亦不容以言命者言性也。”[5]470-471“继之者善也”是从天命之善的角度来说的,“成之者性也”是从性要以质为体的角度来说的。虽然作为性之源头的天命是本,但形而上的性要落实在人身上还必须和形质凝聚在一起。因为二气并非全善,形质也并非全善,所以凝于质的性也就并非全善。
(三)人性中的善质
董仲舒认为孟子的性善论是“未善已善”论,他提出“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3]311,进而提出“民性”的概念,说明人性中虽有“善质”,但善质本身并不等于善,因此“性待教而为善”[3]300,即需要后天的教化与修为把善质实现为善德。
王船山也认为人性中实有善有不善,但他并不否定孟子的性善论,而是强调人性中具有可以认识和实践五常之理的能力,“而五常百行之理无不可知,无不可能,于此言之则谓之性。”[6]33船山“可知”“可能”的思想从荀子而来,荀子说:“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8]443人虽具有实现仁义成为圣人的资质与能力,但成为圣人的资质与能力并不等于仁义本身。船山这里延续荀子的思路,认为人性中具有可以知五常百行之理的资质,但这并不等于人性本身就是善。如果不经过教化与修为,放任人的动物性的一面,就会出现荀子所言“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8]435的现象。相反,如果人能够通过教化与修为,不断把“知”“能”五常百行之理的资质实践为仁义礼智之德,那么就能成就孟子所说的善性。
(四)“善善恶恶之性”与“人性之善征矣”
人性中有善有恶,董仲舒强调人有善善恶恶之性。《大学》载:“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9]7董仲舒继承《大学》“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的思想,将其看作人性中无法消除的自然资质。“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3]34这也是人会好善憎恶的原因。
王船山提出“人性之善征矣”的观点以修正孟子性善论。“人性之善征矣。故以言征性善者,必及乎此而后得之。及乎此,则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道义之门启而常存。若乍见孺子入井而怵惕恻隐,乃梏亡之余仅见于情耳,其存不常,其门不启,或用不逮乎体,或体随用而流,乃孟子之权辞,非所以征性善也。”[10]401虽然人看到小孩落入井中会产生怵惕恻隐之情,但若没有救人的行动,善就没有彰显出来,因而恻隐并不能证明性善。船山的这一思想与董仲舒的“性未善”论有一致性。
但董仲舒与船山对善恶之天道来源的论证思路也有所差异。第一,董仲舒认为天之任阳不任阴,而船山反对朱子“阳先阴后,阳施阴受”的观点,将阴阳等而视之,认为天地乾坤并建,并非阳在阴前。“乾坤并建于上,时无先后,权无主辅,犹呼吸也,犹雷电也,犹两目视、两耳听,见闻同觉也。故无有天而无地,无有天地而无人。”[7]989第二,董仲舒虽然没有义理之性的说法,但是他把仁义的来源归结于天。董仲舒将天心作为仁心,“仁,天心,故次以天心”[3]161,将善对应于阳,阴对应于恶,“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3]329。船山则认为善是阴阳相继之后的产物。第三,董仲舒重建了天的神圣性与威权,而船山从气化宇宙论的角度来解释天道阴阳,解构了天的神秘性。
二、人性的差异性与人性可移论
董仲舒与王船山都从普通人与圣人的差异来看人性资质的差异性,但不完全认同孟子的性善论。董仲舒认为孟子的性善论有其合理性,即当人性与动物性比较时,人性是善的;但当普通人的人性与圣人之性比较时,人性并非全善。“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为,故谓性未善。”[3]304-305他由此提出“性未善”论以反驳孟子的“性已善”论,“而孟子以为万民性皆能当之,过矣”[3]311。他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并非人性实情,如果说“性已善”,就相当于“不几于无教而如其自然”[3]311。
王船山发展了董仲舒将普通人的人性与圣人之性相比较的思路,认为孟子是从人性与动物性的根本差异处看人性,由于形成人的形质优于植物、动物,从而认为人性皆善。“乃其为质也,均为人之质,则既异乎草木之质、犬羊之质矣。是以其为气也,亦异乎草木之气、犬羊之气也,故曰‘近’也。孟子所以即形色而言天性也。”[5]468相较于孟子,船山认为孔子注意到了人性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认为气之生质的理虽然相同,但质不同,所以“性相近”。“孟子惟并其相近而不一者,推其所自而见无不一,故曰‘性善’。孔子则就其已分而不一者,于质见异而于理见同,同以大始而异以殊生,故曰‘相近’。”[5]470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就是为了说明人性并非皆善,而要靠后天的教化与修为去弥补气之质的差异。
(一)人性是否有差异
董仲舒区分了人性资质的等级:“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3]311-312圣人与斗筲之性不能改变,而中民之性可以通过教化得到改善与提升。“与孟荀谈普遍意义上的‘人性’不同,董仲舒特别提出了‘民性’的概念。”[11]4“质于人道之善,则民性弗及也。”[3]304他把民众与圣人相比,提出“性未善”的观点,强调中民才是需要被教化的对象。
与董仲舒把人性资质划分出三种等级的思路不同,王船山把人性分为“先天之性”与“后天之性”。先天之性是由天所成就的,而后天之性形成于后天的学习与实践。“后天之性,亦何得有不善?‘习与性成’之谓也。先天之性天成之,后天之性习成之也。”[5]570船山认为,告子是把人初生时的人性状态当作人性本身,这种看法视人性的先天状态为一成不变,忽略了人性在后天的变化。“悬一性于初生之顷,为一成不易之侀,揣之曰:‘无善无不善’也,‘有善有不善’也,‘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也,呜呼!岂不妄与!”[4]57船山对人性的理解与其气化宇宙论思路保持一致,把人性放在动态的生成变化过程中去考察。他不只将先天之性作为人性,也将人性在后天的发展变化纳入人性论的分析范畴。
(二)人性可移论
董仲舒认为,圣人和斗筲之性是不可改变的,中人之性才是可移的,所以其教化论的对象是中民,也只有中民能代表普遍人性。如果人性中没有善质,仅凭外在的教化也不足以成就善;如果没有外在的教化修为,善质也就不能转化为善行。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外在廉政的制度建构与教化也能让人性向善。“至意虽难喻,盖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贵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遍矣。以为本于见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谓哉?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3]140-141
在船山看来,人性是可移的。第一,从“天命之谓性”的角度而言,人性可移。天道生生不息,天对人之所命以及人对天命的领受是无时无刻的,并非仅在人初生之时。“天命之谓性,命日受则性日生矣。”[4]56因此,人性并不是在出生时就被形塑固定的,而是在后天的生长发展中不断生成变化的。“性也者,岂一受成侀,不受损益也哉?”[4]56 “天日命之,人日受之。命之自天,受之为性。终身之永,终食之顷,何非受命之时?皆命也,则皆性也。天命之谓性,岂但初生之独受乎?”[4]56-57质言之,人性与天道流行一样,是日生日成的。第二,从“习与性成”的角度而言,人性可移。船山把气质之清浊刚柔的差异归因于质,而非气。学习与实践能够改变气,气能改善质,从而促进人性的生成。正是由于天不断在赋予人天命,人不断从天那里感受天命,因此人才能在日常实践中不断更新自己,人性也随着习性的养成而不断成就。“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4]54也就是说,学习实践与人性是共同成就的。
董仲舒与王船山都把人性划分为先天与后天两部分,都认为人性经过后天的教化与修为是可以变化的。在先天人性部分,虽然存在资质上的差异,但人性中都有成就仁义的资质,只是这种善质需要经过后天的修为才能得以实现。在后天人性部分,二人都从养气的角度讨论了人性的变化。船山认为,气能变化质,人性是日生日成的,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待人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董仲舒认为中民之性的改变既要靠内在的修为,也需要以圣王为主导的外在教化。“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3]302“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质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3]313
三、心性修养论
(一)董仲舒“心栣”论与王船山“心之几”论
孟子继承《中庸》“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的思想,提出“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2]158。诚就是至善,四端之心也皆是善。董仲舒说:“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3]294“心”的得名就来自于人之诚性,但他并不认为“人之诚”就是善。董仲舒提出人之诚性来自天道,天道有阴有阳,人之诚性也有善有恶。既然心之名来自人之诚,那么人心也有善有恶。但心还具有“栣”的功能,即控制、禁止恶念:“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故心之为名栣也。”[3]293心之所以具有这种对不良情欲的管控能力,是由于天之所赋的栣之能力:“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3]296
王船山从“心之实”与“心之几”两个层面考察心的活动,从“心”之动静的角度分析心之善恶。“仁义,善者也,性之德也。心含性而效动,故曰仁义之心也。仁义者,心之实也,若天之有阴阳也。知觉运动,心之几也,若阴阳之有变合也。若舍其实而但言其几,则此知觉运动之惺惺者,放之而固为放辟邪侈,即求之而亦但尽乎好恶攻取之用。”[5]502仁义是心的实质内容,心又由阴阳二气构成,当心向“阴”运动时,会受到非理等不良因素的干扰,于是产生不善的认知。如果放任心受不良欲望的驱使,那么心就不能发挥善性。因此,船山强调“则以明夫心之未即理,而奉性以治心,心乃可尽其才以养性”[5]722。即以善性为宗旨和纲领去控制心,使心尽其才能去扩充四端。反之,若任由心之自由发展,则尽心的结果是放荡无涯,也就失去了尽心之职责。因此,对“心之几”的洞察与省思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其慎独的修养工夫论。
综上所述,董仲舒认为心之诚性本身就具有善恶,只是心先天具有“栣”的功能,能够抑制人的过度欲望,从而为善去恶。王船山则认为,心之实就是仁义,是纯善的,如天道一样由一阴一阳构成,是真实不虚的;而心的知觉运动变化,即“心之几”,有善有不善,就如阴阳有变化一样。如果任由心的知觉运动,就会舍仁义而追求放浪邪耻;如果能专心追求仁义,则会提升人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
(二)董仲舒的正心养气论与王船山的养气移性论
董仲舒曰:“循天之道,以养其身,谓之道也。”[3]444人道要依天道而行,这也是养身的正道。养身之道要从平正内心这个根本处开始,“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内心其本也”[3]449。因为心是意念产生的源泉,意念纷杂,则心神烦扰;心神烦忧,则气息不通。“故君子闲欲止恶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身之大者得矣。”[3]452人应当减少欲望、止住恶念,正心养气以养身。“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3]449
人由阴阳二气构成,而心是气之君,因而静心可以养气。“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何为而气不随也。”[3]448“天气之于人,重于衣食。衣食尽,尚犹有闲,气尽而立终。故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气从神而成,神从意而出。”[3]452那么如何养心呢?荀子认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8]46。董仲舒则认为人之诚性有贪有仁,不能以诚养心,而要以义养心。“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3]263心有好利之性,要通过义来节制内心对利益的过度渴求,以达到平意、静神、正心之效果。而让人抑恶扬善,就要发挥心“栣”之功能。“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3]293
王船山提出“奉性以治心”,尽心之才以养性的心性修养论。心念之几是可移的,“周子曰:‘诚无为。’无为者诚也,诚者无不善也,故孟子以谓性善也。诚者无为也,无为而足以成,成于几也。几,善恶也,故孔子以谓可移也。”[4]57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12]176朱子言:“人物之所以异,只是争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则与禽兽无以异矣!”[13]81所谓“争这些子”,就是人性与动物性的根本差异,也就是仁义礼智。船山把孟子所说的“几希”划分为“在天之几”和“在人之几”两部分,“有在人之几,有在天之几。成之者性,天之几也。初生之造,生后之积,俱有之也。取精用物而性与成焉,人之几也。”[4]57“天之几”是成之者性,是天所赋予人之性;“人之几”既包含出生时的气质,也包含后天的修为与积累,是人的心念知觉运动变化。人性是“取精用物而性与成焉”,即汲取天地之精华、耗用万物,在生命成长过程中,人性也在教化修为中不断生成。
在性与心的关系上,船山认为“性不知捡其心”[5]717,即性不能去控制心,但“心能捡性”。“性只是理。‘合理与气,有性之名’,则不离于气而为气之理也。为气之理,动者气也,非理也,故曰‘性不知捡其心’。心则合乎知觉矣。合乎知觉则成其才,有才则有能,故曰‘心能捡性’。”[5]717理不能离开气而存在,理是气之理,性是合理与气而言的。心能调动知觉,让知觉为心所用,进而将心的才能调动出来以实现仁义礼智。如果不能调动和发挥心的能力,就不能彰显人异于禽兽的卓越性。“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色而研其理者,人之道也。”[5]458动物的感知和生存能力是一种本能,而人不仅有此本能,还有自主自觉的意识,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弥补先天禀赋上的不足。“禽兽有天明而无己明,去天近,而其明较现。人则有天道而抑有人道,去天道远,而人道始持权也。”[5]458 因而尽性不仅是尽已有之性,也是尽未有之更好的善性。
概言之,在心、性、气三者的关系上,董仲舒的思路是以义养心,正心以养气;王船山则提出以心捡性,养气以移性。王船山把气质之清浊刚柔的差异归因于质,而非气,“质,凝滞而不应乎心者也”[5]469。“盖气任生质,亦足以易质之型范。型范虽一成,而亦无时不有其消息。始则消息因仍其型范,逮乐与失理之气相取,而型范亦迁矣。”[5]469质一旦形成就凝滞,不能呼应于心,如果气任由凝滞的质,气质就不会改变。船山认为孟子存养浩然之气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存养正气来改善不善之质。“若夫由不善以迁于善者,则亦善养其气,至于久而质且为之改也。”[5]469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12]294气的改变也能带动体的改变,“气移则体亦移矣”[5]469。
结"语
董仲舒与王船山人性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探究人性的天道基础上,二人都从阴阳角度说明人性与五常之道的来源。董仲舒用“天次之序”与“受命于天”将五常与五行对应,船山从阴变阳和的角度解释五常的来源。董仲舒重建了天的神圣性,船山则将天还原为物理之天;董仲舒认为阳气为善,阴气为恶,人由二气构成,因此人性中有善有恶,而船山认为善恶并不是先天的,二气和合产生善,二气不合产生恶。第二,董仲舒认为心之诚性本身就有善恶,只是心先天具有“栣”的功能,能抑制人的过度欲望,从而为善去恶。船山认为心之实就是仁义,是纯善的,如天道一样由一阴一阳构成,是真实不虚的,但心的知觉运动变化,即“心之几”,有善有不善。在修养论上,董仲舒提出正心养气论,船山提出养气移性论。第三,在人性论建构上,他们都认为人性资质存在差异,也都区分了先天之性与后天之性。董仲舒的人性论为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奠定了思想基础,船山则以张载气本论为基础,在批判程朱理气二分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先天之性与后天之性,是对董仲舒“善质”与“成性”思想的发展。但是,王船山否定了董仲舒“中民之性”与圣王之教的说法,认为“日生日生,习与性成”,即人性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经过后天的教化与修为而不断变化的。由此可见,王船山的人性论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更具有现代性的思想指向。“王船山告别了那种形而上学的普遍性,个体性的意识,成为一种更新了的思想传统与新的时代意识的中心。当然,现代性意识的出现,在王船山那里还有多方面、多层次的表现。”[14]514在船山看来,教化不是由圣王主导的,而是由人自发自觉的意志展开的。基于此,人们不再局限于追求一个固定的自我模式,也不会因先天禀赋不佳而自怨自艾,而是在更广阔的世界图景里不断超越自我,更新生命与德行的品质,不断创造属于人的卓越与荣耀。通过对董仲舒与王船山人性论的比较分析,不仅可以勾勒出儒家人性论的演进轨迹,也可以看出儒学从帝国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思想嬗变。
【 参 考 文 献 】
[1]班固.汉书.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黄开国.董仲舒人性论新说.哲学研究,2022(9).
[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锺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4]王夫之.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1962.
[5]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张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
[7]王夫之.周易外传.长沙:岳麓书社,2011.
[8]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思问录∥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
[11]李慧子.“性未善”与“成性之教”:董仲舒论人性与教化.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1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
[13]黎靖德.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
[14]陈赟.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编校:龚江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