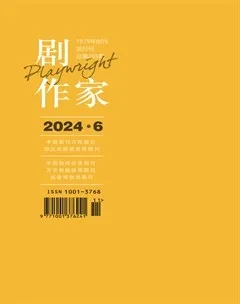从《伤心咖啡馆之歌》看孟京辉风格及后戏剧剧场理论
摘 要:孟京辉作为国内先锋戏剧领头人物,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孟氏风格,其风格充分体现了汉斯-蒂斯·雷曼的后戏剧剧场理论,即通过打破传统的剧场空间与表演模式,以一种紧扣主题又抽离的呈现手法,为戏剧呈现提供了更多的表达可能性。本文将以孟京辉作品《伤心咖啡馆之歌》为例,简要分析孟京辉风格与后戏剧剧场理论的具体实现。
关键词:后戏剧剧场理论;孟京辉;先锋戏剧;戏剧审美
话剧《伤心咖啡馆之歌》改编自卡森·麦卡勒斯的同名小说,小说描述了社会边缘人物:一个跛子、一个驼子、一个坏种的爱情故事,一场荒诞的三角畸恋。原著为传统叙事,对风景有大量描述,作者以第三视角来书写这个故事,并在其中掺杂个人对小说中人物行为的评价,故改编难度颇高。孟京辉运用自己的孟氏风格“操刀”了这部剧,为其注入先锋精神与自己的戏剧审美,使整部剧从一个痴男怨女的爱情故事变成一个孟氏先锋戏剧。
后戏剧剧场理论视角下的孟京辉风格
孟京辉风格充分例证了雷曼后戏剧剧场理论①,其打破舞台戏剧以文本为主、一切服务文本的传统,运用实验式的排演方法不断探索脱离文本后如何贴切表达主旨。孟氏风格常用的呈现手法是对原著做抽象性改造,轻情节,重情感,以求达到一种与原著神似但不形似的效果。以《伤心咖啡馆之歌》为例,爱情是这部戏不折不扣的主题,故而孟氏改编也紧抓爱情主题。剧中艾米莉亚小姐过着物质富足、精神上近乎自洽的生活,她微跛、强悍、不近人情,是无法触及的“孤岛”,直到一个叫李蒙的男人出现,征服了“这片荒芜土地”。李蒙是一个驼子,但爱情总是在无法理解的地方发生,艾米莉亚小姐狂热地爱上了李蒙。她向他倾诉自己此刻的情感、截断的记忆,展示怪异的收藏,连同全部身家贡献于他。李蒙代替她腿上的护具,狂热的爱让她感到自由。直到那些记忆里避之不及的部分出现,一个男人——马文·马西,艾米莉亚的短暂的前夫,一个坏种。
正如艾米莉亚痴恋李蒙一样,马文·马西也曾痴恋艾米莉亚,痴恋到浪子回头、送上所有,痴恋到因得不到回应而生恨,远走他乡。如果将爱与恨标注在温度计两端,那么愈发炽热的爱愈容易在心灰意冷后降温至极度的恨,这场以报复为目的的回归,注定了三人虐恋的结局。
马文·马西爱艾米莉亚,艾米莉亚爱李蒙,李蒙又奇异地爱慕着马文·马西。完全闭环的三角恋的冲突增加了戏剧性效果,也是众多爱情戏常见的情节设置。《悲惨世界》中艾潘妮、马吕斯、珂赛特的这一组和《海鸥》中妮娜、特里勃列夫、果林这一组都是知名的三角恋架构。孟京辉打破戏剧三一律的常态,以戏中戏的呈现手法在《伤心咖啡馆之歌》引入契诃夫经典戏剧《海鸥》的片段以此致敬这位戏剧大家,但同时也给本来跳跃的时间线增添了理解的难度。两部戏的相同之处都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热爱舞台的少女妮娜爱上了追求者特里勃列夫的母亲的情人果林,她仰慕于果林的才华,追随他回到莫斯科,成为一名演员,后来被果林抛弃。而追求者特里勃列夫在绝望中开枪自杀。通过跳跃的时间线展现爱情中失意者的孤独,胜利者的残忍,胜利的旌旗从不长久地立于某人的阵地。你不爱他,有人爱他;她丝毫都不爱你,她就会疯狂痴恋他人,即使不符合世间任何一条被检验过的真理。爱作为可以长久讨论挖掘的话题,不只在舞台上,也与舞台下观众的故事契合,观众通过戏剧寻找自己,察觉自己也曾在爱中孤独,也曾以一种冠冕堂皇的名义,去向对方递上一把朝向自己的刀,与主角一起陷入爱,感受爱,被爱伤害。
有趣的是《海鸥》的作者契诃夫的创作风格同样弱化了戏剧冲突,大量运用象征手法及抒情手段,这与孟京辉本人的理念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打破传统戏剧的固有格式是需要勇气的。《海鸥》曾在初上舞台时遇冷,又在重新排演后被验证为一代经典。这场声势浩大的致敬,也许也是导演对先锋戏剧的一点私心。
以先锋审美打破舞台常规
孟京辉擅长通过拼贴、留白、新媒体技术应用等手段打破舞台实践的虚拟性。舞台上放置着一只指尖虚指的巨手,几处白色的小房子,天上悬浮着一条诡异的鱼,桌上酒瓶散落,演员妆容惨白,不像一部话剧,整个空间充满“未来感”,并没有固定的边界,反倒像是一场后现代主义的摩登大秀。舞美奠基了这部剧荒诞、矛盾、魔幻现实的风格。
整部戏舞美色彩以极致的黑白搭配灯光之缤纷,灯光下的演员起初好似废旧橱窗里的苍白模特,冷酷无情,以发出连续的不含意义的连串字节来抒发感情。后方是刺目红光,与剧场的漆黑结合,以强烈的黑红对比暗示“伤害”与“毁灭”主题,整体设计上既有大开大合的美式风格又与日系亚文化风格结合。
舞台背景以黑色为底,直到结尾处大幕拉开,金属钢质材料组成的背景好似墙体爆出的青筋,张牙舞爪地展露冷冽的光。舞台右上方有支乐队在现场演奏,曾经创造出《米店》的音乐人张玮玮为“伤心咖啡馆”注入“歌”的灵魂,让人仿佛置身livehouse,即使不需酒精也能让人体会到对先锋戏剧的晕头转向。音乐元素是孟氏戏剧不可或缺的一环,从早期作品开始,屡用不鲜。剧中迷幻电子乐的使用为整台剧目增添了一层审美意蕴。
演出中幕布忽然从观众席快速掠过,数千小球落下,快速地分割剧情进入戏中戏片段,艾米莉亚摇身一变成了契诃夫剧作《海鸥》里的妮娜,同样的对被爱嗤之以鼻,同样热诚地不顾一切地爱着别人,同样地变成爱情的遗弃儿。浪子马文变成了自怨自艾的前任,李蒙变成了被追逐的远方,两条内核相似的故事线在舞台上跨越了时间、空间,遥相呼应。戏中戏作为先锋戏剧的常用手段,也是孟氏风格对戏剧结构丰富化要求的审美体现。
最大化发挥演员肢体表演
后戏剧剧场理论认为应当在戏剧的形式法则之外进行创作,在孟京辉的实践中展现为挖掘演员个人表演的极限,反文本化的趋势也促使着演员提高自身肢体表达。饰演艾米莉亚的演员黄湘丽与孟京辉合作多次,是典型的孟氏女郎。她是一位有着优美的肩颈线条和强大肢体控制能力的女演员,一切影像、灯光、音乐都不自觉地衬托着舞台上的她。她一头银色假发,如同所有孟氏女郎一般气质叛逆却不疯癫、张扬却不傲慢,恰如其分地表演出一个因为爱情迷茫的女人。孟氏女郎总是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在舞台上疯狂地释放自己全部能量,像她们的“工服”红裙子一样有着内在的几欲爆发的能量,然后又因一次突然的释放后变得脆弱易碎。两位男主角的演出大胆,富有张力,同性之间的对手戏让台下的大多数观众在大篇幅的茫然中终于找寻到这场三角恋的吊诡之处。整部剧中充斥即兴肢体、小语种语言念白、无意义呓语等抽象化表演形式,让故事走向变得诡谲,在压抑下释放能量。
舞台上演员的声调和动作都脱离了程式化,每个演员的动作都难以赋予其具体意义,似乎只是跟着音乐节奏、剧情发展而改变姿势。黑格尔在《美学》中曾预言戏剧舞台手段会各自独立发展。彼得·布鲁克认为:“戏剧动作的核心是注视,戏剧产生的源头,以及形成戏剧的本质,用直观的形体表达戏剧的思想,观众和演员同时获得自身的发展。”[1]P12孟氏戏剧显然贯彻了这一点,将主要意义的呈现放在肢体语言与舞台设计上。剧中多次使用小语种语言,并未配有字幕,对本土观众来说适应需要时间。传统戏剧盛行的几十年里,观众已经习惯从有意义的文字中捕捉信息,当出现一串无法捕捉的文字或语言时,只能在“不知所云”和“五味杂陈”之间思绪跳跃。一方面可以认为这种呈现能唤起观众的思考,使观众以旁观者身份从高处注视发生在眼前的一切,另一方面则是让观众在社交媒体上评论时大倒苦水。
结语
彼得·布鲁克指出:“每个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每个时代也都有自己的风格。想要精准定位某种风格是不可能的。”[1]P10人类始终在探索戏剧的边界的路上找寻戏剧的本质。戏剧究竟是商业环境下的产品,还是创作者自由的艺术表达,后戏剧剧场理论下,太多戏剧以先锋为名,多艺术元素的堆叠方式,特异化的强调差异与创新,为了强化情感而对叙事极度弱化造成的观众理解困难,反文本中心化导致的被消解的意义等诸多质疑使后戏剧剧场下的先锋戏剧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这与整体环境有关,也与创作者有关。作为这个时代后戏剧剧场理论的践行者,孟京辉曾坦然认为“新的就是好的”的戏剧风格是否能如契诃夫的作品一般从不被理解成为一代经典,迫切需要时间与观众的投票认可。
参考文献:
1. 彼得·布鲁克著,邢历译:《空的空间》,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注释:
①汉斯-蒂斯·雷曼著《后戏剧剧场》,书中,雷曼概括了20 世纪70 年代至90 年代欧美剧场艺术中出现的变革趋势。这种趋势反对文本至上的剧场创作结构方式,强调剧场艺术各种手段(文本、舞台美术、音响音乐、演员身体等等)的独立性及其平等关系,并将其命名为“后戏剧剧场”理论。
(作者单位:西安儿童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姜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