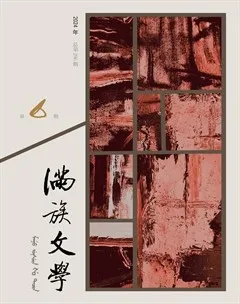村庄册页(散文)
1
在乡下,每一栋房子都是有主人的。不用看户口本,不用户主亲自澄清,那证明印在每个人的心里。
人们都会出面作证,这栋房子里住着谁。他们说的谁,通常不是一个人。老人说的是老人,孩子说的是孩子。有时候那“谁”只是一段对话,一阵笑声,一个院子里长出来的一片庄稼,或者圈里拱食的几头猪。但是他们说,没错,房子的主人就是他。眼神和语气都非常肯定。
他们说的就是一段记忆。在记忆里,主人的身影渐渐高大,植物和动物的面貌逐渐清晰,围绕着主人各自生长。
经过一栋老房子。
那房子是村子里最破旧的房子了,又低又矮,老得如同屋里那对摇摇欲坠的老人。每年春天,院里的土都会被翻新,撒上各样种子。邻居帮着忙活完这些事情,走出院外会轻轻叹息:唉,周褐。
“褐”音同于“黑”,描述的是老头子的肤色。他沉沉的脸色像一辈子都没有打通的井,黑咕隆咚的,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飘着一团令人难以捉摸的阴影。无儿无女的他和老婆子艰难地熬着日子,若没有邻居相帮,他们活不到下一个太阳出来的明天。
在后来的某一天,人们经过,发现那里成了一片空地。周褐的房子、周褐的院子、周褐摸过的围墙、周褐家门口那棵结着黑色桑枣的树都统统不见了。好像夜里一阵风来过,把什么都抹得干干净净。人们对着空地怔怔地,唉,周褐。
房子的主人早已住在人们的记忆里,记得很深。哪怕主人已化为一抔泥土,但他们的声音和气息还在空气中游走,好久好久都不会散去。后来人没有见过房子的主人,新的历史才会在这片空地上悄然长起来。又一些身影,又一些笑声,又一些琐琐屑屑的日常缝缀着记忆的边角。
母亲也是房子的主人。
她曾经只承认房子是父亲的。走在村里,别人喊她,曲治延家里的。母亲回头,笑着轻轻应答,等同于承认房子是曲治延的。有什么关系呢?将曲治延跟她联系在一起,那栋房子才有了温度,是两个人共同堆砌起来的温度,像燕子的巢穴。曲治延是一撇,她是那一捺。她才不在乎那一捺先出笔,还是后出笔,她只是愿意紧紧跟随在那一撇后头,感受着日子里头的安逸、忙碌和小小的快乐。这样的心情怎么会轻易告知每一个人呢?
那栋房子的主人后来就是母亲了。
怕她一个人孤单,我接她来城里住。母亲睡得早,起得也早,她摸摸索索地下床,不知道做些什么好。在暗影里发了一会儿呆,就说,送我回乡下吧,那里才是我的家。她惴惴不安的语气像个孩子,满脸写着悲伤。我第一次发现离开那栋房子的母亲,就像丢失了魂魄。
又回到老房子里了,母亲不知有多快乐。手脚勤快的她在房前屋后走来走去,疼爱的眼光抚摸着院子里的角角落落,像跟每一个被她冷落的生命深深道歉。
我们都明白了,只要母亲在世一天,这房子就只认得母亲。母亲是她真正的主人。
村子里有些房子的主人离世很久了,后代都远走他乡,房子再无人居住。屋檐下燕子的巢穴空空荡荡的。主人一次次回来,却敲不开房门,房门被日子里的尘埃糊满了。主人在村子里游荡,许多主人在村子里游荡,他们无家可归。
燕子去别的村子做巢穴,别的村子也走了很多人,也空了很多房子。燕子在树梢上徘徊,叫声哀怨。
狗无去处了。这个村子的狗跑到另一个村子里,又跑了回来。它们四处寻找主人。它们脑子里灌满的都是昨日主人对它的召唤,对它的呵斥,对它一点一滴的疼爱。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它只会不停地寻找,最终老死在其中一个村子里。
房子的主人像花,谢了一朵又开下一朵。然而下一茬花总不及上一茬茂盛,村庄的大树就渐渐枝叶稀疏,从有限的枝丫间漏下斑斑驳驳的阳光,人在阳光下走动,村头有一个,村尾有一个。远远晃动的人影使村子骤然间显得又大又空旷。
阳光貌似也老了,它眯眼打量眼前的世界,竟然渐渐陌生。那些从前的人呢?从前的事呢?从前的欢声笑语呢?莫非他们又在另一个地方组成了村落?
又一个春天,我坐车去乡下看望母亲。从村子里经过时,我看到许多房子的主人在院子里忙碌,他们的孩子又吵又闹把房盖都要拱起来了。我微笑着跟遇到的每个人打招呼,我的手在空气中不停地摆动。没有人知道我的脑海中在播放着一部多么热闹多么生动的电影。那些我熟悉的人都是电影的主角,他们在某一个时间段存在过,这是世间的任何力量都抹杀不掉的。
我走在一栋老房子前,停下脚步。一个后背微驼、白发苍苍的老人从院子里蹒跚而出,我激动地叫了一声:妈。我搀扶着老人走进这栋阳光下的老房子。
在梳理房子的记忆时,我总是快乐又忧伤。我感谢那些房子的主人,他们把一个简朴的道理刻在我的心上:我来自哪里,我的根将扎向何处。
2
村庄是一本书,被房屋、河流、山脉、庄稼以及一切住在村庄的事物装订成册。没有标注页码,第一页也可能是最后一页。
书里记录着房屋的位置,河流的走向,山脉的高度,庄稼的变化。还记录着风的呵欠、雨的歌唱、猫爪踩过房瓦的细小响动。当然,人也是书里的文字,人的喜怒哀乐,穿衣吃饭构成了书中会流动的文字,这种文字别具一格。
每个人出生,就为书中增添一道风景,在书册里,从某一年点缀到某一年。我认为我的出生就是一只小蝌蚪的诞生,村庄是我的大池塘,我摆动着尾巴从村东头畅游到村西头。
而一个人去世,不是天上星星的减少,而是书册里空间的减少。原来,他占据一个羊圈那么大的地方,现在他瘦成一个字符,只够挤进一个名字。那个雨天,李二丫从山坡上被人抬了回来。她的头和身子都蒙在塑料布里,只露出一双白嫩的脚,像是对人诉说她还未来得及绽放的青春。从此,我只记得李二丫这个名字,有关她的一切都渐渐模糊。村庄的书里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橡皮擦。
我慢慢长大,与村庄的孩子玩各式各样简单的游戏。傍晚时,我们在高屯的草垛边玩藏猫猫。芬要回家吃饭了,我们跟兰继续玩。兰也回家了,我们跟峰和萍玩。我回家时,看到芬端着饭碗坐在她家墙头上吃饭。是一碗稀软的苞米粥,黄得耀眼。芬挑了一筷子大酱拌进粥里,当着我的面吃得满嘴香甜,鼻尖上还滚出几粒圆滚滚的汗珠。
我抿着嘴唇,飞跑着回家,第一眼就往我家的饭锅里瞅。果然是苞米粥,像铺了半锅金子,袅袅地冒着热气。我咧开嘴笑了。吃饭时母亲端上一盘萝卜瓜咸菜,就着苞米粥,我们一家八口人吃出村庄最响亮的声响。我还伸出舌头往碗边舔去,像我们家的狗一样,把碗边舔得干干净净。一家人看着我都忍不住笑了。
其实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声响。村庄的书册像个大棉布口袋,把每个窗口里流淌出的声响都搜罗进去,然后排列组合。吃饭的声音,走路的声音,人扛着锄头走进庄稼地的声音,牛拉犁猪打圈的声音都用不同的字符勾画出来,使村庄的书册丰富又多彩。
我长大了,书里装进我越来越多的声音,还有我的思考和面对世事的疑惑。
浩子是我们村的少年,他因为杀死了邻居赵奶奶而被判了刑。他的父母亲在村庄里抬不起头。母亲教育我说,人过留名,让我不要做像浩子那样的人。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名字和名字不一样,有的名字温暖,在世间就会长出温暖;有的名字邪恶,在世间就会遭人唾弃。
村庄这本书里啥样名字都有。村庄那么大,装得下阳光,也装得下秽气。
读初中那几年,是我人生历程中一段幸福时光。整个镇里的少年都在一所中学读书,我因此知道在我们村子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村子,它们都是一本书,书里有房屋,有河流,有山脉,有庄稼和密密麻麻的人。每个人都愿意从自己住的书里溜达出去,好奇地阅读别人的书。
我的同桌波住在水库边。波每天骑自行车来学校,路上用一个小时。冰天雪地,波骑车到学校,长长的眼睫毛上挂一层霜。我看到他时就像看到一个从蓝色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老人,他眨巴下眼睛,就能蹦出一条浑身披着银鳞的鲤鱼来。
波是这么对我们描述水库的:水库真大,绕着村子家家户户的门前流淌过去;在水库边走一遭,那些蹦出水面的鲤鱼和鲢鱼会看花你的眼睛。波的村庄原来是用蓝色做底的。蓝色,多么美妙的颜色。是天空的蓝,是海洋的蓝,是少年眼眸中纯净的蓝吧?是一眼可以看透,再望一眼,又深邃无比的蓝。
村庄的书没有栅栏,也没有上锁,所以谁都可以从书里走出去,谁也都可以从外面走进来。波大学毕业后留在外省工作,他成了别的村庄的长居客。为了去看一次波说的水库,我结识了波的哥哥。当我站在水库边,像把少年的一个梦轻轻拾掇起来,心里荡起说不出的甜蜜和激动。波的哥哥想牵我的手,想了想又羞涩地放下了,我们把目光不由自主地投放到那片蔚蓝的水域上。我果然看到水库的边界线在波的村庄曲曲折折地蜿蜒出去,像一个身影魁梧的老人缓缓伸出的有力双臂。我没有与波的哥哥走到一起,几年以后他也成了别的村庄的长居客。
小蝌蚪有一天也会长大的,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我像许多人一样从村庄游到了城里。只不过是一朝一夕的改变,人却像站到了高处,打量村庄的目光里蓦然生出一份辽阔和疼爱。
走得越远,我越习惯翻书,翻阅村庄这本书。尤其当我坐车回城的时候,抛向窗外的目光就被村庄一切熟悉的事物缠绕,我一遍遍读他们,想象着他们从前的样子。
村庄明显瘦了。母亲家后院紧挨着粮库,粮库昔日盛满粮食的巨大粮囤像一头萎靡的骆驼,残缺的囤壁摇摇摆摆,不定哪一日就会轰然倒塌。我还看到村庄那么多闲置的房屋,爬山虎占领着墙壁,野草去屋顶撒下种子,唯独燕子不去。燕子嫌弃那儿荒凉。
母亲也不喜欢荒凉,她想凑热闹,却不知去哪里凑。桥对面的高婶卧病在床一年了。母亲去看她,说你快点好起来,能走路了咱们一起去赶集。高婶的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她伸出枯瘦的手,握了握母亲的手,那泡泪雨点般砸到了枕巾上。
我逐渐懂得了怀旧和想念。当我睡在城市的床上,还是习惯一遍遍把村庄的书册翻开。我读书里的房屋,读书里的河流和童年藏猫猫时丢下的点点滴滴快乐的笑声。这个时候我就离村庄近了,我分明是睡在村庄的大床上,头顶是一轮黄灿灿的明月,撒下的银辉是村庄给自己蒙上的面纱。狗胡乱叫了一通,睡了,乌鸦哇哇地从一棵树落到另一棵树上。村庄如同掉进一口深不可测的井里,只一心一意孕育一场香甜的睡眠。
那一夜,书的厚度达到了我们乡村的鼎盛。
3
从半空向下俯视,村庄的屋顶只有红瓦与灰瓦两种色泽,简单朴素,沉稳大方。它们被村庄的绿树不规则地切割开,无数瓦片像成千上万尾鱼在绿海里欢乐游弋。
清晨的第一缕炊烟从屋顶的烟囱里吐出来,悠悠荡荡,扶摇直上。这是农家人起床的信号。于是灰瓦和红瓦一同见证村里人悠长而忙碌的一天。屋门被推开,男人担着铁皮水桶出门,咣当咣当一直响到大门外,在街对面人家的门前停下来。那里有一口水井,石头砌的井沿,辘轳悬在井中间。因井水清冽甘甜,附近人家吃水都到这里来提。男人熟练地收放着井绳,卖力摇动着辘轳,随着哗啦呼啦的声响,装满水的铁皮桶子很快从井里探出头来。粼粼波光中映照着男人健壮黧黑的面孔,比灰瓦要明亮一点,比红瓦要黯淡一点,这是灰瓦和红瓦共同调出的色泽,它们又都属于村庄。
男人默不作声地做着这一切,女人的声音则要丰富一些,高调一些。离开灶台,她端着簸箕来到鸡圈,“咕咕咕——咕咕咕”,金黄的玉米粒在指间飞扬,花翅膀的大公鸡争相啄食。喂完鸡了要喂猪。猪圈在大门外,酣睡了一夜的猪娃早就等不及了,刚听到女主人的脚步声在附近响起,就仰起圆滚滚的脑袋挤到猪槽边等候着。“唠唠唠——唠唠唠”女人唤着,“你闪一边去,让着它点。”女人用猪勺子敲击着那头胖猪的脑袋,娇嗔地骂着。这些声音或尖或细,或脆或亮,都被灰瓦和红瓦悉心收藏着。一同收藏的还有女人喊孩子起床的声音,端盘子端碗收拾饭桌的声音。这些声音编织着动人的旋律,带着浓郁的庄户人气息,被灰瓦红瓦一同谱进清晨的乐章中。
从东山坳爬出的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半面屋瓦都浸没在金黄色的璀璨中。而村庄的脚步似乎慢了下来,男人女人都去地里干活了,孩子们三三两两去了学校,守着村庄的只有一些散游的狗和落在房瓦上叽叽喳喳唱歌的麻雀。老人这个时间还要睡一次回笼觉。灰瓦红瓦继续把这一刻的安静记录在册,拽一缕阳光包住书皮。
在这份安静里,村庄的事物都以最欢喜的方式自由生长。清亮亮的河水绕着村庄缓慢流淌,带着故事涌来,带着故事远去;庄稼大口呼吸清新的空气,用力吸收着土壤里健康的养料,抽枝拔节,茁壮生长;远山近树都自在地沐浴在阳光里,勾勒出村庄里盛夏时节最葱茏最丰腴的线条。
每次凝视这种宁静,灰瓦红瓦都有一种要与村庄万古长青的念头。是血溶于水,是鱼儿投身于江河,生出万般亲密与留恋。它的瓦片里已记录了无数个闪烁飞逝的日子,它懂得村庄的辛苦和艰辛,也分享着村庄的愉悦和飞扬。它是村庄历史的书册,是村庄发展最真实的记录者,更是村庄挺起的额头,一道道深纹里,存贮着诉说不尽的故事和汗水。
黄昏光临村庄时,村庄被又一次的忙碌唤醒。鸡鸭、牛马、猪狗以不同的嗓门、不同的腔调汇成磅礴的大合唱,仿佛一场音乐会闭幕前的压轴表演。在这丰富的长腔短调中,西山巅的云霞缓慢地给村庄着色,树梢啊,屋顶啊,菜园子啊,处处金光流溢,华丽绚烂,勾勒出一幅色调明快的画作。灰瓦红瓦顺势往画作上盖上一记邮戳,有力地证明此画作的专属权。
雪是在夜深时不知不觉飘起来的。雪落无声,似乎怕惊扰了农家人的好梦。灰瓦红瓦敞开怀抱迎接一场好雪的到来,任它从头至脚将自己盖得严严实实,难得的一床轻柔暖和的大棉被。而村庄里,各家各户的草垛也分了一床棉被,结冰的小河也分了一床棉被,从村子延伸向远方的道路都分到了棉被……村庄在棉被下舒活着筋骨,陶醉在“瑞雪兆丰年”的喜气中。
论资历,灰瓦红瓦深知自己是村庄的元老。它总是把眼光不自觉地瞟向井中的辘轳、院子里的碾盘、耕地的犁杖、拉谷物的马车,深情地凝望寻找着。它们也是村庄的元老,来自哪朝哪代尚未可知。但古老能与古老遥遥相望,就像一个老人垂暮之年仍有老伴相守左右,欣慰之情无法言表。
说不清这古老是哪一天被打破的。琉璃瓦的出现对灰瓦红瓦构成了赤裸裸的挑战。有些人家果断放弃用了几十年的灰瓦红瓦,请进鲜艳明亮的琉璃瓦披盖房顶。瓦居然不是一片一片村庄匠人之手颇费周折镶嵌于屋顶,而是一大块一大块酣畅淋漓地加盖其上,有点体力的人都可将琉璃瓦盖到房顶,这完全违背镶瓦之道。作为村庄古老事物之一,灰瓦红瓦拒绝承认琉璃瓦是瓦,它疼惜那些靠镶瓦为生的乡村匠人。镶瓦的日子,匠人有多风光啊,他们简直是将军,每一块瓦片都受着他们的调遣。当那些瓦片密密实实地落于房顶,如优美的鱼鳞在太阳底下闪光时,匠人黝黑的脸膛绽放出最得意的微笑。从此,每一滴雨都将顺着瓦片滑落,每一阵风都无法穿透屋脊。
然而,古老与现代在村庄里正悄无声息地发生着碰撞。每一次碰撞,古老的事物都要被逼退一点。那一次是辘轳,那一次是碾子,那一次是马车,那一次是躬身钻进玉米地除草的身影……一切都不复从前。古老似乎已成陈旧的代名词,它正一步步缩进角落里,无奈地等待着时间将它瓦解,消逝。
从空中俯瞰村庄,仅有的灰瓦红瓦像游不动的小鱼,带着村庄沉甸甸的历史,沉落于时间的河床。它们是村庄最后的吉光片羽,带着雄壮的回声,在无数村庄人的记忆里美哉!美哉!
【责任编辑】涉 祺
——南粤古驿道梅岭驿站创作实践
——以西宁市城西区贾小巷片区改造项目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