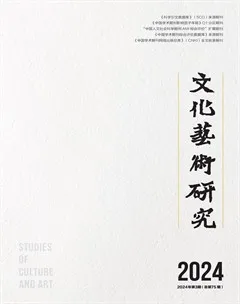元宇宙的三重现实性
摘要:元宇宙还远未实现,不能直接描述其实在性现实(Realität),但元宇宙理念试图填充人的意义世界,为人提供一种新的生活现实,为当下前瞻性考察其在世性现实(Wirklichkeit)提供了可能。元宇宙的在世性现实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元宇宙奠基于人类感官的解读,并创造性地满足人的需求,自然是属人的;元宇宙与人的行动密切相关,其中所蕴含的三重创造性模仿亦契合阐释学上的主体实践结构,不断丰富人的自我认识;元宇宙通过不断往复的过程,作为游戏现实充实人的日常生活,在感官确认、第三方权威、主体性统一和阻抗经验四个向度上为人提供不同于传统艺术媒介的行为约束性和参考预设性。这三个层次的考察以一种审慎的自反性,分别借助哲学人类学、诠释学、现象学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追问元宇宙的现实性,或可为技术时代批判性反思人的境况提供一些线索。
关键词:元宇宙;现实性;小说;技术;布鲁门贝格;利科;游戏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24)03-0055-12
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是人类的艺术创作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在口传时代,人类的集体创作通过舞蹈、绘画、民歌等形式来描述祭祀仪式和生产实践,用神话和史诗来解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书面时代,艺术创作得以更准确地通过文本保留下来,同时,创作也有了鲜明的作者意识,个体对世界的独特观察和想象融入了更为丰富多样的艺术创作之中;随着印刷时代的到来,文字和艺术创作被更广泛地接受,知识与信息遍布世界,人们不再恪守独一的宏大叙事,世界变得更为丰富而多元。应该说,人类历史伴随着创作媒介的发展,人类也随之对现实不断有新的理解。元宇宙理念的出现,便足以表明,数字时代的当下,人类通过富有颠覆性的艺术创作,对现实有了不同于传统媒介时代的新理解。
如何理解元宇宙的现实性?这个问题一经提出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质疑:对于一个建立在技术与媒介基础上的虚拟世界,谈何现实性?这个质疑能在本体论层面轻易获得其合理性——元宇宙无法脱离技术设备而独立存在,当然无法获得自然之物所具有的现实性。但在元宇宙的设想下,技术将全方位参与人的日常生活,构建人的存在和生活世界,人的日常生活将从真实可见的物理世界脱离出来,扩展到技术所构建的虚拟世界,在此,现实概念并非与客观现实必然同一。在德语中,有两个词来表达“现实”这个概念,分别是Realität 和Wirklichkeit:Realität 侧重于被认识和衡量的物或对象,某种物性(Dinglichkeit),往往以科学现实为基准,乃是实在性现实;Wirklichkeit 不局限于对象本身,也强调物的意义和价值,包括所有能够发挥作用之物,如神话、幻象和信仰等,故而并非仅止于能被纳入科学考察的对象,堪称在世性现实。人的在世处于无限的意义和互动关系网络中,其现实没有清晰的边界,无法穷尽,用科学方法将其切割为各种封闭的系统,才能得出与质料(Materie)密切相关的实在性,予以准确把握。因此,谈论一张椅子的现实时,既可以从物理层面谈论其客观的实在现实,也可以从功能、情感、象征等层面谈论其为人所提供的在世现实。而在谈论元宇宙时,鉴于元宇宙尚不具有可供衡量的物性,其所仰赖的扩展现实、数字孪生、区块链、虚拟引擎、人工智能等各类技术的现有水平尚不足以实现元宇宙,各方的具体协调模式仍有待探索,自然无法追问元宇宙的实在性现实,但我们仍可追问其在世性现实,即是说,元宇宙的理念一旦借由技术实现,将给人带来何种生活现实?人将如何体验这种现实?这便是本文所要围绕而展开讨论的问题,以阐明元宇宙的现实性。
本文将分为三部分展开:首先,从元宇宙理念的基本内涵出发明确元宇宙的属人性,并在元宇宙创造性满足人需求的可能中展望元宇宙时代人的生活世界,为理解其现实性提供认识基础;其次,从诠释学的角度阐明元宇宙理念所蕴含的实践结构,以彰显其现实性的作用机制;最后,从元宇宙现实的内容层面追问元宇宙为身在其中的人提供了何种约束性和预设性,以文本世界中的可能现实为参照,批判性思考元宇宙中游戏现实的基本特性。
一、元宇宙的属人现实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一个为人所创、为人而设的虚拟世界,元宇宙只对人而言才具有其现实性,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属人的世界。为人所创,因为它出自人的创造,是人的作品(如果将“艺术”一词还原为拉丁词ars 所广泛指涉的创造性,则堪称人的艺术作品),而非自然的造物;为人而设,因为它基于人的感官系统并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而设立,只有人才能进入其中,其现实性只能被人所接受,只对人有效。
这种属人性是直接内在于“元宇宙”理念的设想中的。目前,“元宇宙”这个概念仍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韩国学者Sang-Min Park 和Young-Gab Kim 合作的一篇详尽的技术性报告中,整理了50 余条不同学者给出的关于元宇宙的定义,既有各种技术方面的具体设想,也有理论层面的精要概括。[1]有些学者将元宇宙视为一种“传统电子空间的三维扩展”(a three-dimensional extension of the traditionalelectronic space), 一个满足“ 真实性、普遍存在、交互操作性、可扩展性”(realism, ubiquity,interoperability, extensibility)四要素的人造虚拟世界;有些学者则更倾向于将元宇宙理解为“虚拟扩增的物理现实与物理性持续的虚拟空间”(virtually augmented physical reality and physically persistent virtualspace)的综合体。为了便于厘清元宇宙与自然现实的相互渗透,及其对人生活世界的影响,本文的考察采用更为狭义的外延,将元宇宙限定为“有别于自然世界a 的虚拟空间”,而非两者的综合体。
综观现有的定义可以看出,元宇宙理念包含三条重要原则:
Ⅰ . 基于人的需求,通过技术构建一个能被人类感官系统所接受、被人类认知系统所整理,最终被视为同物理现实般真实的虚拟环境;
Ⅱ . 为上述环境构建完整的体系和法则,使其获得大众皆可接受并认同的普遍性,以及不依赖于任何单一集体或个人的独立性,以保证其持存性,或者说“物性”;
Ⅲ . 确保虚拟环境和物理现实的交互融合。
在现实世界,人类已经开展了围绕这三条原则筹建元宇宙的探索实践。比如:近年来开始流行的沉浸式体验便是对原则Ⅰ的探索;而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的流通和交易,以及对虚拟地产的投资(如果足够严肃,而非作为一种噱头),则无不预设了一个自洽经济体的存在可能性,这便是原则Ⅱ的体现;此外,虚拟货币在现实世界某些团体和社区流通、购买现实产品和服务的事实,以及各种跨媒介叙事,则是原则Ⅲ的实践雏形。这三条原则的探索实践并无时间先后。技术已然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我们已然生活在技术之中,而技术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而飞速发展,所获得的正当性和可靠性使得某种理念甫一问世便投入技术的怀抱;而且,技术的历史沉淀和最新发展使得理念的技术化过程越来越轻便而高效,那么现实世界的技术实践能同时分别沿着上述三条原则的方向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就元宇宙理念的内在逻辑而言,原则Ⅰ仍不失为元宇宙的根本前提和基础。一方面,元宇宙必须在解读人类感官和认知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配于这个系统的自洽的虚拟世界;另一方面,元宇宙在满足人类需求的驱动下获得发展,逐步丰富人类的生活世界及其现实。这就决定了元宇宙绝对的属人性质。
(一)元宇宙现实作为人类认识的产物
元宇宙作为人通过技术而创造实现的作品,其基本内容首先便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与复制b,以呈现一个对人而言可居的世界。只有当一个可感可理解的世界真实地呈现在人眼前并被集体共享,乃至模糊了虚拟空间与自然现实之间的边界,人类才可宣告元宇宙初具形态。当前,科技领域对沉浸式体验、智能穿戴设备、虚拟现实(VR)等方面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远未达到元宇宙的要求,但亦不乏对元宇宙形态的探索,如2013 年成立的虚拟现实平台AltspaceVR,2015 年成立的去中心化线上虚拟现实平台Decentraland,2017 年发行的一款大型多人线上虚拟现实游戏VRChat,通过穿戴设备将世界各地的使用者连通至同一个虚拟三维空间,允许使用者进行实时互动,但其中呈现的景物、人像、空间感等方面内容都远未达到自然世界的真实,也就只是有着VR 技术加持的社交平台而已。
这种真实是完全奠基于人的感官系统和认知系统之上的。身体的“架构功能”(framing function)在持续地参与虚拟空间中物的赋形[2]。一个生命体,如果不享有人类的感官系统,便无法进入元宇宙,后者对其也就自然不具有现实性;倘若它享有人类的感官系统,但与人类处理认知材料的方式有异,仍然无法获得一个可理解的虚拟世界,而只能陷入混乱的感觉碎片当中。故而现实世界的山川草木必然无法感受元宇宙里的清风吹拂,虫鱼鸟兽也不会被元宇宙中的脚步声惊走。即便是其他高等智慧生命,由于不与人类共享感官系统和认知方式,也不能直接进入元宇宙,除非在技术层面也实现了对它们的感官系统和认知系统的全面解读和应用,并将相关成果付诸元宇宙的技术构建,才可能实现元宇宙对它们的开放准入。
可以说,元宇宙的现实首先关乎的是人的认识现实的可能性。这种不直接从物自身而从人的认识结构出发构建世界、追问现实的方式,显然是康德(Immanuel Kant,1724 — 1804)的首创。他的批判哲学将感性(Sinnlichkeit)和知性(Verstand)视为人的两种根本认知方式:物体首先在感性中被人直观而成为认识的对象;借由直观,对象刺激人的感官而作用于人的表象能力从而成为(严格说来,只对人而言的)现象。物体在现象中只是感性直观杂多的集合体,而知性则需要通过想象力的先天综合将杂多的感性材料统摄于概念之下,以作出判断,经验也便由此形成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首句便开章明义:“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开始”,正文也直接强调说:“经验的可能性就是赋予我们的一切先天知识以客观实在性的东西”(Die Möglichkeit der Erfahrung ist also das, was allen unsernErkenntnis a priori objektive Realität gibt)。[3]200,[4]150 因此,对人而言,现实乃是人所能够经验的东西,不可能出现在人的经验中的东西不能被人所认识,自然也就不构成人的现实,或者说,对人而言不具现实性。而在经验的发生过程中,物的显现首先被感性处理成以时间和空间为先天结构的感性杂多,知性再对后者进行综合统一,于是物体甫一成为认识对象便在人的认识能力的作用下发生变形,其自身(即物自体,Ding an sich)从未在认识中出场。由此,物自体在人的认识中被悬置了,甚或可以说,对于人所要构建的现实而言,物自体无足轻重。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元宇宙纯乎是一种康德主义的技术实践。物自体在此毅然被抛弃,现实的展现直接从表象开始。“表象”一词的德文Vorstellung 源自动词(sich) vorstellen,后者意为“将某物呈现在(自己)面前”。元宇宙在技术层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表象问题,即让物清晰地呈现在人的意识面前,而无须追问物本身的自主存在。批判哲学为自己划出界限,要求纯粹知性概念的运用不能超出可能经验的对象而直达物本身。这一自限性在元宇宙的技术实践中则体现于它对人自身的表象能力的挖掘,而轻忽对人之外的现实宇宙的探索,这也就决定了元宇宙的现实只能是一种围绕人而存在的自限性现实。如果将康德主义的认识论结构贯彻始终的话,现实世界与元宇宙之间也就存在某种程度的同质性:人所能够理解的现实始终是种在世性现实,人所认识的世界只是一种“元宇宙”。正如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的洞喻中所展现的那样,人们只能看到洞壁上投放的影像,而无法看到背后事物的模型及其实在。[5]272-276 当元宇宙所提供的影像不是仅仅停留在电脑屏幕上供人观看,而是充满人的感官,令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之时,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便有了更多的孔隙性,而两者的直接互通也就更为可能了。
(二)元宇宙现实作为人类需求的产物
但是,不同于自然现实的无目的性,元宇宙本身在其真实之上承担着更高的使命,即创新性地满足人类在现实世界无法轻易满足或者根本不可能满足的具体需求。对人类需求的细化与再现,也就成了元宇宙生成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从根本上讲,元宇宙要满足的也无外乎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 — 1970)所提出的人类生理、安全、情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种不同层次的需求[6],以增强人的幸福感。有所不同的是,在自然世界中,人类需求的满足遵循等级次序,只有对水、食物、空气、睡眠等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了,人们才会依次追求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保障,与他人建立亲密的联系、获得归属感,在群体当中获得认可和尊重,以及突破自我、实现个人潜能。人的肉身性在此决定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必须首先维持物理性生存才能逐步满足其他精神需求。而元宇宙被人的感官和认知系统处理并接收之后,肉身性的直接影响便不复存在,肉身桎梏的挣脱(或者说,虚拟身份Avatar 的使用)将为各种创造性理念的产生与施行提供广阔的空间,从而能够同时探索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而无须遵循某种等级次序。现有的网络技术已经极大程度地颠覆了人类需求的满足方式,其发展始终与后者息息相关。电子邮件取代了传统的通信方式,计算机文档处理功能取代了打字机,影像处理技术引入了观看世界,有了留驻时光的新可能;社交需求和购物效率则直接刺激了网络技术的现代发展;前两年的疫情对现实世界的切割又催生了远程办公、线上会议、网络教学等技术应用的新样态。元宇宙借助沉浸式技术在现实世界之外所构建的真实必能进一步颠覆和拓展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重塑人的生活世界。
人的五种基本需求直接关涉个体经验和群体关系两个层面。就个体经验而言,元宇宙通过技术调动人的感官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a 之余,可以为人提供各种感官享受。让一道美食刺激味蕾,引出一段高昂的交响乐激荡鼓膜,将一片异域风光倒映在视网膜上,在指尖触摸到远方情人的脸颊……或者同时刺激多种感官,营造速度感、沉降感、高空感、窒息感等等,纯粹经由身体而经验到的“体验”将远远超过赛博格艺术的范畴而得到近乎完满地呈现。电影技术在经历了从2D 到3D 的发展和对4D的探索之后,在元宇宙时代能够提供给观众全方位的感官浸入,观众得以直接进入电影的剧情世界去体验角色的命运起伏、生老病死,在角色视角与观众视角的随意切换中获得共情与净化(Catharsis)。这种新的观影体验甚至令人有足够理由心生疑虑:这是否还可以称为电影,抑或应该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而得到重新命名?电影艺术是否该随着元宇宙的到来而逐步退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舞台?
元宇宙对安全需求的满足或许也将首要着眼于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居住。现代技术已经在起居、出行、休闲、健康等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类曾经居住于大地之上,自然生灭,在与天地万物的亲密中探索生命的诗意,而技术的强力则要驱散神秘与未知,将人安居于精致的“玻璃房”(Glashaus)里,不容一丝尘埃[7]——技术借由对医学的介入延长了个体的生命,同时借由对居住的介入而在淡化人作为个体与时间的独特关联,因为自然世界并未在他的个体生命落下任何尘埃,他也鲜为历史涂抹个人印迹。当下智能家居的畅想将在元宇宙时代凭借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融合而得到完美实现,人可以借助数字孪生技术随意将自己的室内空间转换成想要的空间表象:将卧室设置在海滩上,听着海浪入眠;将厨房设置在一片青葱的草地上,蝴蝶在餐盘间起舞;或者将客厅移至星空下,看一场露天电影;等等。
人的情感需求和对爱的渴望是否能像电影《她》(Her)中那样,被一个虚拟存在所满足呢?个人影响力或明星效应在体育、文化、娱乐等领域的呈现又将是何种样态?尤其在自我实现方面,元宇宙将开拓很多新的可能。比如在教育领域,全息影像和沉浸式教学能极大助力启蒙教育提高效率:多种母语环境可以轻松实现,而直接通过沉浸式再现让孩子“亲历”一段历史、一个生化反应或者一道天文奇观也往往比枯燥的讲述更能开启智慧之门。在造型艺术领域,元宇宙或许能即时为人在虚拟空间三维具现自己在色彩、结构、光影等方面的构想,艺术创造的过程有如上帝造物般地“从无到有”,而全息效果又有助于刺激人的视觉感受,进一步启发创作灵感,这就为个体的艺术创造行为提供了更为高效快捷的途径。相信元宇宙能够极大提高艺术的可进入性,拓展其创造空间。
就群体关系而言,元宇宙又能提供何种创新性呢?在区分共同体和社会这两种人类群体关系时,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 — 1936)提出两种不同的人类意志,即本质意志(Wesenwillen)和抉择意志(Kürwillen),以强调群体组织形成过程中所存在的“持续内在关系(das dauernde innere Verhältnis)”[8]。本质意志对社会图景(soziales Gebilde)——包括社会关系、社会价值和社会连结等方面——的接受(Bejahung)立足于该图景本身,而抉择意志对某种社会图景的接受则是为了外在于该图景的目的。前者是通过传统、教育和习惯等自然形成的,先人的思考方式和感受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充实了人的看法、性情和良知,行动的手段和目的构成有机的整体;后者则是通过理性思考所作出的选择,行动的手段与目的之间有着清晰界限,手段始终为目的服务。在本质意志的主导作用下,形成了以血亲、地缘、习俗信仰、兴趣爱好等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而在抉择意志的主导作用下,则形成了以经济契约、租赁、雇佣等关系缔结而成的社会。在滕尼斯看来,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西方历史经历了一个从共同体向社会逐渐演变的过程。而在元宇宙中,本质意志的效力将得到更大释放。人们很容易依据自己的兴趣和喜好结成共同体,毕竟对大多数人而言,元宇宙的基本功能是作为逃避现实世界的休憩之所,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能更快地获得幸福感,人们也就更倾向于自然形成各种共同体。可以想见,对于集体性活动的具现将构成元宇宙的创造性模仿的核心内容,尤其作为其雏形的电子游戏将发展出更丰富多样的多元世界(如电影《头号玩家》中所展现的赛车世界和不同战斗场),满足人们获得他人认同与成就感的需求。不仅如此,元宇宙也为某些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共同体提供了可能,甚或为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提供某种预演,而宗教热忱的集体渲染也可能在其中找到新的有效形式。但由于元宇宙萌生之初就有着资本的介入,而工作概念又是元宇宙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倾斜将不可避免,也必然形成以契约和雇佣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共同体与社会的共存将是元宇宙的基本事实,但群体关系的存在样态必然会在超越现实的地理、国籍、文化限制之外获得更多可能。
二、元宇宙的实践现实
这个奠基于人的感官系统和认知系统,为满足人类需求而人为构建的虚拟世界,并不止于能被人认识而已,而是能够直接作用于人自身。元宇宙必然是现实世界之外的可为人居的世界,否则便不能获得长久的发展;同时也必然是能够影响人之行动的世界,否则便失去其价值和意义。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区分出两种不同的人类行动[9]:一种是过渡性的,作为工具服务于该行动之外的某个事物,即作品;一种是内在性的,并不产生主体之外的作品,而是直接改变主体本身,故而其目的性内在于行为过程。前者乃是ποίησις(poíēsis,即诗学),后者乃是πρᾶξιςa(prâxis,即实践)。既然实践能够对行动者自身产生某种实际结果,这就引申出了实践的另一层含义,即所有能够改变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的人类行为。从这种区分出发,元宇宙现实堪称实践意义上的现实,内在地以人自身为目的,对人自身及其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产生实际的影响。
这种实践现实的作用机制为何呢?狭义的元宇宙,作为一种虚拟世界,乃是对现实世界的创造性模仿,其现实性自然也就奠基于这种模仿之上。利科(Paul Ricoeur,1913 — 2005)诠释学非常关注人的创造性模仿,将亚里士多德的Mimesisb 概念拓展成三重结构:Mimesis I、Mimesis II 和Mimesis III,分别进行预塑形(préfiguration)、塑形(figuration)和再塑形(refiguration)[10]。在此关涉的根本问题始终是语言与行动之间的关系,Mimesis I 作为预塑形阶段即立足于对行动世界的前理解而对人类行动进行语言层面的建构。人的行动不同于物理现象,而是有着更复杂的结构,包括行动者、方式、目的、动机等概念网络;它在一定的习俗、信仰、伦理观念等文化框架内具有特定含义,有其可读性;此外,不同行动有着不同的时间向度,如预期行为与未来相关,回忆行为指向过去,而具体执行则着眼当下,等等。预塑形便是从行动的结构性、符号性和时间性出发进行编码,为塑形提供基础和准备。MimesisII 的塑形则是在语言层面所进行的布局(mise en intrigue),借助想象性变异,遵循时间秩序或者某种因果关系,将个别事件连同其行为人、行动目标、行为方式、人物(及其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行动背景、意外的结果等构成事件张力的异质因素整合成能够被人理解的完整故事,甚或是包含丰富内容的文本世界。
如果说预塑形是行动被转化为语言的过程,塑形是语言层面有条理的自由变形和意义世界的展开,那么Mimesis III 的再塑形则是语言返归于行动、作品借此获得其完整意义的过程。阅读的过程需要读者不断回到文本,重建文本的问题视域;而理解的过程则是将重建的问题视域纳入自己的视域当中,实现历史视域与当下视域的融合,即所谓的“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11]311。理解并不仅止于分析文本的意义,而是要将之应用于读者所处的实际情况a。利科更将理解与读者的主体性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理解就是在文本面前理解自身(se comprendre devant le texte),这并非是将自身有限的理解能力强加给文本,而是要悬置自我,全心接纳文本(当然并非一味盲目被动,而是积极参与其中),从文本所提供的世界中获得关乎主体存在的建议,以构建一个更为辽阔的自我(unsoi plus vaste)。[12]主体的反思,在利科那里从来都是借助作品而实现对意义的占有(appropriation/Aneignung)。[13]因此,Mimesis III 可以被视为行动世界创造性模仿文本世界的过程,读者通过对意义的占有获得了新的自我,这包括对自身存在的新理解和新的行动方式。
从人的角度看,这三重Mimesis 同样在元宇宙中发生。元宇宙作为人的作品,同文本一样构成了人的意义世界,无时无刻不是人的阅读对象。人在与元宇宙的诠释学互动中,不断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更新自我。而倘若不从人而从作品的角度来看这三重创新性模仿,预塑形阶段关涉的则是符号学问题,即如何将行动转码成语义符号;塑形阶段涉及的是一个独立、完整、自洽的语义系统;再塑形则是借由行动主体打通文本世界与现实行动。这个角度转换的价值就在于,主体性的淡化而物性的凸显,换句话说,从理解的层面转换到了技术的层面。于是,显而易见的是,上文论及的元宇宙理念三原则分别契合于模仿的三重结构。
原则Ⅰ正是元宇宙的预塑形。元宇宙对物理现实的扩展也首先要将其转换为语言,不同于文本的预塑形将行动世界转换为人类历史自然生成的语言,元宇宙需要将物理表象以及人的感官系统和认知系统的具体运作转换为计算机语言。技术究竟将如何实现这种转换仍是难以想象的,也许所用的穿戴设备完全不需要现在所通行的那般复杂,甚或有着别的更为高效轻便的进入媒介。可以说,当下所有的技术和理念尝试都只是元宇宙的预塑形阶段,数据传输技术、沉浸式技术、虚拟空间、网络游戏、实时互动、人机交互、区块链技术、虚拟货币等,都只是未来元宇宙的基本构件。原则Ⅱ则是元宇宙的塑形,旨在构建一个全面、有序、完整的虚拟世界,以承载各种满足人类不同需求的虚拟空间。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是“有用”的,不论是用于个人思考、阅读、艺术创作、休眠、情感体验、体能锻炼等的私人空间,还是用于教育、宗教、政治、娱乐等方面的公共空间。每个人的微小举动都即时修改了整个系统的代码信息,使得整个系统无时无刻不处于持续的塑形和自我更新当中——去中心化的美好愿景希望这种更新能够免于任何单一个人或集体的影响。不同于绝大多数文本塑形的个人创作,元宇宙一旦脱离预塑形阶段,便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有如一部史诗,随着人类历史举步向前。元宇宙的物性便在这集体性的持续塑形中彰显出来——如其所是地自然生长。
但这种持续塑形并不能凭空实现,而要借助元宇宙与物理现实之间的良性循环,这便是原则Ⅲ所作出的保障。元宇宙的设想向世人许诺能够实现虚拟世界与物理现实的互通,同时这种互通也是元宇宙自身能够存续的根基。元宇宙对物理现实的接纳和拓展在于为人提供更多的真实经验,而物理现实对元宇宙的接纳和拓展则在于,一方面,增强硬件设施建设,提高其可进入性;另一方面,认可元宇宙中人的行为所具有的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在元宇宙时代,虚拟世界的接入终端设备或将如路边的电话亭或充电桩一般普遍而平常,以满足大众的日常接入和元宇宙自身扩张的需要。同等重要的是,元宇宙的扩张在解放人类精神的同时始终要以人的肉身存续为前提。元宇宙作为人类世界的寄生物,终究不能离开人的存在而生长,而人无法终日沉湎于元宇宙的万千表象而不论腹中饥渴。有鉴于此,兑现元宇宙中的行为价值在根本上有利于维持现实世界中人的物理性存在。无论是虚拟货币在现实世界的流通,还是工作理念在元宇宙中的引入,无不是出于这种保障。只有当人(或者说人的化身)在元宇宙中也成为生产者而非纯粹的消费者,才有利于持续形成一个有机的模仿循环:自然世界中的需求促使人前往元宇宙寻求满足,而元宇宙因其有着与生活世界相通的价值认定,能够直接影响人的现实处境(situation);新的处境产生了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又促使新的元宇宙浸入。元宇宙的现实性便在于这种循环中实现它与外部世界的连贯统一。
三、元宇宙的游戏现实
元宇宙将作为生活世界的建构性内容向世人展开自身,并不满足于当下技术仅只作为充实生活的附庸性角色,而是要全方位布局人的生活世界。杜威(John Dewey,1859 — 1952)曾强调艺术经验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所有经验都是有机自我(organic self)在与世界进行持续性和积聚性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但不同于日常经验的纯然发生(just happen)、戛然而止,抑或旁出无端、相互错结,艺术经验并非漫无目的,也非机械地高效地服务于某个目标,而是借由动态的架构(dynamic organization)逐步转化内在的张力和抗性以积蓄意义和情绪,直至过程结束时形成一个4 4独立完整的经验,乃是某种日常经验的澄明与强化。[14]
元宇宙可谓践行了这种艺术经验与日常生活的连续。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而言,元宇宙中所能感受到的在世性现实究竟为何?德国哲学家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1920 — 1996)将在世性现实(Wirklichkeit)理解为一种“在人的行为中对人作出规定的约束特性,……人所依凭和考量、所信赖和参考的预设性”(Charakter von Verbindlichkeit, der den Menschen in seinem Verhalten bestimmt […]Art der Vorgegebenheit, auf die und mit der der Mensch rechnet, auf die er sich verläßt und auf die er sichberuft)[15]。若遵循这种实用主义视角来理解元宇宙的现实性,便需要反思元宇宙这种人造物作为人的生活环境将为人的存在提供何种约束性,将为人的行动预设何种前提和依据。这种现实性以其与日常生活的直接整合必然区别于传统艺术形式所提供的现实性。如果小说这种成熟的传统艺术形式诚如布鲁门贝格所说为人提供了可能现实(Wirklichkeit des Möglichen)[16],那么元宇宙所提供的现实则堪称游戏现实(Wirklichkeit des Spieles)。
就技术实践而言,游戏乃目前元宇宙的主要探索渠道,各种网络虚拟游戏不断开拓着技术构建现实的可能。就元宇宙存在的本原方式而言,无论它将被未来技术赋予何种物质形态,因其旨在为人提供经验,便始终仍是种伽达默尔意义上的游戏,即一种不断往复的过程,或者说运动的往复(Hinund Her einer Bewegung)。游戏是没有根基的,仅作为媒介提供相应的规则和指示,也不单凭游戏者的意识或行为获得自身存在。游戏者遵循游戏规则和指示采取行动,得到规则或他者的反馈后再进一步行动,如是不断往复,游戏在这个过程中显现自身,并在持续的展开中自我更新。因此,游戏并不委身于主体性的自由,而是相较于游戏者的意识有着优先性,随着往复过程的推进,游戏者被限制于特定领域中,并将游戏的存在感受为超过自身的现实。元宇宙作为集体共享的虚拟空间,是无根基性实存的集体游戏,借助技术发挥媒介功能,在调动全身感官参与的往复运动中为人提供各种经验。
这种伽达默尔意义上的游戏同样也是小说所提供的审美体验的存在方式,阅读过程实则是读者与文本持续进行互动的往复过程,每次互动过程的结束都在完成一个利科诠释学意义上的模仿循环,而小说的可能现实也在阅读的往复游戏中逐渐显现自身。但小说中的审美互动毕竟无须技术的介入,也无法提供全方位的感官体验,这就决定了小说与元宇宙所提供的现实有着不同的样态。诚然如此,小说和元宇宙都旨在建构可居的世界,小说这种成熟艺术形式中的现实特征仍不失为一种参照,有助于对未来成熟元宇宙中的游戏现实进行前瞻性思考。
在考察小说的可能现实时,布鲁门贝格总结了西方思想史上出现的四种基本现实理念。每种现实理念的出现都伴随着全新的时代特征,但新理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理念的消失,而是共同构成了人类理解自身生活现实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在特定时代,其中某种理念可能起主导作用。首先,是即时明证性现实(Realität der momentanen Evidenz)。这一现实理念源自古希腊时期,它预设现实由自身显现,在其以令人信服的力量显现自身的瞬间便不容置疑,以至于直接成为感官经验。于是在柏拉图的洞喻中,突破枷锁的人来到洞外时,他的精神能够看4到真理之“光”。柏拉图所要求的理性之“眼”自然不同于世俗之“眼”,前者是对终极真理的瞬间认知和认可,后者只囿于现有之物的感官呈现,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对人的行为约束有着相似的逻辑——眼见即为实。其次,是受确保的现实(garantierte Realität)。自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 — 430)以降,整个中世纪作为人类精神的自我理解史,逐步认识到思想无法单凭自身将既有现实中的庞大假象尽数消除,只能通过一个复杂的形而上学过程才能通达明晰性,并将上帝视为人类知识之可靠性的责任担保人。再次,是一种自我统一的前后关系的实现(Realisierung eines in sich einstimmigen Kontextes)。这种现实理念与主体密切相关。近代哲学的开拓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 — 1650)试图通过主体自身来奠基人类知识的有效性和明证性,所有知识都需经由“我思”(cogito)来检验;沿着这条思辨路径,康德将“我思”(Ich denke)视为自我意识——作为纯粹的本源的统觉(Apperzeption)——所自发给出的表象,而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则奠定了先天知识的可能性[3]136,[4]89;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将一切认识对象(包括经验主体本身)都悬置起来,于我们而言的真理性和现实性脱离了先验主体性(transzendentaleSubjektivität)便毫无意义可言,后者的意向性建构更是决定性的——乃是纯粹自我提供了可行路径,对象才得以现实化为真切在此(wirklich da verwirklicht),通往至高意义上被最终奠定的知识与通往普遍自我认识(universale Selbsterkenntnis)同一。[17]于是,现实借由相对于主体的现象学展开而达成,并非一次性被给出,需要不断在统一性中构建自洽的体系,未来的展开很可能打破至今为止所沉淀的统一体而改写现实。最后是种阻抗(Widerstand)的经验。在古希腊,人切实把握自在之物仍是可能的;但中世纪神学将世界视为创世者的作品之后,人类通往自然本身的道路便被切断了,知识在唯名论的影响下沦为符号的世界;主体一经发现,便支撑起了整个人类现实,物自体被置于先验主体所构建的现实之外;而阻抗则是科学迅猛发展之下物的回归,除了精神分析所揭示的主体潜意识对主体自明性的动摇,微观粒子、基本常量等知识的拓展也构成了对主体的不屈从甚或否定,人只能将之接受为基本事实(factum brutum),追加确认为现实的组成部分。
这四种现实理念凸显出四个人类行为的约束向度,即感官确认、第三方权威、主体性统一和阻抗经验。这四个向度可以作为展望未来元宇宙中游戏现实的线索。元宇宙的成熟形态作为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将借助技术为人提供新的行动依据和约束性预设,其现实性便在于四个约束向度将具有的新样态。
感官确认首先是日常生活中人类行为的基本依据。人们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作出即时判断,继而采取行动。这种对现实的确认自然免不了各种常识和前见的干预,使人的行为陷于盲目和被动。而在小说中,文本世界的敞开悬置了客观世界,抛开前见,或者背离常识,为人提供不同于客观世界的可能性,人可以在想象性变异的世界反思不同的行为范式,而无须即时作出关乎自身实际行为的抉择,这便构成了小说的批判性维度。此外,即时明证性现实在小说中的显现需要读者的积极参与,通过想象和理性认知,在意识中将小说里的描述捕捉为完全的现在性(Gegenwärtigkeit)。伽达默尔将艺术作品中的这种时间性称为“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11]132,即是说,小说中的事物借由阅读而活化为与读者同时的存在,每次成功的阅读都需要超越作为介质的小说本身去获取事物的同时性。这里仍有柏拉图主义的余韵,读者真正的直观对象并非小说本身,而是其所传递的理念,他只有通过积极的阅读才能在自己的意识中“看”到小说中的事物,而小说的可视性即在于借助丰富的诗性语言传达某种理念之“火”。这种感官确认在元宇宙中被彻底抛弃,不同于小说的同时性需要读者完成,元宇宙中的即时明证是被直接给出的,甚至于,元宇宙务求借助技术达成即时明证,即时明证的实现是其成熟的标志。元宇宙中的技术媒介(穿戴设备或其他媒介)通过解读人的感官,能直接将各种表象性变异传达给使用者,使人无须想象便能获得某种被集中强化的直观体验,当下性占据着整个经验空间,让人无暇顾及未来或是追忆过往。技术实现即时明证的能力随着技术的迭代不断发展,力求使人在行动的往复过程中忘记技术的介入,实现技术的退场,人们在元宇宙中回归日常生活,在近乎自然的状态下凭借自身的感官确认即时作出行动抉择。这也就意味着小说中的悬置的取消和批判性维度的缺失。
第三方权威的奠基是行动依据和约束性预设的第二个向度。行动抉择并非基于自我对当下形势的判断,而是出于对某种创制者的信任。上帝曾被视为万物的创始者和现实的奠定者;在现代社会,法律分有了这种神圣性,成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参照和约束;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常常出于对某个人的信任作出自己的行动抉择。这种现实范式在小说中集中体现在作者的观念。作者是小说中可能世界的创造者,也就不免成为理解文本的权威,“作者中心论”可谓天然构成了传统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观念,希望透过文本去追溯作者的意志,或如浪漫主义那样追问作者的创作天分。这种追问对于作为生活世界的元宇宙而言则是令人不安的。如同柏拉图洞喻中洞壁影像是被第三方投放的,元宇宙也只是被专业技术人员所精心安置的感官世界(尽管这种安置无法完全克服算法“黑箱”里的未知)。人并未直达自然物本身,只是感知到能被轻易篡改的影像。无论人们在其中所见所闻多么近乎自然,都不免受到某种目的性的影响。资本的介入更加剧了这种目的性的增殖,与元宇宙去中心化的理念相抗衡。在这种前提下,权力悄然而入,人的行动抉择就很难是自由的了。
第三个约束向度是主体性统一。行动建立在对所处境况的综合考量之下,这种综合既是外在关系的前后一致,更是主体性的自我统一。每个认识对象在主体面前的显现都有赖于特有的意向结构,这种结构被统一整合于先验主体当中。小说的阅读便伴随着可能现实的这个约束向度。小说文本是一个统合的句法结构,阅读体验随着读者与文本的往复互动而展开,读者需要跟随文本的引导而不断在意识中理出前后一致的故事线索,才能更好地构建可能现实,捕捉其现在性,并由此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做出某种预期。如果情节的实际展开与预期有所冲突,读者便要重建故事的统一性,直至文本结束,获得小说中可能现实的整体认识。这个过程与主体借由文本理解自身的过程是同步的,主体也在不断基于主体性的自我统一而借由阅读丰富和完善自我认识。鉴于现有设想,元宇宙将冲击外在关系的前后一致和主体性的自我统一。在元宇宙时代,各种虚拟空间的创建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每个空间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规则,而不同空间的行为规则很可能是相互冲突的——比如搏斗类游戏空间可以允许人相互拼杀,而交友类空间则要求人们彼此友善——如果人长年沉浸于不同的空间,缺乏统一性作参照,很可能丧失对行为规范的基本判断。元宇宙的神话属性便体现在:无视统一性,能够创建法则不一的不同空间,以及赋予人物强大的完人形象。生活世界的割裂伴随着主体的割裂。人们在文本阅读中能够获得主体性,而元宇宙恰恰在消解这种主体性。既然能够轻易在不同的虚拟空间重启不同的日常生活,抉择就不再需要慎重;既然能够轻易做出行动,人的脆弱也就被轻易遮蔽,人际关系中的伦理考量便无足轻重了。也许在元宇宙中,只有坚持自主创造、加强人际交流,才能保障主体的价值。
阻抗经验的向度在于物性的显现。物作为基本事实也具有人的行为所要参考的约束性和预设性,这种约束在物获得优先性时便可能直接对人的行为和存在构成直接的冲击。就小说而言,阅读并非是为了把握作者意志,也不停留于文本的语言结构,而更是要把握潜藏于文本背后的意义世界。这种意义世界的开显便构成了其物性,并随着作者意愿的模糊和文本流传所获得的历史性而日益彰显,而逐渐成为主体(如读者)无法主观任意驱使的现实成分(如小说主人公的基本性格和遭遇)。元宇宙作为游戏,先天有着相较于游戏者的优先性。元宇宙的技术介质一旦搭建完成,便能不断进化和自我更新,发展成永无休止的游戏,这已然接近于自然物的运动形态。元宇宙的自然发展似乎是没有目标和方向的,迎合着人的主观欲望和需求,不让人心生厌倦,逐渐消磨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所依托的具体技术本就务求从日常生活现实中退场,主观能动性的缺失就更加剧了元宇宙物性层面的陌生化。一旦技术失控(如人工智能获得了某种意向性),便将全方位颠覆人的生活现实,给人的行为和存在带来灾难性影响。
结 语
人类从未停止过建构自己的生活世界,元宇宙只是其作品之一而已。不同于以往创制的是,元宇宙不再向外考究自然的奥秘,或是借由精神生产丰富文化世界,而是反求诸人的肉身,将人的存在置于集体共享的感官幻象之中。自反逻辑乃整个元宇宙创制的基调,当下对其现实性的前瞻性考察也必须遵循一种自反性,任何对元宇宙的直接描述都是乌托邦式的想象。
故而本文采取了三条谨慎的自反路径:在哲学人类学视野下,元宇宙解读人类感官,旨在满足人类需求,其现实具有浓厚的属人性;在诠释学视野下,元宇宙能够融入人的实践,也即丰富主体自身的活动,同时,元宇宙作为人的创造性模仿,其现实性在于其三重模仿结构为人构建的某种连贯统一性;在实用主义视野下,元宇宙则分别在感官确认、第三方权威、主体性统一和阻抗经验四个向度上为人提供行动依据和约束性预设。
可以说,本文的有效性全然基于对人本身的关注。在科学主义和效率原则大行其道的今天,对人的遗忘或物化从未停止,而在元宇宙时代,也即技术变得无所不能的时代,人的境况又将遭受怎样的挑战呢?这也许是所有人在享受技术便利之余的顾虑,值得持续批判性思考下去。
参考文献:
[1]Park, Sang-Min, and Young-Gab Kim. \"A Metaverse: Taxonomy, Components, Applications, and Open Challenges\"[J]. IEEE Access, 2022(10).
[2]Hansen, Mark B. N.. New Philosophy for New Media[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8.
[3]Kant, Immanuel.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14.
[4]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张竹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Maslow, Abraham.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M]. New York: Harper amp; Row, 1954. 35-46.
[7]Benjamin, Walter. Gesammelte Schriften 2, Aufsätze, Essays, Vorträge[M]. Frankfurt: Suhrkamp, 1991. 213-219.
[8]Tönnies, Ferdinand. Studien zu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M].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2. 224-225, 242.
[9]Aristote. La Politique[M]. Trans. Jules Tricot.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2005. 36.
[10]Ricoeur, Paul. Temps et récit, tome I[M].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3. 87-129.
[11]Gadamer, Hans-Georg. Wahrheit und Methode[M].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9.
[12]Ricoeur, Paul. Du texte à l'action[M].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6. 116-117.
[13]Ricoeur, Paul. De l'interprétation: essai sur Freud[M]. Paris: Ed. du Seuil, 1965. 56.
[14]Dewey, John. Art as Experience[M]. New York: Perigee Trade, 1980.
[15]Blumenberg, Hans. Realität und Realismus[M]. Berlin: Suhrkamp, 2020. 9.
[16]Blumenberg, Hans. Ästhetische und metaphorologische Schriften[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47-73.
[17]Husserl, Edmund.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M].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91. 23, 39.
(责任编辑:孙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