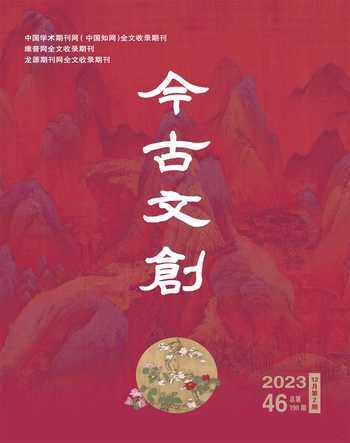筠州时期苏辙佛禅交际诗研究
【摘要】苏辙曾两度谪居筠州。第一次谪居筠州时,他与洞山克文、黄蘗道全、聪禅师、景福顺长老等人相识,交往甚密,唱和颇多。苏辙接触悟道于“搐鼻因缘”,其更信奉临济宗黄龙派。诗中禅元素较多,多有与佛禅相关的典故和佛典语,使得其诗充满佛禅意味,成为该时期苏辙诗歌创作的一大特点。苏辙好用“老”“病”“贫”“寒”等词,诗风偏向深沉,但字里行间透露出苏辙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第二次谪居筠州时,苏辙心性已大不如从前,不仅仕途渺茫,彼时好友相继圆寂,此时他以佛道之学作为精神支柱,潜心学术著作的创作,留下的诗歌作品不多。
【关键词】苏辙;筠州;佛典语;佛禅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6-008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6.024
一、苏辙与禅师的交往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辙与其父苏洵、其兄苏轼同列唐宋八大家,生平学问深受父兄影响,官至尚书右丞。苏辙一生任官,仕途却不顺畅,尤其是两次贬谪筠州,对苏辙为官从政的“壮心”产生了重要影响。谪居筠州期间,苏辙与众多禅师交好,留下许多唱和诗,其中收录在《栾城集》中的与各禅师相关的作品有三十二篇。从《栾城集》存诗来看,苏辙交往的禅师涉及有名可考者近十五人:洞山克文禅师、黄蘗道全禅师、景福顺长老、聪长老、明雅照师、圆照禅师、元净禅师、琏禅师、慧永、慧远、何道潜、医僧鉴清、医僧善正等。
因筠州黄檗山是中唐著名禅师黄檗希运的驻锡地,也是临济宗的策源地,凝聚着浓厚的佛禅气息,且苏辙所交往频繁的禅师中如洞山克文、黄蘗道全、省聪、景福顺等人均为临济宗黄龙派人,故其所接触的佛禅思想更倾向于临济宗。在景福顺长老向苏辙讲述了马祖道一禅师与百丈禅师间著名的“野鸭子”公案后,苏辙心受启发,于元丰七年(1084)三月作《景福顺老夜坐道古人搐鼻语》,诗云:
中年闻道觉前非,邂逅仍逢老顺师。搐鼻径参眞面目,掉头不受别钳锤。
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盐我是谁?惭愧东轩残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饴。①
其中“搐鼻径参眞面目,掉头不受别钳锤”,说明苏辙受到点化,不用再受别的禅家的锤炼敲打了。可以说,是在景福顺禅师“搐鼻因缘”的点拨下,苏辙悟到了实相真谛。《五灯会元》列顺禅师为临济宗,为南岳下十二世,列苏辙为南岳下十三世,将苏辙列为临济宗黄龙派上蓝顺禅师的法嗣:“参政苏辙居士,字子由。元丰三年(1080)以雎阳从事,左迁瑞州搉筦之任……公咨以心法,顺示搐鼻因缘。已而有省,作偈呈曰……” ②
元丰二年(1079)巳未,“子瞻以诗得罪,辙从坐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 ③需要说明的是,苏辙第一次贬谪筠州虽然与其上书营救苏轼而被牵连有关,但更大的原因应该在于其本人在朝中坚守原则、刚正直言,导致其树立了不少政敌。此时政治上虽看不到转机,但不是完全无路可走,因此他依旧心系朝中大事,关心百姓苦难,到元丰七年(1084),量移为歙州绩溪县令,此后又陆续经历升迁和贬谪。可以说,苏辙虽为上蓝顺禅师的法嗣,但他的心却始终关切着“俗”,处于“亦僧亦俗”之间。
二、苏辙佛禅交际诗的艺术特点
(一)苏辙佛禅诗的交际性
在苏辙与禅师交游的诗歌中,往往围绕着苏辙本人与禅师之间的交好关系而作,形成一种交互式的联系。以诗的标题为例,如《赠景福顺长老二首》《问黄蘗长老疾》《谢医僧善正》等,均以“赠”“问”“谢”为题,说明了苏辙作诗的目的。以诗的内容为例,如苏辙于元丰六年(1083)三月所作《问黄蘗长老疾》,诗云:
四大俱非五蕴空,身心河岳尽消熔。
病根何处容他住,日夜还将药石攻?④
元丰三年(1081)苏辙以罪谪高安时,与黄蘗道全禅师相识,道全禅师见辙后称赞道:“君静而惠,可以学道。”黄蘗道全,俗姓王,洛阳人。时住持祖师道场,发扬黄檗宗。此诗作于黄蘗禅师告知苏辙自己患病后,苏辙寄诗劝其服药以治病,体现出苏辙对好友的关心之情。苏辙是被贬的官员,又因事务缠身,不能入山见黄蘗道全禅师,“师每来见,辄语终日不去。”由此可知,苏辙与黄蘗道全禅师交谈甚欢,友人的慰藉为苏辙疲惫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禅意乐趣。再如苏辙于元丰七年(1084)十月所作《回寄圣寿聪长老》,诗云:
五年依止白莲社,百度追寻丈室游。睡待磨茶长辗转,病蒙煎药久迟留。
赞公夜宿诗仍作,巽老堂成记许求。回首万缘俱一梦,故应此物未沉浮。⑤
白莲社,源于佛教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此处以白莲社美称圣寿寺。赞公,唐京师大云寺主,此处以赞公比聪老。这首诗便是对聪长老寄给苏辙的诗的回复。苏辙回想起谪居筠州期间,他与聪长老的同游时光,一切因缘恍然如梦。此时苏辙即将离开筠州,赴任歙州绩溪县令,于临分别时拜望聪长老,从而作下这首诗。再如《次韵洞山克文长老》,诗云:
无地容锥卓,年来转觉贫。偶知珠在手,一任甑生尘。
窜逐非关性,顚狂却甚眞。此心谁复识,试语洞山人。⑥
“洞山人”,即洞山克文禅师。洞山克文,又称真净克文,俗姓郑,法名克文,是宋代临济宗黄龙派二世,黄龙慧南禅师的杰出弟子之一。蘇辙谪居筠州时,真净克文禅师住持筠州洞山道场,历住圣寿寺、洞山等地。苏辙在《洞山文长老语录叙》云:“元丰三年(1080),予以罪来南,一见如旧相识。既而其徒以语录相示,读之纵横放肆,为之茫然自失。” ⑦该诗通过描写与洞山克文禅师互通心意的场景,体现出苏辙与洞山克文长老关系亲密、交情匪浅。
综上可知,苏辙与筠州禅师相交游留下的诗歌作品,有许多都是在书写日常生活,表达对友人的思念与关心,诗中记录了苏辙与禅师的交游经历,表现出双方的深厚友情,全诗甚至可以当作书信来阅读。
(二)苏辙佛禅交际诗的艺术特点
首先,苏辙在与禅师的交际诗中擅用佛典语。苏辙谪居筠州这段时间以来,在佛禅知识的学习和禅宗氛围的影响下,他的诗歌中出现了许多佛典语。如《次韵洞山克文长老》一诗,其中“偶知珠在手”一句,在《苏轼诗集》卷四十五《乞数珠赠南禅湜老》中,引清查慎行注《木槵子经》云:“当贯木槵子一百八个,常自随身志,心称佛陀,达摩僧伽乃过一子,具如彼经。” ⑧此一百八个木槵子相贯,即数珠,也就是苏辙所说之珠。偶知,为专心佛法之意。珠,喻要言妙道。⑨《问黄蘗长老疾》中“四大俱非五蕴空”,“四大”即佛教中以地、水、火、风为四大,认为四者分别包含坚、湿、暖、动四种性能,人身即由此构成。因此用作人身的代称。“五蕴”则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的总称。前一种属于物质,后四种属于精神,是构成人身的五种要素,佛教认为众生的身体都是此五蕴和合而成的。⑩这句话的意思即是有形的无形的皆已不存在了。在《谢洞山石台远来访别》中“稍谙真际自虚澄” ⑪的“真际”为佛典语,指宇宙本体,亦指成佛的境界。《赠景福顺长老二首·其二》中“禅心海月圆” ⑫的“禅心”为佛教用语,是指清静寂定的心境。佛典语不仅出现在苏辙与禅师唱和交游的作品中,甚至还出现在同时期苏辙与一些官员、友人的往来诗歌中。如《毛国镇生日二绝·其二》:“闻公归橐尚空虚,近送《楞严》十卷书。心地本无生灭处,定逢生日亦如如。” ⑬《楞严》即《楞严经》,“心地”为佛典语,指心,即思想、意念等。佛教认为三界唯心,心如滋生万物的大地,能随缘生一切诸法。“如如”,即《楞伽经》所说五法之一,指永恒存在之真如。
其次,苏辙在佛禅交际诗中多借用与之相关的典故。苏辙诗歌向来有较强的说理性,他的诗中常常出现化用典故的诗句。谪居筠州以来,苏辙在用典时往往会因为唱和对象是禅师而选择借用与佛教相关的古人典故来表达。如《次韵洞山克文长老》中“此心谁复识,试语洞山人”一句,化用唐代诗人姚合所作《寄九华费冠卿》的“此心谁复识,日与世情疏”。费冠卿,字子军,池州青阳人,唐代著名隐士。其撰写的《九华山化城寺记》记述了新罗僧释地藏金乔觉的身世和卓锡九华山的经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历来受文坛和佛教界的重视。再如《雪中洞山黄蘗二禅师相访》中“不妨明镜无纤埃”,见于《宋高僧传》卷八《唐蕲州东山弘忍传》载:“初,忍于咸亨初命二三禅子各言其志,神秀先出偈,惠能和焉。乃以法服付慧能,受衣化于韶阳。⑭”弘忍选嗣法弟子,命寺僧各作一偈。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惠能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可见,苏辙所用典故切合了唱和的对象,将更加贴合禅师思想的典故化用为诗句,更能体现出其学识的渊博和对禅师好友的尊重,以及苏辙在谪居筠州期间受禅宗思想的影响。
另外,苏辙此时的诗风深沉邃密。有学者认为,苏辙个性内敛,便自然而然地以为其内心沉静淡然,诗歌语言平淡自然。但仔细阅读苏辙写于筠州的诗歌便能发现,用“淡静”“平和”无法完全概括此时他的诗风特色。首先,作为被贬谪的诗人,苏辙感到自己是“罪臣”,在他的诗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描述:“予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予以罪来南”,“元丰三年(1080)辙以罪谪高安”,可见其心中总是将此次贬谪当作一次不好的经历。笔者认为,此时苏辙的心态实在称不上“平和”。如苏辙在《次韵吕君丰城宝气亭》中所写“功成变化无踪迹,望断中原百尺楼” ⑮的这句牢骚话一样,可以看出他心中的失意很盛。第二次贬谪筠州,可以说此时的苏辙是真正的年迈体弱,尤其又是在政治上备受打压,接连被贬,已经毫无返回政治中心的可能性。在北宋末年的党禁之下,苏辙处于政治禁锢的境地当中,只能选择以闭门索居的生活方式度过晚年。其次,谪居筠州时期,苏辙的诗中多出现“病”“贫”“寒”“老”“愧”“潸然”“萧条”“萧瑟”等词,更是他对于自己的谪居生活的整体反映。“每惭菜饭分斋钵,时乞香泉洗病身” ⑯,“无地容锥卓,年来转觉贫”,“山中十月定多寒,纔过开炉便出山” ⑰,“坐令颠老时奔走,窃比韩公愧未能”等,均体现出苏辙此时的状态其实并不算好。若要强行给他的诗风加上一个“平淡”的帽子,也只能是被他压抑过后的情感表现。那么,苏辙谪居筠州的生活如此困顿,其内心便一蹶不振了吗?非也。苏辙与当地禅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如他在《谢洞山石台远来访别》中写道:“窜逐深山无友朋,往还但有两三僧。共游渤澥无边处,扶出须弥最上层。”这些与之交往的经历使得他的生活在困窘中有一些逍遥、自在,反映在其诗歌中,便是一种失意中仍抱有生活希望的人生态度。而这与他接受到的禅宗思想是分不开的。面对陡然失意的朝堂之变,他说“纷然变化一弹指,不妨明镜无纤埃”;面对岁月几经变换时,他感慨“风云一解散,变化何不为” ⑱;在学习禅宗思想时,他甚至能以“四大俱非五蕴空,身心河岳尽消熔”来解释一切皆空的道理;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这段经历时,他得出“回首万缘俱一梦,故应此物未沉浮”的结论。综上,与其说苏辙诗风是淡静有味,不如说其诗充满着他的深思,或以深沉邃密来概括则显得更为恰当。
综上,苏辙谪居筠州前后总计约十年,从仕途失意的沉闷到顿悟禅宗的深沉,其心性在与禅师道人的交游当中产生了缓慢而深刻的变化。苏辙虽已悟到实相真谛,却因一颗“入世心”而无法像普通的禅师一样做个闲散归隐之人。许是天意安排,他再次被贬。第二次他被贬为降授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他选择了熟悉的筠州。此时回来,熟悉的禅师好友早已陆续圆寂,他便独自参禅修心,体悟自我,從而排解晚年被贬的郁闷之情。可以说,两谪筠州的经历是苏辙一生中的关键节点,一谪让他明白佛禅能改人心性,解人忧愁,二谪让他知晓佛理教人隐忍自省,安宁自得。通过考察苏辙谪居筠州时与禅师道士交游的情况,分析此时他所做的诗歌创作,我们既能看到苏辙对待佛禅的一片虔诚之心,也能明白佛禅修行对他心性变化的重大意义。
注释:
①(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②(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卷十七,临济宗南岳下十三世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76页。
③(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后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3页。
④(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页。
⑤(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9页。
⑥(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页。
⑦(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6页。
⑧(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32页。
⑨(宋)苏辙撰,蒋宗许、袁津琥、陈默笺注:《苏辙诗编年笺注》卷十一,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922页。
⑩赖永海主编,赖永海、高永旺译注:《维摩诘经》卷上,方便品第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0页。
⑪(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页。
⑫(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266页。
⑬(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页。
⑭(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上册卷八,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2页。
⑮(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页。
⑯(宋)苏辙著,曾棗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
⑰(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
⑱(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
参考文献:
[1](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宋)苏轼著,(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宋)苏辙著,蒋宗许,袁津琥,陈默笺注.苏辙诗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9.
[5]释道世.法苑珠林[M].四部丛刊本.上海涵芬楼景印本.
[6](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赖永海主编,赖永海,高永旺译注.维摩诘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喻世华.苏辙两谪筠州考论——从生活、艺术、审美角度分析[J].同济大学学报,2013,(06).
作者简介:
彭琛,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