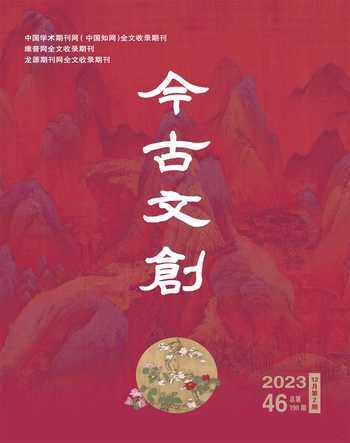陈染小说集《潜性逸事》中的嵌套叙事研究
【摘要】《潜性逸事》是当代女性作家陈染的中短篇小说集。小说集《潜性逸事》具有双重嵌套叙事结构,第一篇《潜性逸事》构成了文本的叙事层,而后面的十三篇小说则构成了文本的次叙事层。次叙事层以叙事层主人公雨子的心路历程作为内在线索,以梦境作为重要的叙述方式,呈现出女性在婚恋经历中追寻爱情、质疑性别秩序和反叛性别伦理的心理发展过程,立体地展现了女性心理空间。
【关键词】《潜性逸事》;嵌套叙事;梦境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6-005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6.017
梦境在陈染的小说文本中具有重要意义,如《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我”与母亲的复杂关系通过梦境和幻想人“伊堕人”[1]65-106得以呈现,《破开》中“我”与殒楠的关系也是在梦境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1]128-136。“在陈染的小说中,充满了对男性霸权话语的反抗,但有意思的是她们的反抗都是在梦中和想象中完成的。”[2]对比其他几本小说集的内容,《潜性逸事》在梦境书写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与内在连贯性,这部小说集中大量地运用了梦境的话语形式,表达了对男性中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质疑与反抗。这部小说集具有双重嵌套结构,叙事层由《潜性逸事》一篇构成,呈现出女主人公雨子三个阶段的心路历程,分别为依赖婚恋的女性心理、婚姻出现裂痕阶段的女性心理和婚姻破裂之后的女性心理。与第一篇《潜性逸事》中女性主人公雨子的心理状态变化相呼应,余下的十三篇小说构成次叙事层,在统一的梦境建构中,推动对性别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双重嵌套叙事中的文本呼应
在《潜性逸事》小说集的十四篇小说中,第一篇和第十四篇以现实书写为主,第二到十三篇中则具有大量的梦境书写。小说集《潜性逸事》中的后十三篇都可以看作是第一篇小说《潜性逸事》中女作家“雨子”的写作。
首先,两个叙事层在内容上前后呼应。《潜性逸事》中提到雨子所写作的场景是:“冰冷的北风呼啸着从窗前飞过,光秃秃的天空孤独地迎向一面空窗子,一束黑黑的长发从窗口飞扬出去,像一只逃离房间的翅膀或手臂……画面再次定格、凝滞。”[3]9《空的窗》中则描写了一个站在窗口向远处眺望、黑色的头发在风中飘扬的女性形象。《凡墙都是门》中提到:“两年前的这个时节,我认识了雨若。当时我刚刚从一场死去的婚姻中活过来……”[3]235这与雨子的婚姻变故遥相对应,其中提到“我”在经历婚姻变故后“终日躺在床上胡思乱想”[3]235,而《潜性逸事》中也提到“接下来的两天,雨子的很多时间都是躺在床上浮想联翩。”[3]25这两处情节书写也遥相呼应。
《潜性逸事》之后的十三篇小说蕴含着雨子的个人经验和婚姻思考。在《潜性逸事》中,雨子提到自己无法接受在大众面前亲吻,而《嘴唇里的阳光》中的黛二与爱人孔森在公园人群中亲吻;雨子勤劳、温文尔雅而又无比温顺的丈夫的形象,与后文所有婚姻书写中的丈夫形象特点一致;雨子对丈夫的咀嚼声和抠门个性不满而无奈的心理,也投射到后面几篇小说对家庭夫妻关系的思考中。这些特点在后面小说中的重现,是作家雨子经验的流露与思考的延展。
最后,叙事层和次叙事层在心理阶段上具有呼应。在第一阶段中,雨子的婚姻生活幸福而平静。叙事层《潜性逸事》“A重复错误”一节中书写了雨子和丈夫在婚姻生活中的温情,以及步入平淡但是互相依赖的心理状态。在次叙事层中,《空的窗》书写了老人对去世老伴的怀恋以及对自己存在意义的寻找,《嘴唇里的阳光》则书写着女性创伤的治愈,这两篇小说的内容基调是温馨而具有希望的。第二阶段呈现出雨子婚姻与友情的破裂过程。叙事层《潜性逸事》一章中“附件B隐耀之光”呈现出雨子在激情、爱情与婚姻之间的矛盾心理,“C同床时的想象”讲述着雨子在历史和现代之间的精神家园的游离,对忠贞和放荡的女性自我认知的探询。这些部分对应着次叙事层《时光与牢笼》《站在无人的风口》《梦回》《离异的人》《残痕》《碎音》几篇对于女性性别秩序的质疑。好友李眉带给雨子的伤害在《麦穗女与守寡人》中得到了突出呈现。《麦穗女与守寡人》中“我”所面临的失败的婚姻和另一场感情的破裂,对应着雨子婚姻与友情的破裂,而其中“我”试图保护英子对应着《潜性逸事》中雨子说要帮助李眉,英子对“我”的指认,对应着李眉对雨子的背叛。以《麦穗女与守寡人》为分界线,雨子由对性别伦理的质疑变成了对性别伦理的反叛,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变成了秩序之外的女性——已婚男性的婚外情人,呈现出雨子此时的复杂心理。相比从《空的窗》到《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的十二篇,《凡墙都是门》情节性减弱而议论性增强,不再突出呈现梦境叙述和非正常的精神状态,以现实笔触自白出自己离婚两年后创伤渐愈时期的心理状态。
由此可以看出,第一篇小說《潜性逸事》讲述了已婚女作家雨子的婚姻变故和友情破裂,而随后的十三篇短篇小说则是雨子写作的十三篇作品,其中呈现出雨子在不同时期的心境变化与性别思考。按照里蒙·凯南的定义,作品中的嵌套结构表现为“一个人物的行动是叙述的对象,可是这个人物也可以反过来叙述另一个故事。在他讲的故事里,当然还可以有另一个人物叙述另外一个故事,如此类推,以致无限。”[4]164《潜性逸事》中雨子的故事被超叙事层叙述者所讲述,构成了第一层叙事,而被雨子写作的十三篇短篇小说,则由叙事层的人物雨子所讲述,构成了次叙事层。叙事层和次叙事层共同服务于女性婚姻问题与精神建构的主题,发挥着“行动”“解释”及“为主题服务”的作用,[4]165-166。因此,《潜性逸事》由双层嵌套叙事构成,以雨子在婚姻破裂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为线索,呈现着婚姻早期、质疑婚姻和婚姻破裂三个时期的心理精神活动,两重叙事层的人物心理具有动态的互动作用,推动着对现代女性婚姻问题和性别伦理问题的深入思考。
二、内叙事层中的梦境表达:认同、质疑与反叛
(一)对婚恋的依赖与认同
雨子最初的形象是纯粹而富于激情的,雨子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去找寻爱情,在刚刚与丈夫结婚的时候,期待着丈夫能够给自己惊喜,在一下午的漫游中具有像恋人一样的幸福感觉,而晚上则会安安静静的与丈夫躺在床上,长时间进行平缓温柔的爱抚与含情脉脉的倾谈。在这样的幸福生活中,雨子内心具有女性的细腻与敏感,充满幸福与希望。与之对应的次叙述文本是《空的窗》和《嘴唇里的阳光》两篇小说。在这两篇小说中梦境书写较少且与现实界限分明,叙述人称灵活多变,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叙述,叙事距离调整灵活。由此可以推断,雨子在这一阶段冷静且理智地进行着写作,呈现出和谐的心理状态。但是《空的窗》也已经出现了关于要“离开”的构想,显露着雨子内心矛盾的萌芽。
《空的窗》呈现出极具浪漫主义风格的爱情幻想,对应着雨子早期追寻爱情的心理状态。在《空的窗》中,老人会花费一个上午为去世的老伴包饺子,因为害怕老伴收不到饺子而大哭。同时,文中饱含希望与力量,瞎女人看到“鲜艳夺目的用黑色勾勒的女人”[3]42,“疼痛的太阳从血红色的冰河里鲜活地跳跃出来,看金翅鱼和雪白的鸟儿以及浓荫招展地一株什么树在冰河背景里共同狂舞”[3]43,表现出女性形象的丰富和女性力量的张扬。其中的瞎女人虽然失去了双眼却并不悲哀,而是希望将故事带给更多的女性,呈现出充满力量的女性生命活力。在这一时期的叙述中,雨子对两性关系也具有心理上的依赖。在《嘴唇里的阳光》中,黛二在牙医的帮助下拔掉了心理的创伤,实际上也呈现出男性引导者帮助女性成长这一传统的两性关系。
(二)对性别伦理的质疑
在心理发展的第二阶段,雨子从结婚早年的幼稚逐渐变得成熟,从最初激烈而摇荡的夏季走向沉静、封闭的冬季,从滚热而变得冰冷[3]9,心理发生了巨大的蜕变。而这些变化之间却充满了空白,给次叙事层留下了大量的意义空间。《时光与牢笼》《站在无人的风口》《梦回》《残痕》《离异的人》《碎音》六篇小说构成了雨子第二阶段心理状态的次叙事层叙述。
在这一阶段中,雨子开始出现离婚的想法,这种背离秩序逃离婚姻的个人情感投射在了文本之中,其与现实秩序的违背性使雨子逃避现实而诉诸梦境,在梦境书写中发泄个人被压抑的愿望,进而一发不可收拾。《时光与牢笼》中第一次大规模地呈现出梦境书写,其梦境源于对现实的不满与无奈。《时光与牢笼》中说:“一个人什么都可以被剥夺,除了一件事:自由选择对待特定环境的态度。”[3]65然而,水水面对亲人去世、丈夫性无能与职场的压力时,却无法在现实中自由选择应对的方式,只能幻想夜空中飞翔的外婆,在梦中反抗着单位不合理的考勤制度。
从而,梦境成为传达个人经验的独特表述途径。《站在无人的风口》中,梦境成为连接不同时代女性心理的纽带,文中的十六岁少女“我”与尼姑庵老女人通过梦境而感同身受,这种梦境的共通,呈现的是具有共同心理结构的女性群体之间才能接续的心理状态,是女性得以逃脱男性话语、传达女性经验的独特方式。这种女性经验与话语难以通过语言直接传达,无法进入主流话语之中。当“我”书写女性历史时,“我”的两个男性密友一反往日的互相敌视,一起动手撕毁了“我”写下的历史,“只留下尼姑庵前院的那个老女人伫立窗前的一段在我手里。”在男性中心文化的历史之中,对女性的历史书写“更注重强制的结果而非强制的过程。他们仿佛是先写出女性的被杀被吃,然后再‘杀死’使其然的环境,犹如先找到女性的尸首,然后再寻找凶犯主谋,但绝不写女性与凶手的搏斗。他们找到并审判了凶手,这是他们的功绩,但整个搏斗真相却相当完整地留在了历史的深处,留在意识层面之下的阴影中。”[5]9
《残痕》更进一步地剖析了社会权力机制,揭露了婚姻现实中的性别伦理陷阱。《残痕》中的主人公“我”在一次疾病中失去了左腿,然而我的左腿却又痛了起来,丈夫明明在《西医外科与行为艺术》一书中找到我左腿疼痛的合理性,却有意否定了我左腿的疼痛,压制我的痛苦。《残痕》中说,“人的两条腿就像是白天和黑夜、现实与梦想、今天与明天的微妙组合一样,交替而行,相依而存。”[3]131左腿与右腿象征着“我”的梦想与现实,“我”在刚遇到丈夫时还处于梦想和现实的和谐状态,后来我在“人为麻醉”之下放弃了左腿,手术签字者则是我的丈夫。“人为麻醉”可以理解为社会对于女性的意识结构化,女性在这种社会要求中麻痹了自我,而丈夫不抛弃残缺的妻子则成了妻子的幸福和丈夫的美德,这个温暖的家庭正是一个悄无声息的陷阱。《残痕》中女性看似荒诞的创伤言说,微妙地揭示了女性的失语状态,其讲述的对象不是具象行为,而是抽象秩序的运行。从《梦回》到《残痕》,动态地呈现出雨子对家庭关系中性别伦理的深入质疑,集中表现出婚姻对于女性梦想的盘剥。
在此阶段的书写中,叙事人称越来越集中于第一人称“我”,甚至《站在无人的风口》一篇中尼姑庵老女人的梦境也是通过十六岁少女“我”的梦境加以重现的。此阶段书写的另一特征是梦境痕迹的加重,梦境与现实的边界相较于上一阶段越来越模糊。性别伦理的阴霾与婚姻生活的裂痕逐渐占据雨子的心理,面对无法直言的创痛,雨子借助梦境传达出感觉的真实。
(三)对社会象征性秩序的反叛
女性本真的自我被社会秩序驱逐与拒绝,男性性别秩序则呈现出虚假与伪善,在此之下,叙述者开始正面挑战男性社会秩序和性别伦理。男性社会秩序规定着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性别伦理规定着女性的辅助地位和贞洁观,女性要从一而终,同时要遵守女性性别伦理要求[6]4-6。《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和《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中的女性则对传统女性性别伦理规约发出挑战,其中的女性形象转为婚姻的第三者。这种“非道德化的故事”暗含着“对伦理化的主流话语的颠覆,至少是震动。”[7]48婚恋第三者是对社会秩序、性别伦理的反叛,同时也是对女性同盟的决裂,这一第三者形象,正突出体现了雨子自我意識的觉醒和对性别秩序的挑战。
雨子的婚姻裂痕一定程度上是由女性友人李眉的介入而呈现的,婚姻的裂痕伴随友情的破裂,将雨子推入爱情与友情双重幻灭的孤独境地。雨子和李眉之间形成的“亲密之险”[3]26呈现出婚姻之中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性亲密关系与异性情感吸引同时存在并且不可替代,友情与婚恋关系中的排他性叠加在一起,就会产生亲密关系中难以避免的亲密之险。在心理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雨子陷入这种矛盾关系之中。次叙事层《巫女与他的梦中之门》《麦穗女与守寡人》《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凡墙都是门》五篇呼应着这一阶段雨子复杂的情感和对诸多关系的思考。
此阶段的次叙事层蕴含着对父系社会之下两性关系的绝望。《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罕见地呈现了女主人公对父亲的依恋,然而这一依恋却屡遭挫折。在父亲的伤害下,文中的十六岁少女借助满足“像父亲一般的男人”的欲望而实现自虐,其中的梦境书写处于“我”的自虐达成时刻。在梦境中,父亲般苍老的男人在吃力地攀爬高耸而雪白的图书馆,对应现实层面,“雪白”是女主人公童年家庭的颜色,而“图书馆”则是“像父亲一般的男子”对“我”的子宫的形容,“雪白的图书馆”是被物化的女性主人公,攀爬图书馆则呈现着男性对女性的征服。当“我”想要作为“人”,以平等的地位,把手轻柔地放在男人的额头上时,那个男人却变成了木乃伊,呈现出“我”被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性所拒绝而带来的创伤。在梦境的第二幕,雄性的年轻笨驴在图书馆下的绿草坪上乱转圈,绿警察到场维持秩序,然而围观者也都变成绿驴加入乱转圈的驴群。文中的十六岁少女被父亲从家中驱逐,被安置到了浓绿色的尼姑庵,绿驴则对应着尼姑庵中“像父亲一般的男子”对我的亲近与追求,绿色的警察则象征着男性秩序力量,然而秩序并没有被维护,不受管束的“绿驴”、绿色的警察乃至不断加入的围观者形成了互相矛盾的男性群体,男性对性别秩序的打破与男性表面上对秩序的维护构成了一出讽刺意味十足的闹剧。
在现实、幻想与梦境难以分辨的状态下,文本中呈现出心理的病态。在文学中,疾病常常被用来象征一个人与其周围世界的特殊关系。[8]35《麦穗女与守寡人》以不可靠叙事呈现出“我”迫害妄想和敌友难分的精神状态,在法庭上,“我”被好友英子指控为诱拐者和行凶者,而“我”的辩护律师则称我为一个“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3]191。这种疾病隐喻呈现出现代性的反讽意味,通过具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我”的视角,展示出现实社会秩序之下对女性的迫害与诱拐。然而,被男性中心文化所塑造的“正常”女性无法意识到这些病症,作为觉醒者的“我”则成为具有“边缘人格”的“狂人”。
从第二篇《空的窗》到第十三篇《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中,梦境书写逐渐增多,梦境与现实界限混淆的程度不断加深。在这些叙事手法之下,故事色彩逐渐昏暗,情感由乐观变为绝望。双层嵌套叙事使现代女性雨子在婚恋变故中的动态心理得以纵深呈现,次叙事层的梦境建构再现出社会秩序运行机制下女性的心理斗争,使情节除了通过文中人物推动之外,具有更深层、更客观现实的内在叙述动力。在梦境所具有的个个性特征之上,文本同时具有社会现实性和普遍性。
三、结语
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从宏大叙事主导文学创作的“共名”[9]358时代走向了创作多元化,个人化叙事取代了时代的宏大叙事。90年代文坛极具代表性的是以韩冬、朱文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创作的极具个人化风格的小说,这些小说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诗歌领域的反社会文化、倾向日常的特点,在这种开放多元的文化空间中,陈染、林白笔下极具个人剖白与心理书写的女性文学创作也应运而生。
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指出,“你在‘五四’女作家的创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困窘:女性的经验要求被本文化,而一旦它们进入本文,又消失于本文中”[5]22。女性的自身经验和男性中心文化之下的话语模式之间呈现出游离于冲突,使女性经验表达往往被男性话语覆盖。而《潜性逸事》通过多层次心理空间,打破既定的社会话语符号内容,以梦境这一高度感性又极具隐喻性的载体传递着无法言说的女性经验,对婚姻、社会以及性别伦理问题做出深刻洞察。其通过梦境来自我伪装,逃避社会权力机制对女性声音的压制和扼杀,使其女性声音得以打破沉寂,呈现出对女性性别秩序、婚姻秩序从相信、质疑到反抗乃至走入孤独困境中的女性心理,对社会制度发出巧妙而有力的叩问。并且,《潜性逸事》梦境叙事并非单纯的梦境描绘,而是对自我意识的解码和再编码的过程,“与其说她的作品充满了丰富的潜意识流露,是某种梦或白日梦,不如说那时相当清醒而理智的释梦行为与自我剖析。”[7]50其通过梦境建构出一个个自我镜像,在双重嵌套结构之下,《潜性逸事》的梦境书写复现出雨子凝视自我、确认自我和疗愈自我的过程,使整部小说集结构为一个立体而动态变化的心理空间。
参考文献:
[1]陈染.沉默的左乳[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9.
[2]承梦姣.论陈染小说的梦境书写[D].扬州大学,2015.
[3]陈染.潜性逸事[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9.
[4]施洛米斯·雷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M].赖干坚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8.
[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
[6]张子恒.性别伦理的价值取向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0.
[7]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J].当代作家评论,1996,(03):47-56.
[8]谭光辉.症状的症状[D].四川大学,2006.
[9]陈思和.新文学整体观 陈思和文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1.
[10](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刘徽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6.
作者简介:
李怡凡,湖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