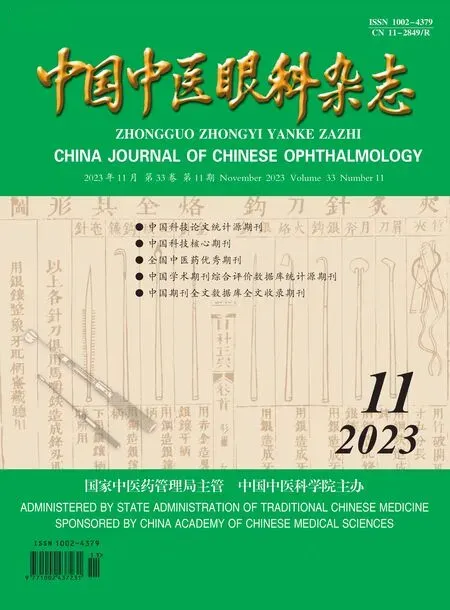基于伏邪理论论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刘思言,严京,芦伟,那爽,高明雪,马若楠,吴正正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DR)是一种与持续高血糖及其他与糖尿病相关的慢性、进行性、潜在危害视力的视网膜微血管疾病[1]。中医药对于DR的防治有着不容轻视的作用,在控制病情进展、减少病情反复、保护视力等方面发挥很好的疗效。本文将探讨伏邪理论与DR病因病机、发病过程之间的相关性,同时将透法治疗伏气温病的治疗思路与本团队治疗DR的用药经验相结合,为DR的治疗提供新的理论思路。
1 伏邪理论概述
1.1 伏邪理论溯源
伏邪,又称伏气,指藏于体内而不立即发病的病邪[2]。伏邪概念最初见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3]云:“是以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屡厥。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可见初期仅将伏邪理论运用于外感病,局限于伏气温病的范畴。此后各代医家对于伏邪理论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应用于内伤杂病的病机分析之中。至清代,王燕昌《王氏医存》[4]曰:“伏匿诸病,六淫、诸郁、饮食、瘀血、结痰、积气、蓄水、诸虫皆有之”,可见无论病邪外感或是内生,只要满足潜伏、隐匿、逾期发作等特点,均可归于伏邪一类,此时的伏邪理论已大致完善。
1.2 伏邪致病特征
伏邪的致病特征可大致概括如下,(1)隐匿性:伏邪之伏即为潜匿、隐藏之意,伏邪致病的基本特点为隐匿体内、隐而不发、逾期发作,故隐匿性为伏邪发病的基本特征。(2)动态性:伏邪的致病过程具有时间及空间上的动态性。时间动态即病程前期的隐匿性与伏邪发病的爆发性。邪伏体内自我积累,由弱变强,机体正邪失去平衡,正邪相搏,斗争剧烈,疾病发作迅猛,呈爆发性,与前期的隐匿发病呈时间上的动态改变。空间动态即伏邪不同阶段的病位变化。邪气侵袭人体之时为由浅入深的病位变化;伏邪外发之时为由深出浅的病位改变。邪伏体内的潜证阶段,也可趋于脏腑经络虚弱之处。故伏邪的发病过程中病位并不固定,呈空间上的动态改变。(3)反复难愈:伏邪多伏于机体深处,若药物未达病位,或未用适当治法导邪外出,伏邪未尽,病情反复难愈;或邪伏于脏腑经络虚弱之处,《黄帝内经·素问·评热病论》[3]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如此恶性循环,正气虚弱无以抗邪,致病情反复,迁延难愈。
1.3 伏邪与伏毒的关系
毒的概念最初见于《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3]中的“苛毒”一词,《金匮要略心典》[5]云:“毒者,邪气蕴蓄不解之谓。”可见毒为邪盛所生、邪聚所衍,可以反映邪气深浅与病情急缓。外感伏毒的概念最初见于《伤寒直指》[6]载:“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国医大师周仲瑛[7]基于“伏邪”与“苛毒”理论,认为毒邪既可外受,又可内生,进而提出内生“伏毒”的立论。内生伏毒往往由伏匿机体的多种病理产物,如水、湿、痰、瘀、热等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积微成著,久酿而成,临床症状多样复杂。伏毒的致病特点相似于伏邪,且致病更加复杂、广泛、剧烈,伏邪致病可使机体功能失调,伏毒致病则会使机体产生相应的实质性损害。由此可见,伏邪为伏毒发生的基础,伏毒为伏邪发病的演变,伏毒概念应归属于伏邪理论范畴。
2 从伏邪理论分析DR
DR为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而中医学认为络脉与微血管具有相似性,主要体现为运行血液与物质交换,故可认为DR发病部位为目络。《黄帝内经·素问·气穴论》[3]曰:“孙络三百六十五穴会,以应一岁,以溢奇邪,以通荣卫”,《黄帝内经·灵枢·经脉》[8]言:“饮酒者,卫气先行于皮肤,先充络脉,络脉先盛,故卫气已平,营气乃满,而经脉大盛。” 可见络脉具有贯通营卫、渗灌气血之功,多血多精则易发郁滞。然目络本身狭小纤细,与其他脉络相比更易发生精微物质的运行及输布不畅,进而聚积伏毒。
糖毒是消渴病特有的发病基础及病理产物,初为糖邪,聚为糖毒,生于脉络,伏于脉络,为消渴病病因的新兴概念。狭义的糖毒为精微物质运行、输布不畅而聚伏于脉络,致血糖升高;广义糖毒则为血糖升高所衍生的其他病理毒邪,如瘀毒、痰毒、水毒、湿毒、热毒等[9]。《黄帝内经灵枢集注》[8]云:“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可见脏腑亏虚为消渴发病的前提。因脏腑虚弱,正气不足,气、血、津液无力运行,脉络中糖分等精微物质无法随血液运行、营养脏腑经络,阻于脉络,久聚为邪,久积成毒,引发消渴。糖毒一旦形成,伏于脉络,络中气、血、津液运行受阻,日久致亏;又可逐渐损及脏腑经络,引发消渴并发症。如此恶性循环,脏腑经络愈加亏虚,产生新毒,导致病情迁延难愈。由此可见,糖毒既是引发消渴的致病因素,又是消渴的病理产物。DR为消渴病并发目络之症,故本病亦由糖毒所发。DR前期糖毒尚弱伏匿目络,故发病隐匿,无明显临床表现。随着病情进展,糖毒自我积累,至增殖期呈爆发性发病,表现为络损、血行于外。糖毒阻络,气、血、津液运行不畅[10],所生之水毒聚于黄斑发为黄斑水肿;所生之瘀毒阻闭目络而致败络丛生,发为玻璃体积血,此类病症皆为极易反复、迁延难愈之症[11]。由此可见,DR的发病过程呈隐匿性、动态性、反复难愈,符合伏邪致病的特点。故认为糖毒是导致DR发生的内生伏邪。糖毒伏络的隐匿性也类似于现代医学[12]的“代谢记忆”理论,即人体长时间处于高血糖状态之下,会造成“代谢记忆”。即使后期血糖控制稳定,血管细胞仍能记忆高血糖阶段的细胞通路及高血糖环境,故糖尿病相关的血管并发症在血糖平稳时期仍可发展。
从DR发病过程来看,疾病前期,目络中伏毒尚弱,络壁屈曲,临床表现为微血管瘤形成;伏毒积聚,瘀毒、痰毒附于脉壁,致轻微络损,血、痰溢于脉外,临床表现为点状出血及硬性渗出的发生;瘀毒再聚,目络闭阻之势,血行不畅,新血不生,视衣失去络脉濡养,临床表现为棉絮斑的形成。根据DR分期标准,上述病理改变为DR的非增殖期病变及增殖前期,此阶段仅出现视力缓慢下降的临床表现,并未引起患者足够重视,体现了伏邪致病的隐匿性。由于DR非增殖期尚属伏邪致病的前证阶段,于此阶段行干预治疗可减缓疾病向增殖期的发展。待糖毒伏络日久,水毒渗入视衣,或痰瘀互结,目络闭阻,败络丛生,病络络壁不固,血行络外,临床表现为黄斑水肿、新生血管生成、玻璃体积血,患者往往出现视力骤降。可见本病的发病过程呈动态性,伏毒不断自我积累,从DR非增殖期的隐匿发作至增殖期发病的来势迅猛是一种伏邪由量到质的转变,符合伏邪动态性的致病特征。
综上所述,DR主因脏腑经络亏虚,糖毒内生,伏于目络所致。目络为本病的发病部位,正虚邪盛为发病机制,糖毒为本病之内生伏邪、发病基础,并衍生水毒、痰毒、瘀毒、热毒,进而导致视衣发生一系列病理改变。
3 伏邪致病可用透法
《蠢子医》[13]言:“治病透字最为先,不得透字总不沾,在表宜透发,在里宜透穿。”张锡纯[14]治疗伏气温病擅用透法以透邪外出,因势利导。现探讨如下,(1)表里俱热—宣透法:张氏多以“最善通窍”之薄荷及“以皮达皮”之蝉蜕宣散伏热,并以石膏清解里热佐之,顺应伏邪外发之势透邪达表;(2)阳明里热—清透法:张氏评价白虎汤中君药石膏的退热之功为“逐热外出”,故白虎汤既可清阳明里热,又具解肌透热之功,其立法体现寓清于透,寓透于清之治疗特色;(3)正虚里热—补透法:张氏认为对于正气素虚兼有内热之人,可以人参补益之力防邪入里、托邪外出。并认为人参与石膏同用,可达“以搜剔深入之外邪使之净尽无遗”之效。《医学衷中参西录》[14]曾记录一则因伏气化热所致目胀痛甚,胬肉遮睛之医案,张氏予宣透之法:生石膏细末,开水送下,令多喝开水至微见汗而愈。其中石膏寒可驱逐伏热,辛可驱散邪气;多饮开水可助石膏因势利导、宣透表里之热化汗出表。此案可见张氏透邪外出、因势利导用药之妙。
4 透法在DR中的应用
DR为糖毒内生,衍生痰瘀湿毒,久伏目络所致病。目络纤细狭小,药难达所,故易留邪,反复发作。临床多用轻清上扬、辛散启闭类药物,既可引诸药上行目窍,又可透邪达表,给邪以出路,可达事半功倍之效。用药时机宜在伏邪未伤及络脉之时,从内清解糖毒而透邪于外,清解糖毒之法包括清热降糖、通络散瘀及利水化痰。由于DR发病前期,糖毒衍生出瘀、水、痰等大量有形实邪,故本病前期治法多以消法为主。尤在泾[5]言:“无形之邪,入结于脏,必有所据”,热毒本为无形之邪,久居体内须附于有形邪毒,非用攻法不去,然恐消渴患者体质亏虚不耐重药,此时运用上述清解糖毒之法分消诸毒,使诸邪势孤无所依,再加以辛散、芳香、轻清之药因势利导,使膜开邪散,邪去正安。同时要考虑到DR患者久病气、血、津液不足,脏腑虚弱,虚实夹杂,病情复杂,不可单用逐邪、透邪之法。“扶正不留邪,祛邪不伤正”,故应配合补益药物辅助正气,使正气盛而助药物透邪达外。中医眼科学者[15]大多认为,DR患者正气素虚,发病过程中的证型变化为阴虚燥热—气阴两虚—阴阳两虚。但本团队认为DR的3个阶段证型分别对应着伏邪体系的潜证、前证、显证阶段。因此,消渴患者前期多用滋阴补气之法,后期可酌加温阳药物。
4.1 NPDR—消透法
非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non-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NPDR)临床表现为视力缓慢下降,视网膜可见微血管瘤、出血、硬性渗出、棉絮斑、静脉串珠、微血管异常等异常改变。NPDR为整个病程的前证阶段,也是干预治疗的极佳时期。NPDR主以糖毒及其衍生的水、痰、瘀毒等有形实邪伏于目络,证属痰瘀互结,气阴两虚。有形实邪宜用消法以渐消缓散,配合透法透散诸邪。故本阶段以消透法为主要治法。其中水毒亢盛者,多见于黄斑水肿,可应用桂枝、丝瓜络、车前子利水消肿,温阳化气;痰毒亢盛者,眼底表现为硬性渗出、棉絮斑,可用海藻、昆布、浙贝母清热化痰,软坚散结;瘀毒亢盛者,视网膜可见微血管瘤、出血,可投牡丹皮、丹参、三七化瘀止血凉血;并辅以密蒙花、柴胡、肉桂类轻清上扬或辛散达表之品既可透毒外出,又有消解糖毒之功。
高健生团队[16-19]善用密蒙花方治疗NPDR,密蒙花方组成为黄芪、女贞子、乌梅、益母草、肉桂、黄连、密蒙花。方中黄芪补气托毒,利水消肿为君药;臣药乌梅性酸,生津止渴;君臣相合,善治消渴,又共司补益气阴以扶正透邪。黄连、肉桂合为交泰,其中重用黄连清热,热毒与痰瘀湿毒分消,使热无所依,合肉桂辛窜启闭、鼓舞阳气以透热外出,二药合用可助君臣共消糖毒;益母草性味辛苦,善散脉络之瘀,又辅黄芪利水消肿;密蒙花轻清上扬,可引诸药上至目络,又合肉桂、益母草两味辛药由里达外、由深出浅,使诸上已散之伏邪有外达之机。经过大量实验及临床应用[16-18]证实,本方可延缓DR由气阴两虚(前证阶段)向阴阳两虚(显证阶段)的转化,有效改善视功能。
4.2 PDR术后—补透法
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PDR)临床表现多为视力明显下降,眼底可见新生血管生成、玻璃体积血、纤维增殖及并发牵拉性视网膜脱离等异常改变。疾病进展至PDR且满足手术指征者,多应用玻璃体切割术以清除玻璃体积血,复位视网膜。PDR为整个病程的后期显证阶段,DR进展至阴阳两虚。同时患者术后正气亏虚、目络受损,络中所伏糖毒及衍生的水毒、热毒、瘀毒易乘虚发作,发为黄斑水肿、玻璃体积血等术后并发症。结合PDR病情变化,总结本阶段证属阴阳两虚,水瘀热互结。本阶段以正气亏虚为主,又有余毒未清,宜用补法以补益正气、托毒外出,配合应用透法透散余毒,预防病情复发,故本阶段以补透法为主要治法。其中术后气血亏虚者可施黄芪、当归恢复正气;阴虚血热者多用生地黄、赤芍滋阴凉血;阳气亏虚者多以附子、桂枝温补阳气;同时川芎、荆芥、防风类药物起到补而不滞、透散余毒作用,应用于术后又有化瘀、止痛之功。
吴正正[20]善用玻切方治疗PDR玻璃体切割术后患者,玻切方组成为生地黄、赤芍、当归、藁本、防风、前胡、黄芪、白术、茯苓、车前子、桂枝、侧柏叶、墨旱莲;其中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为君,赤芍凉血祛瘀为臣,君臣合用加强清热凉血之力,清解络中伏热,以避免血热妄行而致眼底反复出血;当归消瘀毒、养新血,桂枝温通经脉,黄芪、白术补气健脾,黄芪、当归合用善治消渴,四药合生地黄滋阴温阳、益气养血祛瘀,使正气恢复得以扶正托毒;茯苓利水健脾,车前子利水渗湿,清肝明目,二药合桂枝共司通利水毒,预防并发黄斑水肿;侧柏叶、墨旱莲凉血止血,二药助君臣清解络中热毒;防风、藁本、前胡、桂枝性辛散,四药疏通表里,共助目络余毒达表而透,避免伏毒未清,病情反复。
5 小结
基于伏邪理论认为糖毒为DR的内生伏邪、发病基础,目络为本病的发病部位。结合“伏邪致病可用透法”的治疗思路,总结为NPDR阶段运用消透法,PDR阶段术后运用补透法消解目络伏毒,有着透邪外出、因势利导、扶正托毒之妙,临床应用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本文从新的角度分析探讨DR的病因病机、病情发展及治疗方式,为DR的病因病机及治疗丰富了新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