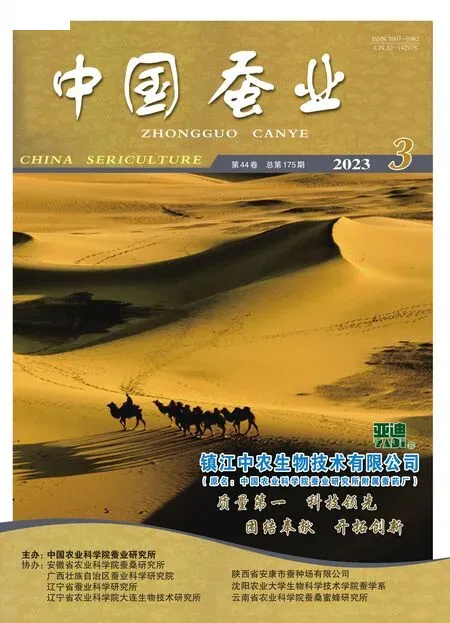新型蚕桑经营主体发展现状与演进规律
梁 巧 杨奕宸 李建琴
(1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杭州 310058; 2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
蚕桑产业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产业,中国是世界茧丝绸生产、加工与贸易第一大国,茧、丝产量占全球的75%[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蚕桑产业获得了长足稳定的发展,桑园面积、发种量、蚕茧产量等均稳步增长。传统蚕桑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产业[2],且主要分布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蚕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特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蚕桑产业规模在先扩张后波动中趋于稳定,生产空间布局不断变迁。2000年以来,蚕桑生产除2008—2009年经历一次较大下跌外,总体比较稳定,全国桑园面积稳定在80万hm2左右。发种量和蚕茧产量则在经历多次波动后持续提高,自2016年以来持续缓慢增长,2021年发种量达1 724.43万盒,蚕茧产量达71.72万t。蚕桑生产水平持续提升,盒种蚕茧产量和效益不断提高,2021年我国桑蚕茧产值达367.15亿元,比2020年增加52.99%,创历史新高[3]。蚕桑生产空间布局持续变迁,自从2003年中西部蚕区蚕茧产量超过东部后,产业转移的进程开始加快,在蚕桑主产省(市、区)形成东部蚕区(指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4省)蚕桑生产缩减、中部蚕区(指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6省)基本稳定、西部蚕区[指广西、四川、重庆、云南、陕西5省(市、区)]规模扩展的“东桑西移”格局[4],近年来向西部地区转移和集中的趋势愈加明显。
然而,我国传统蚕桑产业仍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困境,蚕桑产业经营主体以小农户为主,蚕桑生产依然是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生产技术进步比较缓慢,规模效益比较低。同时,蚕桑生产面临着多样风险,包括自然灾害、蚕病风险和茧价波动的市场风险等[5],这些风险的根源也与蚕桑产业的技术特征和市场特征等相关。然而,小农户的技术和资金有限,再加上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受教育水平低等问题,更是加剧了小农户在蚕桑生产经营上的困境,小农户自身无法实现技术创新和风险缓解。因此,蚕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只能依赖于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小农户联合的组织载体或与小农户开展业务合作,在带动小农户开展生产和进入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截至2020年底,全国家庭农场超过380万家[7],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225万家[8],农业相关企业超279万家[9]。与其他农业产业相比,蚕桑产业的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相对不足,尤其自2006年开始实施“东桑西移”工程后,西部地区蚕桑产业发展迅速提升,但目前仍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组织化程度较低[10-11]。因此,需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在蚕桑规模经营和效率提升、技术指导和服务体系、市场导向和缓减风险等方面的作用,并稳定和蚕农的长效利益联结,从而提高农户收益和产业绩效[12-13]。
基于此,本文系统性梳理新型蚕桑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分析蚕桑家庭农场、蚕桑合作社、蚕桑种养企业3类蚕桑经营主体的演进特征和发展趋势,并讨论新型蚕桑经营主体助推蚕业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1 新型蚕桑经营主体总体发展情况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简称“CCAD”),该数据库包括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基本信息(包括工商登记时间、地理信息、行业类别、经营范围、股东信息等)和年报信息(包括经营绩效、股份变动等)等数据。在CCAD数据库中筛选出行业类别为农业或纺织业,且经营范围包含蚕桑种养的各类经营主体,最终发现蚕桑家庭农场数据始于2013年,蚕桑合作社数据始于2007年,蚕桑种养企业数据始于1980年,从而得到家庭农场(2013—2021年)、农民合作社(2007—2021年)、农业企业(1980—2021年)共8 959家新型蚕桑经营主体的数据库。后续分析中,考虑时间跨度的一致性,使用2013—2021年家庭农场、蚕桑合作社、蚕桑种养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
2013—2021年,我国新型蚕桑经营主体累计注册8 128家,其中蚕桑家庭农场1 523家、蚕桑合作社3 677家、蚕桑种养企业2 928家(表1)。减去2013—2021年间已注销的1 452家主体后,截至2021年年底,在营的蚕桑经营主体总数为6 676家,其中蚕桑家庭农场1 343家、蚕桑合作社2 965家、蚕桑种养企业2 368家。

表1 新型蚕桑经营主体注册总数与在营数量 家
从2013—2021年历年变化来看,蚕桑各类型经营主体在营数量均呈增长态势,但增长速度和规律有所不同,家庭农场在营数量增速先降后升,合作社在营数量增速波动下降,蚕桑种养企业在营数量增速波动呈W型。
与其他农业产业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比,蚕桑家庭农场数量增长率稍高于其他产业家庭农场的平均增长率,而蚕桑合作社和蚕桑种养企业的数量增长率先落后于其他产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平均增长率,但近年来实现了追赶和反超(图1至图4)。由此,全部新型蚕桑经营主体的增速在2013—2016年和2019年低于其他产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平均增速,而2017—2018年和2020—2021年高于其他产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平均增速。

图1 2013—2021年全国农业产业和蚕桑产业的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增长情况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正式提出发展家庭农场,当年家庭农场注册非常有限,因此以2014年作为计算增长率的初始年份。

图3 2013—2021年全国农业产业和蚕桑产业的合作社数量增长情况

图4 2013—2021年全国农业产业和蚕桑产业的企业数量增长情况
2 新型蚕桑经营主体发展分类情况
2.1 蚕桑家庭农场
2013—2021年全国共注册蚕桑家庭农场1 523家,去除因经营不善等原因注销的农场,到2021年仍处于在营状态的蚕桑家庭农场有1 343家。从图5来看,2013—2020年蚕桑家庭农场每年注册数量和注销数量都比较稳定,除了2013年,每年注册数量基本保持在100~200家,大大高于每年10家左右的注销数量,因而在营蚕桑家庭农场数量从2013年的21家持续增长至2020年的905家。2021年,蚕桑家庭农场的注册和注销数量均大幅增加,当年新注册数量达555家、注销数量117家,在营蚕桑家庭农场数量增加至1 343家。

图5 2013—2021年全国蚕桑家庭农场数量变化
我们选取2013年和2021年2个时间节点,观察各省(市、区)家庭农场数量的变化,结果如图6所示。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发展家庭农场以来,蚕桑家庭农场迅速发展,各地新注册蚕桑家庭农场数量逐渐增多,尤其是西部蚕区和中部蚕区,这与产业发展趋势和当地资源禀赋有关。2021年各省(市、区)蚕桑家庭农场数量有所增长且地区间差异较大,其中在营数量最多的为安徽,有281家,这可能与2020年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大力推进蚕桑产业提质增效,强调着力培育专业化养蚕的家庭农场有关[14];其次为四川,有267家在营;重庆、广西和江苏也有超过100家的蚕桑家庭农场在营。2021年在营数量最少的省(区)为新疆和河北,均只有1家蚕桑家庭农场在营,黑龙江和内蒙古则各有2家蚕桑家庭农场在营。

北京、天津、上海、西藏、青海等5个省(市、区)未曾成立过蚕桑家庭农场,讨论中不包含这些省(市、区)。
2.2 蚕桑合作社
自2007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来,蚕桑合作社数量逐年稳定增长。从图7的全国蚕桑合作社数量变化来看,2013—2021年间每年均有一定数量的蚕桑合作社新成立,其中2018年新注册的蚕桑合作社数量最多,达394家。同时,每年也有少量蚕桑合作社注销,尤其是2019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社”专项清理工作方案》后,注销的蚕桑合作社数量明显增多。截至2021年,全国共成立过蚕桑合作社2 511家,除天津、上海、青海、西藏外,其余27个省(市、区)都成立过蚕桑合作社,去除注销蚕桑合作社后,在营蚕桑合作社为2 965家。

图7 2013—2021年全国蚕桑合作社数量变化
选取2013年和2021年2个时间节点,观测各省(市、区)蚕桑合作社数量的变化,不同地区呈现出了差异性发展特点,如图8所示。2013年东部和西部蚕区核心省(市、区)的蚕桑合作社数量旗鼓相当,其中江苏和四川的蚕桑合作社数量显著高于其他省(市、区),北京和宁夏最少,各仅有1家。之后,西部蚕区各省(市、区)蚕桑合作社发展劲头加快,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21年广西在营蚕桑合作社数量最多,达752家,四川、云南和贵州紧随其后。东部蚕区部分省(市、区)的蚕桑合作社数量则呈现减少的趋势,并逐渐退出在营数量的前列,如江苏的蚕桑合作社注销数量较多,其在营数量从2013年的166家减少到2021年的57家。2021年在营数量最少的为宁夏4家、北京5家。

图8 2013年和2021年各省(市、区)蚕桑合作社在营数量
2.3 蚕桑种养企业
从2013—2021年新注册、注销和在营的蚕桑种养企业数量来看(图9),在营蚕桑种养企业数量稳定增长,特别是近年来增速较快。2013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积极作用于我国蚕丝业的转型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蚕桑种养企业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每年均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新注册成立。截至2021年,全国蚕桑种养企业注册数达2 928家,去除注销的企业,在营的蚕桑种养企业有2 368家,其中被认定为龙头企业的有11家,包括2家国家级和5家省级龙头企业。

图9 2013—2021年全国蚕桑种养企业数量变化
2013和2021年各省(市、区)蚕桑种养企业的在营数量实现大幅度的提升,且在地区间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图10)。总体来看,蚕桑种养企业向中西部蚕区集中,且中西部蚕区内部各省(市、区)趋于均衡发展,东部蚕区则趋于衰落。具体来看中西部蚕区的扩张,广西的蚕桑种养企业从2013年的94家增长至2021年的383家,2021年在营数量位列全国第1;安徽的蚕桑种养企业从2013年的22家增长至2021年的366家,2021年在营数量位列全国第2。2021年除上海没有在营蚕桑种养企业外,天津在营蚕桑种养企业最少为1家,青海在营蚕桑种养企业为2家。

图10 2013年和2021年各省(市、区)蚕桑种养企业在营数量
3 蚕桑生产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
3.1 全国蚕桑生产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
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产业的生产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其中生产规模化主要指家庭农场通过土地集中连片化经营和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的经营模式;组织化指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通过组织制度创新,辐射带动周边小农户、与其达成利益联结,以有效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的经营模式[15-16]。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与从业人数或产出水平相关,往往用农户数或产值(或产量)对主体数量进行标准化,以刻画生产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17-18]。受数据限制,本文用各类新型蚕桑经营主体数量和蚕茧产值(包括桑蚕和柞蚕的蚕茧总产值)的比值以刻画蚕桑产业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具体来说,用“在营家庭农场数量(家)/蚕茧产值(亿元)”表示蚕桑生产规模化水平,用“在营合作社数量(家)/蚕茧产值(亿元)”和“在营农业企业数量(家)/蚕茧产值(亿元)”表示蚕茧生产的组织化水平。
2013—2021年我国蚕桑生产的规模化和组织化均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且近年来增速加快,显示了蚕桑产业的规模化和组织化发展状态良好,但仍明显低于所有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图11)。2021年每亿元蚕茧产值约对应3家家庭农场、7家合作社、6家种养企业;相应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19]计算得出,所有农业产业每亿元产值约对应17家家庭农场、28家合作社、52家农业企业。蚕桑经营主体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偏低,与蚕桑产业本身的劳动和土地密集型特性、机械化和智能化程度较低有关。

2013—2015年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版、2014年版和2015年版《中国丝绸年鉴》,2016—2021年的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表2同。
3.2 蚕桑主产省(区)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
根据2021年蚕茧产值由高到低排列,前10位主产省(区)依次为广西、四川、云南、辽宁、江苏、广东、黑龙江、浙江、安徽和山东。从以每亿元蚕茧产值的蚕桑家庭农场表示的规模化水平历年变化来看,各省(区)近年来的规模化水平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尤以安徽的规模化水平提升幅度最大(表2)。2020—2021年部分省(区)的蚕桑生产可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蚕桑家庭农场数量减少,规模化水平有所下降。

表2 2013—2021年十大主产省(区)每亿元蚕茧产值对应的家庭农场数量 家/亿元
省(区)间比较来看,各省(区)历年位次排列基本稳定,安徽、江苏、四川和山东的规模化水平一直领先于其他省(区),其中安徽的蚕桑生产规模化水平甚至高于农业产业平均规模化水平,可能与其蚕茧产值不高但具有相当数量的经营主体有关。柞蚕主产区辽宁和黑龙江生产的规模化水平明显低于其他桑蚕主产区的水平,可能与柞蚕多以野外放养为主、难以形成规模有关。规模化水平不仅由土地和劳动资源禀赋所决定,也与当地政府对家庭农场发展的引导和支持有关,如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在2020年强调着力培育专业化养蚕的家庭农场。值得一提的是,广西的蚕茧产量自2005年以来一直位居全国第1,2021年广西蚕茧产量占全国的50%以上,但是广西蚕桑家庭农场并不多,广西蚕桑生产的规模化经营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以每亿元蚕茧产值的蚕桑合作社和蚕桑种养企业数量所计算的蚕桑生产组织化水平分别如表3、表4所示。

表3 2013—2021年十大蚕桑主产省(区)每亿元蚕茧产值对应的农民合作社数量 家/亿元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2种计算方式所表示的组织化水平呈现了相同趋势和特点。大部分主产省(区)的组织化水平呈现提升态势,但四川和江苏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近年来随着政府部门对合作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调和引导,部分省(区)的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数量有所减少,导致组织化水平有所下降。省(区)间比较来看,各省(区)位次排列保持相对稳定。蚕桑生产组织化水平较高的省(区)为安徽、山东、广东和四川,但仍大大低于农业产业平均组织化水平。广西、辽宁和黑龙江的组织化水平最低,其中北方蚕区的辽宁和黑龙江以柞蚕生产为主,组织化水平难以提升,历年增长也较为缓慢;广西的组织化水平也较低,仍以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为主,相对于其蚕茧产量全国第1的地位,组织化水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和潜力。
4 结论和启示
本文基于历年不同省(市、区)新型蚕桑经营主体注册和在营数量的数据,梳理了我国新型蚕桑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和演进规律,分析了蚕桑产业家庭农场、合作社、企业3类主体的发展特点。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蚕桑产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数量增长速度与农业产业相仿,3类主体的数量增长趋势大致相同。尽管我国蚕茧产量自2007年起就呈现出规模缩减进而保持稳定的态势,但新型经营主体的数量发展并未滞后于农业产业的平均水平。2013年至今,蚕桑各类型经营主体数量都呈现增长的态势,其中,蚕桑家庭农场的发展势头良好,增长速度甚至高于其他农业产业,蚕桑合作社和蚕桑种养企业发展稳定迅速,在近年也反超其他农业产业相应主体数量增长速度。
第二,各地新型蚕桑经营主体发展与“东桑西移”发展规律相符。具体来说,东部地区蚕桑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速度减缓、甚至下降;中西部地区蚕桑生产经营主体发展较快,但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西部蚕区发展较快,历年新增数量较多,在营主体数量也居全国前列,其中尤以广西和四川为主导;中部蚕区发展较稳定,以安徽和重庆蚕区为主导;东部蚕区的桑蚕种养业相关主体逐渐式微,经营主体数量呈减少态势。
第三,蚕桑产业规模化水平和组织化水平持续提升且近年来增速加快,但仍明显低于农业产业平均发展水平。各主产省(区)近年来规模化水平均有所提升,组织化水平则波动较大,但大部分省(区)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省(区)间比较来看,各主产省(区)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历年位次排列均基本稳定,其中安徽和广东等省(区)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多年来持续领先于其他省(区);北方主产区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有限,这与其品种有关;而广西作为蚕桑生产大省(区),其规模化组织化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规模化组织化经营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从本文分析来看,新型蚕桑经营主体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空间,特别是在蚕桑生产大省(区),需要着力推进新型蚕桑经营主体的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提升蚕桑生产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政府部门可通过多种方式促进蚕桑经营主体的高质量发展,如对于规模生产和工厂化养殖、绿色种养技术应用、资源多样化利用等的支持,因地制宜重点发展不同类型经营主体,并通过经营主体开展跨区域产业链整合实现我国蚕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