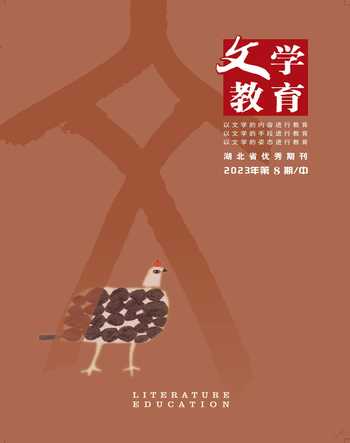国内复杂谓语的研究综述
吴懿婷
内容摘要: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复杂谓语结构值得人们关注并进行研究。传统研究、生成语法、构式语法和认知语法尝试分析其语法特征、句法结构和构式特征,描述较为充分然而解释力却不足,且对复杂谓语中的次要谓语研究比较少。为了达到解释的充分性,还需
复杂谓语构式是两个概念结合形成一个简单谓语。复杂谓语和简单谓语形成对比,后者是谓语由单一成分组成的子句。复杂谓语在传统语法中不被认为是一种语法类型,近二十年来才逐渐开始在语言学中得到广泛的讨论(Croft 2022:397)。
复杂谓语中构成主要主谓关系的谓语叫做主要谓语,构成次要主谓关系的谓语叫做次要谓语。Croft(2022:399)基于复杂谓语中的次要谓语的语义,将复杂谓语分为称为事件复杂谓语(Eventive Complex Predicates)和静态复杂谓词(Stative Complex Predicates)。又将后者进一步分为描述性次要谓语结果性次要谓语(Resultative Complex Predicate 或 RCP)、(Depictive Complex Predicate 或 DCP)和方式复杂谓语(Manner Complex Predicates或MCP)(同上:432-433)。
(1)a.We painted the door red.b. He ate the carrots raw.c. We crawled down the slope slowly.
在RCP中,次要静态谓语描述的状态是由主要谓语表达的行为引起的,如(1a)中,次要静态谓语red是主要谓语paint引起的结果,时间上有先后,且描述的是其中一个参与者door的状态,故此类静态谓语是参与者为导向的。在DCP中,次要静态谓语描述的状态是和事件谓语所表达的事件同时进行的,如(1b)中,次要静态谓语raw和主要谓语ate同步,且描述的是其中一个参与者carrots的状态,故此类静态谓语也为参与者导向。在MCP中,静态谓语描述了主要事件的属性,如例(1c)中次要静态谓语slowly表示的是事件crawl的速度,与RCP、DCP不同,MCP不是以参与者为导向的,而是以事件为导向的,它描述的是事件的属性。
下面从传统研究、生成语法研究、构式语法研究和认知语法研究角度对国内复杂谓语以及复杂谓语中次要谓语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传统研究
传统研究早期多是从传统语法角度研究双重谓语(复杂谓语),但大多数仅仅是对这一现象的描述,而没有深入研究其本质。
任绍曾(1988)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双重谓语的动词为不及物动词。由于双重谓语中的动词为说明主语的特征、属性划定范围,这就决定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表示动作起止或过程的不及物动词可以作双重谓语的动词。也就是说,深层结构的动词谓语和名词性谓语在表层的重叠要受前者动词词义的限制。根据词义,可以用于雙重谓语的动词可以分为八类:来去类、运动类、起止类、升降类、起寝类、生死类、光照类和视听类。并且通过强调句型转换成份移位等测试方法说明双重谓语第二成份起表语作用,与状语有明显的区别。
缪昌义、夏宏钟(2005)探讨了双重谓语的语法特征,认为其语法特征往往通过主要谓语和次要谓语在动词的选择和时态的使用上体现出来,并且有很大的局限性。张庆凤(2007)对英语双重谓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她也认为英语双重谓语的特点通过主要谓语的动词的选择和时态的使用上体现出来;次要谓语可以是描绘性的形容词、名词、现在分词、过去分词,它们用来说明主语在某一特定动作、行为下同时所具有的特征、身份、属性。
以上都是从语法学上对双重谓语进行描述,缺少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二.生成语法研究
常鸣(2018)在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框架内,结合人类语言的基本逻辑模板,重新分析了结果性次要谓语结构的句法特征,探讨了结果性次要谓语的句法地位。人类语言的句法关系可以表征为由 NP和VP构成的逻辑模板,体现的是以动词为结点的中心语和补足语的关系。在逻辑模板中,传统语法中的主语和谓语是基本成分,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为附加成分或附加语。附加语的递归用 XP+表示。树形图中的F是基本的逻辑模板,调变都是在外面的。整个句子还可以名物化成一个结点,占据新生成的句子中的NP位置,依次递归,无限生成。这也恰恰说明了语言的递归性这一特点。附加语与模板的关系比较松散,不需要进行逻辑运算,之上附加关系。它的位置是灵活的,既可以附加在 XP 短语上,也可以附加在模板上,构成 NP+、VP+、F+。
结果性次要谓语和主要动词在词汇层面组合构成了复杂谓语,是动词的修饰语或者主要动词的附加语,其次,主要动词和结果性次要谓语在词汇层面形成的复杂谓语可以看做是词汇化的一个过程。复杂谓语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新形成的复杂谓语只是一个临时的词,在句子运算结束后随即消失,动词V和结果性次要谓语可以看作是复杂谓语的一个语素。
由此看来,结果性次要谓语结构和人类语言的基本结构是一致的,结果性次要谓语只是主要动词的一个修饰成分,且是主要动词的附加语,或动词修饰语。
常鸣(2019)也对描述性次要谓语的句法结构进行了研究分析,以句法学的最简方案思想为指导,基于人类语言的逻辑模板,运用逻辑推导的方法重新分析描述性次要谓语的句法结构,认为描述性次要谓语其实是附加语,其作用是对句法结构的语义补充,并不是保证句法结构完整的必要条件。宾语取向的描述性次要谓语附加在动词短语VP上,并一起向上形成最大投射VP +。主语取向的描述性次要谓语附加在名词短语NP上,并一起向上形成最大投射NP +。
国内从生成语法角度进行的复杂谓语的研究比较少,并且已有研究的研究对象未能覆盖所有类型的复杂谓语及其子类。
三.构式语法研究
叶狂、张建理(2014)在构式语法框架内,提出构式合一的工作机制,来解释英语主语指向 描述类次述谓结构的句法特点,构式3为构式1和构式2合一而成的次述谓构式,其中V来自构式1,D指 depictive 来自构式 2,即主谓宾构式1和主系表构式2合一后构成了新的次要谓语构式3。构式合一生成时要遵守句法、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的允准条件。这一方案可以较好地解释次述谓构式与带独立结构句式和状语指主简单句式的区别,也能解决生成语法、功能语法以及认知语法等前人研究中的难题,在对一些边缘语料的解释上也有所推进。但是构式合一方案是否也适用于宾语取向的描述性的次要谓语和结果性的次要谓语,这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林璐、韩冰冰(2015)在构式语法框架下,从句法和语义两个层面对“N+DP1+DP2”结构中的主语题元、DP1和DP2作了具体的分析,发现DP2和DP1具有相同的成分功能,都用来说明主语题元的行为特征可见,DP1和DP2都可看作句子的谓语,由此认定该结构为双重谓语结构。进而得出“N+DP1+DP2”结构的中心构式形式为主语题元(生命体)+DP1(运动始止/延续+DP2(运动始/延续时状态);另有两个扩展构式形式为:主语题元(非生命体)+DP1(运动的隐喻)DP2(运动动时状态)和主语题元(生命体或非生命体)+DP1(运动起始)+宾语论元+DP2(运动前状态特征)。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两个扩展意义分别通过隐喻连接和多义性连接,与中心意义之间构成一定的继承关系。这种在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下对英语双重谓语结构的解读方式使人们认识到双重谓语结构在结构和语义内容上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和共同特征,加深了人们对双重谓语结构的理解。
国内从构式语法角度进行的复杂谓语的研究比较少,构式合一方案可以较好地解释次述谓构式与带独立结构句式和状语指主简单句式的区别,但是这一方案是否适用有类型的次要谓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且对“N+DP1+DP2”结构的解读也未能涵盖所有类型的复杂谓语。
四.认知语法研究
胡建刚(2007)以“认知语法”和“语义语法”为理论背景,跳出旧有形式语法的研究框架本文从语义出发,对汉语N+VP+VP结构进行了综合考察。同时,以谓词核心理论为背景,提出“原始事件”和“表达事件”的概念,并以原始事件重组为表达事件后的不同语义关系为标准,实现了把汉语同形结构 N1+VP1+VP2三分为单句、复谓结构和复句。其中,当VP1和VP2实现为核心谓词与其场景语义之间的固有语义关系时,VP1+VP2 重组为一个表达事件,句法上对应复谓结构。提出“静态语义格”和“动态语义格”的概念,即把由介词引进的语义格称为静态语义格,把由动词引进的语义格称为动态语义格。汉语一个句子可以同时有两个以上的限定性动词共存,因此其引进语义格的形态既有静态语义格,又有动态语义格。汉语动态语义格的句法实现形式就是复谓结构N1+VP1+VP2。首次从认知出发,探讨了各类动态语义格之所以能通过说话者的透视选择成为透视点的透视动因,分析了汉语复谓结构N1+VP1+VP2形成的内在机制建立了一个共有4大类25小类的汉语动态语义格系统,并指出,汉语动态语义格系统是一个在句法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动态系统,如果V动性特征趋向于弱化,不断虚化,其最终发展的结果就是介词标记。
胡艺芹(2007)以认知语言学中的突显原则为基础,结合图形-背景理論、顺序相似性以及信息焦点对次要谓语进行了分析探究。她认为次要谓语是突显的图形,主要谓语是背景。由于图形-背景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图形和背景可以互换,所以在部分次要谓语句中,主要谓语可以成为图形,次要谓语反为背景她认为主要谓语和次要谓语可以用事件1和事件2来表示,读者只需弄清主语和事件的关系,以及哪个是图形事件哪个是背景事件,而不必纠结于传统语法所谓的句子成分。这一分析的优点是可以确立语义重心,但并不能很好地区分动状结构句和次要谓语句,因为,两者的图形/背景关系相同,如:
(2)a. He sat there silently. b. He sat there silent.
其次,图形-背景理论不能解释句法上的图形可有可无的地位。图形-背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因为一旦图形没有了,就无所谓背景。(2a)中图形silent去掉后理应生成不合法的句子,然而事实恰恰相反,He sat there. 这个句子完全合法。
任绍曾(2011)运用隐喻化来解释,他通过纵向的范畴化关系和横向的配价关系检验,区分了主语取向的次要谓语和宾语取向的次要谓语。他认为主语导向的次要谓语,如:He left the bedroom happy,在纵向的范畴化关系上要接受NP+become+ADJ 的检验;然后再进行横向的组合,横向上其组合路径是left和bedroom结合,然后left the bedroom提供关系侧面并作为侧面决定体与 happy 结合,最后left the bedroom happy提供关系侧面与he结合。
王娜(2021)从语法隐喻视角研究英语双重谓语的结构,将其形成过程视为从小句复合体到小句的级转移,双重谓语结构的形成机制是“When +主语+ DP1,主语+ be + DP2 +其他成分”的语法隐喻。“主词+ DP1 +和+联结词+ DP2 +其他成分”作为隐喻性较弱的形式,“主词+ DP1 + DP2 +其他成分”的DP结构由于符号史的三个轴和信息的丢失而成为隐喻性最强的形式。
(3)a. She came home tired. b. When she came home, she was tired. c. She came home and was tired
(3a)是典型的双重谓语结构,“she”为主语,“came home”为DP1,表示主语所做的动作,“tired”为形容词DP2,描述主语在动作过程中的状态。根据其定义(3a)的语义是:当她回到家时,她很累。(3b)由两个小句以逻辑扩展关系组合而成。第一个是“When she came home”作为指定时间的次要从句。第二个是主句,也就是“she was tired.”。在(3b)主语相同的情况下,出于经济原则(the principle of economy),可以将其从复合从句转换为具有相同主语并表述隐喻的小句(3c)。主句的主语省略,状语从句的关系词省略时间也被省略了。因此,复合句被降级为由并列连词组合的小句,并具有相同的主语SHE。由于隐喻的过程很可能在整个小句中得到回应,因此,一次等级的上的位移必然会引起其他类似的位移。最后,典型的隐喻形式(3a)产生了。也就是DP的结构:She came home tired.
任绍曾(2021)对含55个双重谓语句的随机语料和含35个双重谓语句的系统语料的分析,结果显示:双重谓语句的语篇性在其成分的语言体现中得到具体表现,而且为从双重谓语句推导语境的有效性所证实。双重谓语句的语篇性及其具体语篇特征是语境决定的,因而可以看作语境的印迹。任绍曾(2022)又从认知功能的视角出发研究英语双重谓语的语义蕴含。双重谓语的内涵意义是结构赋予的临时性。这内涵意义进入语篇之后得到延伸,出现了蕴含意义,即临时性、偶发性、对比性、异常性、结果性和借喻性,主要是临时性、对比性和结果性。这三项意义是涵盖的:结果性含对比性和临时性,对比性含临时性,其余三项以某种方式分属三项主要意义。这些语义蕴含共同适应语篇需要,在语篇组篇和结构中发挥语篇功能。
认知语法的图形-背景理论、语法隐喻等为认知语法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复杂谓语这一语言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其研究对象未能覆盖所有类型的复杂谓语。
综上所述,传统研究集中关注双重谓语(复杂谓语)的语法特征,对这一语法现象进行规定和描写以及区分相似的结构。目前已有的从生成语法角度展开的相关研究都是基于人类语言的逻辑模板来分析结果性次要谓语和描述性次要谓语的句法特征,没有对方式性次要谓语结构进行分析。从构式语法角度提出的构式合一方案可以较好地解释次述谓构式与带独立结构句式和状语指主简单句式的区别,但是这一方案是否适用有类型的次要谓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认知语法的图形-背景理论、语法隐喻等为认知语法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复杂谓语这一语言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其研究对象未能覆盖所有类型的复杂谓语。
总之,国内学者对复杂谓语的研究大多是从语法角度、语义角度和认知角度展开的,生成语法角度和构式语法角度的相关研究比较少,且对复杂谓语中的次要谓语研究也比较少。具有相同表层形式的次要谓语其实是一个语义关系复杂的结构。为了达到解释的充分性,我们还应该对次要谓语做出相对合理的解释。为此,还需要对次要谓语现象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以完善我们对复杂谓语的认识。
参考文献
[1]Croft, W. 2022. Morphosyntax: Construction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常鸣,2018b,基于人类语言逻辑模板的结果性次要谓语句法学再分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138-140+156.
[3]常鸣,2019,描述性次要谓语的句法结构再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0):136-140.
[4]胡艺芹,2007,双重谓语的认知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5]胡建刚,2007,复谓结构和汉语动态语义格的句法实现[D].广州:暨南大学.
[6]林璐、韩冰冰,2015,英语双重谓语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J].《语言教育》3(02):60-66.
[7]缪昌义、夏宏钟,2005,英语双重谓语语法特征初探[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0-62.
[8]任绍曾,1988,三说英语双重谓语[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01):23-29.
[9]任绍曾,2011,英语实义动词如何融入关系小句——对双重谓语句的认知功能探讨[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34(04):21-31.
[10]任绍曾,2021,英语双重谓语句的语篇性[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44(03):2-20.
[11]任紹曾,2022,英语双重谓语的语义蕴含[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45(02):2-14.
[12]王娜,2021,英语双重谓语结构的语法隐喻视角分析[D].西南大学.
[13]叶狂、张建理,2014,构式合一方案对英语次述谓句的解释[J].《现代外语》37(06):783-793.
[14]张庆凤,2007,英语双重谓语的特点分析[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5(02):7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