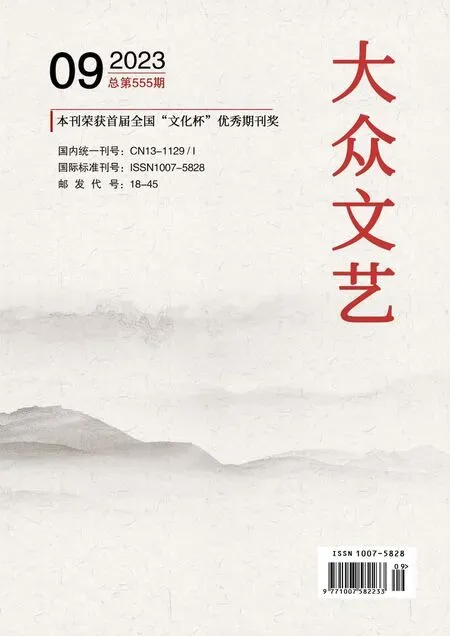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基于儒释道文化的整合模型
郭悦凡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 430072)
一、引言
这是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工业化、互联网、5G等等新概念不断出现,技术的革新也伴随着人们生活方式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观念上的不断迭代更新。如果说还有什么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不易发生变化,那可能最稳定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格结构。人格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中重要的一个分支,过去近百年来西方提出了相当多的理论和架构,也为我们分析中国人的人格奠定了基础。但是心理学并不是一门超文化的学科,人格结构更是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作为一个拥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无疑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这也意味着中西方的人格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当脱离西方理论的模型和工具之后,我们竟不知道该如何来刻画中国人的人格。如果说心理学是一门有着“短暂的历史和漫长的过去”的学科,那么中国人的人格刻画可能是一个有着“始终不明确的定义和更为漫长的过去”的话题。本篇文章针对“理想人格”的领域,试图梳理国内对理想人格不同的阐述,对比西方的理想人格,并为心理咨询的应用提出建议。
二、国内理想人格研究
国内关于理想人格的阐述众多,但是很少形成像西方现代心理学一样的人格理论,运用分析性的实证研究,多数采取更加整体、宏观的视角,对理想人格所应该具备的品质进行举例的论述。本篇文章选择了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释家文化,通过总结这几种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异同,以及和西方现代心理学之间的差异,试图刻画中国人所特有的理想人格模型,并提出在心理治疗领域中应用的价值。
1.儒家理想人格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起始于春秋时期,距今约2500年,对中国人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时至今日,我们每个人仍然要从小学习《论语》《大学》,聆听仁、义、礼、智、信的教诲,儒家文化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鼻祖,很早就刻画了中华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形象,他的理想人格主要分为圣人和君子两个层次。
圣人人格是孔子最为推崇的理想人格,它对个体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内圣外王”是对圣人人格的要求概括:即对内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全心为天下谋福利,不考虑个人的私利;对外要实实在在为社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功绩,圣人人格强调的是道德修养和经世致用的协调统一。孔子认为只有尧舜等古代贤明的帝王才可以匹配圣人人格,显然现实社会中普通人很难达到这样的层次。孔子认为自己也没有达到这种至高无上的境界,提出圣人人格是希望勉励世人不断朝着这样理想的方向努力,尽量接近圣人人格的层次。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因为圣人人格的境界普通人几乎不可能达到,孔子又提出了低一层级的理想人格境界:君子人格。《论语》中“君子”一词一共出现了107次,足可见此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性[1]。君子人格不要求人们一定要做出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是强调修炼个人的道德品质,相对圣人人格来说更有可能实现一些。君子人格是一种现实生活中更有可能出现的典范,因此,《论语》中大量采用君子和小人的对比,通过日常行为来勾勒出君子人格的形象。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些特征有:一、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表明君子看重的是道义,而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说明勇应该受到义的约束,遵守道义对君子来说是最重要的;二、先仁后智。如果说圣人人格强调的是仁与智的统一、内与外的兼修,那么君子人格显示出在两者不可兼得或有所冲突的情况下,理想的人格是先追求仁、再考虑智,君子人格偏向于“内圣之学”,讲求自我反省大于向外开拓;三、勤俭好学。“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强调君子不应该追逐和沉湎于肉体的满足和欢愉,或是迷失于功名利禄的欲望,生活简单知足就好,应该更多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工作勤劳敏捷、言语严谨慎重、学习谦虚勤勉[2][3][4]。
孟子在孔子理想人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增添了一个更低层级的理想人格:大丈夫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非常推崇大丈夫人格,并且本人立志要具有这样的人格。大丈夫人格核心的品质就是修养内心的“浩然之气”,稳住心中的“道义之锚”,无论身处怎样的人生境遇,都能坚持仁、义、礼、智的原则,处变不惊,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2]。
孟子的大丈夫人格相较于孔子提出的君子人格,是在孔子强调“立志”的基础上,增添了“养气”的元素。孟子明确了关于“立志”的定义,志就是所谓的道德理性(仁义),而气就是非理性,大丈夫人格讲求志气结合,也就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结合。孟子的叙述中指出,志的产生要优先于气,气伴随着志产生,气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产生于任何不义的行为;气的性质、地位相对于志来说是次要的,气就是为了配合志,没有志的话气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修炼大丈夫人格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不断地修养“浩然之气”[5]。笔者以为,所谓的“气”通俗来说就是指一个人周身的气场和氛围,这种氛围的散发是源于我们内心的道德准则,而我们有必要通过修养这一份气场来使自己的内心滋养在光明、磊落的环境下,反过来监督和维护自身道德的准则。无愧道义、坚守本心、坦坦荡荡,是大丈夫人格的核心要求。
儒家文化中倡导的是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但通过对孔孟理想人格层级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在普通人内圣外王难以兼具、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儒家选择的是优先内圣之学,君子人格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孟子也指出无论在什么外界环境之下都要坚守自己的“道义之锚”,但是在对外界的影响上,大丈夫人格无法保证能够做到博施济世,独善其身也不失为理想中的追求。这三个不同层次理想人格在建功立业上一步步地退守,也为接下来和道家理想人格的融合奠定了基础。但是总体来说,儒家文化最推崇的理想人格仍然是“圣人人格”,其核心的特点是“内圣外王”。
2.道家理想人格
道家文化也是一种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流派,魏晋风骨时至今日仍然令人艳羡,“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赤壁赋》)道家的形象就好像乘风而来御风而去的仙子,令人憧憬而缥缈不已。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道德经》是道家文化著名的经典之作。其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理想人格的概念,但是老子多次建构“圣人”这一人物形象,可以说,这个“圣人”的形象就代表着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但是这里的“圣人”和儒家所推崇的“圣人人格”相差甚远。老子崇尚的圣人最核心的品质特点是:知足不争、自然无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至善的理想人格应该拥有像水一样的品质,滋润万物的成长发展却不与任何事物抢夺利益,处于他人都不愿意在的位置,这样就接近于“道”了。老子提倡的无为不是无所事事或无所作为,而是尊重任何客观事物本身随自然规律的发展,不去进行人为的强求和干涉[3]。
庄子在老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了道家的理想人格。可以用“真人”来代表庄子眼中的理想人格,真人人格所具备的核心特质是:摆脱束缚,绝对自由。“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庄子·大宗师》)所谓的“真人”睡觉的时候不会做梦,醒着的时候没有忧愁,不刻意追求口舌等感官上的享受,一呼一吸之间气息深长持久,仿佛和天地融为一体。庄子所谓的自由不是西方语境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笔者认为,其中包含着这样几层内涵:一、摆脱任何人为的束缚,回到原始社会最本真的状态。西方语境下的自由固然也包含有摆脱束缚的意蕴,但并没有崇尚原始社会的内涵;二、物我两忘,万物齐一。西方语境下的自由是对个人主义的讴歌,而庄子笔下的自由则是一种物我两融,天人合一的状态,此时已经没有自我,也没有他人,自然也就谈不上个人主义或者是集体主义,这是一种超越这两种主义之上的整合状态。
总结来说,道家文化倡导的是一种出世或者说游世的价值观,它和儒家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儒家文化希望在现实和此世的世界,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而道家文化想要回到人类最初的原始社会,留恋朴拙、自由生长的田园风光[6]。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社会,也决定了它们对于理想人格不同的见解。儒家文化中圣人人格“内圣外王”要求的是在集体主义中保持绝对的道德,以及凭借一己之力带动整个社会集体的发展;而道家文化中的理想人格可以归纳为“真人人格”,这种人格的核心特点是“自然无为,物我两忘”,它反对以人为的力量强制或干预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发展,在这种状态下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自然也就谈不上个人和集体的区分。道家文化为儒家文化宣扬的理想难以达成时寻找了一个出处,他们退回到心里的“原始社会”里,不再强调家国天下的概念,甚至人与万物之间也开始没有明确的划分,一切回归到天地最初的蒙昧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道家文化的理想人格中要比儒家文化多上一个维度:时间的维度,这种人格中不仅包含了我们的现在,还包含了人类漫长的过去。
3.释家理想人格
释家文化作为一种宗教文化,最初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距今约1800年,比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都要晚上不少。佛教里面有着纷繁复杂的变形,其中禅宗是中国佛教的集大成者,最初由达摩大师传入中国,融合了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和生活习惯,逐渐褪去了晦涩的外衣,被更多中国人所熟识和接受。
面对生命中种种的挫折、苦难,儒释道这三种文化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而这背后也映射出不同的理想人格。儒家的答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算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就算明知建功立业求而不得、就算兼济天下之梦看似虚无缥缈,也要坚定内心的操守、坚持践行理想的道路;道家的答案是“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他们选择抱朴守真,退回到内心的原始社会,退回到未分化状态下与自然万物齐一的和谐,不去理会现实社会的矛盾和纠结,一切遵循自然无为的天道;而释家给出的答案是“忍受痛苦直到超越因果循环”,当面临无法选择又无从避免的人生苦难时,他们不断为自己寻找着归因,企图获得内心的平静,而当实在找寻不到原因的时候,他们选择相信这是上辈子的“业障”,一切都是因果循环,人永远生活在轮回的苦海里。既然是自己前世种下的因,那么自己必须忍受并穿越这苦果,直到有一天超越生亦悲、死亦悲的轮回转世之循环,到达彼岸的极乐世界[7]。
正因为有着这样因果循环的世界观,释家的理想人格可以概括为“超人人格”,其核心的特点是:一、超脱世俗。虽然道家文化中也有超脱世俗的思想,但是道家中的世俗更多对应的是人际的现实社会,他们倡导的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建立起原初本真的联结;而释家文化中的世俗则不仅局限于此,还包括了万事万物、甚至宇宙轮回。在释家文化的眼里,万般皆空,“空”才是世界的本质,人要争取达到一切皆空、一尘不染的境界;二、慈悲为怀。虽然儒家文化中也有博施济世的思想,带着很强的道德色彩,但是这种道德更多还是辐射在宗族、国家以至人类的层面上;而释家文化中的道德思想则超越了亲疏远近、超越了物种甚至于时空,是一种普度众生的道德观念;三、安忍苦难。总体来说,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中都部分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但它们彼此之间的动机截然不同。儒家文化的经历苦难更类似于一种过程,或者是磨炼自身的手段,是到达“内圣外王”理想的必经之路;道家文化更多把一些苦难解释为天道、自然的规律,在这种不断地舍弃外物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回归本真的快乐;而释家文化中的苦难类似于一种生命的本质,人类不过是因果循环中的一环,只有安忍苦难、感受“我空”,才有可能“涅槃”,超越因果的循环[8]。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立足于现实和此世的世界,道家文化是回归原始、古朴的社会,那么释家文化则是将希望寄托于彼岸的世界。这个彼岸不能简单地说是未来,甚至也不能归结为来生,因为释家文化中的时间观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接近于一种环形的状态,他们真正渴求的是跳出时空的循环。从这个角度来看,释家文化的理想人格又比道家文化要多上一个维度,它不仅在线性的时间中寻找答案,更在超越时空之外的混沌中找寻归途。
三、国内外理想人格的对比
1.自我和不同的超我
现代西方心理学语境下的理想人格更多聚焦于“自我”的层面,强调意识的作用,倡导形成一个和谐的自我,取得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平衡;既能利用经验又能充分结合现实的情况,不被内心自动化的思维模式所支配,最终遵循自我的意志,走上自我实现的道路。这种理想人格中不包含很多道德性的要求和评价,它固然要求人们要遵守基本的法律和道德观念,但过强的道德性束缚和焦虑反而会对自我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可以说它不是以道德尺度作为评判标准的。
而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中的理想人格,则可以说都是聚焦于“超我”的层面,对个体提出了非常高的道德要求。儒家文化的道德观是基于现实社会的,对人从内到外都树立了一套系统的道德指标,标准非常之高以至于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圣人人格”;道家文化的道德观是基于原始社会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道家所提倡的自然无为很接近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状态,但内涵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事实上道家和儒家都追求一种极致的道德状态,只是他们对道德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采取的手段也不一样,道家眼里的道德侧重于“天道”要胜过“人道”,“有为”是儒家实现“人道”的方式,而“无为”则是道家实现“天道”的方式;释家文化中理想人格的道德标观更加拔高了一个层次,达到了一种普度众生的境界,这里的众生不仅包含了儒家文化中所重视的现实世界、也不止道家文化中更为关注的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一种超出了线性的时间观、超越了时空要素六道轮回的在宇宙中所有存在的万事万物,我们对这所有都要抱有一颗慈悲之心,安忍所有苦难的现状。
2.个人主义和关系本位
现代西方心理学语境下的理想人格所追求的是一种个人主义下自我的发展、成长以及自我实现;是一种不伤害他人情况下得以做任何可以发挥自我潜能事情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和自我实现在理想的状况下同样会给社会带来正面的收益,但这并不是理想人格所强调的重点和追求的初心。
而在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中聚焦于“超我”层面的理想人格中,找寻的本身就是一种关系本位的目标,虽然这些目标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儒家文化中强调的是人和社会的关系,理想的状态下应该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博施济世;道家文化中追求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俯仰之间体会自然细微的奥妙之处;而释家文化涵盖的是人和天地万物、因果循环之间的关系,人身处在因果循环的时空链条上,安忍苦难、抱着一颗慈悲之心感受超脱世俗的无喜无悲。
3.在不同的维度寻找答案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无疑是最为主流的传统文化,而当面临这种道德理想难以实现、郁结苦闷的心理困境时,东西方或许给出了不同的解法:西方的答案是回到自我,回归任何不伤害他人的自由,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除了儒家宣扬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还发展出了形式更为复杂的超我的变形,这些在现代以实证科学为导向的西方心理学之中是很少见的。
一种变形是道家文化中回到原始社会“天道”的道德,这种时间上的差异让人联想起弗洛伊德心理防御机制中的退行,只不过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基于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这种“退行”则是退回到历史长河的原初状态,因其具有历史文化上的特点,又有些类似于荣格所提出的“集体潜意识”观念。笔者以为,可以说道家文化是蕴含在中国人心底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当居庙堂之高、博施济世的理想破灭时,我们很容易退回到“无为”的道德理想之中,这种转变甚至超出我们意识的范畴。这一点倒是和道家所追求的精神状态不谋而合,“无欲”“混沌”正是要将意识的强度尽可能降低,进入现代所谓潜意识的状态。道家认为这是精神本来的状态,和天地精神的那种状态相一致,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之下,才有可能实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通向意识所不能到达的“得道”[9]。
另一种变形则是释家文化中向往彼岸超越时空和因果循环、普度众生“超人”的道德,这种道德可以说是“超我”中的“超我”,它不仅辐射现实的世界、自然的关系,还辐射到无穷无尽的未来时空轮回、囊括天地六界的尺度。这种道德观实际上会弱化个人的存在和价值,但也因此弱化了个人所承受的苦难,在和更加广袤的世界以及未来的联结中、在不需要任何外部条件“立地成佛”的教诲里,个人逐渐消解了自己命运中难以承受的苦痛和理想所不能实现的郁结。
四、探索中国人的理想人格的意义
在西方文化盛行的当下,自由很大程度上成了我们每一个人追逐的最核心的目标,自我实现也成了一个人最渴望、最高的追求,这可以从对理想人格的阐述中略窥一二。这种追求和道德是解绑的,很大程度上也不关乎他人的评价和社会的认可。理论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潜能、都能在自由中寻找到自我实现的方向,但是现实中,当我们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后,却常常会感觉到迷茫、不知道自己追求和自我实现的方向是什么,陷入一种不知道自己存在意义的虚无主义之中;也有的人纵情于声色犬马,这固然也是一种短暂的快乐,但享乐后却常常伴随着更深层次的虚无。
探索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其实是在探寻:我们应该用什么来锚定自己,寻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又应该怎样面对追逐路上的挫折与挑战,化解可能最终求不得的郁结和苦闷。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或许给出了一个闭环的答案:我们从古至今都更多追寻的是一种关系本位的人生意义,个人的价值不可能超脱于关系而独立存在,个人的意义也不可能脱离道德和内心的操守,我们追求的终极境界始终是儒家文化中宣扬的积极入世,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但是当现实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我们也会将这种关系本位的追求转而投射向自然,或是投射向更加广袤无垠的宇宙轮回,以此来弱化自身的存在、弱化对苦难的感知,但却依然不改坚守内心道德的观念。即道家文化所宣扬的出世和释家文化崇尚的“我空”并不是站在儒家文化的对立面,而是对儒家文化中理想难以实现时的一种退守和补充。
这对心理工作和心理咨询方面的启示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中所宣扬的追求自我、自由和自我实现作为个人发展的目标,跨文化的嫁接有可能会水土不服,尤其是针对近些年来越来越频繁出现的所谓“空心病”的群体,自我和自由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会对应向虚无,失去了锚定自己之物,就如同一艘船在海上漫无目的地漂流。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理想人格不同的注解、在关系本位上迥异的追求,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指引,寻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及在苦闷时获得一部分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