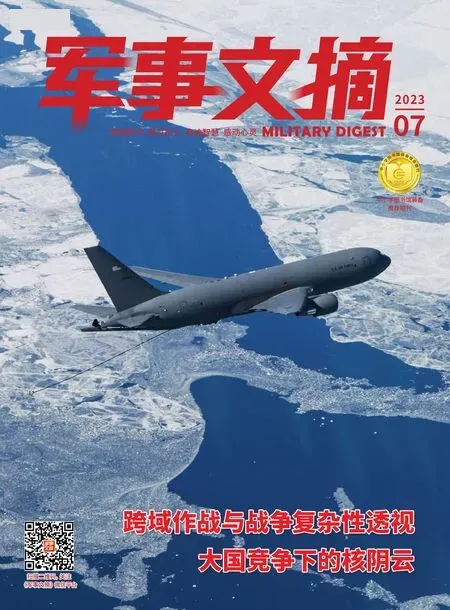世界核军控体系岌岌可危
曾 鹏 谢丰宇
核武器诞生后,国际社会为增强战略互信、促进地缘政治稳定、避免发生核战争,逐步构建了当今世界核军控体系,以期限制核武器的研制、试验、部署和使用,进而阻止核武器扩散、防止核战争,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冷战前期,美苏两国剑拔弩张竞相发展核武器,甚至曾发生“古巴导弹危机”这种将世界推向核战争边缘的事件。20世纪60年代末,美苏核军备形成相对均势,也都意识到核军备竞赛可能导致的恶果,在此背景下构建国际核军控体系成为可能。此后,以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起点,《中导条约》《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军控条约陆续签订,逐步形成了目前的世界核军控体系框架。核军控体系的建立有效避免了核战争的爆发,限制了有核国家及其核武器的数量,为保持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近些年来,美国出于维持全球霸权需要,大力鼓噪大国竞争,不断激化地区矛盾,肆意挤压他国战略安全空间,主动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军控支柱性条约框架,使世界核军控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近日,普京宣布俄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使美俄目前唯一的双边军控条约濒于崩溃,也将世界核军控体系置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美俄双边核军控条约命悬一线
毋庸置疑,美俄由于掌控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核武器,因此在世界核军控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但俄格战争、克里米亚危机、乌克兰危机等事件促使美俄关系持续恶化,美国政府更是宣称重返大国竞争时代,导致美俄核裁军进展趋缓甚至面临中断风险。目前,美俄已先后退出了《中导条约》,仅剩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命悬一线。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闭幕式
1987年底,美苏两国签订了《中导条约》。该条约规定美苏双方均不得生产、试验和部署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的短程和中程陆基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这相当于彻底销毁了一个武器类别,在世界核军控史上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国际社会本想以《中导条约》为起点,推动实现全球无核化。但自该条约签订之后,美俄双方就《中导条约》的争议从未间断。2019年8月2日,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也旋即退出,《中导条约》全面失效。
《中导条约》是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在维持核霸权的基础上,追求战略平衡相互妥协的产物。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核力量发展失衡、俄美关系日趋紧张、地缘政治安全风险增大,《中导条约》赖以存在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改变。《中导条约》的限制成为美国谋求绝对军事优势、实现霸权利益的“绊脚石”。为满足新时期“大国竞争”战略需求,美国政府主动退出《中导条约》,扫清了发展陆基中程导弹的障碍。其实在退约前,美国就已经在推动中短程陆基巡航导弹技术研发,积极推动核武器小型化和低当量化改造。目前,美国正在推动多项新型陆基巡航导弹、新型陆基弹道导弹、陆基高超声速武器研发,射程涵盖近程到中远程,速度覆盖亚声速到高超声速。此类武器的研发和部署将加强美国的前沿存在,增大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
目前,美俄之间的双边核军控条约仅剩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1年2月5日生效,有效期10年。2021年2月3日,经俄美协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延长5年,至2026年2月5日,在条约失效前完成了一次“悬崖勒马”。截至2023年2月初,美俄依照条约,限制了双方核力量的数量,并完成共328次现场视察,交换了25311份通知,有效增强了双方核力量的透明度和战略互信。
2023年2月21日,普京在年度国情咨文中指出美国一边为研发新型核武器考虑进行核试验,一边又要求俄严格遵守条约的规定是“荒谬”的,因此宣布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不会退出且会遵守条约对进攻性战略武器最大数量的要求。作为目前美俄之间仅存的双边核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存续直接影响全球战略稳定与核军控的前景。在近年来美俄大国竞争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暂停将进一步破坏双边战略稳定基础,加剧核军备竞赛和核战争的风险。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便在未来能够继续生效,其前景依旧非常悲观。一直以来,美俄对于该条约是否应考虑太空及网络空间、美国反导系统、俄罗斯新核武器系统和战术核武器等问题上均存在严重分歧。这也暴露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缺陷:该条约主要是对美俄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进行数量限制,但随着美俄在常规武器及多域作战等方面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条约的限制已无法满足维持战略稳定的需求。后期,美俄即便围绕签订新条约、扩充削减内容进行磋商,也必将是一场激烈且持久的拉锯,双方再次签订军控协议的难度很大。
国际多边核军控条约举步维艰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最终实现“无核世界”是全世界的共同心声。世界各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相继签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构成了国际多边军控体系的基础。但这两项国际军控条约的进展却举步维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最近两次审议大会均因美俄的分歧无法达成实质性共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至今也未生效。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68年7月签订,并在1970年3月正式生效。条约确立了核裁军、防核扩散和和平利用核能三大目标,奠定了全球核治理的制度基础,成为了国际军控和防核扩散的基石。该条约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除印度、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等少数国家外,世界大多数国家均是该条约的缔约国。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后规定每5年召开一次审议大会。最近的第十次审议大会原定2020年举行,但因新冠疫情推迟至2022年8月才正式举行。由于美俄在乌克兰等问题上的分歧,本次审议大会未通过实质成果文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历史上,类似结果已经发生了五次,且最近的2015年第九次审议大会因美、英等国阻挠也未达成共识,因此这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首次连续两个审查周期内未通过协商一致的实质性决定。
在本次审议大会上,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在2021年组建的新军事和政治联盟“AUKUS”也是主要议题。在该联盟框架下,美、英可以与澳大利亚分享核潜艇技术,帮助其获得可能使用高浓缩铀作为燃料的核潜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缔约国认为这是对条约防核扩散机制的破坏,可能导致印太地区进一步军事化。许多国家还担心个别核武器国家在防核扩散上执行双重标准,不公平地实施条约的限制措施以阻碍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
总体来看,《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缔约国间的分歧正越积越多。若国际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使得下一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再次未能达成实质性成果文件,那么长期以来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础建立的国际军控体系可能会面临系统性风险。
多边核军控的另一份重要文件《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迄今仍未生效。自1996年开放签署以来,该条约目前已有186个签署国,并获得其中177个国家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力图通过全面禁止核爆炸试验及其他任何形势的核爆炸,达到“全面防止核武器扩散,促进核裁军进程,从而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该条约若能生效,可有效减少核军备竞赛,并避免核爆炸试验给人类和环境带来的各种危害。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放签署以来,对全球禁止核试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各有核国家纷纷按照条约要求暂停了各自的核试验。根据条约要求成立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除积极促进国际社会普遍加入条约外,还建立了针对核试验的国际监测系统。国际监测系统由321个监测站和16个实验室组成,由全球89个国家托管,综合运用地震、水声、次声和放射性核素监测技术,探测和搜集地下、水中和大气中的核爆炸证据。目前,该系统中大约90%已经启动运行,并在对朝鲜进行的六次核试验监测中证明了系统的有效性。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国际监测系统

美苏签订中导条约

世界无核武器区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迟迟未能生效,使其未来发展困难重重。目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美国。美国尽管是第一个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但它至今仍未批准该条约,且近几届美国政府均宣称不会谋求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批评者认为美国的做法是为其恢复核试验留了“后门”,甚至不排除研发新核武器的可能。
无核国家推动不切实际核军控
在世界核军控体系中,无核国家一直在国际反核运动中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先后建立了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非洲无核武器区、中亚无核武器区等众多的无核武器区。这些无核武器区的建立避免了核武器的扩散,展示了无核武器区国家禁核的决心,为全球全面核裁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核武器区的建立与推广也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如中东无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就由于域外大国的利益争夺和外部干涉进展缓慢。
与此同时,无核国家对美俄等国非但核裁军缓慢甚至开启核军备竞赛、破坏国际核军控体系的行径充满担忧和不满。2017年7月7日,无核国家为表达全面核裁军的迫切诉求而推动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于当年9月20日正式开放签署。2021年1月,该条约正式生效。
《禁止核武器条约》与其他国际军控条约最大的不同是首次将核武器定性为非法。此外,该条约也禁止缔约国获得、拥有或储存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禁止缔约国在其领土或其管辖范围内部署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对于拥有、掌握或控制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各缔约国,要以不可逆转方式消除核武器并接受核查;还要求各缔约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全面保障协定。
截至2023年1月,该条约共有92个签署国,其中68国已批约。但美、英、法、俄等主要核大国及日本等美国盟国均对条约表示反对。有核国家普遍认为:当今世界核威慑依旧是维持国际和平的有效方式,而《禁止核武器条约》对核武器的绝对禁止剥夺了这些国家在面临核攻击等严重安全威胁时以核武实施自卫的权利,违背了核军控“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基本原则,因此不切实际。
结 语
从根本上说,现代世界核军控体系是在大国长期博弈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在当前大国竞争日渐激烈的背景下,核力量支撑国家安全的作用日益凸显,美俄争相推动核武器现代化,导致世界核军控体系日趋岌岌可危。
展望未来,核军控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各核大国保持自我克制和及时沟通,防止误判和非意愿的冲突升级,通过分步骤、渐进式的核裁军实现“无核世界”,达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