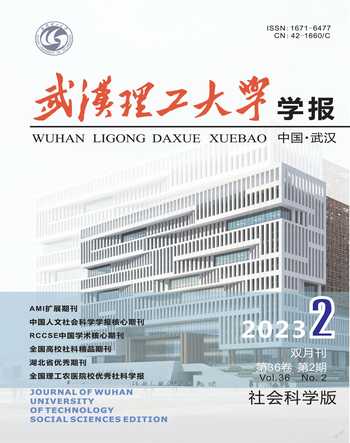从“机会”到“机器”
摘要: 媒介考古学从电影考古学对早期电影器物的重新发现中受到启发,主要受到“法国年鉴派”从研究“电影中的历史”转向“历史中的电影”观念以及福柯“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打断了历史的连续性链条的影响。对“深层时间”的探寻、对电影本身“多样性和异质性”的书写,均体现出西方人对传统媒介史虚无化的担忧,进一步延伸到對人的主体性追求的怀疑。借助于中国传统哲学(间性论),提出“机会”—媒介物—“机器”的循环模型,可以有效消解如下困惑:间性思想排斥人|物分离的形而上学思想,强调人、心、物之间“相几”的生态观念,使断裂的媒介史得以缝合;“物我齐一、物我两忘”的媒介艺术观使“失败”的媒介物得以持续鲜活;对“道”的体认使实体哲学中人的“身心错配”问题得以治愈。
关键词: 媒介考古学; 视听媒介史; 间性论; 相几; 道
中图分类号: J0|02; J120.9文献标识码: A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3.02.017
“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涉及对某种过去、某种古代的渴望。我的一个英国熟人告诉我,当他与德国人谈话时,最令他感到震惊和难以理解的是,德国人渴望他们民族的过去。”[1]媒介考古学依然是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的延续和继承,是古希腊以降文艺美学的媒介学转喻,她关注着一种特殊的隐含在历史叙事中的“媒介失语”症。这让我们看到了另一条隐秘文艺复兴道路的真实门径:波德莱尔、萨德侯爵、玛丽·雪莱以及爱伦坡所构筑的恐怖城堡。那城堡中常年闪耀着用导线连接尸块时发出的电弧火花,栽培着巨大的人形植物和各种黑魔法道具,以及在正史中难以见到的“死物”——那些推动了“真实”历史发生的伟大机器。这些机器驱动了物理学、化学、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甚至文学的发展,整个后现代文明的源头正建立在这些怪诞的视听机器中。因此,德国表现主义首先在欧洲狂飙突进,它不仅是一种新的艺术风格与流派,更是奇异的新媒体大爆炸时代的滥觞(以电影为代表的视听机器)。留声机、打字机、动图幻灯、走马灯甚至致幻剂等视听觉机器(药剂)中流淌出对新的文明的期望与恐惧,成为时代的宠儿或是毒品。以考古学姿态进入学术话语的“媒介考古学”学者们,看似在谈隐没在黑暗中的物,实际是对站在媒介物前端的人的热情讴歌。问题意识的提出在于他们反对观念性的历史,反对一切宏观而虚无的话语,反对不以谱系学逻辑构建的书写和理论。进而,才居心叵测地提出一种新的“人”学,一种媒介化的人,不仅仅是麦克卢汉笔下的《机器新娘》,而是被“真实—想象”所同时构建的具有“人—机器”双重属性的新人。
欧洲精英主义所恐慌的,不仅仅是原子弹和冷战,而且是人在现代性欲求中对主体的永恒渴望而不得。列斐伏尔流亡美国,看到街道上闪烁的霓虹,随即陷入惶恐,但田园诗性的欧洲村落已经无法挽回。他深知,缔造这一结局的,正是所谓的完整“历史”、健全的“人”以及主流文化。在以“西方人”自居的主流文化语境中,人与物被割裂,上帝以及其他精神图腾以绝对距离把人区隔开,人与人以主体性自省并进行精神的独居。
“人的物化、物化的人、人/物相杂的描述所反映的,究竟是人的危机、人的终结,还是人的未来?”[2]只有洞悉人与物的原始关系,无论是回到东方的“心学”语境还是西方人对古希腊话语史的溯源,才能真正消解潜藏在媒介考古学中物之于人的压迫性,使媒介考古学中的问题意识得到消解。因存在论而提出的实体哲学在政治、科学上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人与物、人与心灵一旦经过非自然的撕裂,几乎无法缝合。
中国传统哲学的非实体观是一种强调存续的思想,在“道生之、德畜之”的模型中构建物与物之间自然过渡的运动态势,纯粹形而上意义的“物”被消解在“心”所代表的认识源头。与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间性论强调物的中间性、不恒定性。“机”作为间性哲学的核心思想,从“机会”出发,展开物形成的时间与空间,最终到达“机器”的怀抱,实现物的功能性,达到“万物与我同一”的境界。至此,实体哲学[3]带来的困惑与焦虑在东方思想的关照下得以显现:中间媒介物的死亡与重生不正是人的永恒枷锁吗?在媒介考古学的实体认识论中,物是多,不是一。因此,人独立于多,无法融入,与机器若即若离;而间性论更多能找到人与物的协同关系,从“天人合一”的背景中找到人的真正价值。
一、 媒体考古学背后的精神困局:实体论
(一) 断裂的视听历史
翻开任何一部法国人写的电影史论,从乔治·萨杜尔、丹·布朗或让·米特里,你就会看到卢米埃尔兄弟引领的是一种美学,一种植根于完整历史链条中被赋予崇高之名的思想。这伟大思想的主干又生长出后世无限的枝蔓,跟同样伟大的文学理论纠缠不清。而大多数德国人却从不把斯科拉达诺夫斯基(Skldanowasky)兄弟认作是电影之父,虽然他们比卢米埃尔兄弟更早“发明”了电影:“1895年11月1日,麦克斯·斯科拉达诺夫斯基的‘动图幻灯片作为冬园综合节目之一上映,成为德国首场公映。这场综合演出和马戏不仅促成了电影的诞生,还带来了让电影走进大众娱乐世界的布景、氛围、绚烂和刺激。”[4]威廉二世的军事幕僚们把皇帝不受欢迎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好的宣传家,似乎也有其道理。克拉考尔在流亡美国后开始艺术史研究,最后确定了历史与“物质现实”的辩证关系,提出了颇具争议性但又令人信服的民族心理观。法国人明显在电影的实践中抬高了其艺术身价,而德国人却始终务实地从物质性(商业)出发,取得了第一轮竞争的胜利。第一部在美国大获成功并被冠以艺术之名的欧洲电影,是《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这个影片由戈尔德温影片公司于1921年发行。由于没在纽约发行,票房上失败了。尽管在商业层面不甚光彩,但在小影戏院运动的各个成员单位间却影响巨大,被认为是第一部欧洲艺术影片。”[5]
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混合着精神分析流派的话语体系,不仅突破了好莱坞的市场壁垒,还击退了苏联以“莫斯科艺术剧院”为名而制作的大量影片。好莱坞是高高在上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宫殿,德、法、瑞、意、英伦为代表的欧洲电影只不过是世俗的神庙。从中世纪开始,德国人相对于其他欧洲列强,对经典充满着年轻人特有的批判性。当然,这种批判性在政治层面无异于毁灭世界的核弹,但在历史哲学领域,却无疑充满了光辉。“近代德意志戏剧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不受古代悲剧影响的时期。仅这一点就证明亚里士多德并非一统天下。”[6]德国学者的文本中蔓延的本雅明式的批判一直延续至今,他们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率先举起反抗“赎罪券”的大旗,同时也把神殿历史高高悬置在半空,进入到黑暗却充满偶然、异质性的物质时空中,探寻所谓的“深度”时间。
电影从众多有可能出现“媒介考古学”的“媒介”土壤中脱颖而出,已经说明了西方学者对“物”的概念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反叛依然从德国开始。电影无法像其他的“物”那样被瞬间把握住,不具备实体的特征,亦不能被完备地定义。电影史遇到的挑战最大,这也是动态图像文化重新被发掘的契机。埃尔塞瑟认为经典电影史的叙述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些也至少都是超结构的阐述,形构人们现在使用而且越来越依赖的科技——用个旧时代的字眼,就是意识形态。”[7]其根本问题在于线性历史的排他性组合方式,一如蒙太奇对观众产生的单向影响。对传统历史观念进行质疑有其深层原因,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占统摄地位后导致的社会问题使人们不再相信“进步”的合理性。早期电影实验设备的挖掘印证了历史其实是一堆散落的碎片,而不是连贯的结构性对象,是物的错误使用和归置,是不确定的未来。因此,回溯到媒介发生的碎片中,才能窥见那个导致了存在重大缺陷的“未来性”技术的死亡过程,找到修正未来的希望。
(二) 失败的媒介物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以热情的篇章所关注的所有人并不在于他们的博物学知识和历史影响力,而在于作者本人对他们命运价值的道德判断。“恩培多克勒,这位‘领航人,就像潘提亚在荷尔德林的悲剧片段中称呼他的那样,比他的死更加使我感动的是他的一生,就是由荷尔德林又一次用他自己的那些令人神往的诗句表达出来的他的思想所告诉我们的他的一生。”[8]45在明显歌頌恩培多克勒的章节中,齐林斯基又连续列出了一长串名字:图灵、维那、薛定谔和德莫克里特。这些科学史上的巨匠们在媒体考古学家的书本中以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姿态被重塑,甚至被写进神谱。作者热情地提到了恩培多克勒那双坚守在泥土中几千年的凉鞋,赋予它科学和理想的统一精神。古希腊哲学家被编织进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者的谱系中,后面的名字是波尔塔、基歇尔、普尔基涅、隆布洛索、加斯捷夫。这些游荡在机器草图和实验模型间的圣徒,追逐光、热、电、化学、生理学、解剖学、植物学、文学、艺术、技术的全面创新,与谋杀、梅毒、监禁、纳粹及斯大林主义擦肩而过,只有一张巨大的世界空间拓扑图能够将这些观念联结在一起。
犹如琥珀(electrum)一般,死亡即新生,电力的诞生让媒介考古学家认识到死物的重要性,失败的物足以使他们倾注心血,以完成技术“尚新”之时的通灵仪式。草原真知子在《Baby Talkie,家庭媒介与日本现代化》[9]一文中复活了曾经的“死物”,一个类似走马灯的儿童玩具,一种以技术取胜的新媒介,它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都有着很深的影响。科学观念、现代家庭生活方式、资本主义政治思潮及全球化在“Baby Talkie”大量生产的年代由此撒播开来。隐秘和公开的场域都无法阻止人们对视听产品的热爱,随之以技术性进行开发利用,一如当下的智能手机一样,泛娱乐性成为家庭时光的重要表征。如同所有伟大的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物”一样,技术性亦带来其“死亡性”,是西方物质文化当中实体论的悲剧性赋予该物的第一性。由此,媒介考古学家才极力挖掘其“技术尚新之时”[10],以彰显技术的开拓者们崇高的悲剧性。媒介考古学至此已经成为了古希腊悲剧的“恋物者”改编版本,以机器和技术取代了戏剧性叙事结构,完成了西方传统文化后现代性的话语转译。
(三) 错配的人
齐林斯基笔下的隆布洛索对罪犯头骨的记录和分析,至少启发了电影史上最经典怪物的诞生:尸块是物——弗兰肯斯坦是人还是物呢?玛丽·雪莱是否看过他的研究尚不得而知,但德国民间文学中早有“泥人哥连”的传说。弗兰肯斯坦对自己出现过三次认知:我是怪物——我是人——我是怪物。利用电椅治疗精神病人是西方医学界“引以为傲”的历史,因此电流的产生启发了西方人对生命的重新认知,他们第一次摆脱上帝并试图亲自去剥离灵魂和肉体。交流电之父尼古拉斯·特斯拉今天依然影响着大众媒介,他的信徒以他之名来彰显自己的高尚人格。肉体被与灵魂隔开后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浪漫派艺术的大发展,进而也建立了现代性恐慌模型。弗兰肯斯坦和《巴黎圣母院》中的怪胎,两个灵魂和肉体错配的人。德国表现主义电影[11]中有一个关于肢体重组的寓言:《奥莱克之手》讲述了杀人犯的手如果移植到具有良知的好人身上,依然会不受控制地拿刀杀人。
隆布洛索致力于寻求19世纪人口聚集的大都市犯罪频发的根源,当然,梅毒也是他不得不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一点揭示出波德莱尔之死似乎并不是特例,而是一种社会性事件。“体重和身高、毛发、胖瘦、血液、头颅、大脑、尿液分泌、经期、感官感觉、性敏感度、廉耻感、痛感、残暴程度以及其他一些参数,这些都以统计数据的形式表现出来,又使得彼此之间产生多重的相关,为的是得到最为重要的诊断结果……”[8]211他认为女性犯罪的原因是她们的身体劣于男性的身体,是错配的人。
身体零件自身的错误搭配、灵魂与身体的错误搭配都导致了失败的结局,与所有的中间媒介物一样,人的崇高、善良等美德被埋没在制度建造者的蓝图中。弗兰肯斯坦的新娘也被文学和电影“制作”出来,使本来已不堪重负的男主人公在精神层面得到了一丝慰藉。中国大陆导演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中,王志文饰演的文明戏导演拿着女人大腿的戏份足以成为中国媒介考古的重要目标。人的灵魂脱离于实体而寄居他物,是西方当下泛娱乐的重要母题,也是各种朋克世界观得以构建的基本理论,是西方人摆脱身体灵魂错配的大众寓言。
二、 中国传统艺术哲学背后的精神乐园:间性论
与实体论不同,中国传统艺术哲学强调事物的非实体部分。任何事物均处于运动发展的“间性”位置,不强调其观念性本质,摆脱事物的本质——现象二元论,而以“阴阳、强弱、曲直、虚实、隐显、藏露”等非实体性对立情状替代实体论中的存在、范畴、概念、属性等单一维度的意向性话语。换句话说,间性论(interalogy)是用对时空运动连续体的合理描述来取代形而上学的罗格斯方法。“人们之所以对这些概念及其所对应的现实感到陌生,是因为自柏拉图以来,哲学甚至连近代的中国哲学研究,都是以本体论(ontology)为基础和出发点的。间性论提供了一条不同于本体论的‘新的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思路、方法和范式。这个‘新之所以被打上引号,是因为它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古典哲学中就已生根发芽,并在‘百姓日用而不知中成为中国文化的思想根基。”[3]间性论的根本在于万物统一于道,人与万物并未有绝对的隔阂,而是“相生、相克、相几、相像、相济”的关系,人的根本属性是居于动物性和神圣性之间的,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就是对道的尊崇与信仰。由此,历史亦是从道中衍生而来的具有统一性的间性对象,是为“春秋”之间也,与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保持一致,形成历史与文化的一体两面状态。
(一) “几”(幾)—与“戈”相倚—幸福的人
对传统艺术哲学起到重要作用的间性论观念以“几微”开始,逐渐演变成“形、势、象、意、境”等相辅相成的时空单元。“间性思维还体现在对事物的运动变化态势的认识上,如中国哲学与艺术中所说的‘不得不然的‘势、《周易》中所讲的作为‘权之始和‘变之端的‘几微,都并非实体性事物,而是事物存在的状态。”[12]所谓“几”,是指人的意识勃发的初级状态,是意念对客观世界进行关照的持续状态。“几”通“机”,是事物发育发展的“枢机”,是运动冲突的关键性因素。根据周敦颐的总结,儒学亦成为“通几之学”,是孔子讲的“克己(几)复礼”的核心要义。《通书·圣第四》:“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几”所以是“有无之间者”,意味着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以“几”为主导的,是事物诞生的原初动力。而“几”之中,也隐藏着中华视听史的关键要素。“几”的繁体为“幾”,右侧形部为执戈之人,且戈上有丝带装饰。这是隐含在文字中的密码:审美与武器的统一场域。中国的先民从战争中发掘到审美的意味,体验到主观心性和欲念的重要性,以极富诗意的智慧把视听体验用文字媒介记录下来。
李笠翁在《闲情偶寄》中向世人传播了一种中国式的器物文化观,而他自己又以戏曲理论家闻名于世,这种双重身份使我们能更加便捷地对传统世俗生活和艺术进行审视。李渔的写作被认为具有中国特有的“乐感文化”,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他不同意那种悲观主义的偏颇态观念,而相信世界和人生尽管非常不完美,可总的说来还是可爱的,足以使人满意的,人类还有爱情、家庭温暖和友谊,有读书、写作、闲谈、散步、垂钓、种花、莳草和发现、发明之乐……喝茶、品尝美味,等等。”[13]李渔倾心于视听(舞台)艺术,并能通过自省认识到自己无法达到传统儒家的世俗要求,转而追求对物质的探究。这一转变跟西方媒介考古学对欧洲大陆哲学体系的背叛有异曲同工之处。与齐林斯基及笔下隆布洛索等与时代脱节的人相比,李渔对活人更感兴趣,他的工作更具有时代性和享乐主义。而西方人更喜欢从新柏拉图主义开始的苦行,与宗教宣扬的“施虐——受虐”后的精神反思有关。
通过对心物之间“相几”关系的探讨,即心灵对不同对象的审视与反向回馈接收,中国人与自然对象或人造对象的关系处于和谐的状态,本质上都是对道的体认。因为这种和谐共处的心物观,人得到美的财富,形成了健康的人格(君子人格),从而实现幸福。西方人因为无法平衡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很难得到这种幸福,总是寄希望于个体的绝对自由。因而西方的形而上学实体论,是一种把人归于绝对范畴的哲学。
(二) “戏”—与“戈”相生—连续的视听历史
中国的视听媒介史在近代西方以电影机器为代表的工业潮流中逐渐湮灭,成为需要保护的民族资源。然而,无论西方机器的入侵如何激烈,以“戏”为代表的视听媒介依然保持了自古以来的社会功能和存在状态,并反向对现代视听产品进行同化。在中文中,“戏”可以是“戏剧”,也可以解读为“游戏”“戏耍”,强调感性上以情绪为关照对象的语境,兼有娱乐的意味。戏的繁体字是“戲”,《说文》中解释为“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14]也就是说,从形声角度考虑,与兵戈相关,与战事有关。与此同时,“武”字也从“戈”,而音韵相通,武通“舞”、通“巫”,因此早期先民的审美关注对象从视听层面来讲都与军事斗争有关。所谓“三军之偏也”,进行合理推论,是指辅佐部队的专门队伍,与现代军队中的文艺团体相当,以歌舞、形体鼓舞士气[15]。从古希腊史诗及世界各民族史诗亦可以看到,先民对武装斗争的关注是超越其他事物的,审美领域也不得不受其影响。
从古代巫术仪式向成熟戏剧过渡的历史中,不论舞台、道具媒介物如何变迁,都必须在“戏”构建的理念和审美范式中进行创新。武、舞同源,戏剧又以乐舞、歌唱制成综合性表现形态,但都有“戈”的部分贯穿其中,因此,武器也成了早期文化艺术中最重要的实物媒介。戏曲艺术成熟以后,基本形态又分为“唱、念、做、打”,基本叙述类型可分为“文戏、武戏”。类似今天动画作品的皮影戏更是以武打作为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因此,中国古代视听史以“戏”的观念而非媒介物构成(电影影戏观也受其影响),以道的统摄性取代了西方实体论对不断分化的媒介物的追逐,从而消解掉对“死物”考古时的悲剧性。直到今天,以“兵戈”产生的鼓舞属性为核心图腾的艺术仍然是中华艺术的主流。
(三) “我”—与“戈”相济—鲜活的媒介物
既然儒学是“通几”之学,要义在于“克己复礼”。礼即理,是对道的回溯。“己”通“几”,认识自己即需要认识自己的心性欲念,才能认识自我,进而反思自己,达到“修身”的目的。认识自我只是第一步,目的是认识到“我”——“以手执戈”的威仪,即审美意识。因此,“通几”,也是通向审美活动的途径。中国视听媒介史当中,不存在所谓线性和非线性观念,只有统一的审美追求,即以戏剧视听语言为标准。物存在于“道德”与“形势”之间,是这两者的现象符号,因此从物到审美是直观可通达的,无需西方存在论美学的推论与还原。因为其直观的审美性,因此,东方的物是鲜活的,媒介亦然。
即使今天,戏曲的创新也要符合传统唱腔的审美规范。在戏曲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媒介物当中,每一种都有独特的审美功能,不会像西方媒介考古学中的“死物”一样因为失去其使用性而丧失其他属性。千百年来,梨园丰物不过“选资、修荣、治服、习技”所需而已,人们亦不谈论物的生死;物只在人主观感受到“万物与我同一”的情境时才具备生命特征,譬如对于造纸术的认识。《天工开物·杀青》篇写到:“物象精华,乾坤微妙,古传今而华达夷,使后起贪生,目授而心識之,承载者以何物载?”纸作为最重要的媒介物,承载着历史更迭、人间教化,因此,物对于古人而言,没有无意义的物,必须有其超越性的使命。中国人不太关心造纸技术的“新”“旧”之别,只关注其“物以载道”的功能。西方媒介考古学注重对媒介物使用性之时效性进行批判:“‘时间是媒介考古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媒介考古学的历史观常常被表述为‘非线性的历史观,其中就蕴含着如何看待‘时间的问题。”[16]这里的“时间”即齐林斯基从古生物学考古中提出的“深层时间”概念,摒弃那种从革新、进步的线性时间观,选择以早期生物多样性发展为代表的平行时间观。中国的审美活动在“物我两忘”的“物与我”之间,忘却的当然也包括“时间”,庄子分不清自己和化蝶的关系,当然不会在意我变成蝴蝶的时间问题。在审视历史的过程中,中国的间性审美观念不会在意卓别林先拍默片再拍有声片的问题,只会以“卓别林美学”进行共时性关照。
三、 通“机”之学——从“机会”到“机器”
从间性论出发,寻找非实体哲学的关系构型,推理出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是永恒的运动,其载体是空间与时间。从间性哲学的认识论来看,“几微”是运动尚未开始的酝酿阶段,如“桃之未兆、婴之未孩”,而物的形成是人的心性与物“相几”所产生的结果。任何物的存在必须首先有不同“心机”的交汇,即“机会”;通过人的实践赋予其时间、空间、材料,以容纳这种运动,形成物即“机器”——机之“器”也。器是“机”的实体部分,是间性哲学对实体的描述,是指物的空间性延展,比实体哲学更强调过程性与关系性。媒介的发生与发展通过间性哲学心物——物物“相几”的特征来进行关照,可以有效对实体哲学媒介观中的机器恐惧进行消解:物与人并非控制与反控制关系,而是处于从“机会”到“机器”的循环的两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居于物之间,物居于人之间。
(一) 媒介的发生——“机会”
间性论视角下的旧媒介与新媒介从属于不同的“相几”结构。
中国传统视听媒介装置纷繁复杂,除了走马灯、皮影戏以外,各民间曲艺流派都有自己的专用道具,其目的是创造经济价值。文人墨客以“琴、棋、书、画”为媒介,出于传递价值、传承文化、修身养性等目的。大型媒介物的出现背后是迫切的传播需求,如王权所需的政治传播手段必须足以对受众心理产生巨大的控制,如殷商时期青铜鼎器的铸造。根据加拿大学者伊尼斯对传播语境的分析,对时间和空间的偏好是媒介物形制需求的关键[17]。时间、空间,都是间性概念,非实体结构,是媒介物形成的必要条件。而媒介发生问题,除了社会动力以后,需要充分的信息、正确的决策及其他物质条件——总称“机会”。这里的“机会”,指旧媒介诞生所需的各种物质间的相互关照关系,引发了人为的实践活动,体现出旧媒介的物物“相几”属性,也体现出旧媒介在时间上的低效性,在空间上的统治性。
新媒介的诞生,使得丰富多彩的媒介物被一种统摄性的技术所取代,反向引起人心性欲念的勃发。“在维多利亚时代,一种有效的长距离即时通讯技术诞生了,前所未有地将全世界更加快捷也更加深远地联系在一起……革命性地改变了商业模式,诱发了新型犯罪,并将它的使用者湮没在泛滥的信息洪水之中。”[18]互联网作为划时代的新媒体,其实在维多利亚时期已经建立了,它们大大缩短了人们传递信息的时间。马化腾亲口承认,在创立QQ软件初期,也亲自参与一线营销并冒充女性陪男客户聊天[19]。《周易》屯卦六三爻辞:“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不论是维多利亚时期诱发各种犯罪的互联网,还是后来腾讯公司的成功,都是新媒介兴起的典型案例,都离不开人心中稍纵即逝的欲念,产生“君子几”的感受。因此,媒介本身与道德无关,只有使用他的人需要承担后果。媒介物的产生,是所有动念的心灵共同促成的,是无数“几”的交汇,也是引起心动的那些物象产生的后果。心物“相几”,体现出新媒介在时间上的高效性,在空间上的虚无性。
新媒体主要以人的心性之间“相几”构成发生的潜质,媒介物被工具化,失去了自己本身的价值,成为媒介考古的“死物”;而旧媒介以物物之间“相几”的关系而使自身成为媒介的一部分,不断散发新的活力。旧媒介走向艺术,新媒介走向技术。
(二) 媒介的形成——“机器”
“机器”包含时机(心性欲念释放的节奏)、一段时间的持续性实践、物质材料的加工以及媒介物最终的形态。它本身并不承担媒介职能,只负责媒介技术的发展。从“机会”到“机器”,有一个转化过程,旧媒介是“机会”—媒介物—“机器”,新媒介正好相反:“机器”—媒介物—“机会”,媒介物始终居于自己的命运的两端。
旧媒介与新媒介发展过程中的“机器”阶段是不一样的。旧媒介从“机会”出发,寻找合适的物,通过实践加以改造,使物媒介化,形成跨越时间的存在。《左传·宣公三年》有关于铸造带有饕餮纹饰青铜大鼎的介绍:“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这里的青铜材质与饕餮纹都在传播统治者的意图,使人有敬畏之心。用重器以载大道,是古代媒介物对物物“相几”产生的“机会”的合理利用。而成为“机器”后的媒介物走向了艺术的角度,跨越式发展成另外一种媒介。新媒介首先依靠新的“机器”,引发使用者的心性欲念,使无数的人心“相几”运动,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旧交替,退出历史舞台。
因此,西方媒介考古学也可以说发源于“现代性”技术焦虑症,为了不断引发欲求不满的心性能量,必须不断制造可以利用“机器”的机会,使人落入恐慌的陷阱。于是,随着技术性“机器”被不断制造出来,商品经济得到巨大发展,人们从旧世界的思想牢笼中摆脱出来,逐渐脱离土地和沉重的旧媒介,转而投身到新媒介所需的庞大“内容”产业中。内容与机器不断循环往复,机器不断升级改造,内容又推动着社会思想的变迁,这就是新媒介的历史作用。只是,这种社会价值却不能够消解人在机器海洋中陷落的苦闷,人们在看到媒介机器失去其鲜活性时会产生巨大的失落感。怀旧这一经典母题在传播学话语中始终有其价值,也与人对生命的鲜活性渴望有关。
面对制造新媒介的“机器”,不仅要挖掘其“技术尚新之时”的价值,还要前溯到媒介物形成后的“机会”阶段,发掘出由人性刻画的隐秘纹饰,使其彰显人在“机会”—“机器”相互转化中的核心位置。这亦是间性论对实体论媒介观的消解,对现代性问题的东方回答。
四、 结语
西方媒体考古学建立的基础是历史断层中消亡的媒介物。“在研究各种先进的媒体技术的同时,会越来越倾心于某些古代的幻想家和造型家,而對于他们这些人,我在我接受大学教育时从来没有接触到,那时,实际上是把他们排斥在媒体科学的讨论之外的。”[8]11之所以齐林斯基和其他媒介考古学方法的拥趸会重新发现古代的媒体遗迹,主要还是背后人的历史境遇。从其他途径(文学、艺术、主流学术)很难了解到的人从媒介的化石断层中站出来,给了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和文化的机会。从表面看,他们追求“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历史碎片,实际上在呼唤采取合理的方式对待人身上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倾向。近代西方哲学以反理性对抗理性,以现象学抵抗二元对立和形而上学,均不能解决西方文化中人的“罪性”和悲剧性。而间性论告诉我们,人是媒介物产生的起点,媒介物的“生死”是人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交织的产物,物象是居间性、中性的,人与物是生态链的不同环节而已。最终,媒介考古学对人本身的认知问题得到消解,用传统艺术哲学的审美姿态吸收掉现代性焦虑。
[参考文献]
[1] 列奥·斯特劳斯.德国战后哲学的现存问题[M]//何祥迪,译.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斯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第2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67.
[2]孟悦.什么是“物”及其文化:关于物质文化的断想[M]//孟悦,罗钢.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
[3]商戈令.间性论撮要[J].哲学分析,2015,6(06):54|65,193.
[4]Klaus Kreimeier. The UFA story|A History of Germanys Greatest Film Company 1918-1945[M].Translated by Robert and Rica Kimb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5.
[5]Tony Guzman. The Little Theatre Movement: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Art Film in America[J].Film History,2005,17(2/3):261|284.
[6]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M].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76.
[7]托玛斯·埃尔塞瑟,于昌民.媒体考古学作为征兆:(上)[J].电影艺术,2017(01):75|83.
[8]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媒体考古学[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9]埃尔基·胡塔莫,尤里·帕里卡.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M].唐海江,主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20|144.
[10]施畅.视旧如新:媒介考古学的兴起及其问题意识[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07):33|53,126|127.
[11]熊文醉雄.德国表现主义电影艺术特质浅论:从《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到《大都会》[J].戏剧之家,2010(04):57|59.
[12]黄念然,杨瑞峰.间性与中国古代艺术结构创造[J].江汉论坛,2018(04):88|93.
[13]胡元翎.李渔小说戏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23.
[1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团结出版社,2020:1576.
[15]林和.九歌与沅湘的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0.
[16]罗艺.媒介考古学的历史、方法及走向:兼评《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J].新闻记者,2020(05):88|96.
[17]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7.
[18]汤姆·斯坦迪奇.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M].多绥婷,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15.
[19]马化腾.马化腾自爆冒充女孩子陪人聊天[EB/OL].爱奇艺,(2018|12|18)[2022|10|09].https://www.iqiyi.com/w_19s3x1nxnt.html.
(責任编辑文格)
From “Opportunity ” to “Machine ”:
Chinese Philosophy as a Resolution to Media Archaeology
XIONGWEN Zui|xiong
(School of Arts,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Hubei,China)
Abstract:Media Archaeology was inspired by film archaeology in the early cine|machines.Its affected by two reasons: the first one,“French Annals School” changed to make researches on “the film in the history” from the opinion of “the history in the film ”;the second one,“knowledge archaeology” and “genealogy” of Foucault broke the continuous chain of history.The finding of “deep time” and the describing of “variety and heterogeneity” all embody westerners worries about the nihility of media history as well as the doubts of pursuits of human subjectivity.With the help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interology),a circulation model of “opportunity|media|machine” could be established to solve the confusions: interolory excludes the separ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material but emphasizes the ecological ideas of human being,heart and material in which existed a “xiang ji” construction that setured the broken media history; The media art concept of “I and material equals one”,“I and material forget each other” make the “abortive” media materials alive; The identification to “tao” cured the illness of “body|heart” mismatching.
Key words:media archaeology; the history of audio|visual media; interology; xiang ji; Tao
(上接第111頁)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patial Dubin Model
LI Shen|yan HU Shao|bo
(1.School of Economics,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Hubei,China;
2.Shizhen College,Gui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yang 550200,Guizhou,China)
Abstract: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core of the overall modernization,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enterpri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direct ac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 spillover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e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uses SDM to test empirically the direct and spatial effects.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Firstly,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and direct promotion effect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i.e.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will drive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this region.Secondly,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which mean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in this region will drive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surrounding regions.Thirdly,the depth and degree of digital finance use have significant direct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hat is the stronger the depth of digital finance use is and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digitization develops in the region,which can improv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enterprises in the region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Finall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ing digital finance,policy recommendation has been put forward to promote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improv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increasing the depth of digital finance use,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regions in China.
Key words:digital finance;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patial Dubin Model;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