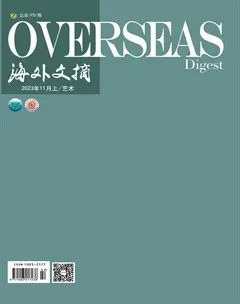跨文化交际中社交语用失误的成因分析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由于缺乏对不同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或者忽视对具体语境的考虑,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的发生已成为普遍现象。本文区分了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旨在从理论背景和案例研究的角度分析社交语用失误的成因,以期帮助外语学习者增强跨文化意识,提高语用能力,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随着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与普通人的生活联系也日益密切。与此同时,由于在社会环境、历史文化、地理风貌等多方面的差异,跨文化交际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障碍。其中,语用失误是跨文化交际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也是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深度分析语用失误成因对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语言学家珍妮·托马斯(Jenny Thomas)首次提出了语用失误这一概念,并采用二分法将其分为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这为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及其原因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年来,纵观国内外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大都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对比和分析。虽然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而对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没有明确地进行分析。本文则缩小研究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交语用失误层面,以期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来揭示社交语用失误的各种原因[1]。
1 社交语用失误概述
首先,明确语用失误这一广义概念是非常必要的。语用失误这一概念最早由珍妮·托马斯提出,指的是听话者未能理解说话者话语的用意。在珍妮·托马斯看来,一个人如果在表达思想时犯了语法错误,就会被认为是“说得不好”。然而,如果违反了诸如礼貌原则等交际原则,则会被认为是“表现粗鲁”或“不真诚、不诚实、居心不良”。在中国,学者何自然认为,所有导致交际失败的错误都被称为语用失误。
在语用失误这一大范畴下,珍妮·托马斯进一步指出了如何区分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珍妮·托马斯指出,当说话者赋予某一句子的语用力量与以目标语为母语者最常赋予该句子的力量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时,或者当将第一语言中的言语行为策略不恰当地转移到第二语言时,就会发生语用语言失误。简言之,语用语言能力意味着恰当地使用语言来完成言语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语言学习者会受到母语的影响,将语义或句法上与目标语表达等价的句子转移到目标语中,但这并不正确,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交际习俗。
与语用语言失误相比,社交语用失误不仅涉及交际者的语言知识,还涉及交际者的文化知识。因此,社交语用失误指的是交际者不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没有选择恰当的语言而导致的错误。在跨文化交际中,社会价值体系的多样性和思想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并不总是能得到很好的解释。此外,与社交语用失误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情境知识。语用参数包括时间和空间、语域、正式程度、角色和地位、信息传递媒介、主题等。如果一个参数发生变化,其他参数也会同时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境下说得恰当的话语在另一种情境下可能就不适用了。因此交际者应注意语用参数的任何变化,否则可能会出现社交语用失误。由此可见,社交语用能力可以归纳为在特定语境中言语行为的恰当性[2]。
值得注意的是,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绝对。在不同的语境下,或从不同的理解角度来看,一些错误既可以归为语用语言失误,也可以归为社交语用失误。
2 社交语用失误成因分析
2.1 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在东西方文化中,主流价值观的推崇是有一定差异的。在多数东方文化中,尤其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更加推崇集体主义精神而非个人主义。以社区为导向的社会不仅强调个体对他人的责任,也关心个人的自我反省和成就。相比之下,以个人为导向的文化高度重视人们的自我价值、功能、尊严和利益。它倡导自由、平等和友爱,鼓励人们追求自我独立。这一观念在语言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self-reliance”和“self-esteem”等表达自我意识的词汇在英语中很常见。此外,英语是世界上唯一将“I”写成大写的语言。
2.2 民俗与宗教信仰的差异
作为文化历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民俗是一个民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以及心理结构的生动写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习俗,它们承载着特定的情感。在跨文化交际中,各国习俗的不同必然会产生社交语用失误。例如,“禁忌”这一现象在民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禁忌是指“不能说和不能做的”。由于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禁忌”引发的语用失误迫切需要关注。例如,在西方某些国家,数字13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因此应避免使用。在日本,数字4和9备受鄙视,因为它们的发音分别与“死亡”和“苦涩”相似。在中国,人们倾向于用“老”来表示尊敬和赞美,但这在西方人看来却暗含贬义。为了避免此类冲突,交流双方应学习不同习俗的独特特征[3]。
宗教因素有时与习俗相互影响,使交流更加复杂。宗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因为人们依赖一些抽象的精神来指导日常生活。在英语国家,大多数人信仰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世界的主宰。根据其原则,人生而有罪,因此必须用生命来赎罪。然而,在中国文化中,由于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情况并非如此。这些思想相信苦难对人的塑造有积极意义。在跨文化交流中,交际者不能用本国的宗教信仰去评判他人,以免产生误会。
2.3 母语文化的干扰
当交流者来自同一文化背景并共享一种文化,他们之间就很少能看到文化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仅在个人知识、文化素养和信息方面有所不同。但在跨文化交流中,除了这些因素外,文化影响尤为突出。研究者盛炎曾说:“在人们学习第一语言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自我认同。由于第一语言与其关系密切,其第二语言的学习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自我认同的影响。”他的观点指出了母语对二语习得的文化干扰。在学习者接触外部世界之前,他们已经拥有一个包括价值体系、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认知风格、语言模式等在内的本土文化模式。当置身于全球背景之下时,交流者会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参照现有的思维模式来应对他人。这种现象被称为语言迁移,它指的是将先前的学习带入新学习情境的心理过程。
语言迁移可分为正向迁移和负向迁移。前者是当两种文化有一些共同之处时,了解一种文化将有助于学习另一种文化。但后者则意味着干扰。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越大,误解发生的概率就越高。当人们试图在交流中找到他们母语中的对等词时,社交语用失误就会通过负向文化迁移发生。例如,中国学生在翻译相关谚语时往往会基于表面词语进行直译。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英文翻译为例,多数人往往会基于中文结构将其直译为“有人更喜欢萝卜,而有人喜欢青菜”(Some prefer radish but others prefer cabbage)。而这一翻译在西方文化中却无法理解,因此需要根据文化差异将其意译为“胃口偏好”(Tastes differ)。多项研究表明,负向迁移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发生。一个常见的因素是学习者的水平,即较低水平的学习者更容易发生负向迁移,因为他们在目标语言中可用的资源较少。
2.4 不恰当的教学方法
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在国际交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开设英语教学有助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中国已开设各层次英语教学课程多年,然而现如今的教学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教科书、教学方法和教师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许多教科书缺乏文化背景知识。在教学中,许多材料过分强调语言规则,即局限于单词、语法、句型等单方面的操练,很少强化交际功能。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常见到如表1机械练习表:
这种练习确实有助于学生掌握语言结构,但却忽略了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境。因此,学生认为只要他们能够成功背诵这些语法规则,就可以顺利地与英语国家交际者进行自然的对话。其次,由于各类考试的需要,语法翻译法在中国被广泛采用。使用这一传统教学法的结果是学习者语言结构方面表现优异,而实际交流能力却不足。第三个重要因素是教师的角色。作为课堂的组织者、参与者和监督者,教师应设计真实有效的学习任务,活跃课堂氛围,引导学生注重文化差异,以产出为目的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4]。
2.5 不同的非言语行为
跨文化交际中的社交语用失误不仅来自言语行为,也源于非言语行为。非言语行为,如面部表情、手势、声音和谈话者之间的距离,能够表达语言无法表达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恰当的体态语可以使交流变得更加轻松有效。例如,握手作为全世界通用的手势,被视为问候的信号。但有时体态语也可能引起误解,因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往往用不同的形式表达相同的信息或对相同的体态信号有不同的解读。例如,点头通常表示“同意”,但对一些印度人和一些因纽特人来说,它并不意味着“是”,而是“不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社交距离的差异。阿拉伯人喜欢身体接触,他们见面时经常拥抱对方并触碰对方的鼻子。但日本人见面时却显得极为正式,并且肢体触碰是不被接受的体态语[5]。
因此,为了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流,交际者不仅需要知道“说什么”和“怎么说”,还需要知道“如何行为得体”。换句话说,他们应该能够恰当地使用言语语言以及与该特定语言相匹配的非言语行为。
3 结语
综上所述,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的发生是极为普遍的,因此能够正确区分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对交际者寻求相应的解决对策是至关重要的。语用语言失误呈显性特征,学习者可以通过加强对目标语言的知识理论学习从而减少此类错误的发生。而社交语用失误的成因较为复杂,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需要交际者深度挖掘隐形的原因。本文通过具体例证,从五大方面系统分析了导致社交语用失误的许多因素。交际者应根据具体语境,关注文化差异,从价值观体系、习俗、宗教信仰、第二语言习得和学习方法等多方面提高语言交际能力。■
引用
[1] Gass, S.M. & L. Selinke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 Introductory Course [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1.
[2] Jenny Thomas.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3,4(2):91-112.
[3] 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4] 盛炎.语言教学原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10:238.
[5] 张彦群.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文化原因浅析[J].天中学刊,2005,20(3)183-186+229.
作者简介:高晴晴(1991—),女,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讲师,就职于嘉兴南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