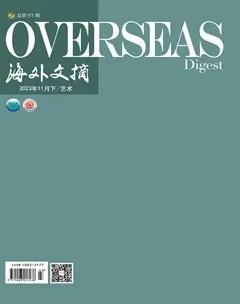《牧誓》文本价值考
王国维曾提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西周初期,是周礼形成的重要时期,《牧誓》作为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不仅反映出周朝统治者的观点,也反映出周礼的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牧誓》作为“纸上之材料”证明牧野之战的真实性的价值必然不用再多说,但其中反映出的深刻的天下观、天命观、战争理念、女祸史观等,鲜被讨论。对《牧誓》文本价值进行剖析,深入探寻《尚书》所反映的时代思想,对丰富商周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从天下观、天命观、战争理念、女祸史观等方面出发,对《牧誓》的历史文本价值进行深入探讨。
1 《牧誓》展现出周人对商人天命观的承袭与发展
《牧誓》中体现出周人对商人天命观的承袭。一般来说,殷商时期人们信奉的神灵主要有三种:上帝神、自然神、祖先神。殷商时期,国家信奉的主要是上帝神,上帝神是可以命令自然神,并凌驾于祖先神之上的。然而在盘庚迁都后,随着商人不断地强化上帝神和祖先之间的拟血缘关系,商人也开始重视对祖先的祭祀。如《尚书·商书·盘庚上》中盘庚劝告臣民时,其中提到的一条就是:“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从与享之。[2]”此后,历代商王更高频地强调自己的先祖。《牧誓》中周武王对于商纣王的指责,其中第二条就提到:“昏弃厥肆祀弗答。”这里,周武王指责商纣王轻视对于祖先的祭拜,不予答拜。同样,《尚书·周书·泰誓》中也说:“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不仅指责商纣王不祭祀上帝神,也批评他不祭祀祖先。很明显,《牧誓》展现出周朝初期对于商朝的天命观的一种继承。
同时,《牧誓》也表现出周人对商人天命观的发展。《尚书·商书·西伯戡黎》中有记载,商朝的大臣祖伊劝谏帝辛,但是帝辛却自大地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商纣王十分自大,认为自己“生不有命在天”。这里表现出商人对天命的一种绝对笃信。正如邹国力在《周初的“天命”思想武器》中提到的,周初“天命观”最大的区别就是“天命靡常”[3]。换句话说,就是周人对于天命没有商人那么笃信,他们认为天命是可以转移的。结合《牧誓》可以看出,周武王所提供的伐商的一个核心理据就是商纣王无“德”。从个人品行上来看,商纣王好酒淫乐,沉迷美色;从祭祀上来看,商纣王不祭祖先;从人才任用上来看,商纣王不用同祖兄弟,而任用有罪之人;从对待民众上看,商纣王残忍暴虐、重敛苛政。而这种种都表明商纣王无“德”。相反,这也是在侧面表明,周武王本人有“德”,因此有资格行“天之罚”。现在,商纣王有“亿兆夷人”,但是“离心离德”,而周武王有“乱臣十人”,并且“同心同德”。所以,周武王可以代表上天征伐商纣王。因为,周武王有“德”,而天命是可以转移到有“德”之人身上的。《尚书·商书·汤誓》中商汤同样提出了“天之罚”,但是商汤在伐商之后,仍然心存惭愧,担心“来世以台为口实”。相较于商汤,周武王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惭愧,可见“天命靡常”在此时形成为一种正统的观点。因此,《牧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周初“天命靡常”的观点。
2 《牧誓》揭示了天下兴亡、国家更替的规律
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对于如何更好地治理天下,使得王权稳固,周人有自己的认知,《牧誓》对此有一定的反映。《牧誓》中周武王痛斥商纣王暴政,细数商纣王暴行。周武王既是在指出商纣王的无道之处,实际上也是在说明伐商的正当性。从天下观的角度来看,周武王的这段发言亦揭示了早期国家更替的几点规律。
一是民心所向者得天下。《牧誓》中周武王在誓词开头,先是慰问了遥远的西方的人,然后是各个友邦的君臣以及来自各个地方的战士;在誓词中间,痛斥商纣王无德,失去民心;在誓词结尾,又强调不禁止跑来投降的人。无论是对于敌方还是己方,周武王都极力争取团结,争取民心。《道德经》中提到:“圣人无平常心,以百姓心为心。[4]”《管子·牧民》中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5]”关于民心,一直是国家得以长久的基础。《尚书》第一篇《尧典》中便有提到百姓之重要性。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地更换朝代,始终在证明民心所向才能使得国家兴盛、政权长久。
二是节俭勤勉者得天下。《牧誓》中提到商纣王宠爱妲己,荒淫无度,耗费大量人力与物力来纵情享乐。这在《史记·殷本纪》中有更为详细的表述:“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最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6]”这里,足以证明商纣王的荒淫无道。自古以来,能够节俭勤勉的君主往往统治得更为长久。《尚书·周书·无逸》中周公总结殷商统治的经验,就举了多个例子。其从正面依次列举“肆中宗享国七十有五年”“肆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节俭勤政,体恤百姓,与商纣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只有不贪图享乐、廉洁清政的君主方能在位长久,为百姓爱戴。
3 《牧誓》第一次提出争取敌军归降的军事策略
《牧誓》中记载:“弗迓克奔以役西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禁止能够奔来投降的人,使他们帮助周国。这一策略实际上是为了争取敌军投降,瓦解敌方军心。《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周武王这边的军队则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百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从两军的战士数量上来比较,周武王率领的战士数量是远远少于商纣王的,想要赢取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不容易。此时,战前提出这样的策略对于争取民心是很有作用的。《史记》中又记载:“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商纣王的军队在正式开战时,纷纷倒戈投降,期待着周武王的到来。这说明周武王运用这一军事政策,争取到了民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牧野之战的胜利。文中详细阐述了周武王在战前对士兵的动员与训诫,这意味着早在商周时期,古代军事家对战争本质已经有了深刻理解,他们不仅重视武力等绝对的战争力量,同样也重视人心向背、战争谋划、战术运用等相对的军事力量。
对比《尚书》中记载的几场著名的战争,周武王的“弗迓克奔以役西土”的策略都是史无前例的。这首先表现出周武王个人超群的军事智慧,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出周王朝一以贯之的“敬德保民”的统治思想。“敬德保民”的核心是“德”。商纣王不修德行,不祭祖先,任用罪人,暴虐百姓,以致“天之罚”。周武王从商纣王的统治中吸取经验,认为避免“天之罚”的关键在于敬德保民,这是周礼形成的基础,是周礼的精神内核。不杀投降的人,并且让他们帮助周国的建设,毫无疑问体现了周武王的“德”。而这种理念也成为批判商纣王、伐商的合理依据,同时也从反面证实了“敬德保民”与天命之间的联系。周武王的这种理念,自公刘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诗经·大雅·公刘》中记载了公刘迁豳,率领百姓安居乐业的史诗;《尚书·周书·无逸》中记载:“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可以说,周武王所采取的这种军事策略,是周朝能够代替商朝的关键一招。
4 《牧誓》标志着女祸史观的初步形成
张菁在《中国古代女祸史观的源流——从“牝鸡之晨”到“嬖幸倾国”》中表明女祸史观“与天命史观、英雄史观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7]。同时张菁又指出:“商周更替成为妇女史上的分水岭。”《牧誓》正是一篇反映商周更替时期的文献,其中的女祸史观已经初步形成。《牧誓》中:“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说文解字》中解释“牝”的意思是“畜母也”[8]。周武王列举商纣王的罪状,首先指出的就是商纣王沉迷女色,而后才提及商纣王不祭祀祖先。在十分信赖天命的商周时期,女祸能够先于祭祀,作为伐商的首要原因。实际上已经说明,女祸史观在此时已经正式形成,并且是政权交替时候的重要理据。
《牧誓》中形成的女祸史观对后代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女祸史观自《牧誓》时期形成,而后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一直作为重要的上层统治观念被不断地强调与重申。如《国语·卷七·晋语一》中记载晋献公征讨骊戎,把骊姬俘获回国,并对她宠爱有加。这个时候,晋国大夫史苏告诫其他大夫:“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今晋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宠,虽当三季之王,不亦可乎?[9]”这里,史苏说晋献公本来就德行不高,现在还宠爱骊姬,并把晋献公比作夏、商、周三朝亡国的君主,认为晋献公也会重蹈他们的覆辙,“亡无日也”。又如荀悦的《汉纪》中记载汉成帝欲立赵飞燕为皇后时提到:“殷之兴也以有娥。亡也以妲己。[10]”又如《隋书·卷四十一·列传第六》中记载,晋王杨广想要纳南朝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为妃嫔,但是遭到高颎劝阻:“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11]”最终,张丽华被下令处死。另有许多例证,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5 结语
文献的价值可以根据其实现的价值分为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两部分,文本的现实价值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常常被讨论的,然潜在价值常常被忽略。《牧誓》作为一篇处于商周剧变时期的文献,其文献价值十分重要,其中的潜在价值更是丰富。根据前文所论,《牧誓》一文从天命观上来看,其反映了周人对商人天命观的承袭与发展;从天下观上来看,其揭示了古代国家更替的规律;从军事策略上来看,其第一次提出劝敌军归降的军事理念;从女祸史观来看,其标志着女祸史观的初步形成。总之,无论哪种方面,《牧誓》都展现出其丰富的文献价值,对前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今后的我们,依然会继续处在其在几千年前就构建出的精神理念与价值基础之中。■
引用
[1]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孔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 邹国力.周初的“天命”思想武器[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3(3):65-72.
[4] 陈鼓应.道德经译注[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5] 李山,轩新丽.管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9.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3.
[7] 张菁.中国古代女祸史观的源流——从“牝鸡之晨”到“嬖幸倾国”[J].社会科学战线,2013(11):71-77.
[8]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9] 薛安勤,王连生译注.国语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
[10] 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1] 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作者简介:李雪(1996—),女,河南信阳人,硕士,就读于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