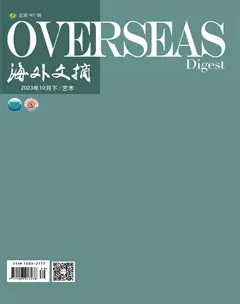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冲突
跨文化交际问题一直是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作为一部以婚姻为主题的电影,李安导演的电影《喜宴》通过展现同性婚姻和传统家庭观念之间的冲突,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碰撞。本文将通过对电影中的角色之间的互动、角色的语言和行为进行分析,运用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等理论,探讨电影《喜宴》中体现的跨文化交际冲突,旨在探讨跨文化交际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其体现的典型文化现象。
1 影片内容与主题
1.1 电影内容梗概
故事的开始以高母给男主角伟同的录音留言巧妙地交代剧情设定。男主角伟同是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有为青年,有一个美国的同性恋人赛门。租客威威是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偷渡客,靠在餐馆打工维持生计。她对伟同有些好感,租住在伟同破旧居民楼的顶层,但因为没有美国公民身份,她难以在美国立足。赛门同情威威,也为了应付高父高母的到来,提出让伟同和威威假结婚。起初事情似乎很顺利,老陈为高家筹办了一场盛大的喜宴,但之后威威的意外怀孕,打破了表面的平静,让谎言渐渐被拆穿。
1.2 电影主题与文化冲突之间的联系
在电影中,儿子伟同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理应承担起为家族延续香火的重责。但是,受西方开放文化影响的伟同,性取向却恰恰和父母的期望南辕北辙。所以,东西方文化观念产生了冲突和矛盾,并且随着剧情的进展愈演愈烈。儿子追求自由平等,需要个性的解放,主张尊重个人的私隐;而父亲更看重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为了延续家族香火,个人可以选择放弃感情和幸福,甚至通过父权来干涉儿子的私生活,进入伟同与赛门的世界。电影通过一个个精心设计的镜头,将中外文化冲突的细节展露无遗[1]。
2 电影中跨文化交际冲突的体现与原因
2.1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思维的软件》一书中说道,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而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与生俱来的集体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凝聚力,将人们天然地凝聚在一起,并对集团中忠诚的分子提供终生的庇荫。
当伟同父母寄来让伟同相亲的表格,伟同无可奈何又不得不撒谎地填写时,赛门表示很是不解,为什么伟同宁愿日复一日地说谎去应付父母,也不愿意直接将自己其实是同性恋的事实告知父母。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大部分人认为婚姻属于个人私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所以电影中的赛门作为个体出现,他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父母并未干涉他的生活和选择,电影中也没有出现过赛门的父母。
而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国家,强调集体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在婚姻中也重家庭,轻爱情,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是整个家族的大事,经过父母的准许是最基本的,而后还要广而告之,举办喜宴,亲朋好友还要给新人礼金以庆祝。婚姻的最终目的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家族这个“集体”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传承香火、延续子嗣的思想也在多处体现,比如高父虽然因重病住院却仍念叨着要伟同娶妻生子。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为了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伟同决定与威威结婚,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取悦父母,伟同不得不为了集体主义社会做出妥协。
2.2 高语境语言与低语境语言
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即为了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们在人际交往的时候在措辞和言语上会更加含蓄委婉,倾向于通过动作、表情、语调等微妙的信息来表达自身的意思。西方文化则是典型的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语言表达直白明快,直接地表露自己的意思,而不是拐弯抹角[2]。
电影中赛门第一次与伟同父母见面时,虽然伟同父母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为了表示对恋人父母的欢迎,赛门还是分别为伟同父母准备了血压计和抗衰老面霜作为礼物。赛门送礼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在送礼物时,表达得过于直接。给高父送礼物时,赛门说,“高伯伯心脏不好,血压高,有了血压计可以未雨绸缪”,高父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眼神也低垂下来,显得十分沉重;给高母送礼物时表示,“这是老年妇女用的抗衰老面霜,防止脸皮松弛”,高母即使理解赛门的意思,也显得有点尴尬。中西方语境文化的不同,让送礼物这一本来双方都高兴的环节,变成令中国父母感到不愉快的场景。赛门的礼物虽然实用,但他直接的表达让伟同父母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身体不再强壮,产生了消极的心情。
2.3 对不确定性因素的规避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霍夫斯塔德认为,“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3]”具体表现就是文化中的成员对于规则的需要,包括成文与不成文规则。
电影中对这一点体现最为明显的是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在上个世纪的美国,同性恋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人们可以大方承认自己的性取向,和恋人自由地生活在一起。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有着紧密关系。美国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美国文化丰富多彩、兼容并蓄,所以美国人在对待新事物上就显得更开放、主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接受程度更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农耕文明形成了自给自足、鲜少与外界交流的文化模式,再加上封建礼教长期对人民思想的束缚,中国人向来崇尚稳定的生活,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的行为接受程度较低。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都很难接受同性恋这一较新鲜的现象,体现了对不确定因素的规避倾向。
3 电影中的典型文化现象
除了典型文化冲突后隐藏的不同文化现象,影片中还有许多细节表现了一些典型文化特征,大部分是典型的东方文化特征,比如尊卑的分明、父亲在家庭中至高的威严、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思想、好面子讲排场等等。
3.1 高权力距离的体现
权力距离指的正是人们对权力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所能接受的程度,中国文化中的权力距离是较高的,权力较小的人对权力的不平衡接受度较高。电影中,高权力距离具体体现在高父与旧时下属老陈相处的这一情节。电影中威威和伟同公证结婚之后,四人恰巧在老陈开的中餐馆用餐。老陈一见高父便立即让服务员为他们免单并赠送菜品,对待高家一家毕恭毕敬,仍称呼高父为“师长”,称呼高母和伟同为“太太”“少爷”,哪怕老陈和高父已经离开部队多年,已经不再具有上下级的关系,理论上是平等的。由于我国高权力距离的文化背景,大部分人已习惯接受自己的角色并努力扮演好角色,也自觉维护尊卑贵贱有别这一观念。在部队里,高父拥有“师长”的角色,在家庭中高父也是权力的掌有者,全家都以高父的指示和态度为行事准则,这也是高权力距离的体现。
3.2 父权至上的体现
高父在家中拥有威严与最高权力,离不开父权制的影响。电影中,自高父来到美国后,全家人的目光便集中在高父身上。吃饭之前需要高父先品尝、点评;高父因伟同不置办盛大的婚礼而生气,怒而离席,全家人都十分惊惧担忧,甚至连赛门都感到害怕;当事情真相败露,所有人都想着如何向高父隐瞒,这些都显示高父在家庭中具有极高的威严。
3.3 传宗接代思想的根深蒂固
电影中曾不止一次提到“传宗接代”的台词。从一开始,高父在老家病重,也惦记着儿子还没有后,拖着病躯来到美国,监督孩子结婚生子;来到美国后,他又对儿媳妇威威种种评判,说出诸如“好生养”之类的话语;再到后来与伟同讲起过去与爷爷的事情,叮嘱伟同延续高家的血脉;至故事的最后,以假装不知道真相、妥协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只为能保住高家的孩子。“传宗接代”的思想贯穿整部电影。
4 解决跨文化交际冲突的方法
正如电影并不是为了提供解决冲突的方案,而是为了展现中外文化冲突这一现象,电影也没有给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电影的最后,父母让伟同追求自己的幸福,更像是一种妥协,一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做出的不得已选择。
在影片的末尾,高父在赛门的生日这天和他进行了一次单独的对话,并送给了赛门一份礼金,和送给威威的差不多。这时观众才知道原来高父早就知道了伟同的性取向,只是他一直闭口不言。父亲以另一种形式接受了伟同的选择,但是为了维持所谓的家庭颜面、为了传承香火而装作不知道。面对现实,父亲选择了妥协,这种妥协无可奈何,却也是一种在文化冲突中寻求平衡的态度[4]。电影中高父和赛门一起坐在阳光中,身上不见了往日威严,眼睛里也没有了往日的自信,反而神情淡淡的。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他也渐渐意识到他与赛门是平等的个体。电影的后半段,高父高母即将离开美国,全家人一起回顾婚礼相册,父亲的脸上泛起笑容,仿佛发生过的一切并不是谎言,他身上重新笼罩上了过往骄傲的光环。但是当看到伟同、赛门和威威三个人的合影时,高父高母被重新拉回了现实,画面仿佛停住了一般,他们脸上的笑容不再。起身道别时,他们将最初对威威说过的话说给了赛门,转身高父对威威说了句“高家会谢谢你”,这句话意味深长又无奈。父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做出了一定的退让,而儿子伟同重新组成一个特殊的家庭模式,既满足他对自由的追求,也妥协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两种文化终于在冲突与妥协中达到一种诡异的平衡,充满黑色幽默。
5 结语
电影《喜宴》展示了上个世纪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冲突现象。导演李安几乎客观地陈述了大的中外文化矛盾冲突在一个小的家庭中的具体体现,给观众提供了一个观察真实的文化交流的视角。但影片的结尾也向我们呈现了,文化的交流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5],只有依靠不同文化的人互相接受、求同存异,才能迈出跨文化交流的第一步。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流的加强,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如何恰当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更是至关重要。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定位文化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尊重其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积极提高自身文化适应性,让文化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交流中不断发展。■
引用
[1] 李冬花.解析电影《推手》和《喜宴》中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J].电影评介,2017(8):37-39.
[2] 彭世勇.霍夫斯塔德文化价值理论及其研究方法[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1):95-99.
[3] 肖仕琼.从霍夫斯塔德的文化价值观看电影《刮痧》的中美文化差异[J].绥化学院学报,2009,29(6):127-129.
[4] 谭凌霞.从《喜宴》和《喜福会》看中西文化差异[J].电影文学,2014(22):76-77.
[5] 陈建平.翻译与跨文化交际[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赵嘉宁(2000—),女,山东泰安人,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