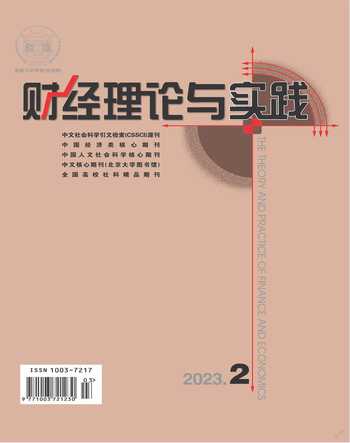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化转型与企业绩效
张志彬 陈卓 欧玲



摘 要:依据2011-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考量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服务化转型在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调节机制。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效应,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最适强度”。服务化转型通过收益竞争优势和成本竞争优势对“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绩效”发挥正“U”型调节效应,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长效激励”。对非高技术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东部沿海企业而言,服务化转型调节效应更显著。鉴于此,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化转型协同发展,持续提升企业绩效。
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型制造;企业绩效;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42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3-7217(2023)02-0122-07
一、引 言
创新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在于确立创新主体对行为利益独占的合法性,激励经济主体高效率与高附加值的产出[1]。服务化转型作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也会对企业创新施加正向引导,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2]。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将有效遏制竞争者“搭便车”行为和模仿侵权问题,保障企业创新的私有利益,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外部性”激励[3,4]。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强化领先型企业的技术优势,削弱技术落后企业的创新意愿,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外部性”影响[5,6]。知识产权保护的效应差异是否说明制造企业可以依托内部策略主动规避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利影响,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长效激励”?有待进一步研究。
随着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传统制造业“薄利多销”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7]。服务化转型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逐渐成为构建企业竞争新优势、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发展[8]、价值链地位攀升[9]等因素驱动企业将服务要素介入到研发、设计等价值链上游环节以及营销、品牌管理等价值链下游环节,进而增加产品和服务附加值,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2]。“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指出,要“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服务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资源投入和产出效率的影响为有效应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负外部性”、实现企业长期绩效增长提供了可能。
已有文献为理解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化转型产生的经济效果提供了有益借鉴。立足于提升企业长期绩效,服务化转型能否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从“最适强度”到“长效激励”的转变?依据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服务化转型对“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及作用机制。在理论层面,使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逻辑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服务化转型行为的研究更趋完善;在现实层面,将为企业优化转型策略,实现长期绩效增长提供实践指导。
二、理论分析與研究假说
(一)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分析
当经济社会处于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时,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正外部性”较为明显。首先,知识产权保护会巩固产权拥有者的垄断利润,为企业创新提供动态激励[10]。同时,知识成果被侵犯问题的减少,使得企业更愿意向市场披露研发项目信息,降低项目融资难度,推动成果创新与绩效提升的良性循环。其次,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意味着跨国公司向海外市场进行FDI和技术许可的防范警惕下降,从而增强了追随企业对高附加值技术和产品模仿的便利性和模仿深度,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11]。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断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负外部性”开始显著。首先,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使追随企业的模仿成本增加,即使企业调动内外部资源对高附加值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模仿,也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被领先型企业用更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替代掉,造成企业资源的浪费。其次,领先型企业可能采取价格或非价格策略对竞争企业进行打压,挤占后者的市场份额,造成弱势企业的绩效损失。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效应,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最适强度”。
(二)服务化转型对“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分析
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过程中对企业内部资源进行的多元重组,为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外部性”以及抑制知识产权保护的“负外部性”提供了支撑。
一方面,服务化转型将优质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投入到研发、设计等环节,有助于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激励;同时,服务化转型推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会有效改进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商业发展模式,推进企业的市场扩张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资源重组,服务化转型将构建更为高效的组织架构,降低企业运行的资源损耗。而且,服务化转型具备的隐性化等特征也有助于企业通过“隔离机制”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弱化领先型企业的市场势力[12]。
与此同时,制造企业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承担调整成本和竞争成本。一方面,制造企业将服务要素在产业链环节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会对企业原有的组织架构等进行适当调整以匹配转型的策略要求,因此导致企业在服务化转型过程中支付一定的调整成本[13]。另一方面,制造企业作为服务领域的介入者,在服务化转型初期往往需要承担进入新领域时的较高的竞争成本[14]。由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 服务化转型对“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绩效”呈现正“U”型调节效应。
针对假说2,服务化转型对知识产权保护“正外部性”的增强和“负外部性”的削弱将内化为企业的收益竞争优势,而调整成本和竞争成本将影响企业的成本竞争优势。因此,从收益端和成本端对服务化转型调节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解释。
从收益端来看。在转型初期,企业服务化转型提供的“产品+服务”的解决方案可能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企业绩效带来直接增长,而研发和培训等内部支持服务也无法在短期内实现企业核心业务能力的增强。随着转型的深入,企业坚持开展的外部产品服务将强化消费者的经济和情感粘性[15],研发和培训等内部支持服务也将对收益竞争优势形成技术性支撑,推动企业获取高收益回报。
从成本端来看。在转型初期,资源调配的合理规划和组织之间的重新磨合将耗费较大的调整成本。同时,制造企业也会支付较高的竞争成本,以获取服务领域的市场信息。随着转型的深入,企业内部对服务领域的认知逐渐加深,初期为进入服务领域所支付的竞争成本开始显著下降。同时,服务化转型组织架构的常态化运行也将降低企业的调整成本。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 服务化转型策略下,制造企业的收益竞争优势和成本竞争优势呈现正“U”型变化特征。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验证假说1,设定如下非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ROAit=β0+β1IPPjt+β2IPP2jt+θXijpt+ δt+μjp+εijpt(1)
为验证假说2,借鉴张峰等[16]的方法,建立非线性调节效应模型如下:
ROAit=β0+β1IPPjt+β2IPP2jt+β3SERit+ β4SER2it+β5SERit×IPPjt+ β6SER2it×IPPjt+θXijpt+δt+μjp+εijpt(2)
其中,ROAit为企业绩效,IPPjt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SERit为服务化转型水平,Xijp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δt、μjp分别为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省份固定效应,εijpt为随机误差项,t指年份,i指企业,j指行业,p指省份。此外,借鉴李仲泽等[17]的方法,在模型中加入时间行业层面聚类。为缓解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对交互项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参考顾海峰和谢疏影[18]的研究,通過总资产净利率(ROA)衡量企业绩效,使用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企业绩效的替代变量,用于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知识产权保护。借鉴仇云杰等[19]的研究方法,以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强度和执行强度的乘积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立法强度层面,由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上位法一旦出台,常常要求各地区在同一时期制定相配套的地方法规或规章制度,因而各地区在同一年段的立法强度基本相同。在执行强度层面,通过测算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法制化程度等5个指标的算术平均值衡量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强度。
3.调节变量:服务化转型。借鉴Fang等[20]的方法,使用服务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测度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水平。原始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中产品层面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服务行业对应的具体业务类别对主营业务收入进行匹配、筛选。对于主营业务收入中表述不明确的,通过查询企业年报信息进行核实和明确。其中,个别企业由于当年分部间抵消为负值,使得主营业务收入小于服务业务收入,从而导致服务化转型水平大于100%。
4.控制变量。参考现有研究[21-22],企业层面选择企业规模(SIZE)和资产负债率(DEBT);行业层面选择反映市场集中度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省份层面选择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FAIG)和人均GDP增长率(PCGG)。
(三)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以2011-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ST、*ST等经营异常的企业;(2)剔除中间退市和数据缺失严重的企业;(3)剔除未公开服务业务收入的企业。样本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中国律师年鉴》等,部分缺失值通过样本期内平均增长率处理补齐。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在首尾1%水平进行截尾处理。
表1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整体来看,总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等数据的标准差较大,数据在样本期内存在较大波动。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差为0.357,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较小,原因可能在于各省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强度基本相同,而仅在执行强度上有所差异。服务化转型的均值为40.14%,与祝树金等[23]测算的41.05%的服务型制造水平基本吻合,而其标准差较大,可能原因在于,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模式多为混入式服务化,导致制造企业开展的服务业务变动较为频繁[22]。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结果分析
表2报告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列(1)未加入控制变量,知识产权保护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初步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影响;列(2)加入控制变量后,知识产权保护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符号未发生变化,且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验证了假说1。具体来看,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低于2.858时,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将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于2.858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抑制企业绩效的提升。列(3)是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一次项进行回归,结果不具有显著性,进一步证明了假说1的成立。
(二)服务化转型对“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服务化转型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列(1)中服务化转型的二次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项在5%水平显著为正,初步体现服务化转型的非线性调节效应。列(2)加入控制变量后,服务化转型的一次与知识产权的交互项在5%水平显著为负,二次交互项在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服务化转型对“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绩效”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调节效应。虽然企业绩效在服务化转型初期会遭遇负向的调节作用,但当服务化转型水平越过28.6%的拐点后,将对知识产权保护下的企业绩效发挥促进效应。此外,28.6%的服务化转型水平拐点,低于40.14%的样本均值水平,说明当前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服务化转型水平已处于正向调节“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绩效”阶段。列(3)中只引入服务化转型的一次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项,结果不具有显著性,进一步验证了假说2。
(三)稳健性检验
1.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稳健性检验。表4汇报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影响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当企业凭借先进技术和产品在市场中获得垄断利润时,可能存在迫使政府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以维持其领先地位的动机,由此导致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绩效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列(1)借鉴吴超鹏和唐菂[3]的做法,将各省至1949年基督教大学数量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工具变量。其中,不可识别检验的统计量P值为0.000,显著拒绝“识别不足”的原假设;弱工具變量检验的统计量远大于10%显著性水平下的F统计量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列(2)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替代总资产净利率(ROA)衡量企业绩效。列(3)将时间固定和行业省份固定调整为时间与企业双向固定。列(4)采用Bootstrap法进行随机抽样回归。列(5)将首尾1%水平的截尾处理调整为首尾1%水平的缩尾处理。表4结果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倒“U”型影响效应是稳健的。
2.服务化转型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表5是服务化转型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列(1)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替代总资产净利率(ROA)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列(2)更换服务化转型水平的测算方式,借鉴刘维刚和倪福红[24]的方法,通过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企业服务化转型水平。列(3)将时间固定和行业省份固定调整为时间、行业和省份固定。列(4)采用Bootstrap法进行随机抽样回归。列(5)将变量数据在首尾1%水平下缩尾处理。从回归结果来看,服务化转型对“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绩效”的正“U”型调节效应通过了多重稳健性检验。
五、进一步研究
(一)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
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主要通过收益竞争优势和成本竞争优势对知识产权保护下的企业绩效发挥正“U”型调节效应。借鉴周夏飞和周强龙[25]的方法,通过勒纳指数衡量企业收益竞争优势(Inc_com),并通过同行业以销售收入加权的勒纳指数平均值进行修正。另外,参考Duanmu等[26]的做法,使用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比值衡量企业成本竞争优势(Cost_com),并通过行业中位数水平进行修正。收益竞争优势和成本竞争优势的测算结果均进行了极差标准化处理。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结果见表6。
从表6列(1)和列(3)可以看出,服务化转型对收益竞争优势和成本竞争优势均具有显著的正“U”型影响效应,说明在制造企业进行服务化转型过程中,企业的收益竞争优势和成本竞争优势均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变化特征。同时列(2)和列(4)的结果显示,企业收益竞争优势和成本竞争优势均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综上说明,服务化转型通过对收益竞争优势和成本竞争优势的正“U”型影响,从而实现了对“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绩效”的正“U”型调节效应,假说3得到验证。
(二)调节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为检验服务化转型调节效应的异质性,从行业、所有制、地区层面对企业样本进行分类,再通过式(2)的非线性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
1.行业异质性。根据国家统计局《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标准将样本划分为高技术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表7列(1)~(2)显示,服务化转型的非线性调节效应在高技术企业中并不显著,对非高技术企业则具有显著的正“U”型调节效应。主要原因在于,高技术企业的发展重点是研发高技术附加值的产品,尚不需要通过服务化转型促进竞争优势的提升。而非高技术企业则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需要通过服务化转型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
2.所有制异质性。根据实际控制人将企业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表7列(3)~(4)表明,对民营企业而言,服务化转型的调节效应依然显著,对国有企业则不具有显著性。可能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对市场变化和资源调配的快速反应,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及时推进服务化转型,从而获得企业绩效的改善。而国有企业对组织架构和资源重新分配的调整较慢,往往无法及时做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内部响应。
3.地区异质性。按照公司注册地将样本分为东部沿海企业和非东部沿海企业。表7列(5)~(6)所示,服务化转型对东部沿海企业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对非东部沿海企业则不具有显著性。主要原因在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需要通过服务化转型构建新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而非东部沿海企业借助要素成本等优势仍能促进经营绩效的提升,尚不存在实施复杂的服务化转型的市场动力。
六、结论与建议
以2011-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效应,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最适强度”。(2)服务化转型通过收益竞争优势和成本竞争优势对“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绩效”发挥正“U”型调节效应,实现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从“最适强度”到“长效激励”的转变。(3)在异质性分析中,服务化转型的非线性调节效应在非高技术企业、民营企业和东部沿海企业中更加显著。
建议:(1)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正外部性”。各地政府应鼓励企业运用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进行质押融资,解决企业研发项目融资压力较大的问题。同时,推动技术专利等知识成果有序流通,避免行业内竞争企业对成熟技术重复研发导致的资源浪费。(2)持续推进服务化转型,并基于资源基础实施差异化转型路径。东部沿海等拥有较丰富资源的企业应注重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要素的投入,以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导向。资源相对缺乏的企业应将服务要素主要投入到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顾客满意度的嵌入式服务业务中,避免资源过度分散配置。(3)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与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协同发展。对服务化转型水平较低的地区,应采取灵活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放在与企业核心技术相关的范围内。对服务化转型水平较高的地区,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执行强度,引导企业将高质量的服务要素投入到价值链研发、品牌管理等上下游环节,推动企业长期绩效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王钰,胡海青,张琅.知识产权保护、社会网络及新创企业创新绩效[J].管理评论,2021(3):129-137.
[2] 刘斌,魏倩,吕越,等.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J].经济研究,2016(3):151-162.
[3] 吴超鹏,唐菂.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6(11):125-139.
[4] Parello C P. A north-south mod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skill accumul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8,85(1-2):253-281.
[5] 贾宗穆,张婧屹.研发效率、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繁荣[J].财经研究,2022,48(7):138-153.
[6] Maskus K E.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novation in services[J].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2008,8(3):247-267.
[7] 贺灿飞,余昌达.多维邻近性、贸易壁垒与中国世界市场的产业联系动态演化[J].地理学报,2022(2):275-294.
[8] 祝树金,王哲伦,王梓瑄.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与制造业服务化[J].国际商务研究,2021,77(3):14-25.
[9] 周大鹏.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3(9):17-22+48.
[10]胡凯,吴清.R&D税收激励、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的专利产出[J].财经研究,2018(4):102-115.
[11]寇宗来,李三希,邵昱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南北双赢[J].经济研究,2021(9):56-72.
[12]李佳.因果模糊与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J].中国工业经济,2006(4):122-126.
[13]Cook M B, Bhamra T A, Lemon M. The transfer and application of product service systems: from academia to UK manufacturing firm[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6,14(17):1454-1465.
[14]Mathieu V. Service strategies with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benefits, costs and partnership[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2001,12(5):451-475.
[15]胡查平,周強,周名丁.制造业服务化:概念、战略优势及能力需求述评[J].贵州社会科学,2020(1):160-168.
[16]张峰,战相岑,殷西乐,等.进口竞争、服务型制造与企业绩效[J].中国工业经济,2021(5):133-151.
[17]李仲泽,陈钦源,张翼,等.企业金字塔控股结构与金融化[J].科学决策,2022(8):40-58.
[18]顾海峰,谢疏影.互联网金融影响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吗?[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42(6):10-18.
[19]仇云杰,吴磊,张文文.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研发绩效吗——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87-98.
[20]Fang E E, Palmatier R W, Steenkamp J B E M. Effect of service transition strategies on firm value[J]. Journal of Marketing,2008,72(5):1-14.
[21]许和连,陈碧霞,张旻钰.专利质量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47-55.
[22]陈漫,张新国.经济周期下的中国制造企业服务转型:嵌入还是混入[J].中国工业经济,2016(8):93-109.
[23]祝树金,罗彦,段文静.服务型制造、加成率分布与资源配置效率[J].中国工业经济,2021(4):62-80.
[24]刘维刚,倪红福.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技术进步:效应及作用机制[J].财贸经济,2018(8):126-140.
[25]周夏飞,周强龙.产品市场势力、行业竞争与公司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4(8):60-66+97.
[26]Duanmu J L, Bu M, Pittman R. Does market competition dampe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39(11):3006-3030.
(责任编辑:钟 瑶)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erv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share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China
ZHANG Zhibin1,2, CHEN Zhuo1, OU Ling1
(1.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2.Hunan Provincial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Research Base,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9, a non-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nd a moderating effect model are applie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the moderating mechanism of service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has a positive and then negative effect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there is an “optimal intens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ervice transformation has a positive U-shaped adjustment effec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firm performance” through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revenu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cost, realizing the “long-term incentiv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For non-high-tech enterprises,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eastern coastal enterprises, service transforma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In view of thi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to promote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serv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Key words: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 moderating effect
收稿日期: 2022-09-28
基金項目: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一般项目(QL20220230);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A189)
作者简介: 张志彬(1979—),男,湖南桃江人,博士,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