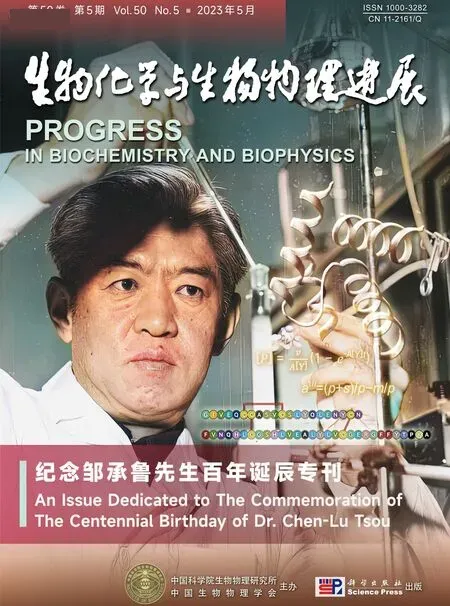酶促聚合:绿色的高分子材料合成技术*
李若雨 陈英翾 韩浩博 温 凯 安泽胜** 李全顺**
(1)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分子酶学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12;2)吉林大学化学学院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12)
酶促聚合是指以酶为催化剂介导单体聚合构建高分子材料的途径[1]。与传统的化学聚合相比,酶促聚合由于反应条件温和、环境友好及高度立体和区位选择性等优势,已成为高分子材料合成领域中的研究热点[2-3]。不仅如此,酶促聚合还具有如下优势:a. 底物的高度专一性,可以极大提高底物的转化率,且没有副产物的生成;b. 催化剂可以回收并重复利用,有利于降低合成成本;c. 酶促聚合可以在无溶剂、水相、有机相及多相界面进行;d. 能够有效催化金属催化剂难于实现的大环内酯类单体的开环聚合;e. 容易实现聚合物末端的结构控制,达到对聚合物修饰和改性的目的。作为一种新兴的聚合方法,酶促聚合为高分子材料的合成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环境友好的途径,是高效合成功能高分子材料的有效方法,对于促进化学和材料工业向绿色和清洁化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1984年首次报道酶促合成脂肪族聚酯以来,酶促聚合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目前,氧化还原酶、水解酶、转移酶均成功应用于聚合反应,其中氧化还原酶被用来催化芳香族化合物的氧化聚合和烯烃的自由基聚合,转移酶被用来催化合成多糖和聚酯,水解酶被用来催化制备多糖、聚碳酸酯和聚硫酯等。本文将着重介绍脂肪酶催化聚合、酶促可逆失活自由基聚合及酶促化学偶联聚合方面的研究进展,并讨论了当前研究的局限及未来发展方向。
1 脂肪酶催化聚合反应研究
脂肪酶(lipase,EC 3.1.1.3),是一类水解由有机酸和醇形成的酯键或类酯键(羧酯键、硫酯键、酰胺键)的酶类,其主要生理功能包括参与脂质代谢、信号传导以及维持生物膜结构的完整性。除了能够催化甘油酯类的水解和合成外,还能够用于催化酯交换反应、表面活性剂及聚合物的合成等。脂肪酶催化的聚合反应包括缩聚反应(polycondensation)和开环聚合(ring-opening polymerization)两大类[1](图1)。

Fig. 1 Two major routes of lipase-catalyzed polymersynthesis:ring-opening polymerization(a)and polycondensation(b)图1 脂肪酶催化聚合物合成两种途径:开环聚合(a)及缩聚反应(b)
1.1 酶促缩聚反应
缩聚反应是最常见的一种合成聚合物的方法,它可以方便地控制聚合物主链的结构,达到对聚合物进行改性的目的。与开环聚合相比,缩聚反应在单体的合成及选择范围上具有明显的优势。酶促缩聚反应依据单体类型可以分为羟基酸/酯型(A-B型单体)的缩聚及二元酸/酯和二元醇(AA-BB 型单体)的缩聚[4]。
A-B型单体是指末尾两端的基团互不相同且可以互相反应的单体。这类反应的优势在于,无需像AA-BB 型缩聚反应中控制单体比例为严格的1∶1否则难以获得高分子质量聚合产物。脂肪酶能够有效催化多种不同链长羟基酸/酯底物的缩聚反应,如6-羟基己酸、10-羟基癸酸、16-羟基十六烷酸、18-羟基十八烷酸、3-羟基丙酸甲酯和环氧蓖麻油酸甲酯等[5]。AA-BB 型缩聚反应根据单体及反应类型的差异,可以分为酯化和转酯缩聚两类,前者反应过程中有水分子的生成,必须采用减压或者添加分子筛的策略才能获得高的反应转化率和产物分子质量。该类酶促聚合反应所制备的材料,由于结构与和性能的可调控性,成功应用于药物/基因的可控递送与释放,如碳酸二乙酯与1,8-辛二醇/三(羟甲基)乙烷[6]、癸二酰氯和N-甲基二乙醇胺[7]、L-谷氨酸二甲酯盐酸盐与2,2-(二羟甲基)丙基-三丁基溴化鏻/1,4-丁二醇等[8]。
1.2 酶促开环聚合
酶促开环聚合反应由于不生成离去的副产物,因而容易获得高分子质量、分布均一的聚合物,同时开环聚合反应可以通过对引发剂和终止剂的控制来制备末端官能化的聚合物以及进行多种单体的共聚反应来赋予聚合物多种特性,因此开环聚合反应在酶促聚合研究与开发中备受重视。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及其单体的易得性,使得环状内酯在酶促开环聚合反应中研究最为普遍,成为酶促开环聚合反应的代表类型。
酶促开环聚合反应中,β-丙内酯、(±)-α-甲基-β-丙内酯、β-丁内酯、β-苹果酸内酯、δ-戊内酯、ε-己内酯、8-辛内酯、十一内酯、十二内酯、十五内酯、十六内酯、1,4-二氧六环酮、1,3-二氧六环酮等单体的聚合均获得了良好的效果[9]。同时,在化学催化剂无法聚合的γ-丁内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酶促聚合能够获得数均分子质量(number-average molecular weight,Mn)为800 g/mol左右的寡聚物[10]。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金属催化剂催化大环内酯类单体的聚合仅能获得寡聚物,而酶促聚合无论在催化速率还是在产物分子质量上都远远优于传统金属催化剂[11]。
多种来源的脂肪酶及酯酶成功应用于酶促开环聚合反应,如南极假丝酵母(Candida antarctica)、黑 曲 霉(Aspergillus niger)、褶皱假丝酵母(Candida rugosa)、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ce)、洋葱假单胞菌(Pseudomonas cepacia)、特异腐质霉(Humicola insolens)等微生物来源的脂肪酶/酯酶以及猪胰脂肪酶等[12-13]。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为固定于聚丙烯酸树脂的Candida antarctica脂肪酶B(Novozym 435)。然而,酶促聚合仍存在酶在有机介质和高温条件下催化活力及稳定性差、难于实现与化学催化技术的一步偶联等问题。因此,开发新型高催化活力和稳定性的酶催化剂对于酶促聚合反应是十分必要的。该团队从来源于极端环境中的嗜热菌闪烁古生球菌(Archaeoglobus fulgidus)和多节闪烁杆菌(Fervidobacterium nodosum)中成功钓取了嗜热酯酶基因AFEST和FNE,以ε-己内酯的开环聚合为模型,实现了聚酯类材料的合成[14-15](图2)。该过程中,反应单体转化率接近100%,合成产物Mn低于2 500 g/mol,有望作为聚氨酯的软段部分及药物递送载体;以单底物一级动力学为模型,深入探讨了酶促聚合反应的Michaelis-Menten 动力学,结果显示,两种嗜热酯酶均对单体ε-己内酯具有更强的结合能力(Km值分别为0.093和0.35 mol/L,远小于Novozym 435(Km=0.72 mol/L));计算机辅助分子模拟技术证明,嗜热酯酶与单体ε-己内酯形成了更为稳定的氢键网络,二者具有更低的相互作用能。利用嗜热酯酶FNE 在细胞膜上嵌合表达的特点,以嗜热酯酶FNE 工程菌全细胞和细胞碎片自固定化酶为催化剂,同样实现了聚合物材料的高效合成,上述催化剂较游离酶展示出更高的催化聚合活性、热稳定性、有机溶剂抗性及操作稳定性等[16-17]。

Fig. 2 The 3D structure of AFEST(a)and FNE(b)used in polymer synthesis图2 应用于聚合物合成的嗜热酯酶AFSET(a)及FNE(b)结构
2 酶促可逆失活自由基聚合
自Staudinger 提出高分子线链学说以来,高分子学科在过去一个世纪蓬勃发展,聚合物材料几乎被用于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精确控制聚合物的分子质量、分散度和拓扑结构对提高材料的性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烯烃的自由基聚合产物占工业聚合物的40%~50%,但传统自由基聚合慢引发、速终止的缺陷,限制了对聚合物结构参数的控制。与之相比,以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reversible addition-fragmentation chain transfer polymerization,RAFT)和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om transfer radical polymerization,ATRP)为代表的可逆失活自由基聚合(reversible deactivation radical polymerization,RDRP)通过控制活性链和休眠链之间的平衡,使每条聚合物链几乎同步增长,同时通过降低自由基浓度来减弱双基终止和不可逆的链转移,解决了传统自由基聚合的上述弊端[18-19]。
面对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两大社会问题,绿色化学的概念应运而生。RDRP 的催化/引发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经历着从传统的热引发和金属催化向以更绿色、环保的方式实施RDRP的转变。其中酶促RDRP因其独特的温和、高效、耐氧等优点引起了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极大兴趣。相对于酶促开环聚合和缩聚反应,酶促RDRP 的发展只有十余年,但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兴奋的进展[20-21]。本部分将结合酶促RDRP相关研究报道,重点介绍酶促RAFT和ATRP的研究进展。
2.1 酶促RAFT聚合
2.1.1酶催化除氧的RAFT聚合
与传统自由基聚合一样,RDRP也存在易被氧气猝灭的弊端,在RDRP开始之前需要采用惰性气体(如氮气或氩气)吹扫或者冷冻解冻泵循环技术将氧气去除[22-23]。繁琐的物理除氧步骤限制了RDRP 研发的效率,增加了操作成本,不利于将RDRP“从实验室跃上生产线”,解决RDRP不耐氧的缺陷对推动高分子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很早之前生物学家就注意到氧化酶在氧化底物的同时,将氧气还原为H2O2。他们利用葡萄糖氧化酶(GOx)在有氧条件下能专一性地催化β-D-葡萄糖生成葡萄糖酸和H2O2的特点,来消耗溶液中的氧气,但是直到2014 年,酶催化除氧才被用在RDRP 领 域。Stevens 课 题 组[24]在进行热引 发RAFT聚合的过程中,通过添加GOx和葡萄糖来消耗溶解在溶液中的氧气。他们发现GOx 具有出色的除氧能力,即使在敞口反应瓶中,仅需加入0.1~ 0.25 μmol/L 的GOx 就能保证聚合顺利进行。此外,GOx还具有较高的温度和有机溶剂耐受性,在添加80%的正丁醇或乙腈的PBS 中,在45℃下聚合150 min之后,酶的活性几乎没有降低。
由于GOx 的鲁棒性和出色的除氧能力,成为酶促RDRP中最常用的除氧酶。在测试的复杂溶剂中,通过RAFT聚合所获得的聚丙烯酸羟乙酯都具有较低的分散度(Đ≤1.2)和较高的端基保真度。当使用GOx 在高温下或毒性较大的溶剂(如N,N-二甲基甲酰胺(DMF))中进行除氧时,可采用固定化酶的方法提高酶的温度和有机溶剂耐受性。Yuan 等[25]使用金属有机框架ZIF-8 将GOx 进行封装,测试发现在DMF与水(1∶1)的混合溶剂中,将溶液加热到80℃后,相对于初始的游离酶,GOx的相对活性高达73.7%。GOx高的除氧效率使在更复杂、除氧更困难的反应装置中进行RAFT聚合成为了可能。相较于瓶式反应器,在多孔板中进行RAFT聚合更加困难,这是因为聚合溶液的空气接触面积与溶液体积的比值更大,溶液体积更小,对氧气更敏感。Stevens 课题组[26]使用GOx 除氧,实现了仅需40 μl 聚合溶液的低体积耐氧性高通量RAFT 聚合。Tan 等[27]将GOx 除氧的高通量聚合用于聚合诱导自组装来制备具有不同形貌的聚合物胶体粒子,相较于Stevens 课题组采用的热引发方式,该研究采取的引发方式是光引发。连续流聚合除氧更加繁琐,往往需要先在反应瓶中除氧,然后将聚合溶液转移到进样针中,这降低了实验成功的概率。最近,Cai 等[28]将GOx 除氧的聚合诱导自组装体系扩展到连续流聚合中,用于大规模制备聚合物纳米颗粒。
除了使用GOx 除氧之外,其他更有特色的酶催化除氧RAFT聚合体系也崭露头角。该研究团队先后将吡喃糖氧化酶(P2Ox) 和甲酸氧化酶(FOx)用于除去RAFT 聚合体系中的氧气[29-30]。相较于GOx,P2Ox 具有更广的底物范围,对葡萄糖和氧气的亲和力更高。重要的是,其催化葡萄糖除氧生成的2-脱氢-D-葡萄糖具有更强的抗水解能力,不会降低溶液的pH值。FOx的底物甲酸仅有1个碳原子,更加具有原子经济性,FOx催化甲酸氧化产生的CO2很容易从聚合体系中排出,不会造成废料的积累[31]。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酶催化机理的了解,越来越多的氧化酶将会被用于RAFT 聚合,针对不同的体系,选择合适的酶进行除氧是十分必要的。
2.1.2酶催化引发的RAFT聚合
在所有的RDRP 中,RAFT 聚合体系的组成最接近传统自由基聚合,外源自由基的加入是必需的(光裂解RAFT试剂引发的聚合除外)。因此,对于酶催化除氧的RAFT聚合来说,往往需要与其他的引发方式(如热引发、光引发)相结合。在这些聚合体系中,酶仅仅是用来除氧,不涉及到产生引发物种。对于利用氧化酶除氧产生的H2O2与其他化学反应(如芬顿反应、氧化还原反应)级联的体系,将其归类为酶催化除氧的RAFT 聚合更加合适,这是因为这些体系没有利用酶的催化功能产生引发物种[32]。目前酶催化引发的RAFT 聚合包括使用辣根过氧化物酶(HRP)催化的RAFT聚合和光酶催化RAFT聚合。
HRP 是一种含血红素的金属蛋白,其以H2O2或烷基过氧化物为氧化剂,催化酚、苯胺和β-二酮等化合物的氧化反应[33],如HRP催化H2O2对乙酰丙酮的氧化反应,产生的乙酰丙酮自由基可以释放到酶外,引发自由基聚合。虽然这一过程很早就被研究并用于传统自由基聚合,但是直到2015 年,第一例酶催化引发的RAFT 聚合才被报道。Zhang等[34]使用HRP/H2O2/乙酰丙酮三元引发体系,在合适的链转移剂存在下,首次实现了高效、可控的酶催化RAFT聚合。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催化体系不具有氧气耐受性,聚合开始之前需要使用氮气吹扫的方式进行除氧。此后,该研究团队巧妙地将酶除氧与酶催化引发结合,先后发展了GOx-HRP、P2Ox-HRP、FOx-HRP级联催化体系[29-30](图3)。相较于外加引发剂的方式,酶催化可以连续稳定的产生低浓度的自由基,这对多嵌段聚合物和超高分子质量聚合物的获取是至关重要的。利用P2Ox-HRP级联催化体系,在开口反应瓶中合成了十嵌段聚合物;在封闭反应瓶中,无需事先除氧,获得了控制良好的超高分子质量聚合物(Mn=2 003 kg/mol,Đ=1.35)。利用FOx-HRP 级联催化体系,以高通量的方式在多孔板中合成了不同结构的超高分子质量聚合物,最低溶液体积仅为50 μl。

Fig. 3 Enzymatic cascade catalysis for RAFT polymerization图3 双酶级联催化RAFT聚合
原叶绿素氧化还原酶、DNA 光解酶和脂肪酸光脱羧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三种天然光酶(光依赖性酶)[35-37]。光酶催化兼具光催化和酶催化的双重优势,激发了非天然光酶催化自由基有机合成和高分子合成的发展。该研究团队将常见的黄素蛋白(GOx 和P2Ox)转化为光酶,合成了几类目前RDRP领域具有挑战的聚合物,如基于非共轭单体的超高分子质量聚合物和星形聚合物[38-40]。光酶催化RAFT聚合的机理如下:在无氧状态下,GOx或P2Ox 的辅因子FAD 被葡萄糖完全还原为FADH-,其被光激发后变为还原性更强的FADH-*,FADH-*可以将电子转移给RAFT 试剂/单体,从而引发RAFT聚合。即使聚合体系存在氧气,GOx也可以通过其天然的除氧功能将其耗尽,使用氧气探针测试发现,使用GOx 除氧可以使溶液中的氧气降低为接近于用氮气置换的水平。当氧气被完全消耗之后,过量的葡萄糖依旧可以还原FAD,因此该光酶催化体系具有氧气耐受性。这种催化方法,不仅适用于溶液聚合,也适用于包括分散聚合和乳液聚合在内的异相聚合。
目前适用于引发RAFT 聚合的酶的种类较少,仅有上述2 种引发方式。其他类型的酶催化反应,若是能产生自由基引发物种,也有望被用于引发RAFT聚合。
2.2 酶促ATRP反应
2.2.1酶催化除氧的ATRP反应
ATRP 通过可逆失活建立活性链与休眠链之间的平衡,原则上适用于RAFT体系的氧化酶都可以被用来去除ATRP 体系的中的氧气。需要注意的是,在ATRP体系中,氧化酶除氧产生的H2O2可以氧化CuI,通过类芬顿反应产生羟基自由基引发新的链生成。例如,Enciso 等[41]在利用GOx 除氧时,发现所得聚合物的Mn是理论值的1/4左右。在加入丙酮酸钠之后,所得聚合物的分子质量与理论分子质量接近,聚合得到了良好的控制。这是因为丙酮酸钠与H2O2反应,生成了水和CO2,避免了羟基自由基的产生,H2O2的浓度对ATRP的影响以及丙酮酸钠清除H2O2的限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种以丙酮酸钠作为牺牲试剂的酶催化除氧的方式,不仅适用于引发剂持续再生催化剂(ICAR)的ATRP, 也适用于电化学介导的 ATRP(eATRP)[42]。借 助 于GOx催化除氧的ATRP,Navarro等[43]制备了一系列生物医学相关的聚合物刷,并测试了它们对人血浆的防污性能,结果表明,在GOx 存在的情况下制备的涂层比不含GOx时制备的涂层会排斥更多的血浆蛋白。
除了采用化学的方法(添加丙酮酸钠)去除酶催化除氧ATRP 体系中产生的H2O2,Enciso 等[44]还巧妙地将GOx 除氧与HRP 催化级联起来。该体系中,利用HRP 催化H2O2氧化乙酰丙酮产生的乙酰丙酮自由基将CuII/L 还原为CuI/L,成功实现了酶级联催化的ICAR ATRP(图4a)。在这种情况下,氧气成了不可或缺的“燃料”,只有体系中存在氧气才能有效驱动ICAR ATRP。当体系中的氧气被排净之后,聚合就会停止;当再次通入空气之后,聚合可以重新启动。这种通过切换体系的氧气浓度来从时间上操控聚合的现象是十分有趣的。

Fig. 4 Enzyme-engaged ATRP图4 酶促ATRP反应
目前用于ATRP体系的氧化酶仅限于GOx,其他在RAFT 领域已被应用的氧化酶如P2Ox 和FOx尚未被用于ATRP。可以预见的是,这些酶是适用于在ATRP 中进行除氧的。但是,将这些酶用于ATRP 需要考虑其经济因素和现实意义,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氧化酶除氧产生的H2O2会与CuI发生反应的问题。随着更多的化学方法或者生物催化体系被引入到酶除氧的ATRP体系中,这一困境将会被打破。
2.2.2酶催化ATRP反应
事实上酶催化在RDRP领域中最早的应用就是利用金属酶去催化ATRP[45]。传统的ATRP 依赖于使用过渡金属(如Cu 和Fe)络合物作为催化剂来实现聚合物链-卤化物的可逆失活。大多金属蛋白也含有金属的催化中心,这一共同特征表明金属蛋白可被用于催化ATRP[20](图4b)。2011年,Bruns课题组[46]和di Lena 课题组[47]几乎同时报道了使用金属酶催化电子转移活化再生催化剂(ARGET)的ATRP工作,实现了N-异丙基丙烯酰胺、聚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和聚乙二醇丙烯酸酯等水溶性单体的可控聚合。
目前被用来催化ATRP反应的酶包括HRP、血红蛋白、漆酶、过氧化氢酶等。与传统的过渡金属配合物不同,这些酶的金属催化中心紧密结合在酶内,使金属不易释放到溶液中,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重金属污染聚合物的可能性。例如,N-乙烯基咪唑(NVIm)很难使用传统的ATRP 方法进行聚合,一方面是因为该单体聚合的活性低,更主要是因为NVIm 和聚合后生成的PNVIm 都容易与金属离子结合,导致金属从ATRP 催化剂中剥离[48]。Bruns 课题组[49]利用漆酶催化的ATRP 实现了NVIm的可控聚合,这是因为漆酶中的铜离子与蛋白质结合成铜蛋白的形式存在,避免了NVIm 和PNVIm 与其结合。聚合结束之后,漆酶可以通过简单的纯化步骤从聚合物中定量去除,得到纯净的PNVIm。基于该仿生组装的理念,Jiang等[50]实现了具有过氧化物酶活性的次铁血红素六肽(DhHP-6)在金属有机框架材料中的组装,该组装体不仅具有良好的过氧化物酶活性,同时能够高效催化ATRP反应,合成产物Mn高达为45 900 g/mol,多分散性为1.27(图5)。该催化体系不仅具有良好的操作稳定性和循环使用能力,更重要的是,有效避免了ATRP 反应中金属催化剂的痕量残留与潜在毒性,在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领域中展示了较化学催化体系更为显著的优势。此外,通过接枝反应将血红素接枝于金属有机框架材料表面所构建的人工酶分子,同样展示出良好的ATRP催化活性,合成产物Mn高达33 200 g/mol,同时该人工酶分子自身所具有的过氧化物酶活性,能够有效催化废水中酚类污染物的降解,在生物环保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51-52]。
酶催化ATRP 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但是目前使用金属酶催化ATRP所得聚合物的分子质量较低(Mn<10 000 g/mol),分散度较大。这是因为在聚合过程中,聚合物链需要进入酶的催化中心,随着聚合的进行,聚合物链不断增长,导致其进入酶催化中心的难度不断增大,使聚合失去控制。随着对聚合机理的不断研究,以及对蛋白质工程对酶催化性能的提升,酶催化ATRP将会更容易得到控制良好的聚合物。

Fig. 5 ATRP reaction using DhHP-6 nanobiocatalyst图5 DhHP-6组装体催化ATRP反应
3 酶促化学偶联构建聚合物材料
3.1 酶促聚合与化学聚合反应偶联
随着科学的发展及相关领域需求的不断推进,对聚合物结构和功能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进而对聚合物结构和材料制备方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今单一结构与功能的均聚物材料已难以满足生物医学领域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并行串联聚合是基于多种聚合反应的一次性或同时一锅法串联的新型聚合方法,该方法常被用于制备复杂结构和功能的聚合物,代表一种高效和经济的绿色合成策略。其中,ATRP与酶促聚合反应的偶联是被研究最为广泛的串联反应之一[53]。酶促聚合与ATRP 反应的偶联得益于双功能引发剂的加入,Br 原子引发ATRP 反应,末端羟基则驱动酶促聚合反应的进行,其可以通过级联或者一锅法模式进行反应,制备具有特殊结构与性能的多嵌段聚合物(图6)。Zhang等[54]以2,2,2-三氯乙醇作为引发剂,成功实现酶促ε-己内酯开环聚合反应和苯乙烯ATRP反应的偶联,制备了ABA2-型(Y 型)三嵌段共聚物。Wei 和Tao 研究团队[55-58]利用ATRP/光控聚合等技术构建了多种多组分聚合体系,应用于功能共聚物或光学活性聚合物的制备,包括点击-化学酶法ATRP、化学-酶催化酯交换反应与ATRP 或RAFT组合以及酶促手性拆分反应与ATRP组合等。所有这些串联聚合体系都可用于制备多官能度、组成和结构复杂的聚合物,酶促聚合与化学聚合偶联反应将有助于改善复杂大分子制备过程从而拓宽聚合物的应用范围。

Fig. 6 Polymer synthesi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enzymatic ring-opening polymerization and ATRP图6 酶促开环聚合与ATRP反应偶联合成聚合物
开环易位聚合 (ring-opening metathesis polymerization,ROMP)是合成烯烃聚合物的有效手段同时是烯烃易位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Xiang等[59]首次利用烯醇/烯酯作为ROMP链转移剂,制备了具有端羟基/端酯基的功能化遥爪型聚合物,随后将之作为大分子引发剂引发酶促开环聚合反应制备嵌段共聚物。值得注意的是,酶促聚合反应中通常以水、醇、胺等分子作为链引发剂,而该研究证明,高分子链端酯基同样可以作为引发剂引发酶促开环聚合,避免了中间产物的分离与纯化。基于链末端酯基可以引发酶促开环聚合反应这一新发现,该研究团队建立了“一锅法”偶联酶促开环聚合与ROMP 构建嵌段聚合物的策略[60](图7),为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合成与改性提供了新的途径。
除了与活性/可控聚合偶联之外,酶促聚合反应也被用来与其它化学反应构建结构明确的聚合物,例如Ates等[61]通过酶促开环聚合制备了不饱和聚酯,接着通过硫醇-烯键点击化学将该聚酯侧链中双键官能化,这种组合方法提供了一种简便的聚酯修饰策略方法。

Fig. 7 Synthesis of block copolymer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enzymatic ring-opening polymerization and ROMP in a cascade or one-pot manner图7 级联及一步模式组合酶促开环聚合与ROMP合成嵌段聚合物
3.2 酶促合成产物的生物医学应用研究
由于酶促聚合反应制备的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不存在金属催化剂的痕量残留,细胞及动物水平研究均表明,酶促聚合所制备的聚合物材料具有良好的相容性,体内应用时能够避免引起炎症反应,同时材料的疏水特性又能够显著增强药物及基因的递送能力。因此,酶促合成高分子材料的生物医学应用,是提高合成产物附加值、推动产物合成产业化与临床医用的关键。
2011年,Zhou等[62]首次利用Novozym 435为催化剂,以内酯、癸二酸二乙酯、N-甲基二乙醇胺为单体,通过开环聚合和缩聚反应相偶联的模式成功构建了聚氨酯材料,该材料在体外基因转染及体内基因治疗均取得了优于商业化转染试剂的作用效果。在此基础上,多个研究团队通过单体衍生化及聚合物的修饰改性等策略,制备了多种修饰型聚氨基酯及其共聚物,并成功应用于药物递送[63]、核酸分子[64-65]及mRNA 递送[66]等。在此基础上,该研究团队以N-甲基二乙醇胺、辛二酸二乙酯、ω-环十五内酯为单体,通过酶促开环聚合与缩聚偶联的策略构建了阳离子聚酯材料,之后通过化学接枝的策略在该材料的侧链上引入胆固醇分子,成功构建了两亲性胆固醇-g-聚酯共聚物,以该聚合物材料为载体进行miR-23b 及p53 基因的递送,通过p53、miR-23b 的高效、稳定、靶向传输,实现了对肿瘤增殖、迁移与浸润的高效抑制[67-69],为基于具有抗肿瘤核酸分子递送构建肿瘤靶向基因传输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图8)。

Fig. 8 Chemoenzymatic synthesis of cholesterol-g-poly(amine-co-ester)for miR-23b delivery图8 酶促化学偶联制备胆固醇-聚氨酯载体介导miR-23b递送研究
4 总结与展望
伴随着酶催化机制认识的深入及新兴研究手段的应用,酶促聚合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酶促聚合仍然存在酶制剂成本过高、活力和稳定性不足、合成产物结构单一及应用范围有限等弊端,目前该技术尚处于研究开发阶段,距离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当前酶促聚合技术存在的主要瓶颈如下:
a. 酶制剂催化活性和稳定性不足,成本高昂。当前酶促聚合研究中所采用的催化剂主要是来源于Candida antarctica脂肪酶的固定化形式Novozym 435,其在苛刻的聚合催化反应中仍然面临活性、稳定性及重复利用能力方面的难题,同时合成过程中催化剂的用量很高(>5%wt)。因此,开发新型适用于聚合反应的酶制剂,对于解决催化过程中活性、稳定性、成本等关键制约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切实解决绿色生物制造中的关键“卡脖子”难题。
b. 单体及合成产物结构与性能单一。当前酶促聚合技术的类型主要有开环聚合及缩聚两类,单体范围极其有限,导致合成产物结构简单,无法实现在生物医用材料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因此,将酶促聚合技术与特殊化学聚合技术(ATRP 反应、ROMP反应及RAFT聚合等)相偶联,通过级联催化及“一锅法”的模式,能够更好地实现对高分子材料的结构修饰与改性,构建具有特殊结构与功能的聚合物材料。
c. 酶促聚合产物附加值偏低,应用范围窄。酶促聚合反应成本高、产物结构单一等瓶颈,造成了酶促合成高分子材料附加值低、应用范围窄等局限。因此,将合成产物应用于高效、安全的重大疾病药物与基因递送体系,将有利于提高酶促合成产物的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并推动酶促聚合技术朝更加绿色、精细化方向发展。
酶促聚合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药剂学等学科间的沟通架起了桥梁。作为一种新兴的聚合方法,酶促聚合为高分子材料的合成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环境友好的途径,是高效合成功能高分子材料的有效方法,在医药、环保乃至国防等方面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酶促聚合必将实现关键技术上的突破,成为未来高分子材料制备的重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