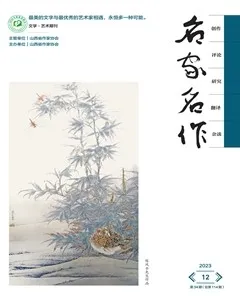《文心雕龙·物色》审美创作论研究
王述良 王清云
《文心雕龙·物色》围绕“心与物”“情与景”的自然审美关系,从“物—情—辞”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立足“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审美发生机制,结合具体作品探究“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一心物相融、情景会通的审美发生场域,提出“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审美创作原则和“适要”“入兴贵闲”“析辞尚简”等审美创作方法。《物色》全篇文质兼美,为中国古典美学审美创作范畴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一、“物”“色”含义之辨
纵观《文心雕龙》全篇,刘勰按照《序志》论文叙笔“释名以章义”的思路,对大部分篇章论题进行了较明确的概念界定,然而《物色》篇却没有明确的“释名”之解,对于“物色”含义的理解,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说“盖物色犹言声色”,认为物色是自然景物的外在声色面貌,这也是当前学界更多赞同的一种观点。陈良运则从审美的角度,通过对“色”的论证,提出“所谓‘物色’就是‘审美’”的观点。前者立足文本,从《物色》篇呈现的情景关系出发;后者则着眼于物色的审美心理。立足篇目本身,对“物”“色”进行考察,可有三方面理解。
(一)物是“道之物”,色是自然之道的内在规律性呈现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四时之阴晴变化等皆为“物色”。《原道》篇中有“观天文以及变”,这些自然景物在“天文”的自然之“道”下呈现为物存在的自然动力,色即是这种天地幻化的“原初动力之色”,是人们探求的最深层审美规律的内在之色,“道之物”呈现的形式即是色。
(二)物是“变之物”,色是主体对自然物变化的感知
刘勰在《物色》这篇中将物色赋予了时间、变化等性质,这种变之物色是人类情感最富有感触之处,刘勰从自然之原道的基础上引入时间意识,“感物之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感时之变”。在此,物的概念不仅是静止之物,而且是融有时间意识的动态之物,变之物的动态含义呈现在物色之“色”上则是人“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直接感受对象——感时体物,从而将人这一审美主体带入“物色之动”的审美体验中。“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四季的变化影响着人的生理及心理,人类的审美意识也随四时之变而“婉转”与“徘徊”,正是“情随物迁”的表现。
(三)物是“色之物”,色是自然之物外在的生动样态
“色之物”是在“道之物”与“变之物”的内在基础上呈现的物之外貌景致,是如自然之物所是的外在样态呈现之物,也就是在本篇中普泛意义上说的自然景色,这一层面的色是刺激我们眼角膜的最外在的“景”,是在时间维度下对空间之物的审美观照。
“物”“色”正是凝结着自然之道、天地之化呈现出朴素直观的活泼泼的生动景物之态,从而在审美主体介入后,得以激发审美主体“情随物迁”的审美感知,外化为“情貌无遗”“情景交融”的审美发生场域,生发出以“物—情—辞”为基本理路的内在审美外铄化的审美创作机制。
二、“物—情—辞”审美创作机制的发生
在《物色》中,刘勰以“心与物”的自然审美关系为核心,以其“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思路,先从自然景物变化“阳气萌”“阴律凝”引起“玄驹步”“丹鸟羞”,微虫尚能感觉到外界景物的变化,作为“物与情”关系萌发的源头,从“物色相召,人谁获安”“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与“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的“情景”交融的动态发展中,由自然之道到人文之道,对“心、物、辞”关系进行探索。
(一)“情、景”的发生:景的呈现与情的感触
《物色》中的“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与刘勰《明诗》中的“感物吟志”、《诠赋》中的“情以物兴”诸说一致。而钟嵘在《诗品序》中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些观点都说明“物”的外在呈现是引发“情、景”关系发生的原因。“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则进一步说明了“情景”关系的发生即“物”对“情”的感召力量。陆机在《文赋》中言:“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钟嵘在《诗品序》中言:“若乃春风春鸟,秋月鸣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附录《物色》篇中引用昭明《答湘东王求文集诗苑书》、简文《答张瓒示集书》、萧子显《自序》等诸家言论,并评曰:“此诸家之言,皆调四序之中缘景生情,发为吟咏,与刘氏之意正同”,皆为此意。
(二)“物—情—辞”的会通:情景的交融
审美是在情对物的主观感知下发生的,“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牟世金、陆侃如在《文心雕龙译注》中说:“诗人受到客观景物的感染时,他可以联想到各种各样类似的事物。”周振甫在《文心雕龙今译》中则译之曰:“诗人对景物的感触,所引起的联想是无穷的。”此两家之言在修辞上的一主动一被动描述,恰好能够说明“情与景”的互相交融性。正是诗人身处宇宙万物之间,自然之物色呈现在诗人眼前,而诗人通过对眼前物色的“沉吟视听”构成了物与情之间的相互交融关系。自然这种关系还是处于内隐状态的,当进入“写气图貌”的自然景物客观模绘与“属采附声”的再造性人文化创作阶段时,情与景的交融才真正呈现了出来:情随物以宛转、物亦与心而徘徊。正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附录《物色》篇中认为,写气图貌是外在的形貌描摹,属采附声是内在的人文化呈现,最终达到“入乎其内,令神与物冥”的境界。这即是“物—情—辞”以审美的姿态会通,从而形成情与景交融相依的状态。
(三)“情、辞”的外化:情的感发与辞的表达
对于“情、辞”关系,刘勰一语综括:“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然而相对于辞的表达、文的创作来说,随物而迁的情尚且处于内隐状态,是处于“感”这一生理与心理的创作发生阶段,并没有外化为人文之文。《物色》以《诗经》为例,用“灼灼”来形容桃花的鲜亮美丽,其中包含着欣喜之情;用“依依”之态来描摹杨柳形貌的轻柔,惜别之情在“依依”中飘摇;用“杲杲”来表现太阳初升的样子,以“瀌瀌”模拟雨雪纷飞的场景,借“喈喈”来效仿黄鸟的鸣叫之音,用“喓喓”表现虫鸣的音韵,生动地将“情融于景”的效果表达了出来。刘勰总结道:“‘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情的内隐状态通过辞的恰当表达得以显现,同时也提出了以辞表情的呈现原则:“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如此,辞表达的完成才意味着从审美感知到审美创作的完成。
三、审美创作原则与方法的提出
(一)描摹状物,志惟深远
刘勰从齐梁时期的创作原则与前代的不同之处入手,结合“物、情、辞”的关系提出了写景文辞的审美特点:“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附录《物色》中说:“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数语,刘氏虽以此评当时,实亦凡写景者所当奉为准则也。”齐梁时期山水诗的审美特色重在形似。刘勰在《序志》篇中对于“弥纶群言”云:“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然而此处刘勰对“文贵形似”的观点却有不明确之处。《文心雕龙札记》中的观点与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类似,认为“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是有自己特色,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钟子翱、黄安祯所著《刘勰论写作之道》中则持相异观点:他(刘勰)不仅指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因而“丽淫而繁句”,而且痛斥“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的恶劣风气。刘勰的上述理论观点,应该说是救治齐、梁之际的一剂良药。这两种完全相异的观点,我们可以从文中找到矛盾的端倪,刘勰指责当时不良文风的观点。显然是对司马相如之辞的否定,是对其“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的指摘。可以看出刘勰反对的是无“情”的巧妙融入,缺乏情景交融,缺乏形神兼备,仅仅是靠修辞的繁杂来模山范水;反对的是《序志》中“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浮诡、讹滥文风。然而“文贵形似”之处紧承下文“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很明显刘勰此处将情融入风景之中,与司马相如模山范水之辞是不同的,在形似的描摹中达到“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的情景交融,情与形似的“色之物”(景)都呈现在文字中,而文辞也能体现出所描绘的面貌,从文字中即可窥探“道之物”“变之物”,从而“即字而知时”。因此,我们认为“文贵形似”与下文刘勰赞同的创作的审美观是一致的,是融情于景的“形似”,而不仅仅是繁缛的雕琢自然之景。
(二)情景交融,入兴贵闲
刘勰肯定文的形似也就是肯定了写景文对“物色”的“密附”,从“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中可以看出刘勰对不事雕琢、融情于景原则的肯定。同时刘勰深谙情与景交融的审美原则,他说景物有固定的形态,然而作者的情思却是会变化的,有时很自然率性地就能达到情与景完美相融的极高境界,有时极尽脑汁却离本意更远。在这种审美原则的偶然性与不协调性上,刘勰以《诗经》《楚辞》为“选文定篇”之据,提出了自己的审美创作要求:抓住要害,“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贵在时见”,这是在创作形式技巧上的审美要求,达到“虽旧弥新”的程度。然而,情景交融的审美呈现还需要更加本质的内在的“心”“情”对物的主动感知,从而外化为“情貌无疑”之辞。刘勰提出了“入兴贵闲”的心境与物相互感召的审美进入方式,心境的闲静状态,如同后世的“虚境”理论,这也与刘勰时代受佛教思想影响有关,在静观状态才能更加接近物色的本义,才能在繁复的景物中用简练的辞句表达出来,而展现的审美意蕴却是“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
(三)心物相召,贵在会通
“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以“会通”的眼界来审视“心、物”发展,人眼中的景物是能够穷尽的而情思却写不尽,刘勰将审美视野的主观性与局限性和审美情思的无限性表达了出来,因此需要继承与革新前人观点,用会通的思维来审视情与物。同时,刘勰也看见了情、物呈现的复杂性与景物对情感的重要影响:“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正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言:“他若灵韵山水,开诗家之新境,柳州八记,称记体之擅场,并皆得自穷幽揽胜之功,假于风物湖山之助。”“所谓取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者,其此之谓也。”审美情感的发生既需要丰富的物色之召,也需要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情有余”的深刻的会通体悟,更需要“文思之奥府”,即恰到好处的审美创作原则和方法。
刘勰《文心雕龙》以自然之道为逻辑原点,目的是论述挽救时弊的文章之道,在审美层面上为我国古典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借鉴,《物色》篇中的诸多观点,则为中国古典美学审美创作范畴的展开奠定了基础。“物—情—辞”会通的审美感知是刘勰由对外在景物的触景之情和对景物变化的审美之感而形成的对时间变化、对宇宙发展的内在深层思考,这种对自然变化、时间流逝的体悟中流淌着中国古典美学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洞察与思考的审美文化血液。被纪昀评为“诸赞之中,此为第一”的《物色》之赞,对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审美环境构造的审美创作机制做了最好的总结:“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