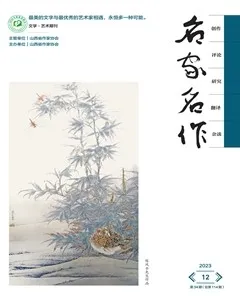《清华简(陆)》“郑武公处卫三年”试探
刘鹏辉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本文简称《清华简(陆)》)中的《郑武夫人规孺子》记载了郑庄公继位初期的史事,郑武公去世后,武公夫人武姜规诫郑庄公吸取武公的治国经验,将邦政属之大夫三年,庄公从之。关于这段史事,传世文献中并无相关记载,《清华简(陆)》为郑国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特别是简文中所提到的“郑武公处卫三年”问题,由于史料缺乏,学界对其处卫三年的时间有多种看法,而对处卫原因探讨较少。通过对《清华简(陆)》及《史记》《国语》《左传》等相关传世文献的研读,本文试图对“郑武公处卫三年”问题进行推测。
一、“郑武公处卫三年”辨析
为方便对“郑武公处卫三年”问题的探析,现将《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相关部分摘引如下:
郑武公卒,既肂,武夫人规乳,曰:“昔吾先君,如邦将有大事,必再三进夫而与之偕图。既得图乃为之毁,图所贤者焉申之以龟筮,故君与夫晏焉,不相得恶。区郑邦望吾君,无不盈其志于吾君之君己也。使人遥闻于邦,邦亦无大言系赋于万民。吾君陷于大难之中,处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如毋有良臣,三年无君,邦家乱也。自卫与郑若卑耳而谋。”[1]
下面先疏通简文中一些字词。
“必再三进夫而与之偕图”之“进”,《说文》释为:“登也。”[2]“偕”字,《说文》释为:“强也,一曰俱也。”[2]结合前后文,此句意为多次拜访大夫并与之谋划。“图所贤者焉申之以龟筮”之“申”字,《说文》曰:“神也。”[2]《诗经·小雅·采菽》:“乐只君子,福禄申之。”[3]此处“申”字之义为重复,将此义放入简文,意为与贤臣谋划又岂能再去占卜。“区郑邦望吾君,无不盈其志于吾君之君己也”中之“区”字,《说文》曰:“踦区,藏匿也。”[2]若以藏匿之义释之当为不妥,《左传》襄公十七年载:“宋国区区。”[4]“区区,小也。”“君己”之“君”字,整理者认为是动词,《说文》释为:“尊也。”[2]则此“君”字当为“尊”之义。“邦亦无大䌛赋于万民”之“繇”字,《汉书·高帝纪上》:“高祖常繇咸阳。”[5]此处之“繇”与“䌛”为通用字,义为役也。
简文大意如下:郑武公去世,待葬期间,武姜规劝郑庄公说:“先君在位时,国家有大事定会多次拜访众大夫并商量谋划。即使谋划失败,先君与大夫也不去占卜,因此君臣和睦。郑国人尊敬先君就像尊敬自己。使人闻知郑国之事,郑国百姓没有过多的赋税杂役。先君陷入大难之中,处卫三年,既看不到郑国,又见不到家人。郑国若没有忠臣,三年没有君主,恐怕就乱了。卫国帮郑国谋划。”
关于“郑武公处卫三年”,学界有以下四种看法:第一,李学勤推测处卫三年在“嗣位之初”;第二,李守奎认为是郑桓公被杀之后的三年[6];第三,晁福林认为在郑武公十一年至十三年[7];第四,程浩认为是郑武公迎立周平王于成周并在周平王身旁辅佐的三年[8][9]。对于以上四种观点,笔者赞同晁福林的观点。下面试据简文及传世文献进行剖析。
简文《郑武夫人规孺子》中,武姜对郑庄公讲述武公处卫时说:“吾君陷于大难之中,处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如毋有良臣,三年无君,邦家乱也。”[1]武姜对庄公说郑武公遭遇大难,且郑国三年无君,则此时郑桓公当已去世。《史记·郑世家》记载:“二岁,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10]二岁即郑桓公三十六年,《国语·郑语》也有相关记载:“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11]但《古本竹书纪年》有不同记载:“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以为郑桓公。”[12]《古本竹书纪年》中幽王死后郑桓公尚在,与《国语》《史记》相左,郑桓公是否死于骊山,学界有不同看法,尚需进一步论证。根据简文,毋庸置疑的是,郑武公处卫之时桓公已死。武姜提到武公处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邦”字,《说文》曰:“国也。”[2]国即指郑国。“室”,《说文》释为:“实也,至所止也。”[2]《说文》“宫”字释为室[2]。宫、室二字字义相近,室之本义为居所,若释为居所,则不妥。《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丈夫生而原为之有室,女子生而原为之有家。”[13]《诗经·周南·桃夭》:“……宜其室家……宜其家室。”[3]此处“室”字与“家”字连用,义为家室,简文“室”字之义当为其引申之义,即家室。这便说明此时郑武公已经娶妻。《史记·郑世家》:“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10]根据《史记·郑国年表》,郑庄公生于武公十四年,叔段生于武公十七年[10],武公娶妻至庄公出生恰有三年之期。郑武公在位共二十七年,从叔段出生的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尚有十年,根据武姜对庄公的厌恶程度来看,若武公在此期间处卫,庄公又岂能顺利继位?故可推断,郑武公处卫当在武公十一年至十三年(公元前760 年—公元前758 年)为妥。
二、郑武公处卫原因探析
(一)东方诸侯之长
春秋初期的郑国在周王室与列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公元前717 年,郑伯朝见周桓王,周王因周郑交恶,不以礼款待郑伯,周桓公对周王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4]周桓公的意思是郑国对周王室东迁功劳至伟。平王东迁得到晋文侯、秦襄公、郑武公、卫武公的帮助,郑武公因此成为王卿[4],《清华简·系年》记载:“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14]正,训为长,郑武公成为东方诸侯之长[14]。由此可见郑国在周王乃至在东方诸国中的地位之崇高。
郑庄公时郑国与周王室交恶,周郑之间不仅互相质子,郑庄公更是在繻葛之战中击败周桓王,使周天子的权威荡然无存。繻葛之战前,周郑虽然交恶,然庄公朝见周王之后,郑庄公成为王卿,并多次带兵征伐。《左传》隐公九年:“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4]《左传》隐公十年:“冬,齐人、郑人入郕,讨违王命也。”[4]可见,作为周王卿士,郑伯有奉命征伐和平乱之责。
从春秋初期郑国的地位和郑伯作为王卿的职责来看,郑武公处卫可能在履行其王卿和东方诸侯之长的义务。
(二)戎狄交侵
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戎狄实力强悍,时常侵扰诸国,对周王室和各诸侯国构成极大危害。
周宣王在千亩之战中败于姜氏之戎。周幽王时犬戎攻灭西周。《诗经·小雅·采薇》记载:“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3]这反映出战争的激烈,可见戎狄之势强。
《左传》隐公七年:“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4]戎人朝见周王,向周室公卿致送礼物,但凡伯无礼于戎,戎人趁凡伯聘鲁时在楚丘击之。《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4]郑庄公三十年,北方之戎侵犯郑国,庄公用公子突之计,击败戎人。《左传》桓公六年:“北戎伐齐,齐使乞师于郑。”[4]齐国受到北部山戎的侵伐,向郑国求援,郑太子忽率军救援齐国。《史记·齐世家》:“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10]山戎攻伐燕国,齐桓公出兵救燕。“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告急于齐。”[10]狄人侵卫,卫向齐求援,齐助卫迁都楚丘。“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10]王子带借助戎翟之力进攻周王,齐国派管仲率军助周王室平定戎翟。“四十二年,戎伐周”[10],戎人再次攻伐周王室,周王向齐国求援,齐国率各诸侯国为周王戍卫。
戎狄的侵扰使各诸侯国饱受摧残,特别是郑、卫、鲁、齐等东方诸国,这也使得各国之间互相协作,共同对抗戎狄。郑武公处卫极可能与当时戎狄频繁袭扰东方诸国有关。
(三)郑武公处卫原因试析
由前文可知,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戎人侵扰诸国,且郑武公为王卿。为此,笔者认为郑武公处卫当为平定侵扰卫国的戎狄,其间过程曲折,因而处卫三年。
《左传》哀公十七年:“十一月,卫侯自鄄入,般师出。初,公登城以望,见戎州。……公入于戎州己氏。”[4]卫庄公登城时看到戎州,《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记载:“此戎国也,而曰戎州者,谓戎国之州里也。”[15]《路史》引梁载言《十道志》曰:“戎本国号,己氏其姓,今楚丘己氏城也。”又引《舆地广记》云:“谓昆吾后,别在戎者,周衰入居此。”[16]《旧唐书》云:“楚丘,治古己氏城。”[17]《春秋地名考略》记载卫国有两楚丘,“一在汉己氏县,以戎伐凡伯之楚丘为名己氏。春秋时为戎州……隋改置楚丘,唐宋元皆因之……今在曹县东南之四十里,此楚丘之在南者也。一在汉白马县,即《水经注》所云者,寻改名卫南。杜佑《通典》,白马,春秋卫国漕邑,卫南,卫国楚丘也。《元和郡县志》,隋置楚丘县,后以曹县有楚丘,改名,《旧唐书》,卫南,隋楚丘县,后改名置楚丘城……此楚丘之在北者也”[18]。由此可知,唐代之楚丘即春秋时卫国之戎州,即春秋时戎伐凡伯之楚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记载此戎在今山东曹州府曹县东南四十里楚丘。[15]鲁隐公九年北戎侵郑,关于此北戎之所在,《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认为在今河南省北境,或在河北省南境[15],在《郑文公问太伯》中,太伯提到郑庄公伐戎的功绩,“世及吾先君庄公,乃东伐齐酄之戎为彻”[1],关于齐酄之戎,简文整理者认为“齐酄之戎疑即北戎,或处于济水与斟灌之间,斟灌在今河南范县东南与山东交界处”[1],根据地理方位来看,侵郑之北戎与卫之戎城相近,并且居于卫、鲁、郑等国之间。
前文推断郑武公于公元前760 年—公元前758 年处卫,此时卫国由卫武公执政,即卫武公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卫武公在位共五十五年,这三年是卫武公执政晚年。《史记·卫世家》记载:“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10]卫武公与郑武公同为姬姓,且曾共助周平王,两国关系应当紧密,楚丘之戎于周衰之时入居中国,周衰应指犬戎攻破镐京,西周覆灭。周王室势力衰微,迁居中原或楚丘之戎则趁机侵害各诸侯国,卫国此时值卫武公晚年,且戎人势力较强,卫国难以抵挡,郑武公此时为王卿,又为东方诸侯之长,有平乱之责,处卫三年当可能为帮助卫国平乱。《郑武夫人规孺子》中武姜说:“自卫与郑若卑耳而谋。”[1]由简文整理者释义可知,“与,犹助也,卑,犹近也”[1],卫国帮郑国谋划,两国在谋划什么不得而知。根据简文,郑国三年没有君主,若没有贤臣的帮助,国家就会乱,之后提到两国“卑耳而谋”,则此谋划当与郑武公处卫有关,郑武公帮助卫国时应是卫国遇到困难,戎人实力强大,郑武公也难以招架。公元前714 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4]。面对戎人,郑庄公仍感到忧虑,郑武公遇挫便不足为奇。在《郑文公问太伯》中,太伯对郑文公讲述郑武公功绩:“世及吾先君武公,西城洢、涧,北就邬、刘,萦轭蔿、邘之国,鲁、卫、蓼、蔡来见。”[1]卫国与鲁国前来拜见郑武公,或许是因为郑武公平乱之故,而郑庄公时北戎侵郑则可能是报复郑国。
三、小结
关于郑武公处卫三年问题,在时间上,笔者赞同晁福林的观点,并结合《清华简(陆)》和传世文献进行了剖析,认为武公处卫时间为其在位的第十一年至十三年。在处卫原因上,笔者通过分析春秋初期郑国之地位及当时东方诸国遭受戎狄之乱的背景,推测武公处卫是为了帮助卫国平定戎乱,但其间遭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