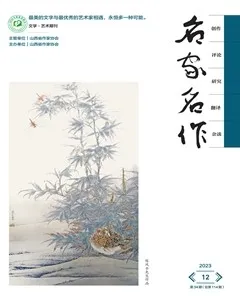论《荒凉的西部》与《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的互文性
张君仪
马丁·麦克唐纳(Martin McDonagh,1970—)以黑色暴力的主题和侵略性、对抗性的艺术风格被归为直面戏剧(In-Yer-Face Theatre)的代表剧作家之一。他是一位具有英国与爱尔兰双重国籍的男剧作家、编剧和导演,出生于伦敦坎伯韦尔,父母都是爱尔兰人,因此有英国伦敦与爱尔兰戈尔韦的生活背景。麦克唐纳的剧作虽然为数不多,但荣获了无数奖项。他的第一部戏剧《丽南山的美人》(The Beauty Queen of Leenane, 1996)创作于26 岁时,首演于戈尔韦德鲁伊剧院,后由英国皇家国家剧院上演于伦敦,继而又在纽约热演,并获得英国戏剧评论圈剧作家新秀奖、百老汇“托尼奖”等多项大奖。在《丽南山的美人》之后,麦克唐纳又创作了《康尼马拉的骷髅》(A Skull in Connemara,1997)和《荒凉的西部》(The Lonesome West,1997),构成了“丽南山三部曲”。
约翰·米林顿·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1871—1909),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剧作家。辛格在其戏剧对话中再现了爱尔兰农民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及富有诗意的语言。辛格在一些戏剧作品中对这些人物嘲讽性的描写招致谴责,有时甚至在剧院引起骚乱。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骑马下海的人》(Riders to the Sea,1903)是一部单幕的抒情悲剧,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辛格最好的戏剧作品。《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1907)是一部纵横恣肆及冷嘲热讽的戏剧,是辛格最有名的作品。两部剧作不仅延续了同样的主题,做出相似的情节呼应,同时全剧中均不断穿插了荒诞的喜剧元素,和爱尔兰乡村语言形成了明显的互文效果。将之放置在爱尔兰民族文化背景之下,由文本内部的对话延伸至文本之间,挖掘爱尔兰人民被边缘化的声音,从而建构自己的民族身份。
一、文本互涉:家庭伦理冲突与暴力主题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研究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好像是一幅引语的马赛克镶嵌画,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1]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也叫文本间性。互文性包括: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 (一般称作intertexuality)。互文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呈现为一个开放、流动与不断演进的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文学观点的修正甚至批判。这种转变不仅强调了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揭示了文学作品的动态性和开放性。在以往传统观念中,作者被视为作品的缔造者、主宰者以及支配者。换句话说,即将作者创作置于巨大且相互关联的文本场之中,这离不开对已有文本进行有意或无意的改写。
在互文性视域下,最直接的策略则是引用,将被引文本的原意与作家的创作意图相结合,往往会突破被引文本的原意而产生新的表达效果。马丁·麦克唐纳的《荒凉的西部》就直接引用了辛格《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中的一句台词作为剧名的参考——“哦,今天,在这荒凉的西部闪耀着圣洁的光芒。”[2]可见麦克唐纳有意延续“荒凉西部”这个空间中的故事书写,将爱尔兰西部神话放置于当代背景下重新讲述,为其扩充更丰富的内涵。
通过化用谚语故事、重大事件、经典典故来完成故事书写的策略更具有民族性。耳熟能详、代代相传的主题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形成各种文本时空,但都高度凝练着本民族共同文化语境中的话语表达。20 世纪90 年代,在英国和爱尔兰戏剧界兴起了“直面戏剧”之风,以萨拉·凯恩(Sarah Kane)、马丁·麦克唐纳等剧作家为代表,以独特的、体验式的舞台实践带领观众直视暴力现场及道德困境。其中,麦克唐纳锚定爱尔兰背景下的家庭伦理、社会道德和国家身份等问题,延续了自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以来回归乡土的传统,运用诸如19 世纪大饥荒等爱尔兰人民熟知的事件引发共鸣,并结合全球化语境进行深入的历史文化反思。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与麦克唐纳的《荒凉的西部》以爱尔兰当地同一个真实的新闻题材为故事原型:“一位在口角中失手用铁锹把父亲打死的青年逃到岛上,受到岛民的保护,躲过了警察的搜捕,后来偷渡到了美国。”[3]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爱尔兰戏剧运动的背景下,辛格用辛辣的笔调讽刺了爱尔兰西部田园神话透露出的狭隘民族主义。麦克唐纳则聚焦全球化时期被殖民创伤所笼罩的爱尔兰民族精神上的荒芜和文化身份上的失语。
此外,两部剧作中的主角都触犯了“弑父”的伦理禁忌,并诉诸暴力抗衡,这种主题上的沿用形成了文本互涉的暗示。热奈特在《隐迹稿本》中对引用的形式进行了区分:直接引用即传统手法上的引用(citation),一般带引号,有准确的参考资料;暗示则是透过一个书名、人名或特定的文字符号,对另一文本进行变换表达或者转述,需要读者对一段表述进行透彻的理解,并能抓住这种表述的变换形式。[4]《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中的克里斯蒂·马洪因争端杀父未遂潜逃,但他竟以此吹嘘而获得了梅奥郡村民的追捧,显示出当地村民对暴力的无端崇拜和伦理混乱场景。《荒凉的西部》中的科尔曼因父亲嘲笑自己的发型就开枪射杀父亲且毫无悔改之意,此后兄弟二人继续暴力对抗并争夺财产。二者任由非理性意志控制自己的行动,此种对伦理禁忌的触犯行为意味着对伦理秩序的根本性破坏。
二、社会伦理失衡:民族浪潮与殖民阴影
萨莫瓦约在《互文性研究》一书的引言中说道:“文学是在它与世界的关系中写成的,但更是在它同自己、同自己的历史的关系中写成的。”[5]纵观爱尔兰民族的历史,从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到大饥荒,时代总是呼唤着作家书写历史、正视创伤。正如托宾所言,爱尔兰小说被具有神话性质的爱尔兰历史所抢占,这种历史是建立在悲剧结局与英雄主义叙事之上的。[6]
20 世纪80 年代的“凯尔特之虎”时期是新旧爱尔兰过渡的转折点,也是爱尔兰民族文化从本土走向世界、从落后走向现代、从一元走向多元的重要转型时期。在宽松多元的环境里,麦克唐纳可以以更冷静客观的态度审视历史创伤问题。他的作品中常出现杀父弑母、兄弟相残等冒犯伦理禁忌的情节,在一定程度上是英国与爱尔兰长期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的隐喻。一方面,面对强势入侵的殖民者文化,大量爱尔兰人成为无根的离散者,他们既无法融入英国主流文化,也无法再回到爱尔兰本土文化中,他们被这种文化错位所撕裂。另一方面,被殖民者模仿和延续了殖民者的暴力行为,正是爱尔兰被暴力殖民剥夺话语后社会伦理失衡、人们陷入精神危机的体现。
根据霍米·巴巴的理论,模拟是宗主国殖民者所施行的一种殖民控制形式,但同时也是一种反抗策略。[7]长达八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20 世纪30 年代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得爱尔兰人民迁居离散,家庭关系破裂和社会异化问题尤为突出。“家”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符号,这个古老的概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它与爱尔兰的文化、历史和价值观紧密相连。因此,以麦克唐纳“丽南山三部曲”为代表的戏剧作品往往以家庭关系破裂为出发点,展现了人们在人际关系分崩离析的异化社会中对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文化身份做出的反思。正如在故事发生的戈尔韦郡,始终被边缘化的爱尔兰文化和长期被压抑的本土述说带来的是扭曲的社会环境,导致手足相残、迫害亲人等故事屡屡发生。在《荒凉的西部》中,过度践踏康纳兄弟尊严的父亲将暴力言传身教,而兄弟二人沿袭了此种兽性因子并采取抗衡手段,以兄弟二人为主的人物无处宣泄心理错位感,最终诉诸暴力。
评论家迈克尔·比灵顿认为麦克多纳在以爱尔兰为背景的作品中,不是挑战爱尔兰人的刻板印象或批判当代爱尔兰社会,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关于爱尔兰的现实……谋杀、自残、怨恨、无知和家族仇恨”[8]。麦克唐纳曾表示《荒凉的西部》中威尔士神父的角色代表了自己的思想和视角,同时借其之口说出了对于宗教信仰、法律漏洞等社会问题的反思。威尔士神父面临着伦理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引导康纳兄弟化解恩怨、避免手足相残是神父的职责,但尝试各种方法后,他为二人的麻木不仁深感痛苦,不得不以自戕的方式为其赎罪。另一方面,他作为神父自戕显然违背了教义。他为此慷慨赴死以后,康纳兄弟仅仅恢复短暂的平静,随后再次互相攻击起来,威尔士神父的伦理诉求始终没有实现。
稳定的社会空间因暴力被打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均表现出一种病态、扭曲的特征,直白展现了当地的伦理混乱局面,刻画了爱尔兰社会的局限性。
三、追寻文化身份:西部神话与爱尔兰性
“爱尔兰性”是相对于“英格兰性”的概念。“英格兰性”的特征是现代化、工业化和都市化,“爱尔兰性”则背靠乡村和田园,以复兴盖尔语、天主教和西部地域为主要表征。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眼中,西爱尔兰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他们还将这里视为爱尔兰文学复兴的基础。在此背景下,爱尔兰西部便成为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基石,叶芝等人用理想和诗意的方式描绘了西部神话,表达了对民族独立的追求。
《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是非传统的英雄悲喜剧,因“轼父”行为受到赞扬的克里斯蒂·马洪来到位于爱尔兰西北部的梅奥郡,在此地,他的“英雄”身份建立在无知村民对暴力的追捧之上,事情败露后,他陷入自我确认的迷惘状态,试图真正通过弑父来恢复身份,“你死了以后可以站在地狱门口摇旗,欢迎我两三个星期以后再到来。我想撒旦也没见过多少人能在克雷郡杀了自己父亲,在梅奥郡又杀一次的吧”[9]。但他最终意识到必须离开这片西方田园才能完成真正的自我成长,这个追求自我认证的过程同时隐现了爱尔兰民族的“自我认证”。1907 年2 月,叶芝在阿贝剧院关于这个戏剧的讨论上说道:“我们开始再次思考他是什么样的人,到底什么才是爱尔兰人。”[10]辛格创作的年代,爱尔兰还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作者诉诸暴力手段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剧中村民对“弑父”的称赞与理解暗示了爱尔兰反抗英国政府的民族决心。辛格将喜剧和恐怖的元素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独立的社区场景,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英雄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揭露了爱尔兰民族个性中的自卑、愚昧和粗暴,但他所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仍然较为传统,希望观众能够在剧作的讽刺意味中醒悟,重新振作拼搏,坚守住民族信仰和文化身份。
弗洛伊德强调,恐惑并非产生于现实中陌生的东西,它只是被压抑至潜意识而日益疏远,当这些事物(以其他形式)再次出现时,会导致个体产生似曾相识的恐惑感。这些被压抑事物的复现又被称为“复影”(double)。复影的出现模糊了过去与现在、熟悉与陌生、意识与无意识的边界。最终,“相同的事情不断地复现,即相同的特征、秉性、兴衰、变迁及罪行,甚至相同的名字在连续几代人身上反复出现”。西部一直是爱尔兰文学中的重要因素,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文学家对爱尔兰民族性、诗性的浪漫主义想象,西部作为反复出现的对象,召唤着爱尔兰人民回溯过去的创伤体验,并时时渴望得到自我主题的确认和稳定的文化身份。
在马丁·麦克唐纳生活的全球化时代,爱尔兰已取得民族自主独立,单一的凯尔特文化渐渐地发展为多元的杂合体。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他的作品中也出现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肥皂剧桥段、流行音乐元素等,同时还借鉴爱尔兰语词汇融入英语,形成了独特的戏剧艺术风格。剧中的人物也或多或少地表露出对美国的排斥以及前往英国生活遭受歧视的创伤记忆,可以看到,以戈尔韦郡为代表的爱尔兰人的诉求始终是稳定的身份认同。
诚如麦克唐纳坦言自己“既不属于英国人,也不属于爱尔兰人”,尽管他拥有双重国籍,但自小的个体离散体验让他成为“居间”状态,传统的身份建构在此失效,形成了特殊的杂糅身份。而他用直面戏剧的方式,以冒犯性和攻击性的姿态解构过去稳定的伦理环境,消解了传统爱尔兰剧作家的田园式书写。剧作家用解构的方式直白揭露爱尔兰的被殖民创伤,反映了其在后现代背景下对异化社会的伦理思考和对爱尔兰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