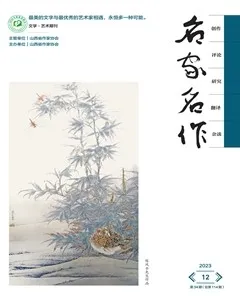《樱桃园》中错位的自我与时间
——谈契诃夫笔下的“多余人”
乔紫菲
别林斯基在谈到“多余人”这一形象时,提出:“这些人常常被赋予了伟大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道德品质,他们本可以大展其才,但却鲜有作为,或根本无所事事……”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彷徨在两个阶级之间,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流浪者身份,因而以否定当下的方式,渴望一个安稳的立足之地。契诃夫以“多余人”对时间的逃避入手,融合俄国文学的独特文化气质,剖析他们优雅外表下精神的风暴和生存处境的狭小。在错乱的时间观念下,“多余人”将自我锁在过去的回忆中,造成面对现实的自我的缺位,从而当现实问题入侵时,出现人格错位和精神失控;圣愚文化传统赋予俄国文学的非理性倾向的特殊气质,在多余人身上凝结成一种对世俗秩序的否定,揭示其群体性的否定气质和漂泊性的生存状态。然而契诃夫仍旧秉持着对个体独立价值的张扬和游戏精神的推崇,试图给予这群四处碰壁的人一次选择的机会,消弭对时代更替本身的价值判断,完成关于时间、现实和喜剧的更深入的现代性思考。
一、时间错位下的精神病状态与返童行为
人与时间的冲突是契诃夫戏剧中永恒的话题,剧中的“多余人”无力应对时代的极速变革,能动性极弱的他们只能将自我埋藏在过去的回忆中,将回到樱桃园视为回到过去的生存空间里。然而人的意志无法控制生活的实际进程,应对现实的自我的缺位造成客观世界的人格呈现的不稳定性,从而出现一系列的精神失常,主要表现为自我意识障碍和返童行为。
剧中人对时间的流逝非常敏感,他们一点点感受着时间对他们所剩不多的安逸的吞噬,而后陷入自我意识障碍。《樱桃园》中的柳波夫遭遇了丧子丧夫的痛苦,流转于巴黎和俄国之间,俄国对她而言是可以逃避巴黎痛苦“现实”的“过去”。她想躲在美好的田园牧歌里,然而来自巴黎的电报比她还先到达,她到达之时樱桃园已经面临不可挽回的破灭。她迫不及待地投入回忆里的内心世界:“我可爱的、美丽的育儿室……现在,我也还像个小孩子……”现实却时刻提醒着她这份期待的破碎:陆伯兴传来樱桃园将被拍卖的噩耗,剧中人物频繁的报时提醒她痛苦时刻的逼近。“太阳落下去了”“月亮升起来了”……时空观念的错乱让她不知道自己该属于哪种人格,她充沛的情感应激性地紊乱,本能地去保护让自我更舒适的精神世界,于是抛下了优雅的社交形象,造成现实人格精神的失控。在收到巴黎寄来的电报时,在柳波夫的心理世界中,过去与现实交织,她做出了“撕碎电报”的戏剧动作,而后又回到“我听着远处好像有音乐吧”的话题,这个音乐性看似是将她带回来现实时空,实际上是将现在时空的物理真实性再一次抽离,回到了她这段一开始的状态“我总是像疯子一样的”,她的精神再一次飞走了。[1]她的情绪大起大落,上一秒还是“多么可爱的花园啊”,下一秒便可以“轻声啜泣”;当彼楷提醒柳波夫樱桃园必然会被拍卖时,柳波夫开始在过去与现实的时间中自我挣扎,她疯狂地攻击彼楷,好像这样就能击退残酷的命运,“您简直是个怪物”“不成器的东西罢了”。这过激的言行无论与她优雅矜持的身份还是天真多情的内心都有极大的反差,柳波夫在错乱的时间观中也迷失了自我人格的归属。
“多余人”没有奋斗的概念,这份成长的缺席让他们活在空想的罗曼蒂克里,饱经挫折又无法克服内心与现实的冲突,于是他们将自我封闭在最自在的童年状态里,出现一系列返童行为。柳波夫用逃避来延续对未来的期待,然而“她所逃避的每一段过去都让她的现在变成了痛苦的折磨,而她所逃避的每一个当下又都变成了痛苦的过去”[2]。在对自我的本能保护机制下,她用孩子的心理来遮挡痛苦的风暴,她的一举一动像极了少女——“(以手掩面)我好像在做梦呐!”“瞧,去世了的母亲在花园里来回溜达呢!”而对于加耶夫而言,他的返童行为透露着一种宿命性的可悲,穿衣服都要别人照顾的巨婴却总突然开启理想和浪漫的演讲,即使什么都不做还会沾沾自喜。家族身处困境,身为男人的他仍然活在温室的幻梦里拒绝成长,由此可以看出契诃夫对他深深的失望和对这类人必然灭亡的预见。
对话的无效化是返童行为最多的体现。安涅和董涅莎相见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自说自话;柳波夫只能听到“卖花园”却自动忽视“还债”的问题;加耶夫总幻想着可以依赖别人天降横财;柳波夫即使已经没钱了还借钱给别人……不止一次有人说过樱桃园是必然会被卖掉的,但他们无法取舍,就像孩童一样将问题甩开,期待被大人拯救。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自欺与放弃行动的方式来对抗这种无能为力感,然而时间并不会因为人物行动的停滞而停滞,困在过去的“多余人”在向前流动的时间中必然会如逃犯般心惊胆战,最后被无情击毙。
二、俄国圣愚文化下“多余人”群体的否定性气质
王志耕教授的《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一书中认为,圣愚传统框架下的俄罗斯文学以其非理性倾向对理性主义加以否定和制衡。这种否定的力量在多余人身上体现为对世俗秩序的否定。[3]尽管“多余人”身上缺失了圣愚文化中苦难与信仰相通的肯定性精神,但圣愚文化中,生命的意义往往以逃离、漂泊和对世俗秩序的破坏的形式存在,这与多余人的生存理念相切合,这种生命的存在形式塑造了俄国文学中多余人抗拒与疯癫的否定性气质。
契诃夫笔下多余人的抗拒行为往往是以理想而非理性的防御机制否认客观的秩序,以一种叛逃乃至狂欢的形式来否定真实的、世俗的世界。“多余人”贪恋短暂的安全感,也对这份感觉高度敏感,当来自外界的压力试图入侵时,便会无意识地开启防御姿态。樱桃园的衰亡触发了他们无意识中的否认机制,他们尽力缝补起每一个话语的空隙,随便什么都要拿来消遣,维持世家大族的热闹体面。陆伯兴说完“樱桃园和别的地产,可全都要拍卖了”,柳波夫不愿面对,就马上将注意力转移到干樱桃的秘方上;剧中的多处停顿已成为整部剧的特色所在,在现实的重压下,无聊的话题无法进行,所以在短暂的停顿里寻找新的话题支点来否认危在旦夕的现实,每一步停顿都承担着被残酷现实乘虚而入的风险。然而任何否认都说明了拒不承认,他们在自我的意识域中接受衰落的庄园,又在无意识域中守护理想化的信念。圣愚文学中对苦难的焦虑书写,在“多余人”群体身上体现为对残酷现实的无力感与一次次的出逃失败,将这类人对世俗秩序的否定态度具象化的同时昭示“多余人”生存处境的狭窄。
圣愚形象在俄国文学中常常被赋予狂欢化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多余人”身上体现为幻想特质的彻底解放和抗拒态度的顶点宣泄。他们自恋,认为自己可以靠闪烁的人格魅力获得拯救,用空洞的最佳期待回击尖锐的现实问题。当庄园的毁灭越来越势不可当时,他们则办起了狂欢的舞会,用最庄园化的仪式来发泄内心的欲望,在结局到来之前彻底麻醉自我。因为每一分一秒都过得不安,所以汲取更浓厚的贵族痕迹作为幻想的依托,以稀释浓烈的危机感。以漂泊和苦修来坚定精神追求的圣愚精神,在“多余人”身上呈现为如小丑一般挣扎于现实时空却陶醉于幻想世界,凝结成一出“丢弃船桨漂泊于幻想世界而无法停泊归靠”的悲剧。
疯癫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直接弃绝的表现,契诃夫以他者视角描写“多余人”与社会文明的悖论,又以疯癫的“多余人”的视角刻画他们在弃绝中的成长演变之路,完成了圣愚精神关于在否定中探索自我、在否定中超越自我的精神品格诠释。旁人视角下的加耶夫说话像乌鸦一样吵闹,是像小丑一样供人取乐。柳波夫固执地维持着早不属于她的浪漫天真,活在贵族时间里的她逐步放弃了在现实时间里的话语权。“多余人”与社会秩序的悖论,是对所处的现实生存空间的一种无力的否定,一旦被认定为疯癫,他们的话语权就被剥夺了,这等于将他们永久地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成为被忽视和遗忘的对象。
而在疯癫人物的视角下,无法理解的社会秩序正在慢慢适应自身,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在成长中正在慢慢回归,他们在与世俗的相互否定中完成了生命意义的探寻。加耶夫被大家讨厌,高呼着陈词滥调,但始终想办法筹钱,最后在社会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处;柳波夫是情感上的巨人,但在最后慢慢回归理性来接受现实;安涅从高呼着美好的世界到最后真正踏上新世界的道路……疯癫的存在的意义不在于疯癫本身,而在于为什么会有疯癫,疯癫给人们带来了什么问题。在这一层面上,契诃夫不拘泥于对“多余人”与圣愚文化中生命存在的外在形式联系起来,而是统领人物完成了与圣愚文化里超越的精神品格和永恒的生命价值的内在融合,以对理性社会秩序的否定,获得“多余人”群体超越性的成长意义。
三、契诃夫残酷精神下的喜剧期待
契诃夫毫不掩饰地刻画出他眼中“多余人”的脆弱和病态,然而他站在社会、世纪之交,看着麻木迷茫的青年人无法对自己的良知撒谎:失智的“多余人”是否活该沦为牺牲品?资本主义的暴政是否借了贵族的消亡来掩盖?残酷的现实囚禁了“多余人”的出路,契诃夫选择用他所擅长的喜剧精神给予这群被裹挟的人一次选择的权利。
“个人意识形态对霸权主义意识形态不畏惧、不迎合、不巴结、不屈服,而是报以轻蔑,立志颠覆之、解构之,使其变得荒谬可笑。这种精神便接近了喜剧精神的境界。”[4]契诃夫在剧中引导性地让“多余人”寻找自己的个体独立价值。尽管契诃夫冷酷的笔触下展现了“多余人”在非理性命运中的挣扎,但人物命运的荒诞都来自他们无法割舍掉生活本身的悖论,而并非自我能力的低下和人性的扭曲,甚至他们总是善良和天真的。契诃夫鼓励每个主体都看护好自己的个人价值,甚至残忍地将他们踢出荒诞的幻梦都可以视为是对其个体价值有效性的保护。观众心理预期里会发生的巨大的不幸并没有发生,老人卸下负担死去,青年的悲伤很短暂,来自资本社会的对他们毁灭性的打击并没有降临,时间依旧向未来走去,契诃夫没有让柳波夫一行拜倒在资产阶级的足下,而是给予他们一次平等的选择现实的机会。“多余人”最后仍旧保持着的内在优越感,实际是在精神上摆脱了环境的束缚——即使不生存在幻想的乌托邦,也仍旧认同自我的价值,使试图创伤自己的时代显得滑稽可笑,这是契诃夫送给“多余人”的喜剧礼物。
喜剧精神的另一个特点是崇尚快意的游戏化的生存状态。“游戏精神是一种鼓励生命力自由挥洒、自发创造的精神,为生活增加喜剧色彩直至将生活艺术化。”[5]在庄园易主这件事上,人物所做的决定全凭自我感受,不顾及理性思考,只在意当下喜忧,哪怕经历了守旧时代的挣扎和疲惫的精神内耗后,他们也只是在“离开—归来—离开”的圆形结构里回到起点。他们一腔激情地到处“惹祸”,却不用承受过多代价,反而在体验过生活的风暴后成长了不少,仿佛人生是一场“万般皆备于我”的游戏。柳波夫可以如释重负地接受樱桃园易主的现实,感性的情感与冷静的现实得到了平衡;费尔司临死前还在惦记加耶夫的冷暖,却不知加耶夫已经学会自己穿上外套。他们的生活跌宕起伏,却又荡漾着哲理的回味,他们夹在时代变革的缝隙里,但他们的身上却被契诃夫赋予了未来属性,不在兜兜转转中沉沦,而是拥有快意地向前走的机会。
契诃夫清醒地认识到每个时代必然会面临美好珍贵的曾经与历史前进的必然之间的悖论,他想要让我们每一代人透彻地认识生活的全貌。得到庄园的陆伯兴放肆地狂喜:“(讥讽的)新的地主,樱桃园的领主来啦!(无意中碰了一只茶几,差点没把烛架弄翻)什么我都赔得起!”他全然忘记里往日对樱桃园的敬重、对柳波夫的爱戴,内心压抑的“庸俗的自我”暴露无遗;而柳波夫一行人,在错乱的时间和精神中饱受煎熬,却已经整装待发奔向新生活。新世界的诞生必然会以母体的撕裂为代价,新的罂粟园未必不会被其他花园所摧毁,陆伯兴也未必不会成为下一代的“多余人”。但离开的“多余人”未必会是永远的“多余人”,他们拥有了重新选择的权利。契诃夫拒绝对时代更替本身做出价值判断,工业社会的飞速发展无法掩盖资本的罪恶,贵族阶级的庸俗麻木也无法否定人本身的独立价值。苏珊·朗格曾经断言: “除了悲剧,是没有永久的失败,也没有人类永久的胜利的。因为只要生命在行进,自然肯定就会发展。”[6]这句话是对契诃夫喜剧精神的终极诠释:永恒的生活无法守护,但改变的机会永远存在。
四、结语
《樱桃园》里“多余人”与时间的矛盾成就了其“内在戏剧性”,在湍急的外部时间和凝固的心理时间的相悖下,人与人的外部冲突被消解,环境所产生的压力造成人的自我失格和精神创伤。契诃夫残酷的客观性让他跳出感性的视野观察世界,新时代必然会刺伤来自旧时间维度的“他者”,然而新时代也无可避免地刻有无力和罪恶的烙印。契诃夫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感来洞察最深刻的问题,他冷静地剖析着“过去”与“现在”在“多余人”精神里两败俱伤的场面,描绘了个人面对时空的渺小,然而他所加入的关于“未来”的书写则消解了悲剧的意蕴,胜者和败者都沦为绵延时空里的玩笑、游戏。契诃夫在人与时间的悖论下审视着,却不刻意批评判断,他认识到时代交替不过是最自然的事情,每次时代碰撞下都会有个体被困在精神牢笼,但在良知与责任感的驱使下,他将有未来属性的喜剧精神送给夹缝中生存的“多余人”,若愿意重新选择则是实现个体独立价值的机会,若仍旧庸俗无为也不过是漫漫时间里的玩笑。在生命的末期,契诃夫借《樱桃园》完成了对现代喜剧的探索,于世纪之交对人类生存与时间进行了最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