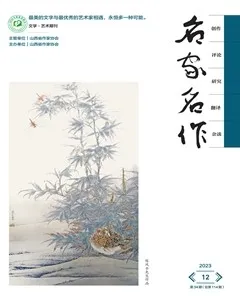论迟子建小说的个性、灵性与智性
——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
吴雪婷
《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小说以鄂温克最后一位女酋长的自述口吻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力量。书中呈现出鄂温克族人的纯粹与勇敢以及一段民族变迁史,表现出鄂温克族人的顽强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小说以厚重的史诗品格和文明进程中的辩证思考令人称道,对鄂温克等民族生存状态和萨满文化的关注更构成了小说的内在肌理。
一、个性艺术的写作风格
作家的作品展现着特有的地域风情,对于作家而言,地域文化积淀尤其具有珍贵的价值。迟子建对鄂温克族写作的思路,也是来自独特的地域文化。作品中的鄂温克人是从游牧发展到定居的,从事着畜牧的生产方式。鄂温克人在山林中牧养和经营的驯鹿是他们的生存来源。人们要随着驯鹿生存习惯和食物来源决定是否居住,所以随着驯鹿搬迁是常有的事情。在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就谱写了一曲关于鄂温克人的艺术挽歌。
美国乡土小说家赫姆林·加兰说过:“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的源泉。”这句话印证着迟子建的创作个人特色。迟子建出生在我国最北端美丽的北极村,那里多种多样的植物和活泼可爱的动物陪伴她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她总是可以感受到自然中生灵的原始气息和本真魅力,得到关于生命最初的理解。从一朵花的春天发芽到秋天的掉落可以看到自然规律的不可违背,但同时也可以感受到生命的从容与释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就表达出鄂温克人对待生命诞生与死亡的接受态度,对待万事万物的良善和对待自然的保护和敬畏。通过作者温婉流畅的语言表达着诗意的生存方式。如“拉穆湖中生长着许多碧绿的水草,太阳离湖水很近,湖面上终年漂浮着阳光,还有粉的和白的荷花。拉穆湖周围,是挺拔的高山,我们的祖先——一个梳着长辫子的鄂温克人,就居住在那里。”①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第12 页。这样具有优美自然风光的生存环境是得天独厚的灵感来源,湛蓝的湖水、明媚的阳光和巍峨的群山,让读者不自觉地陶醉其中。
这样的原生态的地域文化影响着作家的写作风格。在文学创作中,作者在语言叙事方面贯穿着民族化的方言词汇。正是因为民族语言的融会贯通和作者的艺术建构,才使得《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本流畅自如,美好的生态环境和现实的朴素纯真得以水乳交融。在文中,作者侧重描写以听觉为主的感知方式并且传达了主人公的心思变化和感受。在夜晚跳“斡日切”舞时,大家拉手转圈跳舞,一左一右,女人发出“给——”的叫声,男人发出“咕——”的叫声,这声音恰似天鹅从湖面飞过。曾经这声音驱赶过敌人,人们为纪念天鹅的救命之恩,发明了“斡日切”舞。声音也传递着作家的暗示感情基调,在林克去交换驯鹿却被雷劈到那次的雷雨声描写格外让人感到寒栗,“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炸雷,‘轰隆——’一声,森林震颤了一下……雷公大约觉得这雨还不够大,它又剧烈咳嗽了一声,咳嗽出一条条金蛇似的在天边舞动着的闪电,当它消失的时候,林间回荡着‘哇——哇哇——’的声音”。萨满跳舞高歌的声音、动物野兽的咆哮声音和鄂温克姑娘们欢声笑语的声音,在生活中也深深触动着大家。作者在写作民族资料的时候自觉地使用当地鄂温克语言,包括亲属关系的称呼、生产生活器物的命名和宗教信仰的语言等等。东北地方文化曾经受萨满教影响较大,在迟子建的作品中多次展现着神话神歌的独特魅力。在第一人称的作品叙事视角中,曾让“我”一生最惊心动魄且最难以忘怀的时刻,就是达西跪在火葬金得的现场时,向刚变成寡妇的杰芙琳娜求婚的时刻。妮浩伴着噼里啪啦的火声唱起了“魂灵去了远方的人啊,你不要惧怕黑夜,这里有一团火光,为你的行程照亮……那里有星星、银河、云朵和月亮,为你的到来而歌唱”①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第128 页。。迟子建将萨满神歌和经历的事件交融在一起,使作品更具有吸引力。
作者通过语言和歌唱等写作方式传达出了对生命和经历的情感态度。迟子建以饱含温情的笔触演绎着鄂温克族的历史变迁,表达出人类对诗意栖居的追问和探寻。《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语言文字的感染力,使得作者在叙述这一少数民族时更多了些鲜活的艺术审美氛围。
二、灵性自然的神秘敬畏
“灵性”一词近于神性,极具神秘意味,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萨满文化赋予《额尔古纳河右岸》飞扬灵动的想象力、自然奇幻的神秘色彩以及深沉苍凉的美学风格,以其独特的生命品格,神秘诗意地讲述着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迟子建曾说:“在这样一片充满了灵性的土地上,神话和传说几乎到处都是。”②迟子建:《锁在深处的蜜》,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第66 页。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笔下的山川、星辰、动物和植物等,它们无一不沾染着灵性神秘的传说和气韵,显然在这生活的人们会接触到更多的传奇故事。
鄂温克人崇尚自然,信奉万物有灵论。在日常捕猎生活中,对待身旁的树木、水源以及动植物都有不一样的心灵感触。在狩猎熊的时候有特别的禁忌和仪式,要在吃它的时候发出“呀呀呀”的叫声,切熊肉的刀不论锋利与否都要叫“刻尔根基”表现出钝刀的意思,吃剩的熊骨头也不能乱扔,否则可能和马粪包一样差点被噎死,这些行为都凸显出人们视动物为主体的生态意识。在小说中“清晨”的起始部分,“我”的出生就是在父亲林克狩猎到一头黑熊的欢乐氛围中叙述,而且尼都萨满跳到火里并且沾了火星都安然无恙。这具有铺垫性的叙述在后文中处处体现着作者感应自然万物的心态。在“黄昏”中,“我”回想到与拉吉达相识始于黑熊的追逐和瓦罗加的永别也是因为黑熊。两任丈夫的相识与永别,都与熊有关,它是幸福的源头也是终点。在小说中不乏人、动物与自然的灵性感应,在林克出发去阿巴河畔换驯鹿那天,达玛拉似乎有某种预感,在林克临行之前,一次次嘱咐跟随林克去的那只通人性的猎犬。那天暴雨后的彩虹是两条,不一会儿有一条颜色黯淡了,另一条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天象也似乎暗示了林克的死亡。在书中“黄昏”部分,妮浩萨满的孩子一次次因为她救助其他人而去世,一命换一命的结局让她悲痛不已。女儿交库托坎是为了救助当时被熊骨卡住喉咙的马粪包而去世的。交库托坎的名字是百合花的意思,似乎美丽娇嫩的花总是会过早凋落。并且作者在写作时总是淡化着有原因由来的恶,相信人人都是良善温厚的。这片土地的魄力和情怀,延展成了人性的雄浑和美学力量。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教的悲悯情怀内化为作家的生命品格,她用温情悲悯的情怀续写着别样的风采。在文中,重点写了两位萨满形象。其中妮浩萨满的形象令人尊敬,体现出她伟大的人性光辉。小说中无不体现着浸润温暖的人性世界,多次的跳神仪式中的神歌都体现着作者及天意的态度,这种写作丰富了小说中的浪漫诗性审美。鄂温克族人凭借着自身的智慧和勇敢,一次次在苦难中存活了下来。但是在“黄昏”的末尾,饱经沧桑的妮浩萨满在扑灭了1998 年初春的人为引起的山火时去世了。在经历了妮浩萨满这一生的艰难之后,人们感受到萨满的责任与痛苦,就算是拥有神力与大爱的智慧也无法挽救氏族的悲歌,便阻止了新的萨满的诞生。迟子建在文中呼唤着人性的美好,正是萨满形象因其充满人性与博爱而使人们得到尊重。
拥有灵性的大自然是鄂温克人生存的具体条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写到死亡的时候无不体现着族人对大自然的崇拜和守护。父亲林克去世后,尼都萨满举行风葬仪式时,在四棵直角相对的大树上搭了很高的铺。林克是被雷神取走的,雷来自天上要还于天上。这让人体会到深入大自然的灵性、与自然有着密切生存相依条件的人们,在死后还是归于自然。在后文中,金得也是在一棵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金得的善良品行使他选择了一棵枯树,因为他不想让有生命的树随着自己去另一个世界。萨满作为沟通人神的中介,影响着生命形式的寄托。死亡本身是沉痛无奈的,但迟子建在小说中赋予每种死亡以意义,读者感受不到死亡的可怕,因为亲人总是存活于精神世界,是净化灵魂的一种方式。
自然在人类面前所体现的广阔博大和人们献给自然的敬畏与感恩是相互作用的。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认为天上的云朵、身旁的大山、经过的河流都是“我”的老熟人。在迟子建的笔下达成了和谐共生的期待视野,她本身就是自然的女儿,大自然是世界上不朽的存在,它有灵性,会使人与它共鸣。这种神秘的、超然的、充满敬畏之心的感情在文中被赋予人间虔诚向善的真情。
三、智性文化的温情关注
“智性”蕴含着一种自我认知、自我思考和自我反思的能力,既是个体内在产生的一种对外在世界的知觉,也是一种个人的理性直觉。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受中国传统思想熏陶,迟子建追求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理想生命境界的叙述是思考生命智慧的彰显。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家追求文学哲学化的深度境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体现着中国智慧。小说中的鄂温克人始终相信大自然的力量,对自然界的一切都怀有敬畏之心,秉持着人要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文中写道:“我们是离不开这条河流的,我们一直以它为中心……它的支流就是展开的五指,它们伸向不同的方向,像一道又一道的闪电,照亮了我们的生活。”这写出了大自然中河流水源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以及珍惜和保护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描写山峦时写道:“山上的树,在我眼中就是一团连着一团的血肉。”鄂温克人与自然万物的相互依存的心理沟通方式,反映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岩石上画的岩画也成为“我”表达情感和梦想的具象方式,在文中写“我”画的第一个图形,就是一个男人的身姿。“当我在岩石上画完画后,心底又泛滥起温暖的春水了,好像那颜料已经渗入了我贫血的心脏,使它又获得了生机和力量。这样的心脏无疑就是一朵花苞,会再开出花朵来的。”自然中的风物岩石成为“我”整理情绪和培养感情的天然养料,让心绪在自然万物中得到了自洽平衡的存在方式。
在面对生死和两性关系时,迟子建总是可以写出和谐与诗意。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体现出从感性的体悟到理性的沉思,揣度到小说渗透和辐射给我们的灵魂气息。生与死都是生命的过程,人类对生命存在状态和生命本体问题的体察与省思,引发了人自身对于苦难的消逝和对自由的追求。在文中,“我”的一生面对过多位亲人的去世,在生命观念中,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关照着众人的生活,比如“我”的小姐姐列娜在安睡时被冻死,但尼都萨满说她这是和天上的小鸟在一起了,父亲林克被雷劈去世后,每次听到雷声都感到他在与“我们对话”。即使亲人不在真实的生活中,却依然可以寄托希望和思念。在表达男女自然爱欲上,作者在正视自然的情感上进行了和谐诗意的描写。小时候“我”听见过父母在夜里制造出的风声,长大后“我”也渐渐懂得了这些自然美好的事。文中写道“我和瓦罗加是那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就像鱼与水的融合,花朵与雨露的融合,清风与鸟语的融合,月亮与银河的融合”。“我”用了自然界中美好的生灵来表达心情的畅快与万物和谐的感受。这种基于自然而真情的描写是对人性本真关系的呈现,作者引导着读者要用辩证且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自然界的生存规律。
面对社会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变化,迟子建表达出了抒情的批判。文明的相对性凸显,让读者思考着文明的现代性诉求。文化的存在是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它的价值是多元的。迟子建借作品传递了自己的文明观,希望寻求以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的文化观。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等都是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和文明,所以要建立起平等的态度且尊重跨文化交流。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生活中的酷寒、瘟疫、日寇以及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挤压,使得原始文明逐渐走向落寞。小说中展现了一部分年轻的鄂温克人对融入现代化进程中的犹豫和徘徊。伊莲娜带着具有灵气的才华走出部落,来回选择之后在困惑中归于河流。在这期间也有人丢失了“文化灵魂”,结果是在矛盾中走向衰亡,沙合力因偷砍伐受保护的天然林卖黑材而进了监狱。少数族裔的终末,反映出自适者生存的道理。在过去与现在,同一片土地上演绎的历史与现实的旋律组成了一首悲悯的文化挽歌。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对古朴原生态的文明的缅怀,对人生经历“痛感”的演绎,赋予小说伤怀之美。额尔古纳河岸不仅是鄂温克族人的生产生活地,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迟子建用温情哀婉的言语感悟着流俗之间的抗争,体现着生命的体验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