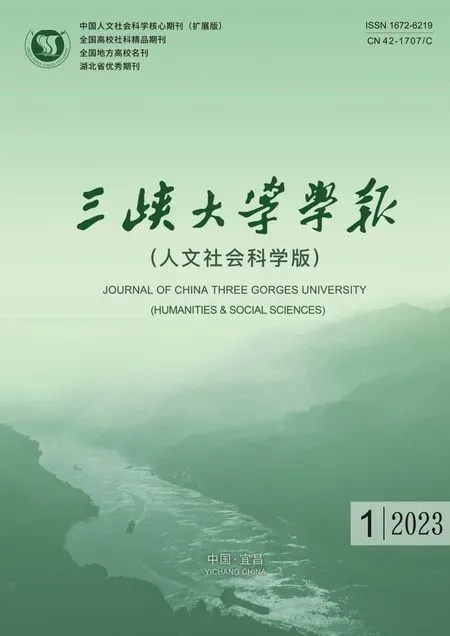曹植的“天路”哲思与心理构成
——关联他在文学创作中的哲学意识
加拿大夏洵若
(上海交通大学 神话学研究院, 上海 200240)
一、背景概念——曹植的“天路”意象本源及相关哲学意识
中国汉魏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曹植,自幼聪慧勤学,“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1]。熟读先秦典籍的过程中,他受到先秦文化的思想浸润[2]53-55,常使用典故、塑造意象,由上古“天人文化”[3]的核心概念引发的“通天”意识便由他传承,且形成他自身的“天路”情怀。这份意识与作者本身的思维高度相关,实际上也关乎人类自古而来的共同特征,即“集体潜意识”。这在需要大量灵感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梦境、冥想等活动时,方能觉醒活跃[4]127-129,恰由于曹植创作多产,时常与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始意象”打交道。“原始意象”形成于“天人文化”时代,由原始先民们对“天”的向往和敬畏[5],制造出有关“通天”的形象造物触发。这一份创造原理,在后世的大文学家曹植的创作中也有体现。那些属于他的辞采华茂篇章里,有紧密关联于上古通天意识的“天路”意象,是被他摘取而贴合自身哲学思维的一份特殊的“情结”。
中华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天”[6],是天人文化的核心构成。最初由于先民被绮丽的天象和天体运行吸引[3],自发产生敬畏和憧憬之感,而后又在中国古老东方智慧国度的沃土,被赋予“皇天”的概念,联系到“国君天子”的政治意识形态[7]3-17。到了汉朝,虽然“天”的地位不再像先秦时那么崇高绝对,但并未完全崩塌,仍有一定权威[8]。尤其曹魏家族,出于政治需求,尊崇上古敬天制度,对曹植的思想影响较大。曹植的“通天”需求,于是便有他作出的个人价值的介入,与他自身的政治事业理想相关,为一种依附“皇天”对君主和天下的情感[9],他的“天路”意象就是相应的一份心理表达。
复杂情况与深邃思绪,成就曹植一生的“天路”[10]之情。这与宗教信仰无关,也非心理分析范畴的疾病式臆想情结,却涉及他的哲学价值,因这份念想深沉而持久,不止一份“意象”,还形成“天路”相关的系列思考产物。他有时直指“天路”,有时塑造与此相伴而辅助“通天”的媒介,亦有被他改良、为己所用的神话元素,并富含政治观念。这些,通过跨文本的对比,加之心理意识形态层面的挖掘,可有所昭示,望能对学界有所启迪。
二、原理剖析——“天路”意象与曹植的取象思维
1.在天之象和曹植对“取象思维”的运用
“天路”在曹植的作品中,自少年时期便已呈现,与他的思维模式相关。他自幼勤学、好思考,具备“取象”思维手法和能力[11],作为一位顶尖的文学创作者,没有停留于感性,而有理性的提炼、哲思价值的整合。“通天”作为他承袭上古文化并加以自身境遇的融合,是他运用最多的一层潜在形象,融入他的取象手法之下塑造的具体素材。其核心观念,就是对“天”和“皇天”的向往、崇敬。如此原理条件下,距离“通天”意识本源越近的意象,越容易含带其本源相关的意识,“天路”可谓是最直观的表达。曹植作品中的取象思维也紧贴这份成因。
中华自古就有“通天”文化传统,古墓出土诸多的“通天符号”器物,例如秦汉时期的画像砖和玉,皆带有升天通神意味[12]。自古亦有“取象”思维方法,可追溯至《周易》及易学文化[13],是曹植自少学习和熟知的。他博学多才,具备高度抽象思维能力[14],本身是拥有哲学观的思想者,视纯粹的文学创作为“辞赋小道”[15]而寄心于政治事业,在表达抒发文学创作之间,也将政治理想等相关的意识形态注入。相当于通过文字媒介,来表达和承载一番理念,其过程本身也蕴含象征对应关系,涉及文学表达手法上的取象原理。
“天路”意象混合了他复杂的思想和多方面关注,凝聚在“通天”需求之上。横跨前后期阶段,不论身处于怎样的客观环境状态,他都不曾摒弃理想,犹如上古先民们对于“天”的憧憬那般,寄心于他心中的“皇天”而意欲为其尽忠献上自己的王佐才干。那种偏向抽象的“天”之向往,流露在他的各类作品。关乎此份核心思维,围绕其产生的具象化意象,即曹植对于“在天之象”(通天)的这一份确切的凝固,就落于他笔下文字组成的“形”——在“天路”这类充斥想象力的描写之中。
2.曹植的“出世化”灵魂观与“天路”媒介
“天路”是虚构的“由地通天”的产物,具有意识形态内涵。由先民们出于“通天”心理而设,“天路”也是古人认为死后灵魂通向天界的路径。此类心理需求处于上古先民的思想核心,他们刻画相应的“灵魂观”,投入相匹配的一系列原始信仰相关的造物,例如楚地的丧葬明器等。曹植的创作受到古楚文化影响,承接屈原和宋玉遗风[16],学术界多有认可,这类古楚文化元素,也被他知晓且进行抽象化提取。曹植的一些虚构类的“神兽”与“神树”(例如“游仙诗”和充满想象力的《洛神赋》等作品),其实就相当于古楚人民对于“镇墓兽”的那种形象塑造和概念摘取,自现实而提升至艺术层面、灌入意识形态、拼凑组合成为一番朝往“天路”行程之上的产物。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游仙诗《平陵东》:“阊阖开,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飞龙。乘飞龙,与仙期,东上蓬莱采灵芝。”[17]其中,“阊阖”就是传说中的“天门”,而“天衢”就是天路的意思。“飞龙”、“仙”还有“羽衣”、“灵芝”,则都是拥有通天涵义的承载体,即通天之“媒介”。普通人出于具体事件需求才会考量生死问题,而对于诗人、思想家来说,不必等到濒临死亡才形成“灵魂观”,正如曹植少年时期就已多有使用“天路”意象,而到后期则更为密集突出[10]。其实,子建与他所处时代普通人的思想观念,多有差异——这些皆是他作为优秀思考者,能够由自身的灵性思索感受到文化浸润的思维反馈。
汉魏时期整体社会采取的灵魂观,已完成“出世”向“入世”的转变[18]。随着人们趋向“入世”,不再追求让墓葬主人通往上古一度吸引人类的“天界”,转为就在墓葬内让其继续“安居乐业”。值得注意的是,曹氏家族在此问题上并未遵循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曹操、曹丕都采取了“薄葬”的形式[19]。曹植作为在后期生存状态犹如“匹夫”的宗亲王族,也遗命子嗣将其薄葬[20],“出世”灵魂观和倡导的薄葬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从横向比较他与当世思潮,跳出其作品之外产生的补充材料证据。
曹植是拥有哲学思想高度的思想家[21]101,他的哲学观除了表达在直接阐述思想的文论之中,也在其看似“感性抒发”的文学作品之内。包含相关的“天路”意识,不单是作者想象力的萌发,也具备文化来源与他自身思想通过“取象原理”形成的意象。结合作者的更多背景价值可知,曹植最在意和向往的一直是政治事业,渴慕有政治作为[22],凝聚在“皇天”这一份抽象化的意象之内,产生与上古先民共振的“通天”精神。因而他会借助上古先民们惯用于表达通天的那种取象思维,进行“古为今用”式的取象再创作。“天路”就是上古的那种通天意识里的一种直接意象,而紧密连接于各类“天界使者”导入“灵魂观”——即“出世”形式的灵魂观,通往天界的需求在此过程中所需要的路径。于是,曹植的取象思维之下,天路就构成了其中的一种关键元素。
3.曹植的“天路”情结及其核心意象
曹植横跨前后期的作品都有“天路”情结,属于他内心自发的结合政治哲思、心慕“皇天”的通天意识。典型的案例,就在他前期贵公子时代,曾写《与吴季重书》,使用“天路”这个词汇,还提到“若木”这种中华上古神话中的神树,即“通天”的媒介。中华古代神话中的神树拥有“通天”功能[23],相当于神话的“天梯”。中华上古神话里“神树”拥有连接天地的作用,而“天梯”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由下自上,垂直型的)“天路”的变体形式。再有关联这一系列意识形态造物的更多“天路使者”媒介符号,比如“龙”,也在曹植的这一篇文章里出现,密集的同类元素汇集。“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蒙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何如何如?”[24]此书信表达的是与时间飞驰、相聚短暂而无奈有关,必然受到“天人文化”深邃浸润,否则不会用到那么多暗指“通天”的意象元素。这对根据历史记载写作速度很快、思若泉涌的曹植来说,自然有感而发的成分理应远大于刻意为之的可能。这也恰好符合了集体潜意识理论当中描述的,灵感迸发而打通了潜意识的隔阂,使得那些承载自上古先祖的“原始意象”得以活跃透露的条件状态。他在向吴质表达的流连于过往美好时间之感的句子中,将“六龙之首”与“若木之华”暗作类比,放置同等的位置,“华”是“花”之意,为若木这种“神树”之精华,而“龙之首”也是龙的精华和关键所在。他执笔写此类意象,就直击关键,绝非巧合,而是他熟知上古神话元素、运用取象思维表述象征构成的证据。这也就是他创作背后的意识原理。
同样在他早期所写的《七启》之中,借助智者“镜机子”之口诉说一首歌曲:“歌曰:‘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兰蕙兮为谁修?嬿婉绝兮我心愁。’”[7]272直指“天路”意象,并与之伴随还有仰视天的动作;其中的“兰蕙”植物意象,相当于一种“神树”的变体,为一种具备“天路媒介”身份的植物形态。在此段前,他还写道“升龙攀而不逮,眇天际而高居。”[17]272由“镜机子”向听众“玄微子”讲述“宫馆之妙”[17]272,透露出浓厚的“天人”意识——视人类在世间的居住为天界下的暂居,最美的居所就是由“天路”去引向的。这些,与在他后期政治理想不得舒展而位于狭小藩地之上,苦闷之时释放畅想而作的《游仙》里所言“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17]143以及《苦思行》中的“我心何踊跃,思欲攀云追”[17]149实则都是一脉相承。都是一种含有对于“地界”现实政治的不满,却依旧难舍,幻想升腾直上,结合“天人”感悟,形成属于曹植个性化的“天路”情结。
在他后期的一首代表作,史学家裴松之也有过记载描写他时常喜欢“琴瑟调歌”[25]自弹自唱的《吁嗟篇》,也有“天路”意象。“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渊”[17]150一句,联合转蓬意象,对于这一颗小小的植物上天入地、随风飘飖的形象刻画生动,其实也就在讲述一段天路历程。从该诗句,可品察出诗人对这条“天路”的向往之态,将其作为终点的本质,是曹植的“通天”意识与“天人”感悟。可是断根了的飞蓬草,实在太过渺小且并无自主飞翔能力,它必须依靠风力等相互作用,飞往哪里也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要“上天”谈何容易!这就是曹植用来自喻和抒发自我悲情的深层情怀,一份意象创作。转蓬与天路二者,可谓相辅相成。只不过转蓬在明,易被看到和理解,天路在隐,融于其广阔背景之中,却实为主角意象转蓬的向往终点,至关重要。如政治类作品《魏德论》中的“超天路而高峙,阶青云以妙观”[17]335,便为这类情结式观感之又一例,结合其政治理想的佐证。这是曹植贯穿一生都执着使用和向往的信念,亦是他的思想承载体的一处本源。
三、案例呈现——“天路不通”的悲怆与讽刺宣泄
曹植在不得志阶段写的作品,大量包含“天人文化”符号,蕴含象征意识;其背后的“通天”需求,结合了政治事业和所谓“仙趣”。曹植是一位贵族诗人公子与政治家,同时有着浪漫精神需求和现实事业抱负,由于凌云壮志未成而产生不满,激增嘲讽感,又更激发他对“地面现实”的意欲逃脱和对于“天上仙界”之追寻。类似于在他的名篇《洛神赋》里,有类似“通天无路”的孤苦悲怆和相应的意象描写贯通,即为全篇一缕抽象式的主题基调所在。在描写主角“洛神”时,“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绿波。”实具备“半路天梯”式的未全“通天”之形态:半空中的轻云,虽遮蔽月亮,实则却够不到;从天而降的雪,借风力回到天上,并不可得;太阳和芙蓉的描绘,都分别用了从下到上的“升”“出”,两个动词,由地及天的意识形态透显。实际上,朝霞虽沾染日之光辉,却终究够不到太阳且很快会消散,就连太阳缓缓攀上了高天也还是得降下来,再次沉入地平线。而莲花即便冒出绿波,向着半空上方舒展,却还只不过根茎在水底泥潭,并不得真正通天而去。这些意象都对应了曹植在此赋中抒发的悲伤,即表面上看似“恨人神之道殊兮”[25]的一段悲伤的分离故事,实则所谓的“道殊”就是那一条“天路”的不可得!其“洛神与君王”相爱相离的悲剧,隐含的就是那一份萦绕心间而不得展现的政治路途。最终,作者连同赋文中描写的君王,一同停留在了那一条望而不得的“天路”之下,“怅盘桓而不能去”[26],戛然而止。
由“通天”这样一种抽象化的心理需求,“天路”是其直接落实的意象。一系列的具象化的“媒介”即天路之使者的造型,或广义上的变体形式的天路,就在曹植的作品中应运而生。比如,《五游咏》中的“六龙仰天骧”所指的龙和飞车;《仙人篇》“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里的“天衢”即天路,还有“飞腾逾景云,高风吹我躯。回驾观紫微,与帝合灵符”[17]131的一系列云、风、座驾和神符之类的媒介;《桂之树行》里“高高上际于众外,下下乃穷极地天”的那棵仙化了的桂树,以及“上有栖鸾,下有蟠螭”栖息的凤鸟和盘曲的龙,皆为天地间的使者;《升天行(其一)》的“乘蹻追术士,远之蓬莱山。灵液飞素波,兰桂上参天”[17]130,仙山、神水、兰桂(神树)一系列的媒介意象;《苦思行》的“郁郁西岳巅,石室青青与天连”[17]149,高山之巅和传说中的神仙洞府“石室”,这些都是带有象征性质的“通天符号”。它们就是联接天地的“天路”之功效化身物,经由诗人的思维投射显现。
正由于该条“天路”艰难,要“通天”不易,曹植的这些素材充斥的作品,才时常伴有华丽之外的沉重悲怆感,混合了他的政治豪情未尽的辛酸。就像在抒发自身抱负的言志诗《薤露行》里,他从“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这样对“天”的情怀开始落笔,感叹生命短暂艰难之后,跳到“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17]138,而后还有龙、麒麟——神话传说体系中的神兽,即“天路使者”[27],蕴含浓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成分登场。最后此诗中他写道“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17]138,隐约像纸张笔墨作出类似花卉硕果垂挂在神树植物般,透出文字作为思想精神的媒介载体,象征着一抹不退的“天路”热血,在政治事业不通的情况下转为“立言”的哲思感言②。
类似地,曹植在《陈审举表》中感叹“然天高听远,情不上通,徒望青云而拊心”[28]335,显而易见就是由他的思维意识引导的肢体行为。若非有“通天”意识,表达话语未被国君听见的情况下,怎会联系到对于自然界的天和青云仰望的动作呢?此“情不上通”也就是一种天路不通的表征,即曹植悲伤无奈的缘由。而他在《谏取国士息表》抒发热切,所用的形容“逍遥于宇宙之外哉!”[28]343也透露了心目中根植的这一抹“天路”向往之情。还有《求通亲亲表》中的“至于注心皇极,结情紫闼,神明之知也。”[28]329表述曹魏宗亲不通往来的苦闷生存状态,和他望能觐见皇上的诚心,之后自然联系到神话传说中的天界“皇极”“紫闼”和“神明”意象,向往感慨,无一不彰显了曹植在这方面确有融于心底的憧憬。
通过此原理,更能了解身为曹魏王侯的曹植公子,作为一名不得志而创作文学之人,怀有的政治哲学视角之下,频繁使用“天路”意象,点出的那一份“君臣”与制度分明的理想国式情怀。从他后期创作的《升天行(其二)》诗作,也能够看到类似的意象,以及化用上古神话中的造型,为己所用的取象手法。再度彰显而表达了他那种恒定不变的意识形态,以及巧妙而高超的意象使用。这首诗起始于“扶桑之所出”,中端描写了一棵上古神话中的神树,在曹植自己的笔下有了意象塑造上的形态转变——“中心陵苍昊……日出登东干,既夕没西枝。”[17]130对比一下便可知晓,有别于传统本源的神话故事中,扶桑仅作为日出之地,若木才是作为日落之地的形象。因此,与其说这是诗人对于上古神话中的神树意象的使用,倒不如认可这是曹植自己改良后的神树造型,即一种“天路”媒介之态。这也是又一份他深谙上古神话元素和取象原理,并且具备理性化、哲思高度的创作意识存在的证明。而后,他在这首诗中写“愿得纡阳辔,回日使东驰”作收尾,则明确点出了意欲回转时光的心理。如此,涵盖活跃澎湃的幻景意象的作品,实则关联最本质的客观物理时间与现实隐射。就类似于早年《与吴季重书》里塑造的那份“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蒙汜之谷”的同类思绪,并且充分意识到“天路高邈”[17]290而怀有遗憾惆怅。这些就是扎根于曹植深层意识之中,关乎基于现实的理想,属于他自身的哲学,并属于他的建功立业报效天下的政治情怀。
如此一份理想追寻,相当于曹植自身争取通往的“天”,就是他深刻的“通天”感悟,注入于“天路”意象的基础。作为一位自小饱读诗书、熟知上古文化经典的学问家[2]53-56,他在运用通天意象时,采取手法原理跟先民于天人文化产生的原始造物活动,异曲同工。正是和曹植受到的“天人文化”及其一脉相承的楚风(《楚辞》等)思想浸润,以及他自身含有的灵性哲思为基础,综合方能达到的情形。因此,上古有关“通天”的媒介,即神话传说中的造物包括龙、凤、仙人、神树(仙化的植物)等,均在他的诗文里频繁出现,尤其在游仙诗里,几乎无一例外包含此类元素。这条“天路”中,各类媒介身份的“天路使者”登场,相互交融,在他的作品中有机化、有条理地串联。这些取象的原理和其背后的“天人”思维,凝聚意识形态层面的脉络,都被他熟悉运用。
其实,曹植对于取象手法继承之外,还有自己的发展和改良,如同他在承袭前朝乐府的过程中,有过“改制新曲”的活动①那般,对于“形”的改制通常是肉眼可见而明显的,对于“象”的引申化使用却显得缥缈而抽象化,常被忽略。像是“天”本就带有虚形,固化为“天路”和通天使者的意象,属于意识形态类的虚构造物,在曹植的诗文作品之中出现,常混入他塑造的幻想澎湃的绚丽场景之内,而被视作普通的文人想象力——这是有失偏颇的。
四、“信仰观”之窥探——政治哲学追求与无关宗教的“天路”情结
至此可见,曹植不止是一位文人,更是有政治理想抱负的政治家,以及形成自身哲学观且带有抽象化思维的哲学家[21]102。他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也会有这种自我定位,并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家在进行创作时所呈现的意识状态。他自小饱读诗书而开启了“集体潜意识”的思维通道,受到上古天人文化思想意识感召,在文学创作之中注入“通天”意象,不仅仅是出于感性层面的抒发,更有出于理性层面的思考,以及有意识地精巧取象运用。
此一类“天路”哲思情怀在曹植前后期都十分强烈,是他的一份特色,也是他并未信奉神仙宗教的一席证据。曹植表明过自己不信仙道的立场[17]353,却有承接上古时期的原始观念,融入他自身的思维,形成自己向往“皇天”的通天意识。藉由“天路”的核心意象,予以表露,所以即便其中包含看似讲述神仙、天界、似“道家”思想元素,不过皆是他承袭自先秦神话传说而摘取、塑造的意象罢了。相当于表达他的这类“通天”诉求的思想承载物,带有“通天”之“象”,却并不是表面看来的仙道之“形”。
这是无关人为宗教而根深蒂固在子建心底的一份“情结”,通过他在不同时期留下的作品中的细节,就可窥探。例如《王仲宣诔》之中,他对于昔日同属建安文人的好友倍感思念,发出王粲离世的哀叹和希望能够重聚的宣言:“我将假翼,飘飖高举。超登景云,要子天路。”[28]362这份诔文感人泪下,并不带有宗教成分,就是他潜意识里希望能通过“天路”重见故友的恳切之情。类似地,到了后期他经历惨淡光景时,也不改对于“天路”的希冀,在《潜志赋》中写道“亮知荣而守辱,匪天路以为通。”[28]242这是一曲失意而不失理想执着的哀伤赋歌,其背后的真实背景和政治意识形态都是强烈的,明显不是关乎宗教而求仙问道的说辞。所以,曹植拥有的不是意欲求仙的心态,而是一份非具象式的“信仰观”——关乎他脑海中的政治理想和潜意识遗留的“天路”意象。这一缕“天路”与上古留存的集体潜意识贴合对应,注入他的“意象群”[29]中,亦为他终其一生的执念。
由于中华文明历来就有着用“天”代表国君的文化传承,曹植在创作中热衷于表达“天”的意象及其引申,如“天路”,就关联于他的此类思想。围绕此凝合而成的天道观[30],就是曹植的哲学思想体系的部分核心。其中,他运用“通天”相关的意象形态(例如龙、神树),便是寄托了一份本源自上古“通天意识”的再生化效应,以上古先民的“形与象”造物文化,为己所用,作为对“皇天”政治理想的记挂。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很多诗文作品显得华丽,幻想漫天飞舞,“仙境”氛围浓厚,却同时作出联想现实的启示,处处提点真切经历,那壮志宏图未展的囚困之境,饱含矛盾张力却融洽的文学内涵,能够存在的原因。从他的行文之中,有时略显跳跃又极自然,随意识流动彰显出一股属于他个性之“气”,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也可窥探一二。比如说,《盘石篇》起首“盘盘山巅石,飘飖涧底蓬”点出的这两份意象,恰好是从天上到底下,且皆具有“通天”的形态在其中,勾勒出一抹虚化的天路贯穿其内。而后描写的一系列景象,皆具有幻彩之色,尤其是“高波凌云霄,浮气象螭龙”[28]74一句,所蕴含的“天梯”式的升腾媒介之物,意象明显。而后面的“方舟寻高价,珍宝丽以通。一举必千里,乘飔举帆幢。经危履险阻,未知命所钟。”[28]74则隐约间具有点出一份抽象式的“通天之路”暗藏各种险境和艰辛,并将物质环境中的路径联系到人事天命、看不见的命运之路,综合凝固成诗人心中的一份意欲展现宏图而不放政治理念的深情。这就是为什么他后续写到了“中夜指参辰”这样在天上的天体意象,又感叹“仰天长叹息,思想怀故邦。”[28]74原本乍一看上天入地、思维具有相当跳跃成分,结合他的“天路”通天意识来理解,则可见都是通顺贯穿,在同样的情理思路之中的。如此一首提到典故“乘桴何所志”[28]74而借助孔子予以感叹、带有政治情感的诗篇,为何要以虚幻式的巨大山巅石和微小涧底蓬作开头,且还融合各类幻境之思在其内,该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所以说,有些人误以为曹植写诗过于华丽而喜铺张排比,觉得他未有直扣主题,甚至误以为他为了炫技逞才,都是对于他的思想和政治哲学不理解才产生的误会。
也如曹植在《髑髅说》里显示的那样,他拥有自己的“曹子”[28]488思想,饱含“天人意识”[9]108和对“天路”的追逐热情。他借骷髅智者的形象表达观点,提到“今也幸变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余将归于太虚。”[28]488将死亡视为一份真实形态,论及生命的道路终点将归于“太虚”即虚幻的天界,而宁愿拒绝重返人间,这其中的一份释然,也与终极“天路”相关。就在这篇应不乏苦闷、压抑和讽刺之意的作品里,文中的“曹子”在偶遇骷髅之时,率先发出的询问“子将结缨首剑,殉国君乎?”[28]488念着的还是国家天下的政治理想,感到为国捐躯是最崇高的死亡形态。无疑,哲学家曹植毕生不忘的就是这样一份豪情热血混合的哲思,这也是他饱含对“天”的情感应运而生的各类创作背后的基础源泉。融合了对于“皇天”的热切,以及知晓终极“天路”目标所在,令他更为执着而甘愿孤独坚持。这亦为他在后期一次次向魏明帝曹叡上书抒发政见的那一抹“寄心”的根源。他充分知晓世间的生命只是暂时的形态,“天”是美好良善的本源与归宿,世间的“通天之路”就是借助为“天”之化身代表“明君”效力而得以完成。于是,曹植的“政治之路”就是他的“天路”,这也是他毕生坚持忠贞孝悌的深层本质之动因。
类似于他的又一佳篇《白马篇》,表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17]135死亡的归宿,就是终极的天路。这些,在他少年之时就已然完成了自我定位,好比《与杨德祖书》里说的,他要“勠力上国,流惠下民”[15],将国放在上对应“天”,也是一份“天人”思维。曹植之所以能够“视死忽如归”而言辞豪迈,除了具备宏远而广大的政治理想之外,本身的“生死观”具备“出世”导向,结合“天路”情结支撑的哲学思想,也是其来源和维系力的一份担保。
在他欲求通天而感无门之时,此份意象同样明显,趋于负面而黯然神伤。如《当墙欲高行》“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17]160他将神话中的龙与升天,跟人的事业攀升作对比,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无疑是可观而浓厚的。此诗收尾在“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这就是一份“天路不通”的意象,何等令人心痛悲伤!这首诗被现代学者判定作于黄初年间,曹植受到小人谗言陷害,不得志于曹丕[28]160-161之际,他在后半段塑造的国君遥远的意境,即是持有茫茫“天路”而心怀悲伤之叹。其中“九重天”,即传说中的天界,比拟为人间帝王的宫殿,是一种紧密贴合的比喻。
这些是曹植的天道观和宇宙精神[31]一并组成的哲学思想[9]113,类比国君皇天与客观真实之天际宇宙的意识形态,巧妙展现。他在代表作《洛神赋》中提到“寄心于君王”[25]的那一份记挂,也是抽象化的,并非针对当时的文帝,所以后来年少的侄儿曹叡继位,他也能一如既往毕恭毕敬,延续着自始至终的“通天”追求而苦苦等待。他对于政治不得志确有不满,而在那类试图超脱于现实、到达天界的幻想类作品中,时不时有隐约暗藏的嘲讽,为一份复杂的“天路不通”式反馈。这也就是为何他在诸多作品里都表达了一种“媒介”助力帮自己到达目标,诸如“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32]或者“愿欲一轻骑,惜哉无方舟”[33]的那种媒介未存、“吾道未果”②的悲伤遗憾。
同理,《洛神赋》中“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也是一种想要有媒介即“天路使者”的心理写照,整体场景为一种抽象化而隐约挪动至水平面上的“天路”形态。对于那并不同于神话宓妃的“洛神”,曹植对其描写也给出取象手法上的改变,写她“将飞而未翔”以及“飘忽若神”“罗袜生尘”[25]等等不同于中华传说客观约定俗成对于神仙行水面无痕迹[28]226、可飞翔等的描写,都向读者们暗示了这并非真正的神仙,而是作者自身的意识折射。并且,这还是一个含有他当时处于黄初年间的苦涩压抑之景象,“通天”无路,纵然再美好(如同他自己)也不得飞翔向天的悲伤故事之化身。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位“洛神”正面登场亮相之际,曹植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而对应其后的“体迅飞凫,飘忽若神”[25]——惊鸿与飞凫皆为飞鸟,游龙和“若神”则相互对应,都相当于“天路”的使者了。“飞鸟”也是曹植显著使用的一份意象[34],文学界不少学者已注意到,不过未有从“通天”意识的角度解读。它们本身具有相似性,都并非如“天”那般至高,在上古人类的思维模式中是可以借助而通向“神界”的依靠,在曹植个人打造的政治哲学之内,就是承载着他的“通天”意愿的一份思想承载体。
这对于“媒介”的依靠,可视为曹植“天路”情结的变体引申。就好似他在早年所写的《离思赋》,提及“虑征期之方至,伤无阶以告辞。”其中所指的“无阶”当然是一种抽象形式的表达,而联系其后他对于此篇赋作的授予人——哥哥曹丕的叮咛话语,“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17]10彼时尚处于他们父亲曹操健在、曹植也未失宠的建安十六年(211),自然不存在曹植需要向曹丕“歌功颂德”,只为他本性心理的流露,出于王侯之家、乱世政客嫡公子的“登天”式向往。同时也展现,他当时意识里的等候时机概念,即:等媒介助力天路以开通的理想化状态。这是早期曹植的一份积极乐观但并非猖狂的少年贵公子心理,合理的流露。到了后期,他的政治事业受阻而生活多有压抑,用以自喻的“转蓬”意象与早年形成的“天路”意象相互融合。如同他的《杂诗(其二)》:“转蓬离本根,飘飖随长风。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28]15其中的“风”“飙”都相当于媒介,拥有输送“转蓬”即作者自喻的助力,而那一份促使诗人甘愿随风去展开未知成败而艰辛苦难路途的动因,就是其“天路”意识,以至于作者感叹“天路”却依然无悔沉浸在其中!他无惧于“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风飘蓬飞,载离寒暑。”[28]51而坚信“千仞易陟,天阻可越”[28]51,却终究无奈于同袍友人不再以及“愧无榜人”[28]51,也就是这样一道“天路”寂寞孤独而艰难,同时仍旧被曹植独自坚持的一份表征。在政治事业受到打压而生活条件也艰辛的后期阶段,曹植并未转向仙道神佛的虚妄追求,秉持着“虚无求列仙”[35]式的无宗教观,而将自身思想伴随文字表露而上升至哲学高度。这是多么难能可贵,也是充分富含理性思维,应当被学界注意,而不再将其视作他过于“张扬”或趋于“求仙问道”的降格处理。
五、总论
曹植的“天路”情结是伴随他一生的价值倾向,不是心理学狭义概念中涉及病态心理的那种精神分析学派所谓“心灵分裂的产物”[4]136-137,不过,这种“情结”概念却和心理背后的动因机制有关,确实是心象与意念的结合[4]136而萌生。通过曹植的创作手段“取象原理”加以运用,对应“天人文化”上古时代的形象造物思维,形成他独特的价值观下的通天意识,凝聚在文字作品里的“天路”意象之上。
在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环境背景下将“天”置于重要地位,“天人文化”是上古时期显著的文化特征[6]。在商周时期就已有用“天”联系国君的意识[7]3,并延续下来,汉魏时期依旧有此崇“天”之风气,这是给予曹植文学创作之中,相关“皇天”的政治意象来源。出于他的内心,则有着更加重要而热烈的驱动内燃,是他对于“皇天”发挥王佐之才的向往,承载了他的寄心。这也就是他早在少年公子时期就已出现“天路”情结之缘由所在,也是他终其一生不曾割舍的一份热血,融入在心心念念的政治理想之内。
由于曹植的优异天资、知识面广博,年少时已有文韬武略的思想和“天人”美誉称号[36],涉及上古先秦的文化典籍,能够从“评说混元造化之端”且从“羲皇以来贤圣名臣”②论起,可见他是一位渊博知识持有者,也是上古文化的爱好者,受到深邃的天人文化浸润。这其中的一份核心概念,即“天路”情结,在他年少时就融入了他的思维体系。“天路”成了曹植自发拥护而向往的一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背景的意象,并通过取象原理,投入进各类作品。从早年的《七启》充满想象力和政治目的的大型篇章,到《与吴季重书》写给文人朋友的书信,还有反映在《九愁赋》《愁霖赋》等辞赋中的神话意象,再到《升天行》等一系列的“游仙诗”,《洛神赋》等凝聚奇幻色彩和现实指代的作品,都与他的价值观形成了精巧而微妙的应和。“天路”成为了曹植的文学作品中,一份含有着哲思化的感悟的理想象征,也作为他的“天道观”和政治哲学[37]73的一部分。
终其一生,曹植秉持着高度信念价值,凝聚理想倡导下的政治哲学,由于事业被压抑,其“天路”被阻拦甚至断绝,他的文学就越发凝结“天路”式渴望通天的元素。到了后期,他的风格沉郁,透显近乎绝望的悲情,在看似虚幻色彩浓郁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上书奏表的文字阐述中,均有围绕“天路”的意象,注入其中而承载深邃悲叹。“天路”就是他承袭自上古文化的思想浸润、结合政治需求产生的综合式意象,贯穿其一生而不磨灭。广义而言,这就是他的理想,也是他并没有信奉人为宗教的证据,组成他的“天道观”和“意象群”,隶属于曹植的哲学。此一份“天路”情结在曹植横跨前后期的思维意识之中都十分强烈,是他不同于其余建安文学家、带有个性化色彩而超越时代的特色。他确实是“建安之杰”[37],成就亦不止于文学,通过文字“流藻垂华芬”[17]135,也让后世得以看见——无关成败,他的哲学思想长存。
注释:
① 参看曹植《鞞舞歌》之序;此亦为他常持有的创作方式。
② 这是曹植《与杨德祖书》中,对于未来情况的考量,人生定位之语;他表示一旦“吾道未果”的情形出现,就将转为“立言”,也正是他日后做到的。
③ 《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描述曹植接待知名学者邯郸淳时展示的惊世才华;那不是仅有才艺能够达成的,实则有哲思价值观和抽象思维运作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