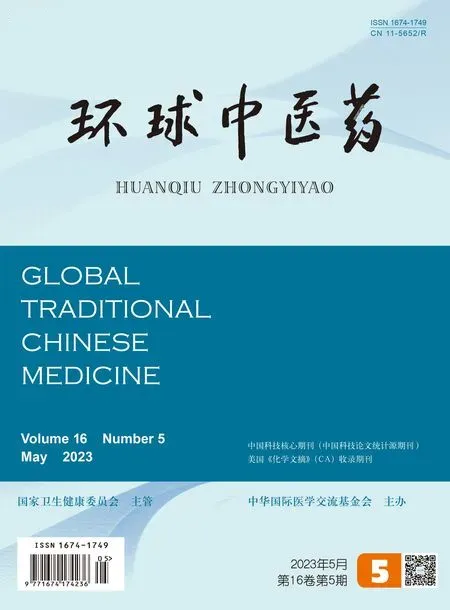从气血水理论探讨肝硬化腹水辨证思路
徐巧笑 张家增 张臻 胡振斌
肝硬化腹水作为临床常见病,其病因多变,病势缠绵难愈,严重影响生存质量,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本病治疗的难点。传统医学根据临床表现及疾病特点将其归属于“鼓胀”范畴,认为鼓胀的发生通常与七情内伤、饮食不节、虫毒感染、劳欲久病等因素有关,是以腹部胀大如鼓,皮色苍黄,脉络显露为突出表现的一类病症。且在其演变过程中,肝脾肾功能失调,气、血、水相因为病,互结于腹中,久则实者愈实、虚者愈虚,形成了本虚标实的病机特点。现阶段临床上对其防治十分重视,笔者基于气血水理论,认为鼓胀发生的关键病机为气滞、血瘀、水停,并通过辨析气血水三者变化特点,提倡以理气、行血、行水、扶正为基本治法,为临床治疗此病开拓思路。
1 从气血水理论到气血水辨证的演变与完善
气血水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机能的物质,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首先提出了气血水的生成来源,如“上焦开发,宣五谷味……是谓气……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是后世医家研究气血水理论的基础。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篇》曰“阳气不通即身冷……其气乃行……名曰气分……经水前断,后病水,名曰血分……先病水,后经水断,名曰水分”[1],提出了气分、血分、水分的概念并对其进行划分,为气血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为气血水辨证提供依据。元代医家朱震亨以气血水为病机,完善了疾病的论治,形成气血痰郁的辨证体系,如在《脉因证治·痈疽》曰:“气得淤而郁,津液稠粘,为痰、为饮,而久渗入肺,血为之浊……血得邪而郁,隧道阻隔,积久结痰,渗出脉外,气为之乱”,阐述了气血水在病理状态下的相互影响。明代医家在对气血水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清楚叙述的同时也丰富了气血水理论。清代医家唐容川《血证论》中提出“水病则累血,血病则累气”的著名观点,认为气血水三者常互生互化,相互影响,相兼为病。日本江户时代(相当于明末晚清)古方派医家吉益南涯推崇仲景之学,提出“气血水学说”,认为气血水三物毒乘之而成证,主张气血水三毒由气血水郁滞所致。纵观古今中外,从气血水理论的形成发展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并逐步形成较为系统的气血水辨证学说。
2 从气滞血瘀水停论肝硬化腹水病机
《素问》曰:“血气者,人之神。”气、血、水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在病理情况下,三者常互相影响,作为重要的致病因素影响的脏腑功能活动及鼓胀的发生、发展。
2.1气滞是最初病理变化
《论衡》曰:“万物之生,皆于气”,《素问·腹中论篇》:“时故当病,气聚于腹也”,气由五谷精微化生,依附于津液,气旺则津液充足,气机通畅则水运正常。关幼波教授云:“见水不治水,见血不治血,气旺则中州运,无形胜有形”,其气血辨证学术思想[2]说明了疾病的发生与转归在于气血的变化,而气机正常升降出入是水液、血液运行输布的基础,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津能载气,气能行津,气机升降逆乱则水液、血液的运行必然受阻。
2.2血瘀是重要病理因素
《血证论·血臌》曰:“血为阴象……气热则结,而血不流矣,于是气居血中,血裹气外”,仲景曰:“血不利则为水。”血能生气,亦能载气,血为气之母,血病及气,血凝不行可影响气的化生和运行。若心、肝、肾等器官循环血量减少,体内血行瘀滞则可导致气水停滞而出现水肿等症状。徐景藩教授[3]认为瘀血郁肝、邪水不化,由此可见,瘀血阻滞是鼓胀病理发展变化的产物,也是一个主要的病理因素;郭朋教授[4]认为瘀血阻碍津液运行,反之,津液受阻致瘀,瘀血消而腹水去,指出活血化瘀应贯穿肝硬化腹水的整个治疗过程。
2.3水停是主要病理环节
《诸病源候论·水肿病诸候》记载:“此由水毒气结聚于内,令腹渐大”,《金匮玉函经》云:“水竭则无血”,当体内水液不能正常代谢,停聚在身体形成“水毒”,再有血行不利形成瘀血,瘀血日久形成水饮,水湿泛溢,甚至血亏,脉中血不足,水液相对增多[5],弥漫三焦,终致气血水湿结于腹中而成鼓胀。赵文霞教授[6]认为肝脾肾功能失调、三焦决渎失权,气血水结于腹中形成鼓胀,其中“水停”是病机之所归。《普济方》中云:“论曰三焦有水气者,气滞不通,决渎之官内壅也……治宜导气而行之,气通则水自决矣。”因而王垂杰教授[7]认为三焦气化不利则水道不通,三焦通利水液运行有出路,腹水得去,治当开宣上焦,健运中焦,疏利下焦为法。
2.4脏腑亏虚是疾病之本
3 从气血水辨证浅析肝硬化腹水的临证思辨与治法
仲景曰“诸病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者,有水,可下之”,指导在腹水的治疗中,发汗、利水、攻逐三种治疗方法。在鼓胀发病过程中,气血水相互影响,不断演变。不同阶段邪正虚实均不同,故治疗上应理气当分虚实升降、行血应审瘀滞凝结、行水详辨轻重缓急、扶正攻邪标本同治。
3.1理气当分虚实升降
气为血之帅,血不利则为水,水不利则病血,气的升降出入是其在人体内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在鼓胀不同发病期中,早期多为气机郁滞,中期气机郁遏,气郁日久化火甚或入血分。张景岳曰:“初病而气结为滞者,宜顺宜开;久病而损及中气者,宜修宜补”,又曰“凡治肿者必先治水,治水者必先治气,若气不能化,则水必不利”,《素问·刺禁论篇》:“肝升于左,肺藏于右”,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提出:“欲治肝者,原当升脾降胃”,因而治疗时当根据不同发病期,因势利导,给邪以出路。包鹏程[11]认为鼓胀始则病气,继则病血,再则病水。气病则血病,血病则气伤,血病水亦病,水病则气塞不通,致使气血水相互搏结而成,运用理气活血逐水法自拟“消癥丸”治疗效果甚佳。杨继荪大师[12]认为肝脏“其体为血,其用为气”、“宜条达,忌抑郁”,鼓胀常由气血水三者往往互为因果,在病早期,偏重于气与血,后期则由气滞、血瘀而致鼓胀,且肝为多气多血之脏,以疏肝理气、活血行瘀为治法,理气活血药也有助于改善肝脏血液循环。
在临证中,调理气机升降一方面以疏理肝气为主,因肝为刚脏主疏泄,以升为常,若肝疏泄功能不及气机郁滞多选用柴胡疏肝汤加减,常用柴胡、郁金、香附、佛手等药疏肝理气之药;若气郁重甚,当以破气化滞为主,常用木香、青皮、厚朴、枳壳等药物;若气郁化火直入血分,当解郁降火为主,常用赤芍、牡丹皮等药物。又因肝体阴而用阳,故需疏肝柔肝并济,治疗常加以酸甘之品如白芍、乌梅等。另一方面以调理脾气为主,脾胃同居中州,为气血化生之源,脾升则健,胃降则和,只有脾升胃降上下通达才能使肝木条达,健脾益气善用香砂六君子汤或补中益气汤,常用党参、苍术、黄芪、陈皮、白术、茯苓等健脾益气之药。
3.2行血应审瘀滞凝结
根据叶天士久病入络学说,毒损肝络,脉络瘀阻,再有《本经》谓庵闾子主“五脏瘀血,腹中水气”,同时,血不利则为水,水血互结为病,治当活血利水,而化瘀则是利水之关键。临床多用下瘀血汤化瘀,选用益母草、泽兰、川芎、丹参、三七、延胡索、郁金等药物活血利水不伤正之品。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如丹参、三七等活血药物在改善肝脏及全身血液循环促进腹水消退的同时可促使肝细胞的再生,恢复肝功能,调节其免疫功能。其中三七味甘微苦性温,入肝经血分,有止血不留瘀、化瘀不伤正的特点,且三七中所含有的三七皂苷、三七素能明显缩短出血,改善凝血,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及溶栓的作用,适用于凝血功能差,凝血酶原时间延长的患者[13]。张仲景在治疗臌胀时运用大量破血逐瘀药配以滋阴润血之品,目的使瘀血去,新血生,使攻而不伤正,补而不留瘀。张国梁教授[9]认为血瘀乃鼓胀之本,血瘀滞脉中致气阻不行,血瘀停滞于内致水液输布失司,治疗该病当活血化瘀、疏肝理气、化痰逐饮。康良石教授[14]基于气血辨证,提出了气道壅塞、水道不通的概念,主张“急则治其标”,先理气活血、清热化瘀以通水道,使湿热毒瘀去,常以郁金、三七粉、琥珀粉等活血化瘀药物。
临证治疗时忌一味行血破血,若单纯使用化瘀消癥、伐肝破坚之品,必伤正气而犯虚虚实实之戒,导致胃气衰败,且腹水易反复。若瘀血停滞日久而化热,常见口渴不欲饮,大便干结,舌紫黯有瘀斑,舌下脉络瘀曲,脉沉涩或沉弦者,常加以丹皮、赤芍、生地等药物活血凉血;对瘀血严重,甚至出现面色黧黑,唇甲青紫的患者,可适当选用水蛭、莪术、虻虫、斑蝥等破血消癥之品。
3.3利水详辨轻重缓急
水为阴邪,体内水停日久,气血化生受阻,正气渐衰,水邪不退,因此临床在治疗鼓胀各型病证之时,当详辨轻重缓急,权衡利弊。对于鼓胀腹水较轻,无明显双下肢水肿,不影响呼吸运动者可采取缓则治其本原则,利水而不伤阴,选用参苓白术散加味,常用防己、车前子、泽泻、冬瓜皮、大腹皮等利水药物。吴鞠通在《温病条辨·治血论》中指出:“善治水者,不治水而治气也”,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强调腹水系虚损大病所致,峻泻则益虚其虚,邓铁涛大师[15]认为在治疗臌胀中,逐水较利水为优,利水慢且伤阴,并总结了甘草甘遂散攻逐水饮法治疗腹胀,且复发率相对较低;赵文霞教授[6]认为治疗鼓胀时制水是关键,以宣上以开水之上源、畅中以调水湿之运化、渗下以利水之下泻为核心治法,使邪从小便去,常用流气、辛散、渗利等阳性动散之品,同时,视病邪兼夹不同,兼施以活血、散结、清热、通络、散寒之法。
利水、攻逐水饮应把握时机,随证制宜,当攻则攻,该补则补,攻止有度,不可偏执。倘若正盛邪实,利水药不足以助水消退,当以攻逐水邪为先,并遵从“衰其大半而止”原则,常选用甘遂、黑白丑、楮实子、商陆、槟榔等攻水药;若见腹胀大如鼓,双下肢明显水肿者,甚至出现水凌心肺、气喘、咳喘不得平卧者,宜攻逐水邪治其标,宜选用葶苈大枣泻肺汤以开其上源、泻肺逐饮。临证中,根据辨证,可加用理气、扶正之品。
3.4扶正攻邪标本同治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臌胀多本虚标实,以脾气亏虚为本,疾病发展到中后期,中土大衰,肝肾精血耗竭,出现脾肾阳虚、肝肾阴虚之象,脾虚贯穿疾病发生发展始终。因此临证时要以扶正为主,攻邪为辅,标本同治。朱丹溪主张:“宜大补中气行湿,此乃脾虚之甚,必须远音乐,断厚味,必用大剂人参、白术,佐以陈皮、茯苓、苍术之类”,这与吴少怀[16]认为的鼓胀根本在于“脾气不足、脾失健运”不谋而合,脾胃是一气周流的枢纽,维系着人体气血阴阳平衡,若出现脾胃功能受损,运化失司,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清浊结聚终成胀病,故治疗该病当先责之于脾,水液代谢正常而新水不生,脾土沃而湿自去,正气盛而邪不可干,因而临床上多选用白术、黄芪、党参、茯苓、苍术等补气健脾药以达培土制水之效,佐以厚朴、砂仁、枳壳等芳香醒脾之品助脾化湿。周信有教授[17]认为鼓胀迁延难愈,气血水互结于内,兼使用大量利尿药耗伤阴液,治当活血消癥、利水消肿为法,自拟扶正消癥利水汤治疗鼓胀切实有效;颜德馨教授[18]表示治疗鼓胀应着重从滋补肝肾之阴入手,本着肝体阴用阳的特点,选用《柳洲医话》名方一贯煎(北沙参、麦冬、当归、生地黄、枸杞子、川楝子)以养肝体助肝用;卢秉久教授[19]崇尚仲景元真本根思想,认为元真之气通过三焦腠理布散全身,滋养脏器是维持人体生命的精气基础,因而在治疗腹水时始终贯彻扶正祛邪的基本原则,在行气、化瘀、利水的同时,常以佩兰、泽泻、山药、黄芪培补元气。
一般来说,正气之虚不外乎伤阴、伤阳,温阳尚易,育阴最难,盖养阴则碍水,利水则伤阴,故用药掣肘[20]。肝脾日虚,水谷精微生化乏源,运化无力,输布无权,病延及肾,肾阳虚衰,肾火无力温煦脾阳,使脾阳愈虚,无以蒸化水湿,膀胱气化不利,开阖失司,致阳虚水盛,当温补肾阳,使所聚之水得以温化或从小便而去,常选用真武汤、附子理中丸合济生肾气丸加减。若患者偏于脾阳虚衰,肢凉纳呆、大便溏烂,可加党参、山药、升麻;偏于肾阳虚,腰膝酸软、头晕目眩甚者,酌情可加用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黄精等。若见腹大坚满、形体消瘦、面色晦暗、口燥咽干、五心烦热,舌红绛少津,脉弦细数之人,此乃肾阳虚衰,阳损及阴致肝肾阴虚,津液失布,水湿内停是也,当治以滋肝肾阴,常选用六味地黄丸合一贯煎加减;若其人阴虚阳浮,可加用如龟甲、鳖甲、牡蛎等滋阴潜阳药物。
4 结语
腹水是肝硬化失代偿期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病率较高,治疗难度大,且易反复发作,是目前临床所需攻克的难点。中医通过“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治疗本病疗效甚好。气血水理论是经前人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得出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仁斋直指方》中说:“盖气为血帅也,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气温则血温”,《张氏医通·诸血门》中所说:“血之与气,异名同类”,清代唐容川在《血证论》中提出:“气与水本属一家,治气即是治水,治水即是治气”的著名论点,启发中医应注重气血水“三位一体”的治疗思路。由此可见,在肝硬化腹水的临床治疗中,应把握气血水三者的动态变化,因势利导,驱邪外出,始终保持气畅、血运、水行,在清除体内毒素的同时注意顾护机体正气。再者,肝硬化腹水本虚标实,虚实夹杂,常见多种病邪相兼为患,便可有是证用是方,当辨证施治,未病先防。在气血水理论的指导下,肝硬化腹水的辨治更加系统完善,为本病临床治疗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