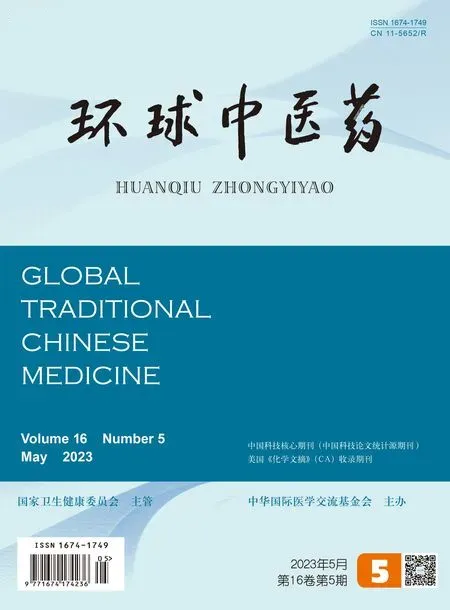酸枣仁性味归经辨析及酸枣仁汤平脉辨证应用经验
倪博文 林雁 于明
酸枣仁是现代中医临床常用的镇静安神类中药。古人云“用药如用兵”,兵性即药性,不识兵性无以谈用兵,不识药性无以论用药。药物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等性能医者均应准确辨识。然而,笔者发现,目前中医学界对酸枣仁性能的认识存在误区。现代普遍认为,酸枣仁味甘、酸,性平,归肝、心经,补肝养心、安神、生津、敛汗,主治失眠、心悸、自汗等。笔者认为酸枣仁并非酸味,归经亦非在肝,主治也不可局限于失眠、心悸、自汗等神经精神系统疾病。在重新认识酸枣仁性能的基础上,笔者以“平脉辨证用(方)药”范式为切入点讨论酸枣仁汤的应用指征,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工作。
1 酸枣仁味甘、香,而非味酸
1.1酸枣仁药味之误源于将酸枣实与酸枣仁混淆
现代教材《中药学》《金匮要略》皆认为酸枣仁味酸。如教材《中药学》将酸枣仁之味表述为“甘、酸”[1];教材《金匮要略》酸枣仁汤释义“枣仁,酸以补肝”[2]。
通过考察不同时期本草著作中关于酸枣的记载可以发现,其药味之误源于将酸枣实与酸枣仁混淆。关于酸枣的记载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经云:“酸枣,味酸,平,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疼,湿痹”[3]。从《本经》之后到北宋时期,本草著作中记载的酸枣之酸大多是在描述酸枣果实,而非其种子。如南北朝《名医别录》载“酸枣,味酸”[4];唐《新修本草》载“酸枣,味酸,平,无毒。主心腹寒热……烦心不得眠”[5];唐《本草拾遗》载“(酸枣)其果酸滑,好食”[6];北宋《本草图经》载“酸枣……似枣而圆小,味酸”[7];北宋《证类本草》载“盖(酸枣)其子肉味酸,食之使不思睡”[8]。有学者[9]通过文献回顾性研究指出,隋唐以前文献记载以酸枣为主,唐宋时期文献同时出现酸枣和酸枣仁,唐宋以后酸枣仁使用进入成熟阶段,其标志为用仁较用实为多。可见,医学史上,酸枣的应用经历了从酸枣实到酸枣仁的演变,并且酸枣仁使用的范围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逐渐扩大,但是对酸枣仁药味的认知却依然延续古代本草著作关于酸枣果实的认知。如明《神农本草经疏》载“酸枣仁,其实酸平,仁则兼甘”[10];明《本草汇言》载“酸枣仁之酸甘而温”[11];清《本草备要》载“酸枣仁,甘酸而润”[12];清《本草新编》载“酸枣仁,味酸”[13];清《本草经解》载“枣仁……味酸”[14];清《医宗金鉴》注解酸枣仁汤亦云“枣仁,酸平”[15];清《温热经纬》载“枣仁之酸,入肝安神”[16]。自明清开始,酸枣仁几乎代替了酸枣实,清《本草述钩元》曰“本经用实,今皆用仁”[17]。
从以上论著可以看出,明清时期著名本草典籍普遍认为酸枣仁味酸。直至现代教材《中药学》《金匮要略》依然认为酸枣仁味酸。《中药学》在中药的命名部分还讲到“酸枣仁以其味酸而得名,苦参以其味苦而得名,甘草以其味甘而得名,细辛以其味辛而得名”[1]。然而,实际上,以味酸得名的实为酸枣果实,而非酸枣仁。此外,古代文献常常出现后代引用前代的情况,文献在传抄过程中受传抄者思想以及当时用药特点的影响,使得原著面貌难以完整保存,也是酸枣实和酸枣仁记载的混乱的原因[9]。
1.2酸枣仁味甘、香的理论依据
药物的认识是先民用感官识别植物、动物、矿物的气味、质地、颜色、温凉属性等来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从药材的质地、颜色、气味等性状角度出发,将酸枣仁的性状特征描述为“种皮较脆,胚乳白色,子叶2片,浅黄色,富油性。气微、味淡。以粒大、饱满、有光泽、外皮红棕色、种仁色黄白者为佳”[18]。这正是对酸枣仁药材性状的客观描述,并且,近年还有中药鉴定学者对酸枣仁外观性状进行质量分析时发现,正品酸枣仁“气微、味淡”,而伪品酸枣仁(理枣仁)“气微,味酸”[19]。可见,酸枣仁的真正气味应为甘淡、微香(炒后油性被激发,香味变浓),并无酸味。
或有学者云酸枣仁之酸味是对其“生津、敛汗”作用的概括。不可否认,“五味”不仅仅是药物真实的味道(味道的味),也是对药物功效的高度概括(作用的味)[20],但是这种解释似乎并不适用于酸枣仁,因为这与其他“生津”“滋液”药物的药性相互矛盾。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生津”“滋(增)液”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区别。“生津”是间接的,是某种物质通过刺激感觉器官而间接地生成津液;而“滋液”是直接的,是含有液体的物质直接滋养机体组织器官。如柏子仁、火麻仁富含油性,故可“滋养阴液”,酸枣仁亦富含油脂,其机理同样是“滋液”,这种机理与乌梅通过刺激唾液腺分泌而间接地“生津”的机理不同。真正“生津、敛汗”的代表药为乌梅、芍药,如《中医学》谓乌梅“味酸……善于生津液”、“味酸……其性收敛”[1];白芍“味酸……酸敛肝阴……敛阴止汗”[1]。
从另一个维度讲,即使认为酸枣仁可以“敛汗”,也不应赋予其酸味,否则具有收敛功效的药物,如牡蛎、麻黄根、浮小麦、肉豆蔻等均应赋予酸味,但事实并非如此。笔者认为,酸枣仁“敛汗”也是基于“滋液”的作用,阴液(正气)足则汗自敛,这是间接止汗法,而非敛汗法。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也有一些医家发现酸枣仁药味之误。如近年有学者[21]提出“酸枣仁味甘,归脾,养脾……不可误认为酸枣仁味酸”。历史中也不乏辨误之言,明·李时珍[22]在《本草纲目》中载“酸枣其仁甘而润”;明·贾所学[23]在《药品化义》中载“枣仁……因其味甘,炒香,香气入脾,能醒脾阴”;清·张璐[24]在《本经逢原》中记载“酸枣,本酸而性收,其仁则甘润”;明·张志聪[25]在其注释《本经》的著作《本草崇原》中更是直接指出历代讹传《本经》所致的谬误:“酸枣肉味酸,其仁味甘而不酸,今既云酸枣仁,又云气味酸平,讹也,当改正”。张志聪之言可谓一语中的,可惜的是,医学史上持这种观点的医家凤毛麟角,不足以影响学术界对酸枣仁药味的主流认识。药味与归经关系密切,药味的错误又导致了归经、功效认知的谬误。
2 酸枣仁归脾、心经,而非肝经
2.1酸枣仁归经之误源于其药味之误
教材《中药学》将酸枣仁的归经表述为“归肝、胆、心经”[1]。教材《金匮要略》指出酸枣仁汤治疗“肝阴不足的虚劳不寐”,方解说:“酸枣仁养肝阴”[2]。有学者统计近10年CNKI、VIP、CBM三大数据库关于酸枣仁汤的研究,结果显示酸枣仁汤证的主要病位在肝[26]。酸枣仁作为酸枣仁汤的君药,在全方中用量独重,决定着全方的归经走向,酸枣仁汤主治病位在肝之误亦是因酸枣仁归肝经之误。认为酸枣仁归肝经的医家是基于对酸枣仁味酸,又基于《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的理论得出的结论。如清·叶天士[14]在《本草经解》中曰:“枣仁……味酸,无毒,得地东方之木味,入足厥阴肝经”。
应看到的是,当代也有学者[9]发现其中端倪,提出酸枣果实味酸,主入肝经;而酸枣仁味甘,酸性小,以补脾为主,兼可养肝。此观点虽然已经发现酸枣仁味酸似有不妥,且以入脾经为主,但是遗憾的是仍未能完脱离酸枣仁味酸、入肝益肝的桎梏。
2.2酸枣仁归脾、心经的理论依据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理论认为药味是决定归经的主要因素。基于前文对酸枣仁气味甘、香的再认识,重新思考其归经,则“甘入脾”“土爱暖而喜芳香”,这种甘香之味首先入脾经而非肝经;质地油润可直接滋养脾胃之阴液而非肝阴。明·薛己在《正体类要》中用四君子汤合酸枣仁治“心脾气血两虚”,正是取酸枣仁归脾、心二经而滋脾养心,故名曰“归脾汤”;明·张志聪的《本草崇原》将酸枣和酸枣仁的归经做了明确的界定:“枣肉味酸,肝之果”,而“枣仁形圆色赤,禀火、土之气化,火归土中则神气内藏……枣仁色赤象心,能导心气以下交,肉黄象土,能助脾气。”
基于上述文献,笔者认为,酸枣仁应以入脾经为主。《中药学》言酸枣仁“养心补肝”,治疗“心肝阴血亏虚,心失所养之虚烦不眠,惊悸多梦”有待商榷,因为补益心肝阴血亏虚,酸枣仁远不如当归、川芎、熟地、芍药、阿胶等药。此外,如薛己、张志聪所言,酸枣仁除了入脾经,尚可入心经。现代有研究表明,酸枣仁经炒制后,可以增强其芳香健脾、养血安神的作用[27],也证明了酸枣仁入脾、心二经。
3 酸枣仁功效滋脾养心,主治不可局限于失眠
3.1酸枣仁局限治疗失眠源自酸枣仁汤治疗“不得眠”的束缚
教材《中药学》将酸枣仁的功效表述为“养心补肝,宁心安神”,临床应用表述为“虚烦不眠,惊悸多梦:本品味甘,入心、肝经,能养心阴、益肝血而宁心安神,为养心安神之要药”[1]。教材《方剂学》将酸枣仁汤归为“补养安神剂”,主治“肝血不足,虚热内扰之虚烦不眠”[28]。
酸枣仁主治失眠是对酸枣仁汤治疗“不得眠”的桎梏。张仲景的酸枣仁汤开创了治疗“不得眠”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仲景为医圣,仲景治疗失眠以酸枣仁为主药,以至于在后世诸多医家心目中,酸枣仁近乎成为治疗失眠的庙堂之药。如南北朝·陶弘景[4]在《名医别录》中载“酸枣仁主治烦心不得眠”。唐·孙思邈[29]《千金方》中的酸枣汤,唐·王焘[30]《外台秘要》中的小酸枣汤,宋·王怀隐[31]等《太平圣惠方》中的酸枣仁煎方,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宁志膏[32],元·忽思慧[33]《饮膳正要》中的酸枣粥,元·危亦林[34]《世医得效方》中的大安神丸,明《普济方》中的酸枣仁煎[35]等均以酸枣仁为主药治疗失眠。清代流传最广的医学教科书《医宗金鉴》盛赞酸枣仁汤擅治失眠,曰:“肝伤精绝则虚劳虚烦不得卧……用酸枣仁至二升以生心血、养肝血……水壮而魂自宁,火清而神且静。此治虚劳肝极之神方也”[15]。
不仅如此,在现代临床治疗失眠时,酸枣仁已成首选药物。有学者[36]统计表明,其在治疗失眠症的方药中,使用频率高达67.3%。并且,无论现代的理论研究、临床研究,还是实验研究大都以酸枣仁作为主治失眠、心悸、焦虑等神经精神类疾病的专药[37-42]。虽然实验研究表明,酸枣仁有镇静、催眠、抗焦虑、抗抑郁等作用[43-45],但是这是基于现代药理学的研究成果,是用现代医学“还原论”的视角看待问题,已经偏离了中医学整体辨证、治病求本的理念。
3.2酸枣仁滋脾养心的理论依据及其据证用药论
其实,《金匮要略》虚劳病是“从脾论治”,酸枣仁汤亦是治脾。基于上文对酸枣仁药性的再认识,笔者认为,张仲景用酸枣仁汤的本意应是滋脾养心,而非养血补肝、宁心安神,理由有三:第一,从《金匮要略》虚劳病的治疗特点来看:(1)五脏气血虚损成劳,治疗上首先重视补益脾脏,其次为肾脏,并无心、肝二脏;(2)对于阴阳两虚的复杂病证治法要点是补脾胃、建中气,用药偏重甘温柔润、健脾补肾。虚劳病的治疗共载7首方剂,或是健脾,或是补肾,健脾之方就有5首(桂枝加龙牡汤、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薯蓣丸、酸枣仁汤)。第二,张仲景杂病重视从脾论治,这从《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也可见一斑,论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第三,教材《金匮要略》记载酸枣仁汤治疗“肝阴不足”之肝脏虚证[2],这与张仲景提出的肝虚证的治法不符。张仲景针对肝虚证的治疗原则为“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肝虚则用此法”,按照这种原则,治疗肝虚证最佳处方应该是酸、苦、甘并重的胶艾汤、当归芍药散,而酸枣仁汤组方中并无酸、苦之药。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张仲景用酸枣仁治失眠是“从脾论治”。张仲景用酸枣仁汤的着眼点应是治脾,因君药酸枣仁以入脾经为主故也,诚如唐《新修本草》所云:“(酸枣)似武昌枣而味极酸,东人啖之以醒睡,以此疗不得眠,正反已。今方用仁,补中益气”[5]。
笔者认为,酸枣仁入心经而发挥的作用只宜记为“滋养心阴”,不宜记为“宁心安神”。因为心主神志的物质基础是心主血脉[46],血能养神,进而间接地起到治疗失眠、惊悸的作用。此外,“宁心安神”只是“对症治疗”,并不能体现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精神内核。引起神志不宁的原因众多,只要能够解除引起心神不宁的病因,诸药皆可宁心安神。如半夏可通过化痰祛湿解决痰浊扰心的问题而宁心安神;茯苓可通过健脾利水解决水饮凌心的问题而宁心安神;栀子可通过清心泻火解决心火亢盛的问题而宁心宁神,等等。记载“宁心安神”的另一个弊端是容易让学者忽视“辨证论治”,走入“对症治疗”的歧途。
总而言之,酸枣仁的运用只要抓住“脾阴虚、心(阴)血虚”之证,据证用药,则其主治可不再局限于失眠。
4 酸枣仁汤及其脉证解析
寒温属性方面,酸枣仁不温不寒,性质平和,这一点历代医家基本没有争议,而如何通过客观手段辨识“脾阴虚、心(阴)血虚”证,需要对酸枣仁的应用指征重新思考。在此以酸枣仁汤“平脉辨证用(方)药”范式为例,介绍如下。
三是积极培育内部人才市场,完善人才内部流动机制。逐步建立分区域、分板块,有形和无形市场相结合的人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市场功能,扩大信息量,增加覆盖面,进一步疏通三支队伍之间、板块之间、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渠道,促进人才系统内部合理流动,减少人才流失。
4.1脾胃气阴虚损、阴火上乘,可以酸枣仁汤主之
酸枣仁汤出自《金匮要略·虚劳病篇》,论曰:“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虚劳是指劳伤所致的慢性虚弱性疾病的总称[2]。《金匮要略》首先提出虚劳概念,后世医家不断阐发,金元时期李东垣对本病的论述最为经典,其提出的“脾胃阴火”学说指出虚劳根源在于脾胃受损、阴火上乘。如“饮食不节,劳役所伤,以致脾胃虚弱”[47],“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阴火上冲,则气高喘而烦热”[47]。脾胃气阴不足,阴为火乘,不得内守,相火亢盛,引动心火,扰乱心神,正是虚烦不得眠的病机。
脾胃阴虚,宜薄之味以养胃阴。“饮食损胃,劳倦伤脾,脾胃虚则火邪乘之而生大热,当先于心分补脾之源”[47]。酸枣仁作为酸枣仁汤的君药,其味甘香、质地柔润,归脾、心经,为“于心分补脾之源”的代表药物。
脾胃气虚,宜甘温益气。甘草在规划教材中对其释义多是调和诸药,为使。如《方剂学》载:“甘草……和中缓急,调和诸药,为佐使药”[28];《金匮要略》载“甘草清热缓急,调和诸药”[2]。然而,经方中甘草的主要作用在于补虚,而非调和使药[48]。因此,甘草为酸枣仁汤中健脾益气的代表药物。甘草合酸枣仁构成甘温对药,气阴双补,中焦气阴充足,谷气升浮,阴火自下行而归于本位。
太阴本湿,脾虚湿益甚。茯苓甘淡,渗湿兼可健脾,尤可引虚热下行,如尤在泾所言:“阴虚者,气每上而不下……补阴益精而以茯苓、泽泻之甘淡助之下降”[49]。茯苓作为方中泻脾胃湿热的代表药物,其与酸枣仁一燥一润,渗湿不伤阴。
虚火上炎不可苦寒清热,苦寒必然败胃、损伤阳气。治疗慢性虚损性疾病,仍应遵循李东垣之训:“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47]。知母正是方中甘寒清虚热的代表药物。
教材对于酸枣仁汤中川芎的解释多是“疏肝”。如《方剂学》酸枣仁汤方解说:“川芎之辛散,调肝血,疏肝气”[28];《金匮要略》酸枣仁汤释义说:“川芎理血疏肝”[2]。笔者认为,不可将川芎的作用局限地解释为“疏肝”,疏肝是基于其辛散之性,亦即“风药”之性,风药不仅可疏肝,尤可发越上焦郁火,即李东垣所谓“泻阴火以风药”。李东垣又谓:“脾胃不足,皆为血病”,川芎性散,走而不守,为气中血药,可以“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进而促进神志恢复。此外,其温散之性尤可宣透因虚而客之外邪。
纵观是方,补泻兼施,以补为主,寒温并用,不燥不腻,切中脾胃气阴虚损、阴火上乘之病机,从而达到滋脾(胃)阴、益脾气、养心血、清虚热、散外邪的目的。
4.2准确辨脉是“平脉辨证用(方)药”的关键
脉象以其客观可察性,在揭示证候本质方面具有其他三种诊法所不具备的优势,其在诊断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张仲景是平脉辨证、据证用方的模式的首倡者,正如其在原序中所言“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而且《伤寒论》各篇篇名均为“**病脉证并治”。《伤寒论》原文中,脉诊经常是指导辨证用药以及判断预后的重要依据,如“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394条)”,“脉浮者,必结胸;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两胁拘急;脉细数者,头痛未止;脉沉紧者,必欲呕;脉沉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140条)”。对于坏病的处置原则,张仲景亦是强调应“观其脉证”。《金匮要略·妇人杂病篇》则云:“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异源。”可见脉象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预后判断具有决定性作用,准确辨脉是辨证和用(方)药的前提和关键。基于精准辨脉的“平脉辨证用(方)药”范式作为临床指导,能够使处方遣药更加客观、准确,建立中医言必有物、事必有征的客观逻辑推理模式,脱离以往只是根据中医经典中以症状组合对选药用方进行佐证的推理模式[50]。
4.3右关和(或)左寸脉呈虚性脉象为酸枣仁汤的主要应用依据
当今的临床与科研过度强调酸枣仁(汤)治疗失眠、心悸、多汗等病症,而弱化以辨证论治思想指导其应用。失眠、心悸、多汗只是一个个症状,症状是表象,其背后反应疾病实质的是证候,而获得证候唯一客观的手段就是脉诊。如《伤寒论》提出小柴胡汤的典型脉证为“脉弦细(265条)、沉紧(148条)”,若“脉迟浮弱(98条)”,兼身目发黄、胁下满痛、恶风寒,非柴胡证,小柴胡汤不中与也。
酸枣仁汤脉证,经文中未加论述,笔者依据上文所论述的“平脉辨证用(方)药”范式将酸枣仁汤脉证进行补充,以便临床应用。《金匮要略》中记载虚劳病常见的脉象有“脉大、脉浮、脉虚沉弦、脉沉小迟、脉浮弱而涩、脉虚弱细微、脉弦大、脉极虚芤迟、脉芤动微紧”。以上经文对脉象的描述是基于脉形、脉势,而未能指出脉位,脉位对于提示病变部位有重要意义,如《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云:“寸口,积在胸中……关上,积在脐旁……尺中,积在气冲。脉出左,积在左……各以其部处之。”由此也可看出,仲景脉法之寸口三部脉位分别对于人体上、中、下三焦。王叔和的《脉经》在此基础上将左右寸口六部脉位进一步细分,并配属不同脏腑,沿用至今,即左寸主心与小肠,左关主肝与胆,左尺主肾与膀胱;右寸主肺与大肠,右关主脾与胃,右尺主命门与三焦[51]。综合虚劳病之脉形、脉势特点,以及对酸枣仁归脾经(右关所主)、心经(左寸所主)的认识,可以认为典型的酸枣仁汤脉证应为:右关和(或)左寸脉或浮大芤迟,或浮虚弱涩,或沉弦细微,或沉小迟紧。
临床中,只要抓住酸枣仁汤的上述脉证特点,就可据脉灵活用方。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应用要点:其一,同是不得眠,脉异须异治。临床中大量患者以不得眠为主诉,但是脉象各异,此时应舍症从脉,或以脉为主,平脉用药。如右关和(或)左寸脉或浮大芤迟,或浮虚弱涩,或沉弦细微,或沉小迟紧之不得眠,可以酸枣仁汤主之;若是以关脉滑数为主要脉象特征,兼见不得眠、心下痞等,提示痰热互结中焦,则可以半夏泻心汤化裁;若是以寸脉上溢而尺脉虚数为主要脉象特征,兼见不得眠、心中烦等,提示心肾不交,则可以黄连阿胶汤加减,等等。如此平脉辨证用(方)药才能有的放矢,而不致落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其二,脉同症不同,平脉用药。尽管疾病的临床表现千变百端,只要辨准脉象,就可以把握证候,脉同则证同,异病可同治。如右关和(或)左寸部见上述虚性脉象,提示脾胃气阴或心血不足,无论脾胃气阴不足消渴、大便硬、反复口疮等症,或心血不足的心悸、失眠、贫血等症,均可以酸枣仁汤加减化裁。
5 结语
综上所述,历代本草和方书著作没有把酸枣实与酸枣仁的药性区别清楚,望文生义,辗转附会,贻误直至今日。医者又奉张仲景酸枣仁汤治疗失眠之说为金科玉律,酸枣仁几乎成为治疗失眠的专药。通过考察不同时期医学著作中酸枣仁药性的表述及其演变的历史,笔者对酸枣仁的药味、归经、功效、主治进行了重新梳理,并提出了酸枣仁汤的“平脉辨证用(方)药”范式。在该模式指导下应用酸枣仁汤,可以开阔其用方思路,并以此方作为出现上述脉型症候的多种病证的基础方。更重要的是,以该模式作为指导可以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率与治疗的有效率。推而演之,“平脉辨证用(方)药”范式可以用于指导一切药物以及方剂的使用,它不仅简明可靠、客观实际,而且能探本求源、伏主索因,进而克服简单机械地“对症治疗”的缺陷,最大程度地恢复中医学“辨证论治”与“治病求本”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