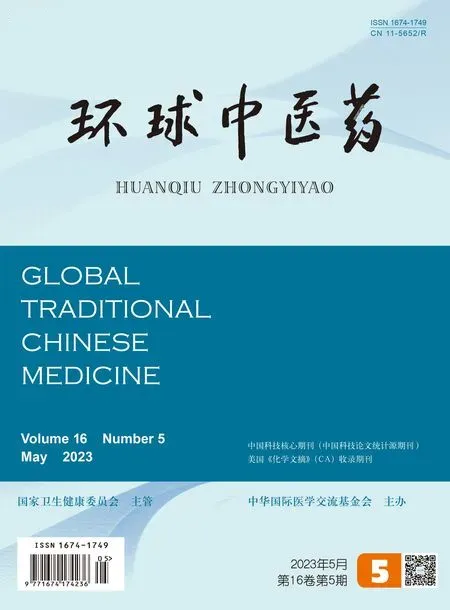从“神机”与“气立”理论探讨荨麻疹的病机与治疗
冯佳悦 张楠 周珍 赵京博 陈周燕 贾海忠
“神机”与“气立”是保证人体生理功能的重要部分,气立在表为门户,神机在里为根结,表里可相互影响而致疾病发生,这与荨麻疹的发生发展与转归密切相关。故本文以“神机—气立”理论为主线,探索“神机”“气立”与荨麻疹发病之间的内在规律,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思路。
1 “神机”“气立”是人体生理功能正常的重要保证
1.1“神机”“气立”的提出与理论发展
“神机气立”理论起源于《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篇》[2]云:“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历代注家对此解读差异颇大,但一致认同其重要性。唐代王冰[3]分别从动物、植物予以释解,认为动物“皆生气根于身中”,故为神机;植物“皆生气根于外”,故为气立。清代高士宗[4]则注之:“五运在中,故根于中者,命曰神机……六气在外,故根于外者,命曰气立”,认为神机气立分别指代五行及六气在天地间的运行变化。现代医家亦认识到神机气立的重要性,范孝叁[5]指出神机是生命内在的自我调节的功能系统,气立是生命体与外部环境进行交换以及适应外界变化的功能调节系统。此外“神机气立”理论还应用于妇科疾病及脑病的治疗,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1.2“神机”“气立”理论内涵
“阴阳不测谓之神”“两精相搏谓之神”,“神”泛指各种变化。机,主枢机,关键之意。张介宾[6]注说:“物之根于中者,以神为主,而其知觉行动,即神机之所发也”,所谓“神机”就是使生命现象内在变化发生的关键。张介宾[6]又云:“神应于中,使之升则升,使之降则降,是其神之可使也”,可见神机“根于中”,是指存在于生命个体内部,控制体内“气”的升降及个体自身变化的部分。为方便临床辨证,将机体所有未与外界接触的脏腑,统称为神机,包括心、血、脉等。然生命体单纯依靠神机是不能长久存在的,还需要时刻与外界进行气的交换。“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物质,“立”即开始之意,如“立端于始”。所谓“气立”就是机体与外环境之间进行内外交流的开端,即人体直接与外界发生关系的部分,负责调节气的出入运动如“水谷入口”“呼吸精气”等。为方便临床辨证,将机体所有与外界接触的脏腑统称为气立,如肺、胃肠、膀胱、女子胞、皮部、目、耳等。神机气立“各有制,各有胜,各有生,各有成”,神机在里,气立在表,二者协调平衡,共同维护生命体的所有生命活动,如若神机、气立自身失调或二者兼而有之,则导致了疾病的发生。
2 “神机”“气立”紊乱是荨麻疹发生的核心病机
2.1外邪侵伏,气立不固为发病根本
气立作为机体与外界沟通的门户,亦是邪气的入侵途径。气立为病常表现为感邪致病和开阖失司两类。《素问·调经论篇》[2]云:“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此“邪”即泛指各种致病因素及其病理产物,根据其病邪属性可分为“阴邪”“阳邪”,影响着发病的性质、类型等。正气是指机体内部的抗病能力,即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种抗病能力是由神机与气立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正气之于气立,比神机更重要。正气充足则气立得固,邪气不能深入神机层面,仅气立部分症状明显,故《素问·调经论篇》[2]谈到:“血气未病,五脏安定,邪客于形,洒淅起于毫毛,未入于经络也。”正气不足气立失固,邪气由此病灶逐渐深入至“神机”层面,恰合《素问·疟论篇》[2]所述:“夫子言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乃发,发则邪气入,入则病作。”相关研究表明荨麻疹发病与呼吸道[7]、消化道[8]、泌尿生殖道[9]等部位的感染性疾病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王琦教授[10]亦指出荨麻疹的发病与传变和过敏体质有密切的从化关系。因此笔者认为荨麻疹发病主要与外邪的入侵有关,责之气立不固。
2.2神机衰运,影响气立为发病关键
神机作为保持机体内部结构与功能有序运转的关键,神机为病则表现为机体内气血运行失调,继而引起其他气立部位病变。《灵枢·经水》[11]云:“凡此五脏六腑十二经水者,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禀,此皆内外相贯如环无端,人经亦然。”经络分布于人体各部,具有输布气血、沟通内外的功能,可见经络是维持神机运转和人体内环境的网络途径,同时也是病邪传递的途径。邪气从病变气立部分逐渐深入神机,如《素问·缪刺论篇》[2]所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持续耗伤神机即内在脏腑的气血津液致使其功能失调,生成病理产物。心气衰弱,运行无力,痰、瘀及各种外邪等阻滞脉络,或日久耗气伤血,致使皮肤末端之络脉空虚,孙络损伤,血虚生风,发为风团。疾病日久,损耗神机,正气不足,气立失固,稍遇外因则内外合邪,导致病情反复。任琳[12]认为荨麻疹顽固难愈的根本在于络脉空虚,邪阻络脉,临床从络论治取得良好效果。
3 基于“神机”“气立”理论的荨麻疹诊疗思路
3.1首察气立,辨明病位
辨病位,即辨别确定病变阶段证候所在的位置,是中医辨证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周学海《读医随笔·升降出入论》[13]云:“大抵治病必先求邪气之来路。”荨麻疹起病之初,邪气由气立部分侵入,在正气的作用下,气立部正邪交争祛邪外出,表现为局部“排邪反应”,因此可根据气立部分的病理变化反应于外的客观征象,辨明具体病变部位。
由于气立部分各脏腑的生理功能不同,疾病过程中所表现的症状体征也各不相同。若邪气侵袭目部,则表现为流泪、眼眵增多、角膜浑浊、球结膜充血肿痛等症;若侵袭耳部,则表现为短暂性耳鸣、耳闷、耳痛、耳痒、耵聍增多等症;若侵袭肺,则表现为喷嚏、鼻塞流涕、咳嗽,咳痰等症;若侵袭胃肠,则表现为恶心、呕吐、肠鸣、腹泻等症;若侵袭膀胱,则表现为尿频、尿急、尿痛、尿量多、尿浊等症;若侵袭女子胞,则表现为白带量多、带下臭秽、白带质地异常等症;若侵袭皮部,则表现为皮部局部渗液等症。通过认识和掌握每一病位的特定表现,即可辨别出不同证候下的病位。
此外,荨麻疹发作时常夹杂气立部分多个部位的病变,如一例明目地黄丸致急性荨麻疹的案例中患者同时伴见目及胃肠症状[14],因此在辨别病位时还需根据不同气立部位排邪表现出现的先后时间进行人为划定,继而针对性地选用相应治疗方法及用药,从而达到“治病必求于本”的境界。
3.2审证求因,辨识病性
陈无择[15]曾言:“凡治病,先须识因,不知其因,病源无目”,因此在病情不断的变化中抓住疾病的本质,对病因作出正确的判断,是对症治疗的保证。《素问·至真要大论篇》[2]云:“夫百病之所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荨麻疹发作与六邪密切相关,临床上以风、寒、湿、火邪最为多见。风善行而数变,与荨麻疹时隐时现、发无定处、瘙痒难耐的临床症状极为相似,巢元方[16]曾明确提出荨麻疹乃风邪所为:“人皮肤虚,为风邪所折,则起隐轸”。《诸病源候论》[16]中亦记载:“邪气客于皮肤,复逢风寒相折,则起风瘙瘾轸”,指出寒邪亦可致荨麻疹发生。然其常反复发作,缠绵难愈,也与湿性粘滞的特性相一致,故有医家认为“瘾疹者,自卑湿而得之”(《景岳全书》[17])。因荨麻疹发作时有皮肤潮红,甚至鲜红,故亦有医家认为火邪可引动荨麻疹发作,即陈士铎《辨证录》[18]云:“人有赤白游风,往来不定……似乎发斑……谁知是胃火之郁热乎。”临床上荨麻疹症状多样,常由多种邪气相兼所致。华佗云:“病因种种不同,述难尽。”临床推求病因时,除了通过分析症状、体征外,还需灵活结合病邪致病特征、脏腑特性、季节地域、体质等以求精准定性,从而为立法处方提供依据。
4 固气立、强神机思路指导下的荨麻疹治疗
4.1祛邪气以固气立
气立以通为要,周学海《读医随笔·升降出入论》[13]云:“病在出入,疏之、固之”,因此祛邪气以固气立为治疗荨麻疹的根本大法。
4.1.1 祛风补虚固气立 若风邪结伏气立致荨麻疹发作,如张仲景[19]述:“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荨麻疹发病多与营卫失和,风郁气立有关,血虚生风生燥,且气血亏虚则藩篱不固,风邪易袭。临床症见风团瘙痒,无明显的寒热特征,症状呈阵发性、突发突止,治疗当以益气补虚之品与风药配伍,临床可予自拟灵枳定风汤,方由八珍汤合灵芝、枳实、五味子而成。八珍汤健脾和中,双补气血,气血充足则腠理致密,风邪难侵,正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素问·至真要大论篇》[2]云:“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枳实辛凉以疏风清热,灵芝甘苦以祛风除湿,五味子酸甘化阴,祛风止痒。全方共奏强中气、扶正祛风之功,如若痒甚,风邪之象明显,可酌加荆芥、防风、僵蚕、蝉蜕之属增强散风搜风之力。
4.1.2 散寒通阳固气立 若寒邪结伏气立致荨麻疹发作,寒邪或由食道侵入或经息道吸入、肌肤附着,藏匿于气立部分,寒邪久着,收引腠理,易凝滞津液成水湿之邪。临床症见风团瘙痒,色淡温低,可见脉沉、紧、迟,舌淡暗、紫暗,苔白厚腻紧致,根部尤甚,治宜小青龙汤。方中麻、桂、细辛通达阳气,外散寒邪;干姜、甘草、半夏可温通脾胃之阳,以杜生湿之源;芍药酸敛以护肝阴,五味子酸甘以护肾阴,使其温散寒湿之邪而不伤正,诸药合用,通腠理之壅实、净气血之浑浊,顽症自除。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小青龙汤具有抗过敏、抗炎等作用,可改善荨麻疹的临床症状,降低复发率[20]。
4.1.3 祛湿行气固气立 若湿邪结伏气立致荨麻疹发作,湿邪阻碍气机,气机不行则水湿困阻,久之与他邪相兼,产生寒湿、湿热、风湿。临床症见皮肤局部风团瘙痒,可见脉滑、数、濡、细,舌暗红、紫红或红,苔白腻、黄腻或厚,治宜自拟除湿利机汤,方由枳术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合滑石、木香、槟榔、石菖蒲而成。方中枳实行气除饮,白术助脾升清,攻补兼施,调节全身气机;葶苈子行水下气,大枣调中补土,斡旋中焦,使升降更和;以木香辛香下气,槟榔辛苦温破滞气下行;石菖蒲去湿逐风,滑石利膀胱而去湿热,全方共奏行气除湿、兼祛多邪之效,亦体现了“气化则水自化”的观点。
4.1.4 清热活血固气立 若火邪结伏气立致荨麻疹发作,热灼津液,敛津成痰,阻于经络,营卫失调,引发内风,临床症见风团色红温热瘙痒,局部喜凉恶热,可见脉滑、数,舌暗红、紫红或红,治宜四妙勇安汤。方中金银花清热解毒,玄参凉血养阴,当归破恶血,养新血,养血养阴,甘草补气养阴,泻火解毒,共收清热活血,益气通脉,平息内风之功。相关研究发现[21],四妙勇安汤具有抗炎、抗氧化应激、改善血液流变学、抑制血栓以及调节血管新生及保护血管内皮的治疗效果。临证时不可拘泥于一方,需结合患者病位病性灵活应用,随证加减。
4.2调血脉以强神机
“血藏脉,脉舍神”,神机失衡常表现为气血升降失常,因此调血脉以强神机为治疗荨麻疹的关键大法。
4.2.1 扶正定风强神机 《成方便读》[22]云:“夫风之中于经也,留而不去,则与络中之津液气血,浑合不分……络中之血,亦凝而不行。”若风邪结伏日久,则耗伤神机精气血津液,邪阻气滞,津液凝涩,输布失常,临床常表现为风团瘙痒,伴恶风、身热、汗多、麻木、偏枯等,治宜自拟黄芪三甲固本定风汤,方在固本定风汤扶正祛风的基础上加上黄芪、龟板、鳖甲、牡蛎。津液相对不足者,祛风及治标为重,益津血为辅;若精血绝对不足者,养血填精为重,兼顾祛风。故加入甘温之黄芪以补气行血、走皮毛而行卫郁;入三甲,取其血肉有情,液多质重,以滋血液而息内风。诸药合用则内外风邪尽除、气血得畅,瘾疹自消。然三甲的选用和剂量比例,总以衡量病机之偏重、矛盾之主次为妙。
4.2.2 扶阳散寒强神机 若寒邪结伏日久,内舍脏腑耗伤神机阳气,脾肾阳虚,以致寒湿滞留在经络,久则内不能温通,外不可透达,缠绵难愈,形成顽疾。临床表现为风团瘙痒,伴严重怕冷、嗜睡、感觉迟钝、身痛、体温血压降低,心率减慢等,治宜四逆汤。附子辛甘大热,走而不守,干姜辛热,守而不走,两者相须为用,激发心、脾、肾脏腑经络元气,从而达到通达十二经脉的作用,善破寒凝而血滞之症;甘草味甘性缓,可缓伏真火,使命根永固。三药合用可散经络寒郁之邪,以达元气振奋之功,终致全身阳气运行不息之果。若偏脾阳虚,可酌加理中丸;偏肾阳虚者,可加肾气丸。
4.2.3 化滞祛湿强神机 若湿邪结伏日久,则耗伤神机,湿性黏滞,阻于经络,使精气血津液郁滞,临床表现为风团瘙痒,伴乏力、怕冷、身重、嗜睡,感觉迟钝、心率减慢,血压降低等,治宜大除湿利机汤。方由除湿利机汤基础上增加桑白皮、大腹皮、冬瓜皮、益母草、茯苓、肉桂、知母、厚朴而成。桑白皮、大腹皮、冬瓜皮三者相合利水之力愈强,意在清除顽固之湿邪,且以皮治皮,加强止痒之效;益母草调经行血,《雷公炮制药性解》[23]言“益母本功治血,故入诸阴之经,行血而不伤新,养血而不滞瘀血”,亦可利水消肿,治疗瘾疹发痒;茯苓健脾利湿,知母化湿除热,厚朴行气燥湿,肉桂温阳通脉。诸药合用,气血通畅,湿邪尽除,神机得旺。
4.2.4 生津祛热强神机 若热邪结伏日久,长久稽留于血脉,瘀阻经隧,暗耗气伤津,气少则无力推动血液运行而成瘀,血瘀进一步发展会损伤阴血,血虚生风,症见风团灼热瘙痒、怕冷怕热、嗜睡、感觉异常、脱水、神疲乏力、体温升高,心率加快,血压降低,治宜生脉散。方中麦冬、五味子酸甘化阴,有“守阴留阳”之效;人参甘温,入心、肺、脾经,大补肺气而泄热,而百脉皆朝于肺,补肺清心则气充而脉复,热消血畅,神机气立得复,瘾疹自消。
5 小结
荨麻疹常见于表证,临床采用疏风散邪,从表论治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但临证时不能局限于皮肤表面疾患,一定要从宏观整体角度来考虑病邪的性质、病位等。“神机”“气立”理论以中医“天人合一”为依据,人生活在天地万物之间,凭借气立形成一个天人相通的,以神机为核心的有机整体。荨麻疹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神机气立”学说的角度来论,其根本原因无非“神机气立”之间的失调。荨麻疹起病之本在“气立”,病邪常经由“气立”部位侵入神机,继而导致神机气立紊乱,引发荨麻疹。因此依据“神机—气立”理论辨证论治,将祛邪气固气立、调血脉强神机之法贯穿于治疗始终,视气立闭塞情况与神机病变轻重,调整用药侧重,圆机活法,为临床诊治荨麻疹提供了全面、深入的理论基础和用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