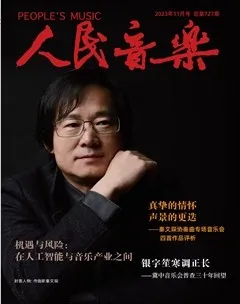创造我们这一代的新国乐
在音乐创作风格愈加多样与个性化、人们的审美趣味也日益多元化的今天, 什么样的民乐作品会更加引人倾听?“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推出的上海音乐学院“民乐新作专场音乐会”或许会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答案。
自2012 年始,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便以“春天的律动”为题,在“上海之春”中亮相。短短十余年,“春天的律动” 已经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一年一度的品牌活动。2023 年4 月3 日,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指挥家吴强携民乐系师生又为我们献上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民乐新作音乐会。本次音乐会共包含有五部室内乐作品、四部民族管弦乐作品和一部古筝独奏作品, 上演作品均为近年来的民乐新作,充分体现了民乐系雄厚的师资力量及其在民族室内乐和民族管弦乐上的教学成果。
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作为中国民族器乐教育的重镇,自建系以来便确立了“演、创、研”三位一体的学科综合发展路线, 创作与演奏形成协调发展、相互成就的格局。因此,在近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民乐系不仅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民乐演奏家,还创作了一批经典的民乐作品,其中由胡登跳首创的“丝弦五重奏”更是正式拉开了现代民族室内乐发展的帷幕,为现代民乐创作的发展铺下了一方厚重的基石。
本场音乐会中的民乐新作,一方面契合了大众对民族音乐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人们对民乐新发展、新动态、新样式的接受能力,因此引起各界的热烈反响。
一
音乐会的上半场共演出了五部民族室内乐新作和一首古筝独奏新作品。20 世纪60 年代,胡登跳先生在民间器乐合奏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室内乐创作的特色和思维,创建了“丝弦五重奏”这一体裁,正式开启了现代民族室内乐探索的历史进程。与民族管弦乐队相比,民族室内乐有着排演灵活、贴合民乐演奏性能等优点,因此一直是民乐作曲家们首要关注的创作体裁之一。本次音乐会上演的五部民族室内乐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当代中国作曲家对于民族音乐语言以及现代民乐可能性的多元探索。
首先登场的是由强巍昊作曲的笛子重奏《》(Sè)。这部作品首演于2019 年上海音乐学院创新团队民族室内乐作品音乐会。作曲家以意会竹笛音色的四叠字以及由四支竹笛构建的四条旋律,勾勒了“竹”这一具有丰富文人意象、具有符号意义、充满生命力的艺术对象。在古人看来,破土而出的翠竹既是春回大地的象征,更是君子刚正人格的反映。细听乐曲,旋律中对竹笛“实音”和“气音”的交错运用较为全面地发掘了乐器的表现力,其中柱式音响和民间竞奏效果的并存更是增添了作品的张力与戏剧性。四名笛子演奏家王俊侃、屠化冰、朱晛、吴非以他们精湛的技巧,将乐曲中充满律动、颇具抽象气息但又不乏中国音乐韵味的旋律,以细腻独到的气息控制技术和圆润精致的音色呈现在人们的耳畔,余音绕梁,久久难忘。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曾说,作曲家创造音乐是为了永恒,而演奏家只是为了满溢的顷刻。四位演奏家的精彩演绎似乎完美诠释了这句富有诗意的美学见解。此外,《》中还有不少具有音响效果的高难技法,可以视为是对乐器表现力的大胆尝试, 同时也展示了演奏家的高超技术。他们对乐曲的出色演绎,仿佛为我们绘制出一幅春意盎然的翠竹图。
20 世纪90 年代, 追新猎奇曾是民乐创作的风尚。而王建民教授却始终强调音乐创作应该追求可听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并在这一观念的主导下创作出了诸如《莲花谣》等既彰显新颖创作技巧,又具有极高可听性的民乐作品。本场音乐会上演的三部原创民族室内乐作品———《龙耀》《茶马》以及《锦绣》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样的特点。
以民乐创作享誉乐坛的王建民先生并非民乐创作的“新人”,但他的“新作”《龙耀》却颇具“新意”。《龙耀》受新加坡华乐室内乐团体鼎艺团委约而作,整部作品采用中国民间音乐多段连缀的曲体结构,其结尾的再现段落,又使作品带有三部性曲式结构的意味。《龙耀》在编制上包含柳琴、扬琴、琵琶、古筝和打击乐六个声部,以琵琶开篇,尽管是弱力度的演奏与宁静的表情,但纵使坐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琵琶的泛音也清晰可辨。一个直观的听觉印象是,旋律的发展由简入繁,层次分明,章法有序。以上行三度和级进下行构建的波浪式主题犹如在狮城日出时咏唱小调的一位少女,五声调式的突出则仿佛是建构了这位“少女”作为华人的文化身份,其中琵琶音色的运用更使这个主题在初现之时充满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羞之色。在音乐进行过程中,这个极具少女色彩的主题多次变形,构建了主题的多重叙事和双重抒情———该主题似乎就是成长并发展于狮城的“鼎艺团”的写照。在《龙耀》的音乐空间里,主题与它的各个“变形”共同讲述了“鼎艺团” 从诞生到如今蓬勃发展的艰难进程———它将华人世界的民族室内乐带到了新加坡,并借由新加坡这一颇具世界主义色彩的飞地空间,将华人的抒情声音散播到世界各地。透过《龙耀》,笔者似乎看见华人群体在20 世纪只身“下南洋” 以谋生计,而后在南洋地区开疆辟土、落地生根的史诗历程。这样的音乐想象当然是来自主题的多重叙事,这一手法构建了作品“以小见大”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特质。在“叙事”的同时,主题的叠进变形有如作曲家不断高涨的情绪,抒发了作曲家和演奏者对于“华乐”的崇高敬意。
如前所述,《龙耀》的曲体结构更符合混合曲式的特征,將中西曲式进行融合,也正是民族器乐创作的趋势。通常,当段落过多时,多段连缀与自由拼接的手法可能会使得作品结构松散,但《龙耀》采用主题动机贯穿式的手法又使得乐曲获得内在的凝聚力,让作品形成了内在与外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辩证统一。
值得指出的是,《龙耀》不仅旋律优美,配器上亦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首先,就宏观布局而言,不同的乐器组合除了制造出意想不到的音色,同时也与曲式的结构紧密相连。例如,作品的首部,琵琶在低音区呈示主题; 中部是柳琴与古筝呈示主题,增加了旋律的厚度;最后的再现部,又以柳琴、扬琴和铝板琴叠奏的方式对主题进行升华。其次,局部段落不同的乐器组合制造出特殊的音响音色。譬如,引子部分扬琴采用拍弦的技法, 铝板琴用弓子拉奏,它们营造出神秘空灵的音响效果。再次,微观层面上,作曲家还兼顾了每件乐器的个性:古筝总是不失时机地用大幅刮奏为高潮推波助澜,中部的快板弹拨乐器交相辉映、各显其能。由此形成了作品整体与局部的辩证统一,又充分彰显了乐曲的重奏性,而非仅是旋律配伴奏的简单形式。
《茶马》是青年作曲家李博禅于2016 年创作的作品,作曲家以室内乐的形式,描绘了古代茶马古道的音乐景观。尽管作品包含二胡、竹笛、笙、大阮等九件乐器,但在作曲家的有机编排之下,九个声部之间仍然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呼应关系,其中打击乐器的使用更是出其不意地增强了室内乐的声响效果,挖掘了民族室内乐“交响化”的潜能。品味《茶马》, 似乎可以体会到作曲家以茶马古道礼赞民族融合的人文情怀。
与《茶马》相比,苏潇以“丝弦五重奏”为体裁创作的《锦绣》则在音响开发上显得相对谨慎。作为王建民的学生, 苏潇在这部作品中一方面延续当年胡登跳先生在创制这一形式时确立的创作特点, 一方面也承继了王建民先生对于民族色彩的重视。在《锦绣》一曲中,民歌《绣荷包》的音调时常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作品的不同层次, 彰显了作曲家对于民间音乐的发掘和应用。在声部关系上,《锦绣》在强调各个声部之独立性的同时,更加追求突出各声部互相追逐、加花的特色。与其将《锦绣》视为是一部民族室内乐,倒不如将其定位为一部有意效仿甚至还原民间合奏乐特色的现代民乐重奏作品。《锦绣》以及與之性质相近的一些民乐作品, 为我们展现了当代作曲家对于民族室内乐这一体裁的“传统化”诠释。
在上半场的五部民族室内乐作品中,由付玄编配的古琴与胡琴室内乐《广陵散》是唯一一部直接改编自传统乐曲的室内乐作品。整部作品由一张古琴和一个以多把胡琴构成的“伴奏组”共同演奏。琴曲《广陵散》以其长大的篇幅、多变的节奏和速度,生动地勾勒出历史上“聂政刺韩王”的悲壮情景。陆笑姿的演绎细腻纤巧,在她的琴缦之间,我们听到的似乎不仅是隐含“杀伐”的金石之声,更是聂政在刺杀韩王时复杂的心理活动。
除此之外,上半场的音乐会中还上演了邓翊群近年的古筝新作《晚晴》。作为身兼作曲家和演奏家双重身份的古筝新秀,邓翊群在近年来推出了多部具有极高质量的新作。2012 年,他以一曲《定风波》崭露头角,其别具一格的作曲天赋开始为筝界所发掘。《定风波》大气的旋律、丰富的技巧展现,在众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随后数年里成为古筝专业学生考学、参赛的必弹之作。此次推出的《晚晴》,在音乐上似乎和《定风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又在很多方面上有所突破。
《晚晴》描绘了盛夏的海岛在快雨时晴的气候特点下,白沙、椰林、碧浪、晚霞之间形成变化万千、交相辉映的无限美景。同样的取裁自古典文学作品的意象,与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诗所不同的是,《晚晴》表现的是李商隐在摆脱往日厄运时倍感幸遇的宽慰。诗中有言:“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固然短暂,但足以让人流连忘返。
二
百年前,郑觐文以“大同乐会”的国乐实践开启了中国民族管弦乐的探索历程, 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作曲家继续以“一手伸向民间,双眼望向世界”的姿态,薪火相传地为民族管弦乐的发展谱写新的篇章。音乐会下半场的四部民族管弦乐作品:徐孟东的《广板》、贾达群的《随想曲·梨园竹调》、王丹红的《狂想曲》和张千一的《大河之北》,不仅彰显了当代作曲家对于传统的继承,同时也突出了他们对于现代乐潮的呼应。
首先登台亮相的是徐孟东于2015 年应中央民族乐团委约而作的《广板》。作品以京剧音调的核心动机发展而成,从曲体结构到音高组织、乐队编配、音乐发展均体现出鲜明而浓郁的民族风格。值得一提的是,担任京胡领奏的霍永刚先生在当日的演奏中很好地把握了京剧的音乐风格,极具穿透力的京胡乐声,犹如整部作品的“龙睛”,为音乐增添了颇为亮眼的戏剧性光彩。
其后登场的《随想曲·梨园竹调》,在乐队的声响效果上彰显了贾达群对于音色之“融”的特质的追求,流露出他早年通过学习绘画所习得的“色彩感知能力”。在这部编制十分庞大、声响效果极其丰满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中,作曲家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幅多元化的民间画作,其中既有戏曲声腔的百转柔情,亦有西北锣鼓乐的铿锵有力,以色彩斑斓的交响之声表现了对古代梨园乐人的丰富想象,整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贾达群建构在“音乐诗学”之上、对于“人文境界”的孜孜追寻。
如何在音乐创作中有效地运用民间音乐,使音乐在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同时, 彰显中国的当代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转换为一种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世界性话语,是当今民乐作曲家尤其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在本次音乐会上,张千一以他创作的《大河之北》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大河之北》是张千一涉足大部头民族管弦交响曲的滥觞。整部作品由《士———燕赵悲歌》《赵州桥随想》《回娘家》《大平原》《梆腔梆韵》《避暑山庄———普陀宗乘》《关里关外塞外》七个乐章组成,本次音乐会仅对其中的第二乐章《赵州桥随想》和第六乐章《避暑山庄———普陀宗乘》进行展演,笔者尤为欣赏第二乐章《赵州桥随想》。在这一乐章中,作曲家将与赵州桥内容相关的两首河北民歌《小放牛》和《四六句》作为两个主题并进行创新运用,通过ABCBA 的拱形曲式结构形象地表现“桥”,以抒情委婉和幽默诙谐相对比的音乐情绪,展现了一幅生动朴实的生活画面。第六乐章《避暑山庄———普陀宗乘》中藏族音乐“囊玛”元素的运用,使整部作品突出了多元音乐并融的特色。当晚的演出中,二胡演奏家汝艺的精彩表演, 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作品中河北人的爽朗气质,最后的炫技乐段更是充分展现了二胡这件乐器对于复杂段落的极强表现力。
除了上述几部综合运用各类民间音乐素材的民族管弦作品外,当晚的音乐会还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极具“流行风格”的管弦乐作品———《狂想曲》。作品系王丹红在2011 年完成的交响乐队伴奏形式版本基础上,于2014 年改编为民族管弦乐队伴奏。尽管十年过去,这部作品似乎称不上是一部“新作”,但它给听众带来的感受却依然是新鲜而令人激动的。作品借用西方“狂想曲”的体裁结构,以融合爵士音调的方式,开拓了扬琴演奏的新语言,为扬琴音乐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在吴强教授的指挥下,乐队的力度变化强弱得当,颇带炫技性的扬琴与乐队相得益彰,营造一个绚丽多彩的音乐空间。
三
此次“民乐新作专场音乐会”已在观众的掌声中落下帷幕,但那些极具质感和魅力的声音注定不会从此消失于音乐的夜空。行文至此,笔者思绪再次回到本文开篇的自问:今天,什么样的民乐作品更为引人倾听? 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什么样的民乐作品才有可能“经典咏流传”?
中国的民族音乐创作早已走过了百年前的稚嫩,历经不断求索的成长期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可谓迎来成熟期的辉煌。但在倡导文化自信、讲好中國故事的今天,置身音乐艺术全球化、放眼国际舞台,民族音乐创作之路应该如何继往开来?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就开启了改进国乐、创造新国乐的民族音乐发展道路,他在近百年前的热切呼吁至今令人共鸣:“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表现我们这一代的艺术。”
“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这不仅是五四时期新国乐创作寥若晨星之际的无奈与渴盼,同样也是百年后民族音乐创作获得极大发展后依然不可忘记的真知灼见。没有新的创造,就没有民族音乐的发展与进步,“表现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就无从谈起。及至20 世纪40 年代,对创造新国乐的呼声愈加高涨,一些民族音乐家指出,新国乐最能代表民族性格与时代精神, 新国乐的创造应当迎头赶上,成为世界音乐之林的重要一员:“新国乐之建设是富有民族的色彩、时代性的而不断前进的一种音乐。”
杨荫浏等音乐学家更是对新国乐的创造充满期待。他曾说:“世界的音乐,已随着西洋的文化,渐渐地流注入我们的文化里面, 我们有接受的必要。国乐最后有与世界音乐互相融合的必然趋势。……国乐有了出路之时,西乐在我国,才能度过它这‘囫囵吞枣的异常阶段而真正达到它自然消化的理想时期。”
遥想中国民族音乐创作转型时期先哲前辈们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对于当下乃至未来中国民族音乐创作当不无裨益。文化自信与民族音乐传统的弘扬,不仅依然需要固守“民族的色彩”,更要凸显“时代性”,同时敞开胸怀、拥抱世界,融会五彩缤纷的世界音乐,让中国文化精神化为动人的声音飞向世界。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和上海音乐学院民乐新作专场音乐会的不断推出,正是民族音乐创作在“律动的春天”里展示民族音乐魅力的生动写照。
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刘育和编《刘天华全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年版,第186 页。
王绍先《新国乐的建设》,《歌与诗》1944 年创刊号,第3页。
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国音乐学》1989 年第4期,第6 页。
冯嘉卉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20 级本科生
(责任编辑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