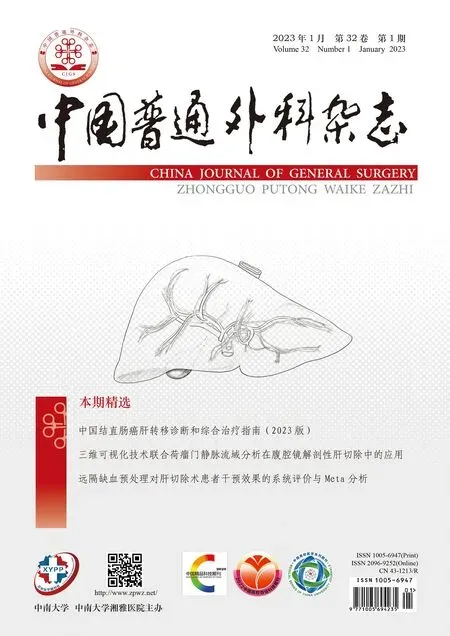肝内异位脾种植6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段克才,杨诚,方鲲鹏,董志涛,隋承军,戴炳华,耿利,杨甲梅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特需诊疗科,上海 200438)
异位脾种植(ectopic splenosis,ES)是指由于脾外伤或脾切除术后所引起的脾组织碎片自体种植[1]。Von Kuttner最早于1910年通过尸检所见首次提出了脾外伤后ES的概念,后Buchbinder于1939年报道了37例外伤后ES的病例[2]。有关数据[3-4]表明,脾损伤或脾切除术后ES的发生率为16%~67%,自脾破裂到ES确诊的平均时间间隔从5个月至32年不等。90%的ES发生于腹腔内,而发生于肝内的ES约占3%,临床上易误诊为肝脏的良性或恶性肿瘤[5]。本研究对我院收治的6例肝内ES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对其病史、影像学检查特点和治疗方法进行总结,加深临床医生对肝内ES的认识,避免误诊该类疾病。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2015年1月—2022年1月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收治的6例肝内ES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的基本资料见表1。回顾性分析6例肝内ES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病史、影像学检查特点和治疗方法进行总结,明确临床诊断要点和治疗原则。

表1 6例肝内ES患者的基本资料Table 1 Basic data of 6 patients with intrahepatic ES
1.2 治疗过程及随访情况
本组共6例肝内ES患者,其中男性4例;女性2例,年龄39~78岁,中位年龄51岁;均有外伤致脾破裂出血行脾切除手术史,脾切除术后至初诊肝内ES时间为20~33年,中位时间27年。6例中4例单纯肝内ES,2例肝脏合并膈肌多发ES;肝内ES伴有右上腹不适者1例,其余5例均在体检中发现;术前MRI或CT检查5例拟诊为肝癌,1例拟诊为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图1)。6例患者均行肝切除手术,术后病理均证实为异位脾组织,肝内ES灶大小为1.5~5.9 cm,中位直径3.2 cm,其中1例肝内2个病灶病理结果分别为肝内ES和肝细胞癌;所切除肝内ES灶都有相同的病理特征,肉眼下可见病灶包膜完整,切面呈暗红色或灰褐色,质软易碎(图2A),镜下可见红髓和白髓,白髓内见淋巴结,红髓脾索不规则,内见血细胞及淋巴细胞,脾血窦连接成网,形态不规则(图2B)。6例患者术后恢复顺利,随访半年均未发现新发ES病灶。

图1 6例肝内ES患者的增强CT/MRI图像 A:病例1;B-C:病例2;D:病例3;E-F:病例4;G-H:病例5;I:病例6Figure 1 Enhanced CT/MRI images of the 6 patients with intrahepatic ES A: Case 1; B-C: Case 2; D: Case 3; E-F: Case 4;G-H: Case 5; I: Case 6

图2 术后病理 A:大体标本(3.3 cm×2.8 cm ES病灶);B:镜下所见(HE ×200)Figure 2 Postoperative pathology A: Gross specimens (3.3 cm×2.8 cm ES lesion); B: Microscopic view (HE ×200)
2 讨论并文献复习
2.1 ES的发生机制及生理意义
相关文献[6-7]报道,ES的发生机制主要有3种:⑴ 脾外伤后分离的脾组织碎片通过直接播散种植,这是ES发生的主要机制;⑵ 术中在使用大量生理盐水对腹腔进行冲洗过程中,会将少量脾组织碎片冲向远离脾区的脏器表面而发生种植;⑶ 脾髓细胞可以通过脾静脉血流经门静脉种植于肝脏,这是肝内ES特有的种植方式,临床较为罕见。本文6例患者中,肝内ES灶多位于肝表面,仅1个ES灶位于肝实质中心,因此,笔者认为肝内ES多为脾组织碎片通过直接播散种植于肝浆膜表面,在生长过程中受腹壁、膈肌或周围组织挤压侵及肝组织。脾脏具有强大的免疫功能,脾切除术后最为严重的并发症是爆发性感染[8],为了挽救脾脏的免疫功能,降低术后爆发性感染的发生率,术中可以将自体的部分脾组织碎片植入网膜,以达到此效果[9]。基于这一理论基础,可见ES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但ES是否具有正常脾的生理功能,目前意见还不一致,相关研究[10]认为异位种植的脾组织应有足够的体积和正常的血供才能发挥正常脾的生理功能。
2.2 ES的种植部位和临床表现
脾外伤或脾切除术后,90%的ES发生于腹腔内,以小肠浆膜、大网膜、壁层腹膜、肠系膜及盆腔多见[11]。由于脾脏的解剖部位位于左上腹,因此左中上腹腔易于出现脾组织的播散种植,而发生于肝脏、膈肌或其他远隔器官较为罕见[12]。当脾外伤合并胸腹联合损伤时,可发生胸腔内的ES,也有文献[13]报道,ES发生于心包、脑等部位。本文统计了相关文献报道的ES所种植部位的相关数据(表2)。

表2 ES的种植部位相关文献统计Table 2 Literature statistics on the implantation site of ES
肝内或腹腔内ES常无特征性临床表现,通常在体检时意外发现[16],大多数患者无症状,少数患者可因ES位置特殊或ES灶较大而出现相应的临床症状,如腹部包块、腹痛、腹胀和肠梗阻等[17]。另若脾组织种植于胸腔或肺实质内可使患者出现胸痛、咯血、胸闷和咳嗽等症状[18]。本文6例肝内ES患者中,1例出现右上腹胀痛不适症状;1例因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导致反复右上腹疼痛,检查中意外发现肝内病灶;其余4例均在常规体检中发现肝内病灶而就医,无特殊的临床表现或不适症状。符合肝内ES的临床表现特点。
2.3 肝内ES的诊断、鉴别诊断
肝内ES的影像学检查方法主要包括:B超、CT检查、MRI检查和99mTc-热变性红细胞(99mTc-DRBC)显像[19],必要时可行经皮肝穿刺活检以明确诊断[5]。掌握了肝内ES的影像学检查特点,能够为临床诊断提供有力帮助,结合相应文献资料,总结出以下影像学特点:⑴ B超表现,超声下肝内异位脾结节常呈圆形或椭圆形低回声结节,边界清除,回声均匀,结节内血流信号较丰[20]。⑵ CT表现,CT平扫表现为肝内实质均匀的结节或肿块,圆形或椭圆形,边界清除,CT值略低于正常肝脏,约为40~70 HU[21];增强扫描动脉期的强化特点根据病灶大小而有所不同,直径≤3 cm的肝内异位种植脾结节多呈均匀强化,而直径>3 cm者多呈不均匀强化或花斑样强化,分析原因为红髓和白髓血流速度不一致,而≤3 cm的脾结节内红髓和白髓排列欠规则,致其血流动力学差异不显著所致[22];门脉期时病灶呈持续性均匀强化,延迟器稍减退。⑶ MRI表现,MRI平扫病灶信号均匀,T1WI呈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DWI呈高信号半ADC图信号减低,与肝脏信号相似;MRI增强扫描与CT强化方式相似。⑷99mTc-DRBC显像,原理是利用脾组织红髓中的单核巨噬细胞选择性吞噬和清除变形红细胞的作用而使脾组织显像,因此有学者认为99mTc-DRBC显像可作为无创诊断ES的影像学“金标准”[23],另由于放射性浓聚脾比肝脏高2~4倍,所以99mTc-DRBC显像对肝内ES的诊断具有特异性[24]。⑸ 经皮肝穿刺活检,镜下见穿刺标本由白髓及红髓按不同比例构成,符合脾组织镜下特点,可诊断为ES[25]。
结合脾外伤或脾切除手术史和各项检查的影像学特点,可以对肝内ES作出相应临床诊断,但临床上通常需要与肝脏的良恶性肿瘤进行鉴别,特别是对既往有肝炎病史的患者,极易误诊为肝癌[26]。祝路民等[27]报道了1例位于第二肝门的ES误诊为肝脏炎性假瘤的病例;杨子祯等[28]报道了1例肝脏及腹腔多发异位脾误诊为肝癌的病例。本文6例患者MRI或CT检查报告均未诊断肝内ES,其中5例诊断考虑为肝癌可能,1例诊断考虑为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可能,因此对可疑为肝内ES的病例可进一步行99mTc-DRBC显像或经皮肝穿刺活检明确诊断。本文1例患者为肝内ES合并有肝细胞癌,因此对肝内多发病灶且既往有脾外伤行脾切除手术史和肝炎病史的患者,应注意肝内各个病灶影像学表现是否存在差异,从而避免误诊、漏诊。
2.4 肝内ES的治疗原则
明确肝内ES的诊断对后续治疗方案的选择至关重要,因异位种植的脾组织可具有正常脾的作用,代偿脾的部分功能,且ES灶生长缓慢,因此无临床症状的肝内ES不建议手术切除;对于出现临床症状,如出血、梗死造成急腹症、慢性上腹疼痛、ES灶较大影响肝功能时,应予以手术切除治疗[29]。
总之,通过对6例肝内ES病例的诊疗过程进行分析总结,笔者认为结合患者既往脾外伤或脾切除手术史,以及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特点,对可疑肝内ES者,可行99mTc-DRBC显像检查,有条件者可行经皮肝穿刺活检,对明确为肝内ES不伴有临床症状者可随访观察。此次分析总结能够加深临床医生对肝内ES的概念、诊断以及治疗原则的认识,为以后的诊疗工作提供宝贵的临床经验。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