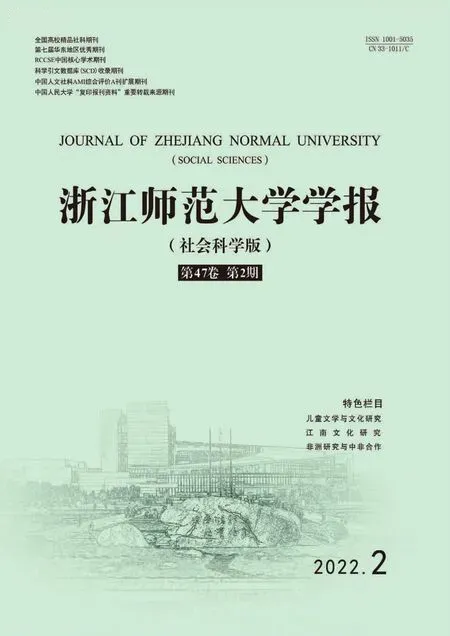儿童文学中的“他者”与作为“他者”的儿童
——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的后殖民主义批评
赵 霞
(浙江外国语学院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对于西方儿童文学批评来说,借自成人文化批评理论的后殖民主义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内涵多层且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术语。尽管后殖民主义首先是如西蒙·杜林所说受到帝国主义侵害的国家或群体试图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一种身份需求”,①但在随后丰富驳杂的理论生发和批评演绎中,它逐渐成为一切弱势/非主流群体寻求其政治和文化身份的独立性与主体性的一种批评行为。正如罗德里克·麦克吉利斯所说,后殖民主义批评“致力于倾听我们历史和文化中那些各式力量压制下的沉默的声音”。[1]xxii作为后殖民主义批评关键词的差异(difference)、多元(diversity)、混杂(hybridity)、他者(other)等,无不指向对那个“压制下的沉默的声音”的关注与关切。后殖民主义批评由此聚焦于文学话语在实施或反抗上述“压制”与“沉默”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西方儿童文学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发展出了两条基本的批评线索:一是沿着一般文学领域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传统,致力于揭示、解释、剖析儿童文学书写中话语霸权、压迫与反抗的现实;二是从儿童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出发,致力于发掘、阐说、反思儿童文学中的成人话语霸权。在前一层面上,儿童文学成为与后殖民主义有关的全部文学话语的一部分;在后一层面上,儿童文学则同时被认为是成人对儿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殖民”。这两个层面彼此交叠,构成了西方儿童文学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多维面貌与深刻内涵。
一、后殖民视野下的文化、历史与经典重读
如果将1970年代《儿童图书中的种族与性别歧视形象》《儿童小说中的性、种族与阶级》等论及种族问题的早期著作的出版,②视作西方儿童文学后殖民主义批评意识的滥觞,把1980年代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先后设立的“多元文化”(plural cultures)、“文化多元”(cultural pluralism)等栏目及一些刊物上陆续发表的种族批评文章视作这一批评意识的素朴演绎,那么一直要到1990年代中后期,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界才开始有意识地将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自觉运用于儿童文学的批评实践。③1996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会刊《书鸟》杂志第4期以“后殖民儿童文学”(Postcolonial Children’s Literature)为专题,发表了有关新西兰、葡萄牙、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后殖民儿童文学发展状况的文章。著有《儿童与青少年文学中的印度次大陆》《儿童与青少年文学中的非洲》《后殖民儿童与青少年文学的批判考察》等书的印裔美国学者米娜·科拉纳在为本期刊物撰写的读者导言中,指出了后殖民儿童文学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理解这一文学创作现实的难度。④1997年,《世界英语文学评论》杂志推出专刊“后殖民/后独立视野:儿童与青少年文学”(Postcolonial/Postindependence Perspectives: 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发表了包括该专刊主持者麦克吉利斯与米娜·科拉纳等学者的后殖民主义批评文章共13篇,论题包括儿童文学史的后殖民主义解读、儿童文学经典的后殖民主义重读等。21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与思考进一步深入。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2016年第4期推出专刊“非裔美国儿童文学与文类”(African 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Genre),探讨美国儿童文学研究中一直受到关注的非裔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该刊2018年第4期又推出专刊“儿童文学中的移民、难民与离散现象”(Migration, Refugees, and Diaspora in Children’s Literature),再次深化了关于儿童文学后殖民主义写作与批评的探讨。21世纪以来,罗德里克·麦克吉利斯主编的《他者的声音:儿童文学与后殖民语境》、克莱尔·布拉德福特的《不安定的叙事——儿童文学的后殖民主义阅读》、安妮·施耐德的《移民儿童文学》、马克·麦克肯尼的《重绘漫画中的法兰西帝国》、布兰卡·科瓦卡兹克的《当代英国儿童文学中的后殖民主义话语》等著作的出版,⑤既拓展和创新了儿童文学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也将儿童文学层面的后殖民主义思考不断推向深处。
这一后殖民主义的批评传统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少数族裔与多元文化写作。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初衷在于为主流文化边缘及之外的“他者”发言。这一“他者”的观念,彰显并强化了对后殖民主义批评而言具有基础性的一系列二分法观念:西方/非西方,白人/非白人,压迫者/被压迫者,主流文化/少数文化……而这种二分法体系的形成与漫长的西方殖民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后殖民主义批评“旨在反思、召回和重建族裔、文化中的他者;长期以来,他们遭到帝国主义西方运用其统治非西方世界的种种体制与策略进行的压迫、误写、忽略、模式化及侵犯”。[2]1为了反抗这种不平等的压迫与侵犯,后殖民主义倡导从文化“他者”的视角,为我们社会和文化中的少数群体发言。这一反抗意识在曾经的殖民或移民社会显得格外突出。克莱尔·布拉德福特的著作《不安定的叙事——儿童文学的后殖民主义阅读》,考察1980年代以来英语文学中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社会原住民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书写,从语言、叙事策略等角度,探讨了儿童文学的后殖民主义写作。同样以移民社会为考察对象,简·韦伯的《文本、文化与后殖民儿童文学》一文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探讨澳大利亚、美国、爱尔兰儿童文学如何摆脱英国儿童文学的“殖民”,探寻和建立自我文学身份。[3]约翰·斯蒂芬斯在《澳大利亚小说中的移民社会与多元文化社会》一文中也探讨了195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儿童小说如何从表现移民社会的主流价值转向对多元文化的重视。[4]
第二,后殖民主义视角的儿童文学历史重读。后殖民主义批评强调从“他者”思维重新思考和理解世界。这一观念下,面向历史的后殖民主义重读引起人们重视。在儿童文学领域,这一批评的主要方向有二。
一是儿童文学史的重读。希瑟·司科特在《追猎历史:儿童文学之外、之远、之下》一文中提出,“有关儿童文学的书写需要转向受到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更多启迪的方向”。[5]22作者以1995年彼得·亨特主编的《儿童文学》为主要文本对象,分析了当下儿童文学史述的殖民主义问题。有意思的是,该文中遭到批评的亨特本人,恰恰也是儿童文学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倡导者。彼得·亨特与凯伦·桑兹在《中心视野:不列颠帝国与后帝国时代的儿童文学》一文中指出了19世纪至今英国儿童文学中的殖民主义烙印,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意识逐渐觉醒的20世纪后半叶,这一殖民主义的传统和印记如何在儿童图书中继续得到传播,以及应当如何引起批评者的敏感与关注。[6]显然,意识到儿童文学历史书写中的后殖民主义问题只是其一,如何将这一意识落实于史述,则是另一项新的挑战。凯瑟琳·坎普肖等主编的《谁为黑孩子写作?1900年以前的非裔美国儿童文学》,试图从文学史不为人注意的缝隙中还原非裔美国儿童文学的激进历史。编者认为,这种想象和还原指向的不只是文学文本,也是对故事背后的文学观念与批评传统的反思。[7]将这些论著放在一起,可以窥见后殖民主义批评实践本身的某种复杂性与难度。
二是儿童文学作品中历史书写的重读。这一批评方向致力于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反思儿童文学中的历史呈现与书写。丹尼尔·哈德以1980年代以来出版的“美国女孩”(The American Girls)系列丛书为例,批评了该系列呈现历史童年生活时历史事实与儿童观念的双重失真。[8]迪特尔·佩措尔德从历史真实性、族裔身份的认识与建构、史撰意识、道德问题的简单化等角度探讨加拿大儿童文学中的多元文化写作问题及其面临的挑战。作者提出,儿童文学的历史书写需要在历史与道德、失望与希望之间寻求多元文化的“乌托邦”理想。这里的“乌托邦”一词,既传递出文化重建的良好愿望,但或许也透露了后殖民主义批评容易陷入的某种理论的天真。[9]2001年,《儿童文学中的白人至上》一书作者多娜莱伊·麦凯恩在为《狮子与独角兽》杂志“反种族主义与儿童文学”(Anti-Racism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专刊撰写的编者导论中谈到了以文化多元为重要观念的后殖民主义批评自身应有的多元规划,以及关于其批评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恒在的裂缝的认识。如麦克吉利斯所说,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方向和目的不是为了把人们带向有关“他者”的确定认知,而应该是鼓励“他者”参与文化游戏的一种持续的努力。[10]
第三,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后殖民主义重读。“后殖民主义的一个方面即是对经典文本的修正重读,指明这些文本如何建构了我们的世界。”[11]12许多儿童文学阅读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作品,恰恰有待后殖民主义批评视角的重新审读。在这一批评潮流下,吉卜林、弗朗西斯·霍奇顿·伯内特等创作上带有鲜明殖民观念与痕迹的作家及其作品,首先成为后殖民主义批评重观的对象。例如,梅维丝·雷默分析了伯内特著名的儿童小说《小公主》文学与电影版本中的殖民主义蕴涵。[12]在彼得·亨特与凯伦·桑兹的解读下,《沃特希普荒原》《小熊帕丁顿》《小黑孩桑波》等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6]约翰·克莱门特·保尔从莫里斯·桑达克知名的先锋图画书代表作《野兽国》中解读出了隐藏的殖民主义蕴涵。在他看来,故事主角麦克斯的幻想旅行,从文字到画面都与历史上的西方殖民行为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13]
其中,菲利普·尼尔关于苏斯博士及其代表作《戴高帽的猫》的批评,可能是影响最大的批评案例之一。2014年,在发表于《儿童文学》杂志第42卷的《戴高帽的猫是黑的吗?——探询苏斯博士的种族想象》一文中,尼尔针对苏斯博士出版于1950年代的先锋童书《戴高帽的猫》所作的后殖民主义解读,代表了这一儿童文学批评方法在其成熟期的典型面貌。首先,它显示了儿童文学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某种开阔性。尽管以苏斯博士及其童书作品为主要论题对象,尼尔的分析却并不局限于文本内部的解读,而是将它们放到苏斯博士本人的创作史、美国非裔文化史及美国当代政治运动的开阔背景上,探讨“戴高帽的猫”这一经典童书形象的渊源及其内含的复杂种族观念。其次,它也体现了当代儿童文学后殖民主义思考的深度。在尼尔看来,“戴高帽的猫”这一儿童文学形象及其衍生的文化产品所携带的批评讯息是丰富而微妙的。它诞生于苏斯博士对于黑人形象模式偏见的批判与创作反思,却也不知不觉使自己陷于新的意识形态陷阱之中。根据尼尔的分析,“尽管苏斯的创作意在挑战偏见,他却从未彻底告别伴随他成长的那些文化观念,并且很可能不曾意识到他的视觉想象怎样复制着他有意反抗的种族意识形态”。[14]81因此,“戴高帽的猫”既是反种族主义的符号,也是反种族主义的假象,既冲破着边界,也强化着边界。2017年,尼尔出版了《戴高帽的猫是黑的吗?——儿童文学中隐藏的种族主义与多元图书需求》一书,就儿童文学中“隐藏”的文化殖民讯息及其“隐藏”的复杂方式,提出了进一步的批判与思考。[15]他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语境下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复杂性。
二、后殖民主义的激进阐释与批评反思
后殖民主义批评信奉“儿童小说是促进或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16]7它以明确的意识形态批判为文学批评的主要目标,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目标。布拉德福特这样表明她的批评姿态:“我的方法不适用于文本‘好’或‘坏’的分类,也非国家文学的排名榜。我相信,文本躲开了创作者的意图,他们既由其作者创作,也由其所处的文化话语生产出来。我阅读这些文本,就是为了辨识造成其面貌的话语塑形与意识形态。我尤其视它们为后殖民文本,来查看其修辞、想象、蕴涵和意识形态。”[17]225就此而言,这一批评方法打开了进入儿童文学艺术世界的另一道隐秘之门。在这里,儿童文学从传统观念下理性地掌握着它的创作者手中出走,进入了更为复杂、多重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话语的交织体系。儿童文学批评也越过针对作品创作意图或阅读效应的显在诠释,而带我们走上了探询个体或群体复杂的主体意识及其承载的文化讯息的道路。由此,儿童文学文本成为批判文化殖民、控诉社会不公的文化战场,儿童文学阅读与批评也成了探讨、寻求社会公义的重要政治行动。
在这一文学批评的基本语境下,过度阐释与激进批判往往在所难免。比如前面提到的约翰·克莱门特·保尔关于《野兽国》的后殖民主义批评,故事里的小男孩麦克斯坐船来到野兽国,被解读为西方殖民侵略必经的航海之路;马克斯简简单单地战胜了野兽,被解读为被殖民者向殖民者的轻易臣服;桑达斯插图中的野兽形象并不可怕,倒显得好笑,正代表了殖民者眼中的被殖民者;野兽们缺乏个性与命名,正是殖民话语中低级存在的象征等。[13]詹妮弗·肖戴克在《〈野兽国〉:桑达克通往黑暗之心的旅程》一文中,也将《野兽国》及其代表的西方经典冒险故事传统解读为“一场关于外部物欲世界里的现实权力与统治的帝国主义幻想”。[18]156这类批评将文学符号可能激发的隐喻想象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针对经典文学的重新解释,往往能够带来出人意料的震惊效果。然而,如果按照这一批评的逻辑,大量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解读出殖民主义的隐喻内涵。如果说自罗兰·巴尔特以彻底“重写”的方式解读《萨拉辛》以来,一切阐释可能都被赋予了理论存在的合法性,那么当这种过度阐释成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常态,其相对于儿童文学自身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力与价值反而下降了。
与之相类似的是布拉德福特针对斯皮尔伯格执导的《E.T.外星人》、玛格丽特·梅喜的小说《家里来了外星人》、吉莉安·鲁宾斯坦的《迷宫之外》等科幻故事与电影的过度解读。布拉德福特引用安德鲁·麦克唐纳等研究者的观点,认为“外星人的故事无一不是殖民的寓言”。[17]204在这一基础立场上,布拉德福特提出了关于外星人故事的两点后殖民主义解读。第一,在这些故事里,代表原住民的外星人形象与儿童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相似,他们像儿童一样,天真简单,缺乏自制,在与成人世界的关系中始终处于相对的权力缺乏状态(relative powerlessness),从而既“与我们相似,又低于我们”。[17]205第二,故事最后,外星人总是因为不能适应地球生活,或是死亡,或是必须离开,返回自己的家园。其中隐喻的意义是:“原住民注定要消失,因为他们不能适应(高级)白人文化,这是移民社会殖民者的普遍期待与愿望。而当代书写通过把原住民划归社会生活的边缘,总体上继续回避着原住民文化的异己性。我们可以根据这类文化模式来解读E.T.、邦德的离开以及卡尔的死亡,因为只要他们归回自己遥远的家园,也就消除了与他们成为朋友的那些白人孩子同文化(以及种族)差异打交道的必要麻烦。”[17]208
显然,结合具体文本的事实,这样的分析看起来不但是过度诠释的,而且是理论至上和观念先行的。事实上,当后殖民主义批评从明确的政治诉求出发开展儿童文学的批评活动时,这一结果几乎是必然的。而其过于激进和远离文本的姿态,也在不断引发批评者的反思。多娜莱伊·麦凯恩在为《狮子与独角兽》杂志“反种族主义与儿童文学”专刊撰写的编者导论中,切中肯綮地谈到了反种族主义、文化多元、多元文化主义等后殖民主义批评观念本身需要面对和处理的诸多疑难,包括针对其教育主义、简化论、政治正确、部落主义等可能倾向的质疑。[19]韦伯和斯蒂芬斯均谈到了儿童文学后殖民主义意识背后可能的殖民主义陷阱:相关创作与出版的初衷虽然是倡导、鼓励多元文化表达,实际上却削弱、限制了这种多元意识。布兰卡·科瓦卡兹克的著作《当代英国儿童文学中的后殖民主义话语》,将更广泛的少数族裔纳入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对象。在有关当代英国儿童小说后殖民主义书写的考察中,科瓦卡兹克既充分肯定了这一创作探索的成就与意义,又提出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反思:一种多元文化创作与出版的良好意图,如何在实践中部分地演变为了商业主义的奇情与景观,从而使这类文学既是突破边界和颠覆性的,又是权威化与排斥他者的。[16]128,125这一论断与韦伯和斯蒂芬斯的观点构成了呼应。麦克吉利斯就此表达过同样的疑问:“令我好奇的是一些意图良好的书籍如何走向了它们明显想要培育的文化差异包容性的反面。”[1]xxxi科瓦卡兹克由此认为,后殖民主义批评本身不应成为某种固化的批评议程,它“既应对社会中少数族裔的多元站位保持敏感,又需时刻抵抗想要将他们规范化的冲动”。[16]127
那么,在儿童文学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语境中,究竟该如何理解政治与文学、观念与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罗宾·博恩斯坦在《种族的天真:从奴隶制度到公民权利的美国童年塑造》一书中,对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做了新的解读。在他看来,小说中有意设置的白人与黑人童年的对比,就其符号表层而言,是通过儿童形象的独特力量传递针对奴隶制度之恶的批判。但比较作者笔下纯真善良的白人孩子伊娃与被剥夺了正常童年生活权利而自暴自弃的黑人孩子托普西,这一两极化的处理究竟是促进了儿童层面的种族理解,还是反过来加重了它的问题?在博恩斯坦看来,小说隐含的逻辑是,“奴隶制度的暴力伤害了托普西的纯真本性,而通过一个白人孩子的爱的触动,这种纯真能够获得部分的恢复或传递”。[20]16以这样的方式,黑人童年的深重苦难仿佛在有关童年的纯真想象中被救赎和抵消了。虽然博恩斯坦的批评是激进的,但这一批评隐在地揭示了后殖民主义批评时代文学不得不面对的一系列普遍难题:文学的某种浪漫本性如何阻碍了同样作为其本性内容之一的文化政治目的的实现?约翰·斯蒂芬斯、麦克吉利斯等学者之所以提醒人们警惕儿童文学阅读中的沉浸体验,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如果说儿童文学既无从告别浪漫,也无法告别政治,那么,如何重新思考、建构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是当代儿童文学批评无从回避的难题。
同时,在布拉德福特等研究者对于后殖民主义批评方法的过度运用中,潜在地隐含了另一个重要的批评命题,即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泛化的后殖民主义文学话语与现象的观念。由于儿童文学是一种与儿童(包括类儿童角色)在社会文化观念和等级制度中的弱势身份密切相关的写作,这一文类本身也指向一种带有后殖民主义性质的文学行为。由此衍生的批评思想和理论,既是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发明,也以其独特的方式丰富了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
三、后殖民隐喻中的儿童与成人
1992年,加拿大知名儿童文学批评家佩里·诺德曼在其主持的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文学理论与儿童文学”(Literary Theor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栏目发表《他者:东方主义,殖民主义与儿童文学》一文,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移用于儿童文学的批评思考,正式奠定了儿童文学语境下另一种后殖民主义观念的传统。从萨义德的理论出发,诺德曼提出了儿童作为一种文化上特殊的被殖民者,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殖民”现象的典型体现的观点。比如:儿童被认为普遍不能为自我发言,只能由成人代言,由此造成儿童与成人之间的高下等级关系;儿童文学充满了成人中心,成人以一厢情愿的想象,扭曲地表现和塑造儿童;儿童文学中儿童的禁声与失声;儿童文学中的权力与控制;儿童作为“他者”被塑造为成人的对立和矛盾等。[21]诺德曼此文在西方儿童文学界影响深广,19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涉及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儿童文学论著都会论及他关于儿童文学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上述理论发明。
事实上,早在1984年,当杰奎琳·罗斯出版其著名的《彼得·潘案例》一书时,这一后殖民主义的批评立场就已经蕴于其中。罗斯在书中指出,以彼得·潘形象为代表的儿童文学经典传统,恰恰代表了长期以来成人对儿童的某种独断、虚妄的想象。[22]诺德曼在《他者》一文中也重点谈到罗斯的观点。不过,在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成人关系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的被殖民者/殖民者关系之间提出直接的类比,则是诺德曼的创举。他出版于2008年的著作《隐藏的成人》,某种程度上正是其上述后殖民主义观念的批评实践。[23]当我们透过后殖民主义的视角看待儿童文学的诸多传统观念,有关这一文类的许多不曾言明或不被关注的艺术与文化问题,便得到了新的揭示与反思。一般说来,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文类的首要特性即在于它是由成人写给儿童的文学作品。这种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文化身份之间显在的不对等关系,从一开始就显明了儿童文学的基本姿态与面貌,也埋下了与此有关的诸多艺术与文化问题。如同麦克吉利斯所说,“儿童及其文学总是后殖民的,如果我们以后殖民一词所指的是站在传统与权力外围或对立面的某物”;某种程度上,在主流批评话语场中承认“儿童与儿童文学”的合法性,本身即是一种体现后殖民主义批评精神的行为,因为“这是一个朝向重新看待经典、重新定义学术与专业批评可以做什么、说什么的姿态”。[11]8-9
如果说20世纪中后期以来,针对这一文化关系的反思开始不断进入儿童文学的批评视野,那么来自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资源则为其当代解剖提供了称手的批评武器。“语言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相遇的基本方式,也是权力关系接受挑战与变更的主要途径。儿童文学的语言实践并体现了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17]6由此,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视角切入,揭示儿童文学文本背后“被殖民”的儿童形象,以及它所蕴含的文化霸权,成为儿童文学批评义不容辞的当代职责。正如“后殖民世界是一个被建造起来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先已存在的世界”,[24]49一种以儿童文学为对象的后殖民主义观念也认为,儿童文学是成人借以建造自己想象和愿望中的儿童世界的基本途径。左那多的《发明儿童》等著作,正是试图揭示这一建造的过程以及儿童在其间作为“他者”的基本身份。他关于莫里斯·桑达克的图画书《野兽国》的分析,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思维。在他眼里,《野兽国》不是一部宣泄之作,而是一部令人不安之作。马克斯的野兽国之行,是一场“野性”的驯服之旅,以马克斯的妈妈为代表的成人要求和迫使孩子去做的,是对既有的成人/儿童权力与等级关系的认同。最后,正如马克斯驯服了野兽,马克斯的妈妈也驯服了马克斯。图画书末页的空白,非但不是马克斯历经想象的冒险之后情绪平复、精神满足的标志,而是荒芜、冷酷、牢狱般的生活现实的象征。在这里,妈妈有如“幽灵狱卒”,给他带来了“还热着呢”的食物。左那多认为,“还热着”的不是食物,而是马克斯与妈妈的关系,后者仍像起初那样“烫手”和“灼目”。[25]184-185由妈妈(成人)提供的食物掩盖了儿童的紧张、焦虑与愤怒。
左那多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儿童文学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激进姿态。在近20年来的西方儿童文学批评领域,它也代表了儿童文学批评的某种基本姿态。曾任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任的瑞典学者玛丽亚·尼古拉耶娃在《儿童文学中的权力、声音与主体性》一书中提出,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文类的特殊性,即在于它聚焦“儿童/成人”的权力等级关系(child/adult power hierarchy)。[26]8尼古拉耶娃的某种后殖民主义批评立场,清楚地体现在作为此书关键词的“他者化”(othering)一词中。在该书结语“成人的自我否定”(The Adult’s Self Denial)中,尼古拉耶娃承认,在儿童文学的语境里,一种“成人的自我否定”是不可能彻底完成的,它或许意味着,儿童文学无论如何都将是一种带有成人“殖民”性质的文化行为。在发表于2019年的《成为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神经科学时代的儿童性》一文中,尼古拉耶娃就此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作为成人,我们如何理解一个孩子的意识世界?我们如何得以知道成为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她反驳了成人能够经由自己的童年经验理解儿童的主张。换句话说,成人曾经是儿童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成人就能理解儿童。结合脑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发现,尼古拉耶娃提出,由于儿童的脑部结构与成人有着很大不同,其感知世界的方式或许也与成人完全不同。当个体由儿童长大成人时,左脑优势取代右脑优势,其感知与认识世界的方式由此也发生了根本的、不可逆的转变,并且,大脑不会保存关于童年感知方式的任何记忆。童年的逝去是永久性的。[27]28-29她的主张显得颇为激进:“我的观点是,一个儿童作家理解一个孩子,并不比他(她)理解一只蝙蝠更多。这是因为成人与儿童之间存在着认知的鸿沟;它是我们的记忆无法填平的一道鸿沟。”[27]26一个孩子对空间(位置、方向、维度、比例)、时间、因果、秩序、自我等的感受,由于其大脑结构的特点,可能完全异于成人。由此,对儿童文学写作来说,并不存在着某个通用的儿童视角的知识。这就意味着,儿童文学中的“儿童”相对于阅读儿童文学的真实的儿童,将始终是一个“他者”。
这样,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罗斯与诺德曼的立场:儿童文学将不可避免地是一场成人对儿童的文化殖民。事实上,在这一后殖民主义的考察视野下,一切儿童文化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殖民事业的一部分。显然,这一观念在为儿童文学批评带来重要启示的同时,也包含了文化虚无主义的危险。由此,上述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观念既在儿童文学中受到普遍的重视,也面临质疑的声音。作为西方儿童文学后殖民主义批评最重要的代表学者之一,布拉德福特在《阅读种族: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中的原生态》一书中谈到文学作品中的原住民形象往往带有儿童特点,似乎落实了儿童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类比关联,[28]但在后来的《不安定的叙事》中,她还是指出,将儿童文学中的“成人/儿童”关系等同于殖民关系的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的身份分歧是不可改变的,但儿童终有一天会长大成人。在她看来,诺德曼的儿童观将儿童理解为某个同质化、去历史化的对象,这是有问题的。[17]7科瓦卡兹克在《当代英国儿童文学中的后殖民主义话语》里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麦克吉利斯倾向于部分认同诺德曼关于儿童文学写作是一种后殖民文化行为的判断,但他同时指出,没有必要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这种文化殖民关系推向极端。事实上,儿童文学的后殖民主义创作与批评不但可用来揭示一种出自成人意愿的话语如何塑造儿童,也可用来为当代儿童提供更多历史、社会与文化建构的可能。[1]xxviii
或许,理解和实践诺德曼式后殖民主义批评观念的最佳路径,不是将重心放在儿童与成人之间不可弥合的殖民关系上,而是强调在儿童文学的书写中,朝向儿童的认识与理解本身是一个需要不断反思、永无休止的进程。诺德曼与尼古拉耶娃关于儿童与成人之间文化关系的激进论断,与其说是要否定儿童文学为儿童代言的合法性,不如说是为了提醒人们不断反思、修正针对这一合法性的认知与实践。诺德曼以一部《隐藏的成人》深入揭示儿童文学背后的成人意识形态,但他从不否认,作为成人,在这场朝向“儿童”这一文化“他者”的无止境的探问与追寻中,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走近和理解儿童。同样,尼古拉耶娃既将儿童文学理解为由成人掌权者专为儿童创造的一种艺术和交流形态,同时也肯定了以儿童文学的方式为无权的儿童发言及赋权的合法性与意义。在她看来,尽管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他者”,却有一部分作家能够凭借文学独特的感知力与洞察力,深入把握儿童对象的某些真实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文学作为成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或许反过来提供了成人借以一窥儿童世界的幽秘途径。这使得西方儿童文学的这一后殖民主义批评思想与传统,最终不是走向极端的对立与反抗,而是通往积极的反思与建构。可以说,这一批评思想开启了在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语境下重新理解儿童和成人的新进程。
结语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作为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思想与方法之一,儿童文学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其激进的批评探索和富于独创性的理论发明,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它所提出的关于“儿童—成人”关系的后殖民主义隐喻,更是演进为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的一种基础思维方式。在这一批评思想的激励和启迪下,西方儿童文学界对儿童文学中的文化殖民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知和更深入的理解。这样的认知和理解,同时深化了人们对于“儿童是什么”“儿童文学是什么”等儿童文学核心问题的认识。
更重要的或许是,儿童文学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始终是一种充满实践意图与实践力的批评。在后殖民主义批评思想的推动下,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自审意识不断深入儿童文学的艺术机体,批评与创作之间相互激荡,彼此加强,共同重塑着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的基本观念、面貌与精神。与此同时,在后殖民主义批评视野的观照下,童年和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研究与批评的重要视角,也成了当代西方文化批评中日益受到关注的批评方向。在这样的探索中,西方儿童文学既借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实现了自身的重要发展,也为更广阔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注释:
①参见Roderick McGillis, “Introduction”, inVoicesoftheOther:Children’sLiteratureandthePostcolonialContext, edited by Roderick McGillis, New York & Oxon: Routledge, 2000, pp.xix-xxxii.
②Council on 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 ed., Racist and Sexist Images in Children’s Books, London: Writers and Readers Publishing Cooperative, 1975; Bob Dixon,CatchingThemYoung1:Sex,Race,andClassinChildren’sFiction, London: Pluto, 1977.
③克莱尔·布拉德福特在其2007年出版的著作《不安定的叙事——儿童文学的后殖民主义阅读》中认为,儿童文学批评界有意识地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展开针对殖民或后殖民文本的分析,“近年”才开始引起关注。参见Clare Bradford,UnsettlingNarratives:PostcolonialReadingsofChildren’sLiterature,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6.
④参见Meena Khorana, “To the Reader”, Bookbird, 1996, Vol.34, No.4, pp.3-4.
⑤Clare Bradford,UnsettlingNarratives:PostcolonialReadingsofChildren’sLiterature,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7;VoicesoftheOther:Children’sLiteratureandthePostcolonialContext, edited by Roderick McGillis, New York & Oxon: Routledge, 2000; Anne Schneider,Lalittératuredejeunessemigrante:récitsd’immigrationdel’AlgérieverslaFrance, Paris: L’Harmattan, 2013. Mark McKinney,RedrawingFrenchEmpireinComic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3. Blanka Grzegorczyk,DiscoursesofPostcolonialisminContemporaryBritishChildren’sLiterature,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15.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
——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