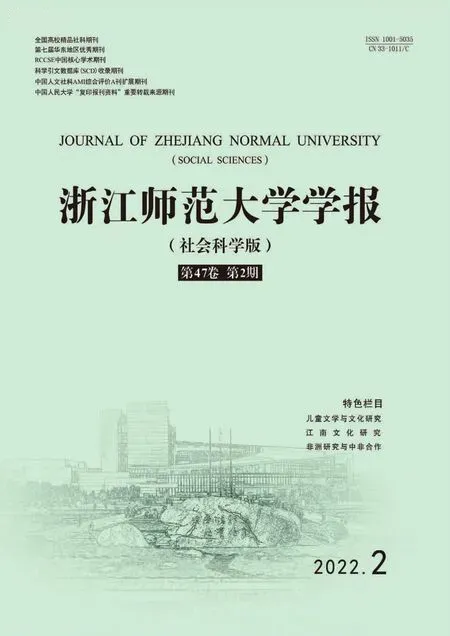滇南景物与江南视角
——论阮元诗作的滇中江南书写
杨增良
(大理大学 文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
“蛮烟”“瘴雨”“荒服”等辞是滇南景物的书写传统,它包括对自然景观与社会人文的印象认知。清姚文燮(1628—1692)有“巉岩终古最穷边,鸟道悬空密箐连”[1]24的诗句被收入雍正、道光两朝的《云南通志》。与阮元同时为官滇南的董国华说“万里违京国,频年滞瘴乡”,[2]陈文述《送董琴涵之官滇南并寄阮公子赐卿》中也有“滇云万里罗甸国,昔在李唐称外域”,[3]诗中“瘴乡”“罗甸国”等印象与江南文化形态相去甚远。蛮荒边远是多数文人对滇南的印象。道光间,阮元以云贵总督身份驻滇,由于江南文人、封疆大臣、考据学人等多重身份的影响,使他的滇南景物书写呈现出与时人相异的话语。作为江南文人,高年远宦使他以江南视角审视滇南景物,在滇南书写了一系列“江南景物”,呈现出独特的审美体验和美学观念。作为封疆大臣,“滇中江南”书写暗合了太平盛世的隐喻;作为考据学人,“滇中江南”书写是清人地理观念变化在文学中的体现,反映了滇南从“蛮荒边远”向内地化转变的需求。因此,阮元融入自我视角、江南经验,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江南化”策略。
一、“江南黄叶村”:江南家园的营造
阮元任职云贵总督后,思想发生巨变。由于高年远宦和《学海堂经解》刊刻完成,他对政治与学术的关心都不如以前。因此,“江南黄叶村”是阮元在滇关注的话题,他曾多次以“江南黄叶村”题大理石的意境。经统计,《石画记》中此主题石画多达五幅。“黄叶村”是归隐的话语隐喻,解释了他彼时的向往。他将督署宜园转变为归隐家园,是解决游宦与归田矛盾的现实选择,并从现实改造与纸上书写两方面塑造了滇南的“黄叶村”。
(一)滇南造景:江南园林的布置
阮元常在繁乱的滇南自然景观、社会生活中发现江南式因素。丁亥年(1827)正月二十日,滇南刚刚雪过天晴,阮元与阮福煮茶于督署宜园竹林。他突然诗情大作道:
滇南才过立春节,已觉春光齐漏泄。忽然一夜北风来,卷落漫天玉花雪。我不见雪已八年,颇似故人成久别。今日东园雪满林,翠柏青杉枝欲折。况是梅花四十株,冷玉寒香同冱结。[4]700
滇南雪景“颇似故人成久别”,而“梅花四十株”也是似曾相识的江南物象。阮福和诗道:“此景教人忆故乡,若忆岭南又殊别。”[4]700滇南景物唤起了阮氏父子的乡思之情。日本柄谷行人认为,“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5]当阮元的乡思之情被唤起,又与他的江南审美经验发生作用,滇南与江南两地的景物也就显得非常相似。《东园残腊》曰“除却雷塘庵外雪,未应春雨更思家”,[4]717《中秋宜园灯月》有“颇来乡思摇银烛,共写诗心入纸屏”,[4]703这些诗句都是滇南景物的书写,却充满着乡思情感的诉求。可以说,游宦与归田、美景与乡思的矛盾,使他常常触景生情。因此,江南园林的营造也就顺理成章了。他在督署布置了“宜园十景”:“仙馆昙云”“虚斋香雪”“南轩赏雨”“山房贯月”“花棚序射”“蔬圃咬香”“石彴观鱼”“宜亭来鹤”“竹林茶隐”“岭怡云”,[4]698都具有浓厚的江南园林之味。园内“岭怡云”是登临眺望之所:“有土山,登之可望四围远近云山。”[4]698“琅嬛仙馆”则用于收藏书画,阮元“以纸书‘琅嬛仙馆’匾,加于木匾之上”。[4]698《揅经室集》又载他“日暮无悰,闲步林下得一石,高五尺,重三百余斤,运置轩前”,在宜园“致爽轩”仿米芾置“上皇山八十一穴之异石”。[4]731
阮元常以大理石装饰督署景点。他将《水中藻荇图》镶嵌于宜园墙壁,说:“东坡与张怀民承天寺步月,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宜园中月下常有此影,而池中藻荇宜如其色,爰嵌置园内亭壁之上。”[6]31可知,阮元发现宜园与承天寺的月下藻荇有相似之貌,遂以石画装饰宜园,模仿承天寺景观。另外,他还将《昆华雪气图》“砌‘香雪斋’东壁”。[6]120《昆华雪气图》是阮元花半万钱所购大理石,但他毫不吝惜,将之嵌于“香雪斋”,显示了他对宜园景观的寄托之深。滇南督署是阮元建构的“江南黄叶村”,他因此“倦向此园卧,便如归我家”,[4]712将督署宜园当作自己的江南家园。
除改造督署宜园,阮元还效仿白居易、苏轼在滇南仿建了“阮堤”,将西湖景观复制到滇南。文献记载了他对滇南“西湖”的捐建历史:“乙未春,大学士总督阮元复倡捐,于插篱处筑堤一道,可由寺南绕出寺北,设涵洞泄水而不走鱼。西轩改造舟屋三楹,旁楼以‘莲笑’额之。水光云影可称名胜。”[7]从“复倡捐”的措辞看,他的倡捐并非偶然。此后,他在堤上分别建造了“听莺桥”“燕子桥”“采莲桥”。“听莺桥”大概是西湖“柳浪闻莺”景观的模仿;“采莲桥”“燕子桥”虽难判断具体渊源,但江南景观的特征亦相当明显。同样,阮元也多次捐赠大理石于此“名胜”。他将《雪浪》第四石“捐置莲花寺中海心亭”;[6]249“省城海心亭放生池榭落成”,他又将《四时山水》四幅“置之壁间”,[6]276为文人提供了江南园林式的雅集场所。
(二)窗牗观景:景物书写的江南园林视角
纸上造园是阮元“江南黄叶村”营造的又一重要方式。因此,通过园林观景视角,督署外的景物也被阮元渲染上江南之色。驻滇期间,阮元与阮福在宜园内分别搭建了东、西二台,成为观览整个昆明田园山色的立足点。《西台》诗曰:“登台万丈列苍岩,远见层坡近平坝。琳宫樵径皆分明,华浦青青绕禾稼。”[4]702诗中景色的构图要素丰富,包括横列的“苍岩”、遥远的“层坡”等远景,以及“平坝”“华浦”“禾稼”等近景,又有“琳宫”“樵径”等人物活动的痕迹。郭熙曾提出山水画要“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琳宫”“樵径”等要素使所写景物具有了郭熙所提出的山水画功能。“苍岩”“层坡”“琳宫”“樵径”等也是山水画的构图要素,可见阮元将这些要素组合成了一幅幅山水画。诗中又有“列”“远见”“分明”“绕”等语辞,使窗外各景物之间的关系变得错落有致。
《登西台》则有:“登台终日见昆华,恰好楼台住一家。玉岭西横皆是翠,彩云南现半成霞。千村绿稻真秋色,十里清滇是海涯。”[4]703诗中“昆华”“玉岭”“彩云”“晚霞”“村落”“绿稻”“海涯”等景物,可简单分为山、水、人迹三要素,而它们又都是“秋色”里的物象,因此,整首诗也让人联想到“江南黄叶村”的画面。再看《暮登西台看碧鸡山色》的景物描写:“夕阳山外沉,暮色起山内。似有烟氤氲,亦非云叆叇。初见青出蓝,继复螺染黛。凝碧已诧奇,生翠亦可爱。”[4]703诗中有“夕阳”“群山”“氤氲”“叆叇”“染黛”“凝碧”“生翠”,再加上“初见”“继复”等变化状态描述,完全是一幅灵动的江南烟煴山水。而“碧鸡玉案边,隐隐有关塞。天成巨屏障,浓色畴能缋”,明确将所见的山川景色比作画屏。然而,这种“黄叶村”式江南山水画面的形成并非偶然,从阮氏父子的西台建造记载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道光六年余初到滇,子福构木以复其境。今四年矣,木渐朽,遂彻之,而迁其台于署西北隅废圃澹泉西南七丈许。台以七千土墼疊成之,纵横上下皆一丈三尺,工朴用省,成之甚易。台腹以梯旋而上,台上又立四壁为八尺之瓦屋,宽其西南窗,使全览碧鸡、玉案诸山之胜。远眺滇池,近挹华浦。碧鸡关戍,如在几案,太华诸寺隐现于华山之麓。朝霞暮霭,风云变幻,殷雷快雪,冻雨皓月,皆可于台上收之;舟帆往来,耕犊出入,春稼秋获,星回火节,亦可于台上遇之。[8]
从“宽其西南窗,使全览碧鸡、玉案诸山之胜”的记载看,园外的田园、山色景物正是通过“西南窗”映入,成为一幅幅江南之景。在江南园林造景中,窗牗是极为重要的构图要素。通过窗牗观景,原有景物的层次会显得更加丰富、立体。明代计成曾曰:“门窗磨空,制式时裁,不惟屋宇翻新,斯谓林园遵雅。工精虽专瓦作,调度犹在得人,触景生奇,含情多致,轻纱环碧,弱柳窥青。伟石迎人,别有一壶天地;修篁弄影,疑来隔水笙簧。佳境宜收,俗尘安到,切忌雕镂门空,应当磨琢窗垣,处处邻虚,方方侧景。”[9]计成明显注意到了窗牗在观景中的作用。清代李渔更说“开窗莫妙于借景”[10]328“以内视外,固是一幅理面山水”,[10]329又说“窗未设以前,仅作事物观;一有此窗,则不烦指点,人人俱作画图观矣”[10]329“坐而观之,则窗非窗也,画也。山非屋后之山,即画上之山也”。[10]330以窗牗借景,实为江南园林特有的审美方式。当今学者也认为窗牗是江南古典园林的衍生物。①阮元的景物观察,正是通过窗牗重构景物,使所览景物变成江南山水画的样式,符合江南园林的审美旨趣,“建造了”滇南广阔的江南世界。它虽不是阮元的私家园林,但也不像明清时期士大夫“纸上造园”[11]那样虚无,可以满足阮元“归隐”的部分需求。
(三)绕屋梅花:宜园中的江南书斋与梅花景观的想象
阮元也喜种植、书写梅花。他曾作诗曰:“六载游踪未到家,春时每忆选楼花。今年得在楼前过,黄腊梅开鬓也华。”[4]566可知他在文选楼前种植过梅花。另外,他还在家庙雷塘庵种植过梅花。孔璐华有诗曰:“雷塘庵外不闻喧,种得梅花似小园……我自闻看莫攀折,伤心更觉慕亲恩。”[12]梅花是阮元记忆的象征,和“亲恩”联系在一起。而“绕屋梅花”是江南书斋景观的再现,是来自江南的审美原型。阮元的滇南梅花景观书写通过两种方式完成:
一是“绕屋梅花”的历史话语继承。《腊月十四夜游宜园》有“古梅三十树,冲寒香半开”,[4]721其中“古梅三十树”,并非宜园梅花景貌的实写,而是其浙江幕内的题图历史话语承袭。阮亨记载:“林梅溪先生名廷和,兄外王父也,以兄贵,貤赠荣禄大夫。居家时建双清阁,积书数千卷,种梅花百本。先生之孙小谿述曾取宋人‘绕屋梅花三十树’诗意,属奚布衣冈、王孝廉学浩为之图,孙观察星衍篆其首,一时题赠甚多。兄诗云:‘家住西山山色里,更教绕屋种梅花。’”[13]474阮元亦说:“三十树梅花书屋者,甘泉林氏季修述曾述祖德而出仕及解组归田之书屋也。”[4]769《书斋清供》记载:“清人陈曼生曾为林小溪制印一方,古篆朱文七字:绕屋梅花三十树。边款做诗:三十树梅花开后,当与君骑鹤扬州。十二楼春水涨时,还共我吹箫孤屿。”[14]从以上三则文献可知,“绕屋梅花”“梅花三十树”都是为纪念林廷和“梅花书屋”而取自宋人诗歌的梅花书写话语。可以推测,由于阮元童年时“尝往来其间”,[15]因此,“绕屋梅花”对于阮元和外家都有特殊的情感意义,故钱大昕题诗:“花与君家有夙缘。”[16]297阮元的童年经历变成了固有的审美经验,故《梅园晚景》又有“园林薄暝鸟初鸣,绕屋梅花香悄然”,[4]706诗中也直接使用了“绕屋梅花”的话语。道光十一年(1831),阮元又“为表弟林小汀怡曾题‘绿绕来青书屋’”。[6]79从文献记载看,林廷和当初的书斋营建及梅花景观布置都是对宋人诗意的模仿,而阮元等人对他的纪念也是抓住这个景观的特征不断重复题咏。因此,“绕屋梅花”是江南文人的一种观念性景观,是以梅花装饰书斋的图景描摹。当然,这种梅花景观也与阮元的江南记忆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当己亥(1839)年表侄林鸿、林薄再携《三十树梅花书屋》画卷而来时,阮元“展卷玩读,枨触于四五十年前情事,不禁老泪之落”[4]769“为之编次成一卷,鸿又钞画卷各名家诗成一卷……尚将补种梅花以咏清白之世芬矣”。[4]769
二是将“绕屋梅花”文学意象作具体画面的呈现。顾名思义,“绕屋梅花”是在书斋周围植梅并将其重重包围。阮元曾说“小溪林二表弟于扬州西山陈家集住屋外多种梅花”,[13]474钱大昕所题诗句“三间屋外暗香匀”[16]297和“横枝绕屋倍便娟”[16]297中的“屋外暗香”与“横枝绕屋”,都可以让人联想到林廷和“绕屋梅花”的图景,是书屋与梅花景观布置格局的再现。阮元滇南宜园“绕屋梅花”的书写,是受外家梅花景观审美形塑的表现。“梅花如屋竹如门”,[4]700可想见宜园梅花的茂盛如屋顶般遮盖着书斋。《倚松书屋春祭斋居》所谓“屋前梅树老于我”,[4]700也是书斋与梅花搭配的“绕屋梅花”景观。宜园“香雪斋”则是“繁枝满覆檐”[4]698的景观,描摹出书斋与梅花互相映衬的文学构图。这种根植于江南审美的书斋与梅花图景,也会让人有置身于江南世界的错觉。
阮元在滇南着意于“绕屋梅花”,还因为它是江南文人集体记忆和身份辨识的文学意象。宋代徐积有“北人殊未识,南国见何频”,[17]赵潘则有“江南此物处处有,不论水际仍山巅”。[18]“北人殊未识”与“江南此物处处有”,反映了梅花在北方的罕见和江南的普遍。因此,梅花审美意蕴的形塑其实与江南地域的关系更为紧密。从宋代开始,梅花意蕴进一步渗入了江南文人的精神世界,江南文人也不断丰富塑造着梅花意象。刘培认为“梅花象喻从南宋以来逐渐被塑造成华夏文化的象征”,[19]胡晓明甚至认为“江南与梅花,往往是二而一的关系”。[20]10即在文学话语中,“江南”与“梅花”具有相通的象征意义。在江南文人笔下,梅花几乎就是江南地域的特产和代名词,“成为寄托文化执念与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19]梅花在清代也是典型的江南地域景观。据《康乾南巡所游景观类型统计分析表》,[21]康、乾二帝游赏的生物景观“梅”有八处,“竹”五处,“荷”三处,“松”二处,其余都只有一处,反映了梅花作为江南景观的重要地位。程杰认为,“江西大庾梅岭、广东罗浮山梅花村、杭州西湖孤山、苏州邓尉、杭州西溪”[22]是清代最有规模和影响的梅花景观。从它们的分布看,梅花作为典型的江南物象呈现阮元的江南趣味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江南隐士行为的效仿与耕读环境的塑造
阮元在营造“江南黄叶村”隐居场所的同时,还将个人形象融入其中,通过效仿林逋与陶潜的行为,塑造自己的隐士形象。同时,由于江南情感的融入,阮元与梅鹤的互动及其躬耕场景,也使滇南被想象为江南世界。
(一)林逋隐逸行为的追慕
林逋是宋代江南隐士,他长期隐居孤山,以植梅养鹤为终身乐事,有咏梅诗八首。林逋存诗虽少,却是梅花审美范式的形塑者,“把梅枝推到了前沿,林逋之后人们艺梅赏梅、咏梅画梅无不着意于梅枝”。[23]他的“植梅养鹤”对江南文人而言具有天然的亲切之感,成为追慕高逸情志的效仿对象。林则徐曾在孤山“植梅养鹤”,重修“放鹤亭”,并在京师开展《饲鹤图》品题,②阮元则赠以《和靖孤山图》。[6]194
阮元的滇南诗作亦多有梅、鹤并置的景观书写。其中《来鹤篇》写道:“云南督署之东园亭馆,花木之胜为历任所未有,心念此间宜有鹤,未几日忽飞一白鹤来,翌日又有一鹤盘旋空中,鸣声相呼。薄暮并集于园。月余,遂驯且能舞矣,作《来鹤篇》:……宜园亭馆清如仙,周遮竹地梅花天。闲阶十仗草如席,惜少皋羽来蹁跹……如此园林如此鹤,屈指廿年无此乐。”[4]698诗中的“周遮竹地梅花天”,是首次映入阮元眼帘的滇南物象,而从“心念此间宜有鹤”的逻辑看,“梅”“鹤”意象是连类起兴的审美结构和固定搭配。见“梅”自然联想到“鹤”,反之亦然。宜园中“梅花”铺天盖地,“白鹤”则在空中盘旋,这是他的江南审美经验与期待。据诗中“屈指廿年”推断,这正是他在浙江任职的时间。因此“如此园林如此鹤”的审美经验,无疑是二十年前江南物象的呈现,亦隐约闪现林逋孤山植梅养鹤的情景。当这种经验、观念,固化为个人的审美模式,那么“梅”“鹤”的同时出现也就不是孤例了。《腊月十四夜游宜园》曰:“残腊月将满,月下宜有梅。古梅三十树,冲寒相伴开。梅边宜有鹤,双鹤立老台。与梅夜相守,不觉清钟催。”[4]721诗中多个“宜”的使用,是阮元深层审美观念的体现。《腊八日园梅有开者》写道:“雪后云阴意冷清,闲随双鹤绕园行。梅花有性真天放,得到开时便纵情。”[4]716《月夜游园》写道:“双鹤静立,老梅南枝,向月耀白,城钟已动,坐赏良久。”[4]716梅、鹤都是同时出现,成为固定的文学意象。这些都是阮元来自江南的审美典范,他说:“若不记之,则此景付之太虚矣。”[4]716
自我与梅鹤的主客融合,是阮元对林逋孤山隐逸情景的诗性想象。“一双白鹤一皤翁”[4]701的刻画,使梅、鹤不再是孤立的江南意象,而是象征江南的场景。阮元似乎每天都在过着卧游江南世界的生活,正所谓“爽垲已瘳双足疾,况于松鹤日相亲”,[4]701他将自己置身梅鹤相伴的环境中。《东园残腊》曰:“几曾孤负好年华,如此园林听放衙。三径有苔皆步鹤,一年无日不看花。”[4]717他似乎在说因投身于营边而错过了与梅鹤相处的好时光。“却为芳林常秉烛,不妨清夜再登台”[4]707以及“窗深时可卧,琴在不须歌。携幼还扶杖,看山更上坡。但达娱意处,休问老如何”[4]708的书写,使阮元的形象不再是勤奋干练的疆臣,而是珍惜时光、秉烛夜游的隐者。因此,督署场景本来的政治内涵被弱化得毫无踪影,变成了江南园林。《以藜为拄杖》曰:“养得青藜出短墙,削成拄杖等身长。扶人石径去行药,拦鹤松亭来啄粮。”[4]703这是他在老病中追求生命体验的秉烛夜游之境。宜园内的阮元有时“登台坐石几,四山云气翻。策杖过南圃,离落成野村”,[4]702有时“石上席狨清坐久,朱霞照我得酡颜”,[4]713有时则“石径不须倚笻杖,共来扶我有双孙”。[4]700这些诗句不仅塑造了阮元闲适的隐逸形象,还引导读者把想象指向江南的孤山。
(二)陶潜躬耕生活的效仿
阮元通过在督署宜园的农桑耕织,效仿体验陶渊明仕隐两得的江南生活。《食家园新麦面》《晚饭于福儿书斋登西台观稼是日剪得七种园蔬桂花紫薇同开》等诗都是宜园农耕生活的书写。他将宜园的菜圃打理得井井有条:“菜圃斜阳小屋晴,绿杉林下晚风清。豆篷瓜架随人坐,瓠叶茄花碍足行。”[4]709他的园蔬长势极好。另外,他的耕作种类从小麦到蔬菜、从桑树到苹果等,应有尽有。但他想要的是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体验,他说:“瓜田引修蔓,菜畦灌香根。摘蔬供晚饭,独乐静无言。试衍陶公诗,可与陶公论。”[4]702目的是通过农桑耕织,找到与陶渊明对话的途径。因此,阮元的农耕也是一种体道生活:“素饱宜知藜藿味,忘机可听桔槔声。闲来颇爱灌园叟,除却肩锄无世情”,[4]709表达了对陶潜的艳羡和模仿。《摘蔬》又写道:
摘我园中蔬,古人诗可味。譬如齩菜根,其香涤肠胃。我园春菜多,绿畦隔花卉。每看家僮锄,亦课园丁溉。折腰手亲摘,倾筐盈且墍。呼儿共晚餐,使识蔬笋气。一家肉食者,远谋问能未?岂可对陶诗,不自惭其贵。此以澹性情,非复计惠费。若云拔园葵,在今亦无谓。[4]700
阮元的农耕活动完全是隐逸生活的体验。通过“家僮锄”“园丁溉”,他的农耕生活不像陶渊明那样“草生豆苗稀”,但也使其成本非常昂贵。然而,这种耕读生活可“识蔬笋气”,所以他说:“此以澹性情,非复计惠费。”
阮元农耕生活的体验性还表现在与人分享成果。《蔬圃齩香》曰:“种菊成老圃,种菜成家园。新霜压肥绿,清妙殊鸡豚。短锄亲手劚,煮以佐晚飱。试语知味者,其香尤在根。”[4]698其时,阮元为云贵总督,伊里布为巡抚,两人在职责上多有重合,故交往频繁,多次以分享农耕体验互相和诗。阮元有《伊中丞过东园蔬饭见示一律即和原韵》《以园中柿芥饷莘农中丞见谢长篇因亦以诗相酬》等诗。当阮元“倾筐送去田家风”,伊里布则“已有长句来诗筒”。耕种,亦是一种诗情。所以诗中又有“既不能为田舍翁,毛锥长剑谁雌雄。不如治事有清暇,可以老圃兼老农”的感叹。这种做不了职业的“田舍翁”,却可在边疆治理闲暇时成为“老圃兼老农”的安慰,完全是文人隐逸话语的表达。
阮元的农耕生活场景书写背后是对江南式生活场景的复原。明清时人有所谓“吴中好风景,最好是农桑”,[24]可知农桑耕织是江南的重要生产劳作场景。所以,阮福《种橡育蚕记》记载:“丁亥冬,家大人向黔中雇佣多人,并购蚕种令各邮以驿马送之,六日而至滇。”[4]699他们在宜园“仙馆东新开二方石池:一栽荷,一养鱼。池上栽苹果树二株,梨二株,并于园南栽橡养山蚕”。[4]708这些都是阮元以情构景方式的体现。
(三)江南耕读场景的营造
阮元还在滇南宣扬江南的耕读文化。他不仅躬耕农桑,还勤奋读书,有“结习难除尚著书”[4]719“案牍判完还把卷”[4]713“掩书颇似学僧静,拙政还当愁我慵”[4]707“借闲一日得披图,静坐幽篁自怡悦”[4]700等耕读生活的书写。阮元由于乐此不疲的著述而眼力下降,他说:“我昔知命年,目力先差池。今复十余载,晶镜屡改移。”[4]712家人因此也劝诫他少读书。阮元作诗曰:“非但养心兼养目,高年远宦少看书。家人劝我言如此,我答家人意可如”;[4]715但他又说“岂有刘伶听戒酒”。[4]715他无法停止耕读生活。滇南士人杨松磐赞曰:“师相读书通万卷,名山石室穷搜遍。”[6]128阮元还常书写与儿孙共同读书、著述的场景,如“才教园客来烘茧,也看家儿学著书”[4]708“就此课孙知雅训,花名菡萏叶名蕸”。[4]709当阮福著成《孝经义疏补》后,他作诗曰:“滇南宦最远,今惟仲子随。仲子文笔拙,经义微能窥。疏经成十卷,阅之颇解颐。”[4]712显得异常高兴。
阮元宜园的耕读书写,是江南士子半官半隐耕读文化理想的呈现,所以其读书、著述又与农桑耕作有着紧密的联系:“笻杖试携铿翠石,菜锄亲把划苍苔。莺流燕蛰谁先到,棠芾桃夭合共栽。山磴看山收画本,竹林隐竹伴茶杯。抱书孙至还教拜,擘纸诗成不用催。适意如斯筹远否,此翁未是镇边才。”[4]700诗中他既“菜锄亲把”栽棠种桃,又悠闲地“看山收画本”和“茶隐”。他不仅展现江南式耕读生活,还写“抱书孙至还教拜”充满天伦之乐的场景。从某种程度上说,耕读是阮元为了书写江南文人情趣的需要,他甚至说“此翁未是镇边才”。与官方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是江南文人的理想,《以藜为拄杖》曰:“早岁校书曾秘阁,老年饮酒未家乡。篱边更待葫芦落,挂向枝头学道装。”[4]703乾嘉学人以追求纯儒为使命,但因书写江南场景的需要,“学道装”也成为阮元此时的向往。阮元是朝廷的封疆大臣,隐逸、耕读生活的书写,不完全是个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实际上还有出于江南文人的身份话语表达和江南情境塑造的需要。
三、“蛮烟瘴雨”的书写传统与“人文江南”的文学话语转换
清代滇南与外界交流变得更加频繁,赵翼、王昶、桂馥等人都到过滇南。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常州阳湖人,性灵派三大家之一。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兰泉,江苏青浦人,“吴中七子”之一。桂馥(1736—1805),字未谷,号雩门,曲阜人。他们是清代的一流士人,对清代文化的形塑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他们都将荒远作为滇南景物书写的基本色调。而阮元营造“江南黄叶村”,将滇南想象为江南世界,是其审美经验和观念与时人迥异的体现。
(一)“蛮烟瘴雨”的景物描写传统
赵翼有“无端岚气蒸蕴隆,幻出白雾粥面浓”[25]124的诗句写高黎贡山之景,但诗中更多是“荒”“奇”“蛮”“怪”“鹘啸”“啼猿”“哀响”“榛莽”等语辞。赵翼还有诗曰:“腾越之花多杜鹃,杜鹃园更花骈阗。我来戎幕暂无事,况有胜友同流连。”[25]129“美景”与“胜友”共同流连,但他却说:“不意绝徼中,有此巨丽观……我为作歌使之传,毋令长此埋没南荒天。”[25]129他为此“巨丽”景色生于“南荒”而惋惜。他还有“瘴雾濛濛似落沙”[25〗123“秋入黄茅人避瘴”[25]124“瘴雾郁蒸胸膈闷”[25]125“五色有浮瘴”[25]125“磷自鬼来浮草碧,风疑虎过隔篱腥”[25]124“山深谷邃无田畴,人烟断绝林木稠”[25]115等,诗句充满异域蛮荒之感。王昶《暮雨望点苍山》则有:“阑风伏雨天濛濛,我行回至邓睒东。龙尾关前午驻马,高阁直上开窗栊。翠峦廿九纷窈窕,溪流十八交冲瀜。朝烟暮霭各萦带,阳岩阴谷殊茏葱。”[26]220“高阁”“翠峦”“溪流”“烟霭”等意象均具江南风景的底色,但都笼罩在“阑风伏雨天濛濛”中,引起王昶共鸣的是对杨慎“穷荒窜谪尚嗜古”的同情。桂馥则有“巉岩万仞走羊肠,蜀道何曾似永昌”“水田插稻春求雨,野火烧山夜照楼”。[27〗623稻田干涸无雨,耕作的野火照亮阁楼,与江南的生产方式差异极大。《永平》诗写道:“边地山城小,衙斋古寺荒。苍苔缘榻上,怪鸟向人狂。箐谷夷獠杂,阴晴气候凉。不知家万里,夜梦理归装。”[27]623永平是桂馥外放任职之地,城里的“雅斋”“古寺”都已荒芜,目之所及乃“怪鸟”“夷獠”景象,毫无江南人文特征。《行县罢独坐口占》曰:“陋甚永平县,官闲且放歌。城荒烟戸少,泉近稻畦多。囹圄生榛莽,衙斋引薜萝。无书慰岑寂,岁月易蹉跎。”[27]623永平虽“泉近稻畦多”,但桂馥以“陋甚”形容之。“榛莽”“薜萝”“荒城”“户少”是景物的主调,他说:“仆来云南求友无人,借书不得。日与蛮獠杂处,发一言谁赏,举一事谁赏。此中郁郁,惟酒能销之耳。”[28]孤独的困境使他反问自己:“来何为?远投万里之边陲。”[27]623
有趣的是,阮元也有《宿永昌池馆,流泉树石湛然清华,名之曰小兰津,并诗示镇府诸公》诗。诗曰:“莫言传舍为他人,汉郡无如此最真。勒石先题古柳貌,引泉应号小兰津。”[4]705他不仅看到“流泉树石湛然清华”和山水相济的“小兰津”,给人以江南景貌之感,而且还说“汉郡无如此最真”,肯定了永昌的历史文化底蕴。另如:“春月竟是山中多,百夷安乐春气和。蛮花飞落山村坡,儿女吹笙跳月歌。”[4]701其笔下的蛮夷安闲和乐、载歌载舞,景物则春气畅和,是另一番具有江南文明之征的景色。
(二)江南意象:阮元江南视角下的心景交流
胡晓明认为:“‘江南’作为文化区域,它的重要基石是自然与民俗,大家公认其最大的自然民俗特色,即‘水乡’。无论江苏、浙江、安徽,甚至中国其他地方,只要有水乡特色的地方,即是‘江南’。”[20]70-71因此,水乡意象是江南地域文学典型的文化符号,而江南生活经验是江南文学意象形成的原因。阮元是成长于扬州的江南文人,江南文化的熏陶形塑了他的审美思维、文学趣味、美学观念等。由于江南审美、记忆和身份意识的融入,其滇南景物的书写从物象选择、意象呈现等层面,都密集地呈现出江南文学的特征。
阮元身在滇南,满眼所见却是江南物象。他常将滇南与江南置于同一维度,以江南经验观察滇南景物,思绪亦常穿梭于江南与滇南之间。丁亥年(1827),阮元在滇南近华浦立石柱测量滇池水位,作诗曰:“浦前刻碣题名处,远想焦山瘗鹤铭。”[4]708东去的流水成为连系滇南与江南的情感纽带。在江南审美与视角的作用下,其滇南景物具有了江南化的特征。《同李文园学使棠阶游太华山憩太华寺》最能展现他的江南化期待视野和文学思维:
寺南启虚堂,万顷何茫然。浩浩天外浪,棱棱草际田。双塔变远郭,片舫识渔船。山外壁更峭,方削不肯圆。搔首或落雁,登顶难采莲。[4]707
诗中有空寂的寺庙、浩荡万顷的湖水、长满野草的稻田以及城郭、双塔、远山、渔船等文学意象。当诗中出现此类意象词群时,读者就会联想到江南的风光。诗中阮元的思维也跳跃于滇南与江南之间。山川、湖水、归帆、古塔以及“采莲”这些文学意象的使用,让滇南与江南的景物变得何其相似。虽然“方削不肯圆”的山外峭壁使阮元感叹“登顶难采莲”,但并不影响他的江南化构图思维。阮元还有“我家贯月船,千里凌沧江。船不到滇池,山房抵小艭。明月随我来,夜夜贯入窗。窗西曲池水,印月得一双”,[4]708诗的想象逻辑与前诗也极为相似。江南水乡的意象成为书写滇南景观的重要方式,《登西台看耕种》又写道:
平野浸清滇,环城百顷田。喜逢新雨后,刚是种秧前。横笛遥村犊,抽帆小港船。碧鸡山色绿,低与稻畴连。[4]708
“平野”“秧田”“新雨”“横笛”“村犊”“帆船”“稻畴”等都是江南式的文学意象,描绘出江南独特的田园风光与劳作环境。
阮元还有滇南纯自然景物的书写:“瘦鹤长随步,幽禽各占窝。引飞新燕子,乱叫野鹦歌。苋染胭脂饭,蚕收栗茧蛾。”[4]708“瘦鹤”“幽禽”“燕子”“野鹦”“茧蛾”等意象亦极有江南特色。他将滇南绿意盎然、草木繁盛的环境以及燕子、野鹦鸣飞的欣欣向荣之景展现在读者眼前,俨然进入江南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的光景。另外还有“风里笋稍抽笔直,雨余荷盖泻珠摇”,[4]712“雨”“荷”“珠”意象让人联想到江南雨过天晴,万顷荷叶上摇滚着玲珑剔透的水珠。
阮元又说“滇南二月初三日,颇似江南上巳天”,[4]707两地不仅有自然景色的相似,还有社会文化的趋近。“穿城为渠塘,灌田做沟浍。家家可流觞,处处响水碓。”[4]704诗写大理城及附近的景观,曲折的流水穿过城市,到处是“水碓”的声音,不仅让人想到江南的生产方式,更让人遥想江南文人曲水流觞的场面。丁亥年(1827)上巳,阮元在东川道阅兵,面对眼前的山川河流,他说:“若把此川当曲水,一觞流去是巫峰。”[4]701从曲折回环的江水联想到江南的曲水流觞,将江南的文化心理、精神投射于滇南景物,使滇南景物、意象具有了江南色彩。
作为来自江南的士人,以江南视角书写滇南景物是江南文化自信的表达,因此他多有“万里西南地,人间别有天”[4]712“不是春秋亦佳日,别有天地非人间”[4]709“家乡事事皆堪意,唯有群花比不如”[4]706的说法。另外,阮元作为云贵总督,在景物书写中有“今日升平同在此,一池秋水十分春”,融入了强烈的疆臣颂圣意识。赵翼、王昶、桂馥三人所览,其实也有“稻田”“寺塔”“翠峦”“溪流”“烟霭”等江南式物象,但他们的诗歌构图却不以江南景观为蓝本,最终呈现出蛮荒瘴疠之象。而赵翼因“短衣匹马出入蛮烟瘴雨中”;[25]2王昶作为戴罪之人入滇而“心如死灰,身如槁木”,[26]340他说:“怨天尤人之念尚不以萌于心,矧弄笔墨骋奇怪,与文士争名誉,其不敢也审矣。”[26]336内心自省使他无意流连光景。清缅战争是清朝历史上最惨烈的边疆战争。[29]异常的气候、艰辛的行军、死亡的威胁,直接影响着赵翼对滇南景物的感受。王昶也说:“盖南方卑湿,炎瘴不以时,故虽英伟特绝之人,久处其地亦卒,不能慷慨如常。”[26]410桂馥则“以不世才擢甲科,名震天下,与青藤殊矣,然而远官天末”。[30]由于焦虑的情绪,他们的滇南景物书写多是“蛮荒”之景,而难有安静祥和的江南世界。他们的书写角度、话语依然继承了前人,而阮元则作出了巨大改变。江南化的书写策略,将滇南景物与江南景物作类比,客观上为当地士人书写乡邦文化提供了另一套话语,除了“蛮烟瘴雨”“万里荒服”,多了“人文江南”的书写维度,为滇南文人建构乡邦文化奠定了新的空间与思路,加快了滇南从蛮荒到人文江南的文学书写转换。
四、滇南历史文化渊源的发现
滇南作为移民省份,文化渊源与江南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清乾隆间吴大勋记载:“滇本夷地,并无汉人……至今城市中皆汉人,山谷荒野中皆夷人,反客为主,竟成乐国。”[31]道光《普洱府志》亦载:“国初改土设流,由临元分拨新习营官兵驻守,并江右黔、楚、川、陕各省贸易客民家于斯焉。于是人烟稠密,田土渐开,户习诗书,士敦礼让,日蒸月化,骎骎乎具有华风。”[32]清代滇南移民虽来自四方,但江南文化对滇南的塑造最为深远。正如杨文定所言,“硐民皆五方无业之人”,[33]作为从事矿业等下层移民,对滇南的文化发展影响有限,而来自江南的仕宦群体更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据统计,清代滇南“146位督抚中,有68位曾在发达的江南地区任过职,占到总人数的46%”。[34]他们通过捐修庙观书院、建造亭台轩榭等,将江南审美观念在滇南付诸实践,对滇南景观进行了江南化塑造。因此,史书也多将滇南文化的发展归因于江南人。万历《云南通志》记载,滇南的“宦戍者多大江东南人,熏陶渐染,彬彬文献”。[35]隆庆《楚雄府志》载:“洪武初,徙江南闾右以实之,渐摩既久,旧俗丕变,埒于中州。冠婚丧祭,多用古礼,服食器用,雅有江南风。”[36]《滇略》载:“高皇帝既定滇中,尽迁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37]雍正《云南通志》载:“永昌故哀牢国也,国初流配独多吴人,语言风俗宛似南都。”[1]35由于大量移民外加江南仕宦群体的倡导,清代滇南的文化根基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其实是阮元以“江南化”书写滇南景物的隐形逻辑与社会基础。
另外,由于清代版图的急速扩张,时人的地理观念也在发生巨变。有学者认为清代官方“一方面通过修订图籍,包括方志、舆图、图册等直接反映地理概念变化的文本,重新构建地理知识体系,以确立和显示其统治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通过确立地域分界标志,划定内地、边地与域外之间的界线,并针对不同区域实行特殊的统治政策,其结果是改变了清代士人的地理认知和边地观”。[38]因此,在官方与士人观念中,清代滇南正从边疆转为内地。《滇系》载:“迁富民以实滇,于是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39]滇南土著的“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实际上是滇南士人政治、社会身份认同“内地化”的现象。阮元作为经史考据学人和主持学术风尚学者,又在任职总督期间撰修了道光《云南通志》,必然对滇南文化渊源与历史叙述话语谙熟于心。因此,江南化的景物书写,实际上还具有在学术上重构地理观念、在政治上回应滇南边疆治理的“海晏河清”,对国家与自己的边疆治理作出肯定的意图,当然也是对清中期滇南士人“学术、文章、经济埒于中邦”[40]的“去蛮荒”与“内地化”的话语承接与回应。
总之,阮元发掘、塑造滇中“江南”,是彼时阮元从精神上返回江南世界的有效途径。其本质是在江南文化精神、审美观念的主导下,以江南地域文化作为审美标准,对滇南山川景色作“江南式”的“书写重构”。它是江南文人惯有的审美思维与经验的表达,彰显了江南地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客观上改变了边疆景物书写的话语传统。同时,将边疆景物书写纳入江南文化系统,是阮元对清代官方与士人的政治、地理观念变化的具体诠释,体现了他对清代文化正统观念的理解与文学实践,是清代政治观念、文人身份意识相互作用在文学领域的表现。“江南化”揭示了清代文学在边疆书写中的内在逻辑和情感思路。
注释:
①姜海鱼等人认为,窗牖作为“园林中的衍生物”通过符号象征人文精神理念。参见《从古代诗意化情境看园林窗牖的演绎》,《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②题词收录于黄泽德《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园暨题咏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③王青认为江南文学“有三个典型意象值得我们重视:第一是南方清秀委婉、妩媚多情的女子,第二就是江南吴地独特的生产方式——‘采莲’……第三就是由文人亲自发现并体认的山水田园美景”。参见《唐前历史地理与诗歌地理中的江南》,《阅江学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