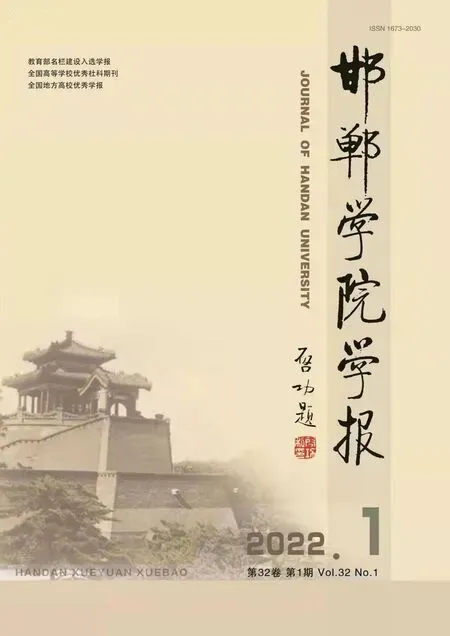“诚”的审美维度
梅涵
(河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一、纯粹至善与纯粹美学
(一)诚之本体——澄明本性
在中国古典美学领域,对于真和自然的纯粹审美一直从未停止,人们往往在审美的过程中以天然去雕饰的真实和纯粹为审美标准去判断客体是否具有美的因素,而《中庸》中的“诚”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发生学上后来从外界逐步获取的,而是本身就有,存于自性之中的。从本体来看,“诚”是本真,其本体不添加任何杂糅,是万物所呈现形态的本来面目,“诚”的本性是质朴与纯真,践行它的过程亦是还原本来无其它异质成分的真我。朱熹释“诚”为:“诚,实也。”[1]5又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1]5周敦颐释“诚”为“纯粹至善者也。”[2]5“真实无妄”意为真实无谬,无妄动则是诚之本性纯然,“本然”也就是天所固有的“理”之本然,即“诚”在本体上是纯正无二的。“纯粹至善”即纯净无染,“诚”作为一种纯粹本真而存在,这种“真实”与“无妄”都是对“诚”的价值肯定。从纯粹美学的角度来看,“纯粹”即是不考虑其他影响审美判断的因素,而要想判断事物的美丑,必不可绕开的就是美感,故这种纯粹即是只涉及美感由来的自身,而不掺杂其他成分,如审美主体的背景、认知、审美能力等等。“诚”从本体上来说,就是人的本性与本心,是原本就有、初始存在的审美自明域,是至澄明又无所遮蔽的存在,常人要做的就是复其“澄明”。因此,“诚”本身就是纯粹真实的,其所带来的美感也纯正无他物,是依靠人的直觉就能体悟到的。从万物存有来看,“诚”作为人的本然之心、性与西方纯粹美学将美终极存在实体化既相关又有其不同,《中庸》中“诚”之道最可贵的在于其化“诚”为万有本来基,“诚”作为本体本身比西方纯粹美学的终极存在实体更具超越意义。
(二)体诚过程——情感安和
此外,中国美学中“诚”的纯粹不仅体现在审美对象本身,还在审美过程中有所显现,人达到“至诚”的过程就是一个获取美感的愉悦过程,即存在着一个完全纯粹的追求宇宙本来面目的过程,在此审美过程中只存在着主体和“诚”,二者形成了纯一无杂的审美空间,通过不动别心的审美方式,继而对自己和宇宙的本相得到更纯粹的认识。“一个不受刺激和激动的任何影响、因而只以形式的合目的性作为规定根据的鉴赏判断,就是一个纯粹鉴赏判断。”[3]59诚作为实现天人沟通的存在,其本身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体“诚”、践“诚”时做到不动心,以自然而然的流动性向诚靠拢,这固然是一个积极的靠近过程,但却不必使我们的本心扰乱受到刺激或影响。在体悟“诚”、践行“诚”的这个过程,我们的情感是安和的,我们的审美判断是不受干扰的,我们既保持了本体与物自体之间绝对纯粹的关系,同时在整个对“诚”追求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消解。西方的“纯粹美学”认为主客二分的实存结构是由自我审美决定和建构的,一旦以功利的态度去审美,美感就会因加入其他可量化的因素而遭受破坏,美就变得不够纯粹,且他们认为在对审美对象进行鉴赏时主体性思维是无法避免被功利等其他念头所干涉的,因此主张无主体性思维,纯粹的审美才能呈现。与此不同的是,“诚”作为沟通道体与性命的存在,有将个体修养功夫论与天命同一的价值作用,中国哲学并不否认主体思维的存在,而是积极利用人的生命意识去体验美感,并在此审美意境中,人与物不执着恢复本身的功利之欲,实现真正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纯粹审美契合。
二、道德审美——“诚”的心性美学
无论是中国美学还是西方美学,对道德都是推崇的,想要判定该事物是美的,不免要追溯它是善的、合乎道德的,尤其是中国儒家美学中极其重视的德性境界,道德对于整个中国哲学审美境界的塑造和意蕴的崇高都起着支撑作用。与其说将道德与美学相结合,不如直接以“美德”代之。在人的审美过程中,我们不免先验地带有个人的情感和主观道德判断,我们总是不由自主的运用个人的道德标准做价值取向判定。一件事是否是美的常常与它是否具有德性或与引起个体道德情感的生发和显现有关。“诚”所代表的道德审美分为两种意义上的善,其一乃境界之善,其二乃人格之善。
(一)境界之善——生生美德
对美的追求,实质上也可认为是一种精神追求,此种精神追求可到达圆善大美的境界与境相,是存于人心的意境。康德明确提出“美是德性-善的象征”[3]200,纵观整个康德的哲学思想体系,不难看出道德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审美的目的最终要服务于道德,对于审美而言,道德化境似乎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儒家的“仁”可使我们感受到真切的体人爱人之情感,道家的“道”怀有对万物生而不恃的母性美德,因此审美主体往往会判定这些是美的。而“诚”亦怀有生生之美德,《中庸》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1]32不明白善也就无法做到“诚”道,它以真实、真诚、圆满的善而存在,周敦颐释“诚”为“纯粹至善者也。”[2]31诚是真实无妄的至善,它所呈现的是生养万物的上善尽美,圣人不需格外用力是因为他已和天道之诚同一,而其他人必须通过自反“择善而固执”,达到了“诚”也就具有了既真实又本心澄静的德性继而化为至善。此“善”可分为两种意义上的善,其中除了易被察识省发的人性善还有境界之善,即“上德”与“大德”,“诚”贯穿天道下落为人之性,使人的生命具有活动性,不至于凝滞,也给予了人之向善的可能性。
从“诚”使人向善的可能性所建构的空间意义上来说,“诚”的这种德性充斥着整个宇宙。鲍姆嘉通曾说“美学是感性学”,这种感性不再是单纯的逻辑理性,包括着情感的涌出,也就是强调在审美时要进行的感情流通。中国哲学特别强调万物一体,体仁之情,“诚”在感性的情感中生发又在由情所生的境中壮大,这是终极大道之善。从横贯来说,“诚”使人能够有道德情感善意的显发与生命万物相感通,以纵贯来说,“诚”将宇宙之善与人之善相接续,使人具备道德心,践行道德意义上的审美可能。“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1]32“择善”本身就有导向人向善向美的正向作用,是主体对美的积极感发。这强调的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诚”与“善”的建构使“诚”真正具有生命意识,对美好德性的追寻就是审美的历程。西方美学家费希特重视审美活动对人类的发展意义,谈及艺术的本质与特征时曾认为任何艺术品是艺术家“内在心境”或“内在情绪”的表现,是“自由精神创造”的结果,主张艺术摆脱桎梏,培养美德。其“内在心境”正与中国所言“境界”有所相通,而在这种“诚”所引导的内在心境中,主体会塑造善的精神境界,启发审美主体的善之意识,并使其施行善行,实现终极道德的挺立,还可循循善诱教化人按照道德意志的方向前进,在时空结构上完善和发展富有生命力的生生之境。
(二)人格之善——成性修养
“诚”作为境界层面的衍生善之本体,还可紧密与人的性命相关联,落实在现实的成性修养论美学思想上,可为人生论美学内容。《中庸》将“诚”作为天道贯彻人道所落实之处,审美主体通过对“诚”至善至美理念的追求,以正向积极之方向为导引,引人向善,将会自然实现道德与人性的连接,在审美的过程中体验“诚”的美德,可以说,实现诚、体验诚这一维度所带来的美感时,在这种审美环境中以诚为目的,以诚为人格善本身就是向善的修养过程。从苏格拉底将道德的问题与美学的问题结合起来,道德承载的美学也逐渐走入了西方美学的视野,舍夫茨别利认为美善同一,主张人天生有道德和美感,即人既有自爱之自我情感亦有仁爱之天然情感。歌德:“艺术应该是自然的东西的道德表现。”[4]419可见从西方美学来看,美与德性的修习也是难解难分的存在,伴随着人对道德的修炼与践行,人的审美境界和对美感的敏锐程度亦会得到提升。钱穆先生认为:“人生大义尽在此矣。则中国之道德人生,亦即是艺术人生。”[5]138在中国美学中,道德与艺术与美是分不开的,也象征着“诚”与“善”的关系是不容分割的。《周易》对修养“诚”的方法进行明确:“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之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2]40“诚”是包括了仁、义、礼、智等天下所有德行的源起所在,是落实于现实人的具体道德规范准则。强调在做到“君子终日乾乾,夕惿若厉”的勤奋以立诚的状态的同时,还必须自觉平息心中怒意,抑制欲望的出现,才能够实现“诚”,由自诚到至诚,人可通过自己的“自诚明”实现自我修养教化,对“诚”的修养过程就是对心性美学的现实践履。
三、诚之圆融与中和美
儒家美学摄取了佛教“圆融义”,并继而发扬为圆融大化之美,其内在结构又渗透着中和思想,“中和”以中为基础,以和为大用,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中道的思想,譬如勇敢处于怯懦和鲁莽之间。朱良志先生认为:“儒家哲学中的中和思想有三个要点:一是中体和用。从哲学基础上看,儒家和谐美学思想当以‘中和’二字为要。中是其体,和是其用。本立而道生。”[6]307即是说以“中”为前提,才能实现“和”。“中”与“和”不可分割,在圆融的状态下共同传达和谐的美的理念。
(一)圆融美
与西方引人悲壮崇高的壮美不同,中国之圆融美包含着对世界的怜悯、生命的通达,是人与所处境界和解之美,可以说西方更偏向与力的抗争,中国主内在调和,这种调和出于圆融并包的美学思想。从佛教语义来看,圆融指圆满融通,无所障碍,即圆融通达的境界形态。如果以分别的妄见来观之,那么宇宙万有,千差万别,是光怪陆离的;如果以世间存有的普遍本具之性来说,那么宇宙间一切事、理、法都融通无碍,是原初的一,是无二的一体,如同水与涟漪,皆源于同一粒种子。“诚”作为周敦颐立论的形上之源,其圆融无碍性为其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找到了根据,而此种“无碍性”可体现为沟通、交感的通达。
1.无二无别义
“诚”作为使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交感的媒介,使人与宇宙万有得以存在感应的可能性,赋予人在审美过程中达成与审美对象混同为一的能力,这种无二无别的境界并不意在消融彼此之对立,而是于此间找寻两者的本质契合,形成圆融的一。“感应美学以审美感应为核心,辩证地解决了审美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认为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美,都是自然与人、物与心、客观与主观交互感应、融合统一的产物。”[7]438“诚”之发用不仅使外物与内心合一,还克服了审美意识与审美经验的不对等,形成统一的契合。“在对美的对象进行审美的观照之中,我感到精力旺盛,轻松自由。但是我感到这些,并不是面对着对象或和对象对立,而是自已就在对象里面。审美的移情作用须与对象打成一片,就活在对象里,我才能在审美中欣赏和感受特有的那种喜悦。”[4]596正如立普斯所论说的移情作用,实现主客体感应时是双感的模式,主体将自己真切情感投射在审美对象上,自我对他者的言说就形成了审美的自我观照。在对“诚”审美时,我们的行为与意识会自觉地向“诚”所代表的天理法则和境界靠拢,“诚”是具有生命的自体,对人的思想行动具有感知性与指导性,令看似并不相通的二物通过情感的互动沟通实现感通,在相互靠近的进程中圆融合为一体,实现外部与内部的协同、外化与内化的统一,形成无差别的精神世界。
2.包涵义
圆即周遍,融即融通。佛教所讲的圆融义涉及到空间性质,《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也。”[1]34“诚”在《中庸》中是一个挺立于天地之间,含有宇宙万有本体在内的存在。无论是《中庸》中的“衍化生命之诚”,还是周敦颐将《易传》中的“诚”提炼出来所形成的人极“诚”,“诚”都是将立体空间引入人身的道体,都涵摄万物。太极是从无极这种混沌的状态中演化而来的,处于混沌状态下的无极加之阴阳五行便可圆融化为宇宙万物,而无极与诚体又是同质的,禀一体气之流行,故“诚”即太极化而为圆融万物的实体。
“诚”不仅承接道体又能下贯人极,这种涵摄体现了中国美学上反复强调的无界性美、“太和”之美,美在于其至大与无所不包,而周敦颐从本体论意义上肯定了“诚”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取消了“诚”的物质性,改为无形象的恍惚。“诚”既像一粒宇宙最小的种子引发一系列万物的生长,又似终极的混沌本体,而人的生命也随着对于真理、“诚”的探索形成一个永恒的体验过程。“诚”本就意味着无穷,这种无穷并不仅仅指其包含的内容无穷,还存在于本身运行的过程中,在这种审美过程中实现了生命的感通。此外,生命意在流转,意在涵摄圆融,从“诚”对人类生命及思维的构造来看,从宏大视角的宇宙到微观的人自身内在,都存有一个不为我们直接感知却又具体存在的“诚”的境界,乃至最后又汇聚成一个无所不包的“至诚”。
(二)中和美——“中”为前提,“和”为大用
1.以中为本
“诚”是天道与性命之间的一道桥梁,可以说没有“诚”的建构,天道与人的性命往往会被分割成为两个互不交流、无法感通的范畴。值得一提的是,朱良志先生明确:“中节合度。执中守一,不是二物相对而取其中者,而是扣其两端,不过也不及。”[6]309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美学对于审美对象的调和是一种内在生命的和谐境界。“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就是和谐,……他们认为万物最基本的原素是数,数的原则统治宇宙中一切现象。”[4]32故其将美的事物以数字比附,其审美视角不免以数字的比例为标准。以至后来的圣奧古斯丁也受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认为现实世界是上帝按照数学原则所创造,故而才显出和谐与秩序,他说:“数以等同和类似而美,数与秩序不可分。”[4]32这是一种典型的形式和谐美学。倘若以数量原则作为和谐美的判定,《周易》作为中国哲学史上较早带有数字逻辑思维的哲学原典,其中不仅体现了“诚”的思想,亦将“诚”与天地人三才建立联系,形成推演的体系结构。周易每一卦的六爻中,蕴含着三种数的模型,《周易·系辞上》:“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8]262上爻五爻为天;三爻四爻为人;二爻初爻为地。以乾卦为例,乾卦所论乃闲邪存诚,《文言》:“九三,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9]13将“诚”作为三爻中位,处于数字之中,相当于人道,处于上爻、五爻代表的天及二爻、初爻象征的地之间。但以西方哲学视角观之,和谐是从数量关系的比例上来说,偏向于经验层面的一种硬性和谐。但美的判定似乎不能以如此简单的逻辑进行推论,不同于将“中”理解为硬性的对立之中心,中国美学认为这是对“中”的理解偏差亦或未达“中”的终极本源,“中”是人心与现实的中间环节,真正的中道是软性的感通与调和,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66而除了上文以数字的形式和谐解“诚”之美,“诚”还是最能代表中国和谐美的审美范畴之一,无论是西方物理还是中国情理,“诚”在两个层次都实现了和谐之美。以“诚”为鉴,“诚”之中和美以守中道为前提,以天人之和与个体性灵之和为用,形成圆满的中和之美。
2.以和为用
对于和谐,西方美学家阿尔伯蒂曾说过:“美是所有部分之间的和谐,各部分和它的存在于中的整体是那样吻合无间,以至减去一分或添加一分,就会毁了整个对象。美是事物各部分间的一种协调和相互作用。这协调是通过和谐所要求的特定的数、特定的比例和安排实现的,而和谐是自然的基本原则所在。”[10]75显然,其美学观点仍然偏于数字的比例有序,属外在的结构形式。中国美学主内在调和,“和”是在事物之间的相互对待关系上之协调与和谐,此种和谐是天与人的交际和谐,理想与现实的协调和谐,存在与存在者的和谐,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自然互动,儒家美学所追求的不似老庄之超脱,不似佛家之空灵,而是在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境遇之下所试图作出的调和之美。“诚”也被提升到超拔于现实的主体上来,实现此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统一的途径。这种积极的审美观表现在“诚”上就是一种天人之间的平衡,对人的精神境界起到调节中和之功能。《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32诚是天运行的道理,追求诚亦是人的行为准则,求“诚”的过程不仅是对“诚”的审美过程还是人与宇宙自然之间愈发和谐亲密的过程,可圆满达成人的外在与内在,实现“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牟宗三先生释“诚”为“诚体”,正因为他把“诚”看作真实的存在,并能为人所感,审美尤其在于对生命的积极体悟,万物一体的体万物之情的感通。通过“诚”的“和”的作用,使人既上达天命,更好地运用天命,又赋予人沟通万物、体察万物的能力,与人和生命体和谐共存。这种调和可以理解为情感意义上的调和与协理,中国哲学向来重视生命向度与情感的发微,情感过于收敛致情无法流通,情感过于外放难免粗野,达到适度的控制是“诚”道所在。
四、崇高之美与以小见大
西方美学思想常以高大的崇高为美,中国人常不以物理状态定义美,往往是超脱的,超越现实又不完全脱离现实的心灵精神状态。朱良志先生说:“小,是外在的物,大,是内在的心。”[6]221朱先生认为,中国人认识到了这个“小”,透过概念之形,观照内在的心,心可超越,可飞腾。正如朱先生所言,中国人善于从点到面,超越至整个宇宙,具有俯仰乾坤的“大化”之美。“诚”之美以概念为凝聚,又可依托心之发用展开,渗透宇宙万有,是“大化”之美的典型。
(一)崇高之美——精神感召
朗吉弩斯第一次将“崇高”作为美学范畴进行研究,并创立了最早的“崇高说”。他认为在“崇高”的五个来源中庄严伟大的思想是最重要的,“大自然把人放到宇宙生命会场里,不仅让人欣赏宇宙壮观,更重要的是参与其中竞赛,在这之中实现伟大人格的挺立。”[4]112他还以小溪与海洋做对比,突出对人类尊严进行颂扬,来自人类原始力量的自尊也正是“崇高”所在。其中康德所说的小溪和海洋所代表的“数量的”与人的尊严所表示的“力量的”两种崇高在这里体现。”康德将力量的崇高局限于自然界,认为这是恐惧的对象又同时引起自己有足够抵抗力而不受它支配。”[4]370中国美学也有此种崇高之美的发迹,其一,“诚”作为本体有崇高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化。”[1]34化于万物的功能常只有超自然的存在才可具备,例如西方上帝等权威,而只有达到“至诚”才可做到化育万物,“诚”是以信仰凝结而成的美的理念,可见“诚”是最高本体,是存在者之存在,即超验之存有,具有崇高性。其二,“诚”之美还在于其以审美个体内心的尊崇为前提,而不依靠外力的威严和超越的力量进行强制与压迫,使人们感到惧怕和妥协。“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1]39只有到达至诚之境,才可创造周行于天下的法规,才有立足世界的根本规律,掌握天地万物化生之法,在此审美境界中,人既可以崇拜“诚”的原始力量,又可以依靠自己德性的培养去继承、延续这种神圣的能量本身,此间自然生发人的崇拜。“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2]32“诚”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本源,也是提升自我尊严与自我力量的根源所在,故欲至圣人境界,就要进行“诚”的修养。“诚”作为万物肇始,既是创生万物最高的存在又是人道德实践的具体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就要求我们激发自尊的内在力量,实现“诚”意味着人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有达到“至诚”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往往来自于我们的尊严等情感,并且“修诚”的过程又可激发人的无穷潜力,提高自我力量的同时又由衷为“诚”的德性而感到钦佩,如此,向着“诚”的强大精神动力之感召而行,实现人的心悦而诚服。
(二)以小见大——意蕴与时空的绵延
1.意蕴之深厚
崇高之美往往以西方美学观点对审美对象进行判断,而中国古典美学擅长以小见大的美学思维,以看似渺小实则无穷的物体作为审美对象进行“大化”处理。“诚”似“小”而实“大”,宇宙万物的生存之道,运行之理,仅用一个“诚”字就可以概括完全,并且其生成万物的实际价值是不可衡量的。其一,以美的理念来看,“诚”日用于彝论,可具体体现为诚信、诚实等具象观念,以宏大视角为基则可发见于诚心、天理的形上最高本体,成为凝聚的理念。“诚”之美体现的是物理现实与心灵境界的关系,故“诚”的法则是广博深厚、悠远而长久的。其二,从其所摄内容的超越性来看,《中庸》:“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甲,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1]35虽天以“小”观之只如微光,可以“大”观之,它却维系日月星辰的运转,覆盖世间万物的生长。地亦如此,以“小”观之,仅区区一撮土,可以“大”观之,却足以承载崇山峻岭,容纳江河湖海。“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32“诚”与天地同质,以“小”观之,在人格修养功夫论之上,是人进行道德实践的规范准则。以“大”观之,则是使人足以获得精神自由的浩瀚存在,是天理流行的内在依据,因其创生万物,故可上达天道,与天命紧密结合。因此,“诚”包含形上与形下两方面内容,是渗透于生命体运行之道的实体,具有不被认识的知性,蕴藏无穷价值,足以使人俯仰天地,察识万物奥秘。
2.时空之自由
审美的以小见大不仅体现在其本身至大的内涵之中,还在于其超越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诚”的时效性是无限的,其美感在于它是充分延伸展开的,在其审美的规定性中赋有自由意识。“故至诚无息中。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1]35“至诚”的道理和法则的运行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既然其是无止息的,那么必然会保持长久,以至于表现出悠久长远,继而广博浩大的特性。因此,“诚”就可以完全的承载万物生命、覆盖万物资始、成就万物化育。“诚”所表现出的境界就是无休止的永无止境的活动与运行,达到这样的境界,审美距离就会被延伸。如此,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壁垒达成“自由境”,而在此“境”里,人能够对生命有积极体悟,超越现实之功利,开发出最大的精神自由,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通过这种自由的审美达到“自失”,即物我两忘、主客体合一的境界,追求“诚”的历程看似是主体丧失于对象之中,实际上却是主体把客体摄入自身,达到自我与他者相和的自由之境。“诚”发展人的自由,培养人对自由感的需要,通过对“诚”等超自然事物参与而自由,又通过对自由的践履,实现自我遮蔽的解放,由解蔽达到无蔽状态。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美学之“诚”的四重维度相互补充,无论是在过去还是未来,无论处于西方美学还是中国美学,“诚”都是美学界中值得探究的一个范畴。而以中西双向审美视野对“诚”进行美学思想的分析,可使“诚”的美学思想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当下我们依然可以结合新时代所产生的问题对“诚”蕴含的美学思想进行阐发,与时俱进,从新的向度发掘其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