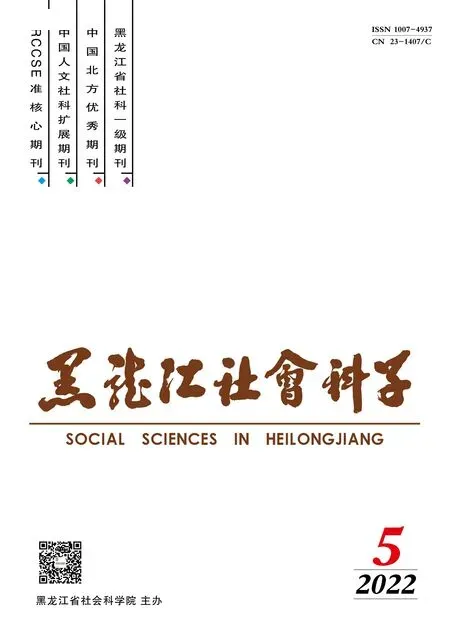辽朝菩萨信仰研究
鞠 贺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菩萨信仰是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辽人所造佛塔及佛像可知,辽朝菩萨信仰的对象为《八大菩萨曼荼罗经》中的文殊、普贤、观世音、金刚手、虚空藏、地藏、弥勒和除盖障这八大菩萨[1]。以上八大菩萨的形象虽常集中组合出现,但每位菩萨信仰的流行程度却不尽相同。其中,观音信仰是辽人菩萨信仰体系中较早受到学界关注的一个领域,但关于观音信仰的类型以及其他菩萨信仰的情况尚存在进一步的讨论空间[2][3][1]。故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对辽朝菩萨信仰情况进行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斧正。
一、观音菩萨信仰
在辽朝菩萨信仰中,对观音的信仰最为流行。景宗长女名为“观音奴”[4]1326,懿德皇后“小字观音”[4]1326;辽道宗继承妙行大师铸造“等身观音”的遗愿,并为此出资:“有司计其物直三万余贯,□库公给。像成之日,铜货有余”(《妙行大师行状碑》)[5]588,均可见一斑。从类型来讲,观音信仰可分为救难型、净土型、智慧型和密教型四大类[6]。而辽朝的观音信仰除具备以上四种类型外,还存在一种独具特色的信仰形态,即融合皇室家神崇拜与观音信仰的家神—观音信仰。
(一)家神—观音信仰
史载天显十年(935),太宗曾因为其皇后饭僧而游幸延福寺,过程中“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4]39。这表明太祖一家曾在延福寺施舍观音画像,可见太祖一家对观音的崇奉。及至太宗时期,观音信仰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史载:“兴王寺,有白衣观音像。太宗援石晋主中国,自潞州回,入幽州,幸大悲阁,指此像曰:‘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兴军必告之。”[4]504至此,辽朝皇室的家神—观音信仰开始出现,对家神—观音的供奉也成了辽朝礼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史载太宗“于拜山仪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非胡剌可汗之故也”[4]。而崇佛皇帝兴宗在位时,通过对拜山仪程序的调整,进一步提升了家神—观音的地位。史载:“兴宗先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然后行拜山仪。”[4]929
可见,在辽朝家神—观音有着崇高的地位。而出于虔诚的信仰,辽朝皇室对家神—观音会进行定期和不定期供奉:定期供奉,在春秋两季;不定期供奉,表现在军事行动前,会有“告白衣观音”之举。正如学者所言,太宗通过塑造家神—观音的护家、护国形象,成功实现了其父太祖化家为国、化祖为神的政治愿望[7]。
(二)救难观音信仰
在出土的辽朝碑刻中,《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反映出救难观音信仰在当时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其中有四首诗宣扬了观音的救难属性,此处不妨列举两例。开国侯刘瑰赞颂观音:“绍名早授昔师记,救苦分临末世来”[5]503;翰林学士马元俊则云:“潜救众生苦恼去,默传诸佛印心来。”[5]502
有学者指出,辽朝的观音信仰之所以能够兴盛一时,主要原因在于救难系观音经典的流布[2]。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其对观音救苦救难的慈悲属性作出了宣传。如:“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8]其宣扬只要“念彼观音力”就可以得到观音的救度,对于佛教信徒显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此外,《法华经》流行于辽朝,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则是《法华经》中的一部分,从而也促进了其的传播。石刻资料显示,在辽朝有专修《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佛教信徒,如董匡信妻王氏“以清净心日课《上生法花观音品》”(《董匡信及妻王氏墓志》)[5]338。
(三)净土观音信仰
在佛教信仰中,观音为西方三圣之一,胁侍极乐净土阿弥陀佛;《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宣扬观音可“接引众生”[9],往生净土。前引《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中,沙门智化首唱“刻雕数向生前就,接救专期没后来”[5]501,便提出希望能够凭借观音的救度往生净土。净土宗在辽朝后期逐渐崛起,观音身为极乐净土阿弥陀佛的胁侍菩萨,必然会吸引信徒更多的关注。
(四)智慧观音信仰
学者指出,智慧观音信仰依托的主要经典是《心经》,智慧观音信仰就是相信观音具有佛教所宣传的智慧[6]386。《心经》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10]848开篇,言简意赅地阐述了佛教的主要思想。统和十年(992)建于清水院的经幢上刻写有《心经》,并附有276个人名,即应为信奉智慧观音者;修建于重熙年间的朝阳北塔塔身也刻有《心经》;而据道宗年间的《沙门法忍再建陀罗尼经幢记》记载,法忍等曾有“镌梵本《波若波罗密多心经》”[5]450之举(另据载,道宗“肇居潜邸,已学梵文”[11],或可推测,在辽朝存在一批懂梵文的信徒)。此外,道宗末年的《寂照大师并门资园湛身铭》有偈云:“四大本来空,六识悉皆同。身本如泡露,知身不久停。悟空无人我,无心境不侵。如如真无为,便是佛菩提。《般若波罗密多心经》。”[12]234其所宣传的核心思想与《心经》所蕴含的义理高度吻合,尤其是“四大本来空,六识悉皆同”与《心经》中“五蕴皆空”“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10]含义基本相同。又,寿昌五年(1099)张惟景为亡故亲人刻有《心经》[5]497;辽朝末年《韩师训墓志》载韩师训“读《金刚经》、《行愿》、《观音》、《药师》、《多心经》等□不计其数”[12]280;《办集胜事碑》载佛教信徒在举办此次法会过程中曾“诵《多心经》一千二百三十六遍”[12]317。可见智慧观音信仰在辽朝也较为流行。
(五)密教观音信仰
密教观音信仰在辽朝也颇为流行,最具代表性的则为十一面观音信仰。据统和四年《重修独乐寺观音阁碑》记载:“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5]88学者指出,在重修观音阁、重塑观音像的过程中,“景宗皇后回鹘萧氏及其女观音奴都曾与谋其事”[13]。在佛教的宣传中,十一面观音具有退敌的殊胜能力。统和二十二年之前,辽宋之间尚未达成实现和平相处的澶渊之盟,时不时会爆发不同规模的战争。因之,对十一面观音的信仰能够给急于求胜的辽朝统治者以精神慰藉。
《大悲咒》,全称《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是密教观音信仰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一。大安五年(1089)《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载志主“日诵《大悲心咒》以为恒课”[5]413。出身后族并礼朗思孝为师的妙行大师,也将念诵“《大悲心陀罗尼》”作为自己的日课;其迁化前,则令侍立左右者“惟念弥陀”[5]585。又,乾统十年(1110)《宝胜寺前监寺大德遗行记》中载,这位监寺大德“诵《观音》、《弥陀》、《梵行》、《大悲心》、《密多心》等经”[5]603-604。可知,妙行大师与这位监寺大德在持有密教观音信仰的同时,兼持极乐净土信仰。再者,《耿崇美墓志》中则出现人名“大悲奴”[12]83。而在著名的房山石经中,也存在辽人所刻密教观音信仰经典,如大安五年张识等刻《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凡此种种,均可见辽朝的密教观音信仰情况。
在佛教信徒的观念中,观音拥有多种能力:既具有在现世救苦救难的能力,还具有在身后接引信徒往生净土的能力;同时,观音又象征着佛教的最高义理,并且具有护国之力。故而,观音信仰在辽朝有着深厚的信众基础,在各种菩萨信仰中成为主流。
二、弥勒菩萨信仰
弥勒菩萨信仰在辽朝的流行程度仅次于观音菩萨信仰,其所依托的经典之一为《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简称《上生经》。检索出土辽碑,不难发现《上生经》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诵读《上生经》的佛教信徒不在少数,自圣宗时期至辽末天祚帝时期一直存在[14]137。
弥勒菩萨信仰的流行,与弥勒菩萨所具备的未来佛身份有着直接联系:弥勒在兜率净土时,其身份为菩萨,而来至人间主持龙华三会时,其身份为佛。在辽朝,尤其是进入兴宗时期之后,社会中末法观念相当盛行;辽朝人普遍认为,兴宗重熙二十年(1051)是末法时代的起点。有学者指出:“弥勒信仰极度重视‘法’的传承与延续,似乎可以说正是法灭思想的刺激继而产生对弥勒下生的期待”[14]130;“弥勒信仰在辽朝社会影响颇大。弥勒信仰与末法思想密切相关,带有救世主色彩。”[15]在辽朝佛教信徒的观念中,末法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佛法的式微:“末法之代,去圣逾远。沙门则道眼昏昧,檀越则信心寡薄,往往陷于饕餮之者众矣。”(乾统十年《云居寺供塔灯邑碑》)[5]615不过,对当下灰心丧气的同时,也产生了对未来佛的期盼,从而造就了辽朝弥勒菩萨信仰的兴盛局面。
在佛教信徒的观念中,尽管弥勒佛降至人间的时间太过长久,但只要精修佛法,便可在身后往生兜率净土,得遇弥勒菩萨,听其宣讲佛法。相比于未来世的弥勒佛,弥勒菩萨更贴近信徒迫切的精神追求,故而弥勒菩萨信仰在辽朝较为流行。弥勒菩萨信仰的流行与净土信仰也存在密切关系,辽朝佛教信徒对兜率净土的追求,带动了对弥勒菩萨的崇拜[16]。
三、普贤菩萨信仰
辽朝存在普贤菩萨信仰,这从碑刻资料中不难看出。如咸雍八年(1072)《特建葬舍利幢记》载:“传戒大师讳法钧,钟普贤之灵,孕凡夫之体”[5]350;再如辽朝末年《崇昱大师坟塔记》载:崇昱大师“历方度化,踵普贤之先踪”[5]582。而道宗时期僧侣道厄殳在其著作《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中提倡“先悟毗卢法界,后修普贤行海”[17]990,这样的宣传自然会提升普贤菩萨在辽朝的影响力。再者,房山石经中的安次县耿殿直所办《清净观世音菩萨普贤陀罗尼经》,则反映出辽朝密教化的普贤菩萨信仰。
史料所见,在辽朝佛教信徒中,有出于信仰而以“普贤”命名者。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承天太后次子耶律隆庆,其小字“普贤奴”[4]1088;《秦国太妃墓志》载志主诸多孙女中有“普贤女”;于辽末短暂称帝的耶律淳,其妻亦名“普贤女”[4]399。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不同时期普贤菩萨信仰都比较活跃。
四、文殊菩萨信仰
文殊菩萨为“华严三圣”之一,与普贤菩萨同为释迦牟尼佛的胁侍菩萨。崇奉文殊菩萨者,自会礼敬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但五台山并不在辽朝境内,于是辽朝统治者在今河北蔚县虚拟了一处五台山[3]。前文提及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作者题名为“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厄殳”[17]989,而圣宗及其孙道宗都有过游幸金河寺之举:“两朝帝王巡幸该地,反映了辽朝道场特色的文殊信仰的兴旺。”[6]37
史料显示,在辽朝存在以文殊菩萨信仰为主的寺院。世宗曾于天禄年间“施奉福寺文殊真容”[应历七年(957)《承进为荐福大师造幢记》][5]20,后来佛教信徒“就奉福寺文殊殿前,又建经幢”[保宁元年(969)《重移陀罗尼幢记》][5]45。奉福寺的文殊菩萨信仰可见一斑。又崇圣院曾“营理大殿三间,中塑释迦牟尼佛,左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大行普贤菩萨”[应历十年《三盆山崇圣院碑记》][5]30;在山西应县木塔第四层中也有类似的组合:“一骑象,一骑狮子的两尊菩萨,应为普贤与文殊。”[18]
密教化的文殊菩萨信仰在辽朝也较为流行,《办集胜事碑》中有诵“文殊五□真言一千八十遍”[12]317的字样;大安年间《沙门守恩为自身建塔记》记录了守恩诵持《文殊菩萨十吉祥陀罗尼》《文殊一字咒》的情况[5]420。而辽刻房山石经中的《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等也反映了这一情况[5]739。
又,圣宗小字“文殊奴”,其得名当是来自景宗或承天太后,亦或是他人提出,得到二者首肯。从这一点也足见文殊菩萨信仰在辽朝皇室的传布程度。
普贤、文殊二菩萨信仰在辽朝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者释迦牟尼佛胁侍菩萨的身份,而华严宗在辽后期崛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兴宗和道宗均礼敬华严宗高僧,道宗还有关于《华严经》的相关著作。学者指出:“以澄观为代表的华严宗人凭借《华严经》之于五台山文殊道场的经证渊源,提高了文殊在华严义学体系中原本并不突出的地位”,“华严类典籍从佛教义理角度出发推崇代表菩萨行的普贤菩萨。”[19]可见,在华严宗信众的信仰世界中,文殊、普贤二菩萨有着较高地位。其典籍《四十华严》,也即《普贤行愿品》,就是专门介绍普贤菩萨的。此外,在辽朝流布很广的《法华经》中也有宣传普贤菩萨的《普贤菩萨劝发品》,对普贤菩萨信仰的流行亦产生了积极影响。
五、地藏菩萨信仰
在汉传佛教四大菩萨中,地藏菩萨在辽朝的影响力相对较弱。能够反映辽朝地藏菩萨信仰的碑刻,目前仅见两方,分别为大康七年(1081)《义丰县卧如院碑记》和乾统五年《沙门□惠为祖父造陀罗尼经幢记》。前者载:“图地藏之十王,备炽盛之九曜”,可见卧如院绘有地藏菩萨之像。后者提到:“古□□记云,京兆人,□王失其名,本无戒行僧,不修善因,患□致死。被二人引至地狱门前,见一僧云,是地藏菩萨。”[5]555这里虽提及地藏菩萨,但其主要目的在于传播“《大方广佛花严经》一偈之功能破地狱”[5]555的功效,是对《华严经》殊胜能力的宣扬。
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云:“此佛顶尊胜陀罗尼,若有人闻,一经于耳,先世所造一切地狱恶业,悉皆消灭”;“若人先造一切极重罪业,遂即命终,乘斯恶业,应堕地狱,或堕畜生、阎罗王界,或堕饿鬼,乃至堕大阿鼻地狱,或生水中,或生禽兽异类之身。取其亡者随身分骨,以土一把,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散亡者骨上,即得生天。”[20]辽朝盛行轮回观念,而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是避免在轮回过程中堕入地狱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咸雍七年《李晟为父母造幢记》载:“亡过父母先亡等,或在地狱,愿速离三涂;若在人世,愿福乐百年。”[5]347又如道宗末年《云居寺志省石塔记》提到:“伏闻汇六道之趣,覆七返之殃,□诸魔,拔众□者,其为尊胜陀罗尼密言也。若尘沾影覆,□□眼□灾或□目耳闻,能灭恒沙之罪。”[5]491可见碑文对于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功效的认知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宣传别无二致。
本来,在佛教信徒的观念中,地藏菩萨可拯救地狱众生,然而,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风在辽朝的流行,弱化了地藏菩萨的影响力。
结 语
在辽朝社会中,流行着对八大菩萨的信仰。尽管在佛教塑像和塔身雕像等中,八大菩萨经常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但由于八大菩萨具备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其影响力也不尽相同。由于具有多重属性和功能,观音信仰在诸菩萨信仰中遂居于首位,以下依次为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和地藏菩萨。值得一提的是,辽朝弥勒净土信仰在诸多的净土信仰中居于主要位置,当时多有讲《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信徒。而除盖障和金刚手二菩萨出现频率较低,影响力有限。在辽朝碑刻中,能反映出观音信仰的共有37方,其他为:弥勒菩萨30方、普贤菩萨15方、文殊菩萨12方、地藏菩萨2方[5][12]。此外,在房山石经中还可见香王菩萨,但当属小众信仰。
不同类型的菩萨信仰,反映了辽朝佛教信徒不同的心理诉求。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过程包括认知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据此可以推知,佛教信徒首先是对诸位菩萨的个体形象和功能等基本情况产生总体认知,在此基础之上产生复杂的情感倾向,最后立足于个体的情感体验,产生不同的动机。这也使诸位菩萨信仰在流行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
菩萨信仰是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菩萨信仰的盛行使佛教信徒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兼顾他人,因此辽朝佛教信徒建义仓、义冢及义桥的事例颇多。再者,在辽朝佛教信徒的观念中,建经幢是大功德,故亦屡为之。这体现了辽朝佛教信徒在菩萨信仰的影响下,产生了自度、度他的情怀,从而使社会上形成了良好风尚。同时,菩萨信仰的流行,也提升了佛教信徒对佛教典籍和义理进行钻研的热情,这也是辽朝涌现出大量佛学著作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