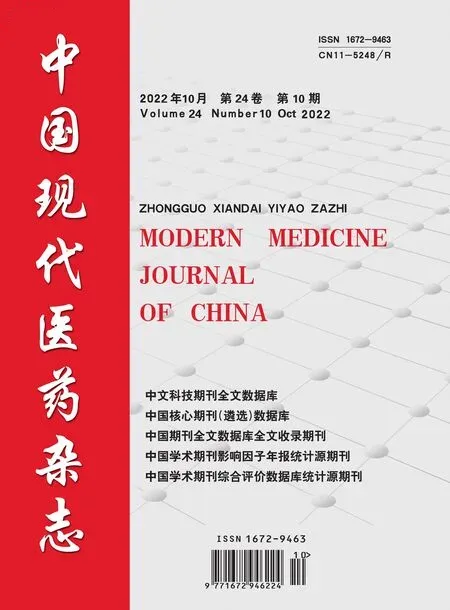亲属陪护对老年下肢骨折患者康复的影响
赵杰 王金露
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逐年递增,老年骨折患者日益增加,老年患者住院卧床治疗期间,需要有专人进行陪护和提供生活照顾。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越来越重视,研究发现,负性情绪对骨折患者的疗效、转归和预后有重要影响[1]。为深入了解老年患者住院期间的陪护现状与需求,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病历资料相结合的方式,探讨亲属陪护对老年下肢骨折患者康复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我院2019年5~12月收治的120例老年下肢骨折患者,其中男55例,女65例;年龄65~85岁,平均75.2岁。按陪护人员类型将患者分为亲属陪护组(53例)和非亲属陪护组(67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下肢骨折类型、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n(%)]
纳入标准:①患者年龄65~85岁,住院时间大于1个月,有亲属或者其他人员陪护;②精神状态正常,能够正常与他人进行交流;③在参与问卷调查前3周,未使用影响认知功能的药物;④对于调查问卷内容,能正确理解和表达;⑤根据病情需要长期卧床,日常生活不能自理。排除标准:①患者及家属拒绝配合问卷调查;②患者在问卷调查前3周,使用影响认知的相关药物;③曾经参加或正在参加其他类似的护理干预。本研究经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
1.2 方法结合专家指导、文献检索、病历资料摘取及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2],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所有患者的陪护情况及心理状态进行调查和评估。在充分理解调查问卷内容的前提下,由患者本人或者家属填写。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患者住院一般情况,文化程度,配偶及子女情况,住院期间陪护原因,对陪护人员、陪护类型、饮食等的需求,对陪护满意度及治疗依从性等方面。统计患者住院期间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SAS、SDS评分测定患者住院前、出院后焦虑、抑郁情况,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
1.3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5.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用n(%)表示,组间比较行χ2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行独立样本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累计发放120份调查问卷,所有问卷均收回,且收回的问卷均为有效问卷。
2.1 患者住院陪护意愿、实际陪护及满意度希望陪护的患者占83.33%,其中希望亲属(配偶、子女)陪护的患者占70.00%。亲属陪护组、非亲属陪护组陪护满意度比较(94.34% vs 82.09%),亲属陪护组满意度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老年住院患者住院陪护意愿、实际陪护及满意度调查结果[n(%)]
2.2 患者陪护需求的主要原因患者陪护需求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心理安慰65例(54.17%),生活护理30例(25.00%),疾病需要25例(20.83%),老年患者住院期间有更多的心理需求,希望通过陪护来改善。
2.3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与非亲属陪护组相比,亲属陪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n(%)]
2.4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两组住院期间并发症发生情况相比,亲属陪护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非亲属陪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2.5 两组患者住院前及出院后SAS、SDS评分比较两组患者住院前SAS、SD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亲属陪护组出院后SAS、SDS评分较住院前明显下降(P<0.05),而非亲属陪护组出院后SAS、SDS评分与住院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出院后SAS、SDS评分比较,亲属陪护组低于非亲属陪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表5 两组住院前、出院后SAS和SDS评分比较(±s,分)

表5 两组住院前、出院后SAS和SDS评分比较(±s,分)
注:与住院前比较,*P<0.05
3 讨论
骨科老年住院患者常需卧床治疗,大多患有慢性病,病程长,效果不佳,使之常感力不从心,心理负担重,这一特殊人群处于疾病的特殊时期,容易产生焦虑、恐惧、抑郁、被嫌弃的心理,感到孤寂、交流能力下降,甚至感到绝望,更为严重的患者会产生消极厌世的心理。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患者能否生活自理,住院期间希望有人陪护的患者占83.33%;而住院患者中,亲属(配偶、子女)陪护者占44.17%,非亲属陪护者占55.83%。相对于临床治疗和生活护理方面的陪护,患者更需要精神上的陪护,希望获得他人的关爱及亲人的情感支持。病情越重的患者生活能力越差,依赖性越强,情感需求越高,这些情感需求只有家属能够满足,能够增加其安全感,改善心情,利于疾病恢复[3]。因此,在临床治疗中,陪护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当今社会竞争压力较大,患者亲属大多工作繁忙,住院后谁来承担看护任务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家庭问题,对于长期住院的老年患者,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选择护工来照顾,目前我国护工多数未进行过系统的医学护理知识学习和培训,常采用机械化的方式护理,使患者易产生强烈的被遗弃感。
根据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理论,即生存、安全、爱与归属、尊重与被尊重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有必要将以患者为中心的整体护理观念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结合,重视社会、心理因素与疾病为一个整体[4]。罗春艳等[3]研究表明,相较于非亲属陪护患者,在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方面,亲属陪护患者得分均更高[5]。本研究结果显示,与非亲属陪护患者相比,亲属陪护患者治疗依从性更高,并发症发生率更低。得到亲人尤其是子女和配偶关爱的患者,良好的家庭支持系统使其提高存在感,得到家庭亲情的温暖。患者情绪稳定、心情舒畅,积极参与健康管理,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提高治疗依从性[6]。心理状态的改善使患者更好地配合治疗和护理,提高机体免疫力,促进机体康复[7,8]。
研究显示,亲属陪护组患者生理、心理满足率在住院半个月内高于非亲属陪护患者组,经过精心的护理干预后,住院时非亲属陪护患者的生理、心理满足率明显提高,说明护理干预可以满足非亲属陪护患者的心理和生理需求,改善身心状态,对患者康复有益[9]。但是再优质的护理也不能替代亲属的陪伴,因为亲情关系使患者亲属在日常陪护中更主动、更积极,对患者也更关心、更体贴。陪护可以满足患者多种生理和心理需求,如减轻孤独、情感支持、提供安全感等,从而改善患者机体状态,提高日常生活能力,使患者以良好的心态配合疾病治疗。
因此,医护人员不但要给予患者心理护理,而且应鼓励亲属陪护,使亲属意识到由他们为患者提供陪护更有助于促使患者积极治疗疾病,改善患者情绪状态,帮助其更快恢复健康,结合两者优势,予以引导,使患者心理状态处于良性循环,提高治疗依从性,为临床疗效提供保障。同时,也应从多方面给予非亲属陪护患者关爱,最大程度地减轻亲属不能陪护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