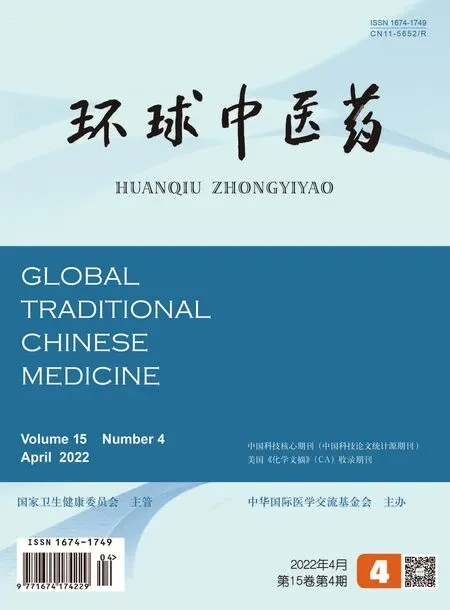从风邪内伏探讨膜性肾病的中医病机及治疗
董晋舟 孙雪艳 申子龙 张见伟 王禹霖 毕聪玥 沈晓琼 郭弋凡 赵文景
膜性肾病是中国肾病综合征的第一大病因,其发病率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中医药对于本病的干预具有重要研究意义。但当代医家对本病中医病机尚存争议,虽多认为本病属本虚标实,本虚或责阳虚、或气虚、或气阴两虚,标实则着眼于风、湿、浊、瘀、毒等各有阐论,可谓众说纷纭。在不同的患者人群中、疾病的不同阶段内,也的确能观察到多种证候。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膜性肾病病机本质,更全面地揭示其病机变化,本研究团队基于伏邪理论,提出“风邪内伏”说,结合六经及脏腑辨证、络脉学说、现代医学发现,讨论本病邪气如何潜伏、其性质如何转化、其病位如何传变,在此基础上,总结中医证治经验。
1 膜性肾病,风邪内伏为始
风邪善窜善入,虚灵流布,为无形之气,侵袭人体时难以发现。膜性肾病起病隐匿,早期轻症患者可仅有尿检异常,或隐匿出现颜面、下肢水肿,严重者周身水肿,符合“虚邪贼风”中人的特点。《素问·水热穴论篇》云:“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胕肿。”此段描述正与膜性肾病起病情状相似,当人体劳作过度,肾气内虚,卫气失司,风邪乘虚而入,由皮肤中人玄府,风气逆乱,干扰水液正常运行,遂可致水液潴留而发为胕肿。
本病病初,经治后水肿尚可速消,蛋白尿却往往迁延难愈,虽然内经云“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但笔者认为病情迁延正是因为风邪不能尽除,循经入里而深伏于脏腑所致。刘吉人在《伏邪新书》中写道:“感六淫而不即病,过后方发者,总谓之曰伏邪。”[1]膜性肾病好发于老年患者,其脏腑气血素亏,风邪乘虚深入,潜存体内,即成伏邪。伏风未发于外则可如“假瘥”,一旦饮食起居失宜,如劳累后触冒外风,或高盐、高蛋白饮食后,体内气机失调,引动伏风,使水湿鼓荡、流行上下,则可致尿中泡沫时消时长,或作或止。
正如张鑫等[2]总结,伏邪具有自我积聚倾向、病机动态演变、潜证导向等致病特点。在膜性肾病中,伏风扰乱经络气机日久,又可内生伏湿、伏瘀等病理产物,病理产物日益积聚,进一步损耗气血、加重气机失调,反过来增益伏风之势。当代医家对于风、湿、瘀等诸多病邪在膜性肾病中的作用论述丰富,如程晓霞教授发现风湿扰肾是本病的始动因素[3];而陈以平教授则发现脉络瘀滞、湿热内蕴是膜性肾病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的病理基础[4]。在临床实践中,膜性肾病患者湿热、水湿、瘀血证均为常见,且可并见。证候兼见时,单利水而血益瘀,单活血而水不行,活血利水尚可破气伤阴,治疗可呈“抽蕉剥笋”之状,常需补益、行水、利湿、活血、祛风等多个层面综合治疗。但从一元论的视角看,本病水湿瘀血等兼夹病邪生于伏风所致的病机变化, 故论致病邪气的主次先后,仍以风邪内伏为先。《素问·风论篇》可为之佐证:“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致有风气也。”
2 病机演变,六经辨证为纲
2.1 风湿相搏,邪由太阴而入
风邪外袭肌表,与太阴里湿相合入里,胶结水血,变生湿瘀,阻塞气机,是膜性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触冒风湿外邪,还是已有脾虚内湿为应,风湿相搏、顽而不化、损耗气血,导致太阴运化输布功能受损、促进湿浊瘀血内生的过程则同。故本病临床常见乏力气短、畏寒易感、腹满便溏等脾肺气虚症候;若进而伤及营血,可见心悸头晕、唇爪不荣、舌色淡黯少苔;或中焦不运,生湿蕴热,则口干不喜饮、便黏、口苦、舌苔厚腻;或兼湿浊则见呕恶、纳呆、周身瘙痒;或水病及血,则见唇舌紫暗、面色黧黑、肌肤甲错等血瘀体征。
现代医学的新发现也可作为太阴受邪之佐证。如侯凡凡院士曾提出PM2.5等空气污染因素与膜性肾病的发病具有相关性,并进一步指出,PM2.5可能使机体产生以磷脂酶A2受体为代表的循环抗体,最终导致足细胞受损,这侧面印证了太阴肺系为膜性肾病发病之门户[5]。此外,有研究发现,在一些儿童特发性膜性肾病患者体内存在高滴度的阳离子化牛血清白蛋白,这提示牛奶或其他食物中的抗原成分可能参与本病病机,太阴脾系运化失调亦可为风邪内伏的重要条件[6]。
2.2 风虚相挟,邪入少阴而伏
《灵枢·百病始生》篇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风邪之所以深入人体,久久不去,是有少阴精气亏虚为内应。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若人能养慎,守其阳神以御其阴精,避风寒、节饮食、慎起居,精气封藏得宜,阳气化阴精而得养,阴精化阳气而卫外充身,即使太阴受邪,而少阴枢转阴阳之功圆融无碍,先天之精助后天之气,邪气亦自得宣布运化而出。相反,若妄加作劳,情志不调,饮食失宜,阳神不守而阴精弛坏,风邪乃得乘虚深伏少阴。所谓“伏”者,与“发”相对而言,即病邪长期潜伏在少阴肾脏,表现为肾脏主水功能的异常,尿中泡沫及水肿时消时长;短期内发作或恶化又可累及多个脏腑,如导致水饮凌心射肺等变证。伏风盘踞少阴,其性开泄,盗精于下,或以伤阳为主,亦可致气阴两伤。
现代医学中不乏风伏少阴的证据。免疫性疾病常累及多系统、且多可反复发作,这与风邪“善行数变”的特点相应。而慢性肾病正是一组免疫功能紊乱造成的自我机体损害,虽有外邪的参与,但外邪祛除后,机体内在自我肾脏免疫性损害却无法终止,王暴魁等[7]因此认为这正是风邪潜存于少阴肾脏的最好证明。
2.3 主客混受,邪自厥阴而陷
“两阴交尽,谓之厥阴”,厥阴为还阴出阳之机,对于疾病而言是邪气深陷、生死之间的最后转机。其病情多危重、寒热错杂。时振声教授[8]曾提出厥阴病本质是阴阳俱衰。膜性肾病若久治不愈,发展至慢性肾衰竭阶段,正不胜邪,阴阳互损而日渐衰弱,乃至阴阳离决,或阴袭阳位、水气凌心;或阴阳痞隔、关格闭塞;或浮阳无根则肝风内动、神昏谵语。此时虽尚有救命之法,而痼疾难除,皆邪陷厥阴、胶结精血,“主客混受”,以至于正气难复之故。
此外,李福生等[9]结合典型病例讨论,认为水寒土湿、阳气郁陷,则厥阴风木当升不升、盗泄肾水于下,是肾病综合征的关键病机。这一观点提示厥阴亦可关系到本病早期进展。厥阴乃“多血少气”之经,涵养精血,内蕴生阳之机,精血不得温升,则伏风转出无望,日渐陷于阴分。
2.4 气展风疏,邪从少阳而出
伏邪之外达必赖少阳“春生之气”。人之一身生发之机,取决于少阳,少阳之气畅,则阳气敷布舒展、生生不息,充于内而达于外,使一身经络之气调达而得以外荣肢节、内养脏腑,一身不正之气得以祛除于外。相反,若少阳之气郁遏不荣,则不足以尽发伏邪于外。
正如吴雄志教授[10]所提倡,“正邪相争则由少阳转出三阳,正邪不争则邪伏三阴”。在膜性肾病中,大多数患者三阴不足为内应,伏风乃得深入,若经补益,部分患者少阳春生之气得复,与内伏之风邪相争,使得伏风从三阴转出,挟水湿阻塞气机而化热于少阳,则可见周身水肿伴口苦咽干、心烦易怒、胁肋胀痛、目赤多眵、舌红苔黄腻、脉弦数等症候。又因太阳、阳明之开阖皆以少阳为枢,故少阳病时常兼有太阳表证或阳明里证,郁热结于太阳则可表现为皮肤瘙痒、头颈汗出,郁热结于阳明则可见大便干结或黏滞,此时通调气机、清热解郁,同时顾护正气,有助于病情向愈。
2.5 游贯纵横,邪气缠绵于络脉
络脉系统外连皮肤、中通经脉、内合脏腑,贯通表里、气血,其生理功能有输布、荣养之共性,又与所在各脏腑之功能相合[11]。《诸病源候论·注病诸候》云:“人气血虚损,为微风所乘,搏人血气,在于皮肤络脉之间,随其游走……去来几微,而连滞不瘥,故谓之微注。”[12]膜性肾病患者多于中老年隐匿起病,与“气血虚损”、贼风“微注”的描述相仿。风袭肌表后,由络脉游走内侵,或与湿瘀等病理产物相合,形成伏邪,最终盘踞“肾络”而致病,而经治疗后,络气通调,伏邪则可由络脉而外达肌表,或透于肠腑及膀胱而随二便出。
所谓“肾络”者,当代医家用之以比拟肾小球毛细血管袢状结构。此乃续叶天士“久病入络”之余韵,从此实现肾小球疾病微观辨证与宏观辨证的巧妙结合。如陈以平教授认为膜性肾病补体活化、膜攻击复合物形成当责湿热或热毒,而毛细血管上皮下免疫复合物沉积、基底膜增厚等病理表现当属“瘀血”证,并将上述病理过程归纳为“湿热胶着成瘀”[4]。刘玉宁教授[13]曾详述“肾络”病分型,提出络弛、络急、络滞、络瘀、络积、络虚等病理变化,以上对于本病治疗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 以风治风,风药通络透邪为治疗关键
俞嘉言[14]云:“失于表者,外邪但从里出,不死不休。故虽百日之远……引其邪而出之于外,则死证可活,危证可安。”引邪外达是伏邪治疗的关键,故活血利湿、行气通络,须贯穿膜性肾病治疗全程。风类药善行善透、无所不至,既可入至幽至深之处,又可达至高至表之位,对于通调络脉、透出伏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治疗时尤须重视风类药的运用,可谓“以风治风”。风既善兼百邪为病,常用的广义风类药,亦往往身兼胜湿、活血、逐瘀、解毒诸效于一身,对于兼夹伏邪可起到相应的作用。如,水蛭、全蝎逐瘀而搜风,僵蚕、地龙通络而息风,双花、连翘散风热而解毒,藤类药祛风胜湿通络,麻黄解风寒而“破癥瘕积聚”。此类风药也正是当代医家治疗膜性肾病的常用药物。
在所有风类药中,本研究团队尤其注重青风藤、穿山龙的使用,二味药通行一身之络气而祛伏风,许多膜性肾病患者经治疗后可出现皮疹、瘙痒,待疹退痒止,肾脏病情亦随之明显好转,此为伏邪由里达表之征象。在此二味药基础上,针对湿、浊、热、瘀等夹杂邪气之偏重,可进一步加减。瘀血重者,加鬼箭羽、刘寄奴、莪术、鸡血藤等活血通络兼养血。湿浊重者,若纳差脘痞,可用小量紫苏梗、木香、砂仁等,辛香轻盈而畅脾络;若大便秘结或黏滞,或大便尚可而好肥甘,师叶天士治湿温“轻法频下”,以土茯苓、土大黄,配伍小量酒大黄,导伏湿、兼活血而理肠络,使伏湿自大肠而出。又善用玉米须、白花蛇舌草,配伍覆盆子、菟丝子等,通涩并施,复肾络之荣养、通水路之滞塞,则清浊自小便而分。病初,邪袭气络,则僵蚕、蝉蜕祛风通络,病久,邪踞血络,则水蛭、虻虫之属逐瘀通络。
4 审察六经,辨病深浅转归为治疗基础
治疗本病一方面须以风类药起引邪外达、画龙点睛之效果,另一方面,则需要诊察病家,探明伏邪内侵的深浅、出入的态势,所在何经,发为何证。
4.1 健运太阴,屋宇坚厚则风歇
邪由太阴而入。本病初起,风气与水湿相搏不解,如风行雨施,发为水肿、泡沫尿,此时治疗总以健运太阴、祛风除湿为要。脾肺气实则如屋宇坚厚、窗密瓦严,风雨自可得避,反之,脾肺虚则如屋陋窗薄,风雨交加,永无停歇。方药往往以四君子汤、保元汤为基础加减化裁。太阴运化不及,水谷津液变生有形实邪,痰气盛者,加白芥子、紫苏子;湿气盛者,加薏仁、苍术;湿浊者,加土大黄、土茯苓;食积者,加焦三仙、鹅枳实;瘀血者加莪术、鸡内金。兼外感时,常加用麻黄、连翘、桑白皮等宣肺祛风。此外,常配合芪鲤鱼汤食疗,以健脾益气,提升血白蛋白水平,减轻水肿。
4.2 枢转少阴,水火得藏则风停
邪气于少阴而伏,在疾病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伏风日益损耗肾精肾气,盗泻阴精阳气于下,进一步加重气机的逆乱。益肾固精、调和阴阳、扶正托邪是治疗关键。根据首都国医名师张炳厚教授“补肾八法”[15],治疗本病可温补、涩补同用,可以菟丝子、覆盆子益肾固精,二者配伍温阳涩精而不至于燥热,精气固涩则阴阳自复。又根据阴阳偏盛,调整二味药比例,阳虚者以菟丝子为主,或加沙苑子,或少量附子、麻黄,以助少火生气;阴虚者以覆盆子为主,或加女贞子,或施以麦冬、五味子以助金水相生;阴阳俱虚、气血皆惫者加以阳和汤阴阳双补、扶正托邪;又有阴阳不交者,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佐以丹皮、莲须、黄连、升麻等清心之品,沟通阴阳。此外,又常涩补、通补并施,例如常以莲须、玉米须同用,前者固涩肾精,后者利水渗湿,两相配伍,清浊自分、相得益彰。
4.3 峻补厥阴,拔瘀生新则风灭
邪气在厥阴而陷。若患者就诊即时,病情尚浅,经治疗后水肿好转,便当注意温养精血,是“先安未受邪之地”,起巩固善后之功。当疾病进展至慢性肾衰竭阶段,主客混受,精血难复,由于厥阴多血少气,易生瘀血,故常需峻补与通络并施,临床中常用动物药,或以血肉有情之品补其真阴,或以虫蚁通络之类祛其败血。如用鹿角镑填精血强腰脊,鳖甲祛败血而复真阴,牡蛎软坚而潜阳育阴,水蛭、地龙等活血通络。此外,植物类药又常用三棱、莪术破血逐瘀通络,大青山灵芝、黄蜀葵花等补益精气,赤白芍、当归、熟地等滋营血以涵养厥阴。
4.4 调和少阳,气畅郁伸则风疏
邪气由少阳转出。伏风发于少阳,欲达不达,胶结水湿而化热,郁遏于三焦,治以通调三焦气机,分消水湿,清解郁热,如此则伏风不与湿、热相结,自得疏解。可用三仁汤宣畅三焦气机,或根据上、中、下焦病情轻重而酌情加减。如常用麻黄、桑白皮,宣肺气、开鬼门,使“上焦得通,津液则下”。又可用薏仁、瞿麦、淡竹叶等淡渗利水之品,佐以少量肉桂、黑附片,取法于栝楼瞿麦丸以助下焦膀胱气化、洁净府。气血生化有源,少阳之气乃蓬勃调达,气机得通,故又可用黄芪、木香、砂仁,调畅中焦气机,益气行气而行水[16]。此外,少阳转出太阳,兼见皮肤瘙痒者,可予张炳厚教授五皮五藤饮,以祛湿活血、行气疏风[15];少阳转出阳明,兼见大便干结者,效法大柴胡汤,选用醋柴胡、酒大黄,行气活血、通腑泻热。
5 验案举隅
患者,男,49岁,以“水肿3月余”就诊。患者就诊前3月余劳累当风后出现双足水肿,伴局部皮肤瘙痒,未予重视。1月前水肿逐渐加重,就诊于北京某三甲西医院,查血肌酐100 μmol/L,血尿酸440.8 μmol/L,血白蛋白18.5 g/L,24小时尿蛋白定量6.04 g,诊断为“肾病综合征”,建议肾穿刺活检及激素治疗,患者拒绝,遂至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门诊要求中医治疗,查血压正常,抗磷脂酶A2受体抗体1039 RU/mL,抗核抗体系列、ANCA、血/尿游离轻链蛋白测定、乙肝五项、肿瘤标志物未见异常。首诊症见:双下肢重度可凹性水肿,尿中大量泡沫,无夜尿,乏力腰酸,稍畏寒,双下肢皮肤瘙痒,时有鼻塞,纳眠可,大便调。舌淡、苔薄白,脉弦细。现代医学诊断:抗磷脂酶A2受体抗体(anti-PLA2R)相关膜性肾病;中医诊断:水肿,脾肾气虚、风伏肾络证。予中药汤药口服,治以健脾益肾固精、理气祛风通络,每月定期复诊。初诊处方:党参30 g、炒白术20 g、茯苓皮30 g、生黄芪30 g、桂枝15 g、苦杏仁10 g、桑白皮20 g、白芷15 g、辛夷10 g、当归20 g、覆盆子30 g、菟丝子20 g、青风藤20 g、玉米须10 g、北柴胡15 g、莪术15 g。患者服药后双下肢水肿,尿泡沫减少,畏寒改善,周身出现大量皮疹,色暗,触之碍手,干燥脱屑,口干喜冷饮。舌淡黯、苔薄白,脉弦细。遂兼治以健脾祛湿、凉血祛风,先后以五苓散、五皮五藤饮等加减治疗,周身皮疹瘙痒仍作,口干转喜热饮,伴眠差,六诊时内服中药乃改予阳和汤兼加益气养血、祛风通络之品,联合归藤洗剂外用养血祛风。药后患者皮疹脱落,瘙痒缓解。复查24小时尿蛋白定量已降至302.4 mg/天,血尿素氮4.97 mmol/L,血肌酐65.3 μmol/L,血尿酸586.3 μmol/L。以养精血、祛风通络之剂巩固善后。
按 患者起病时水肿伴低蛋白血症,表现为肾病综合征,完善相关化验以除外狼疮、肿瘤、乙肝等膜性肾病继发性因素,并据2020KDIGO指南诊断为PLA2R抗体相关膜性肾病。患者劳累当风后起病,劳则耗伤脾肾之气,复触冒外风,风邪乘虚内客经络,气机不利,故外见肢表困乏,风邪循经入里,内袭肾络,鼓荡水湿,肾气化失常,精微下注,湿浊上逆,故见水液泛溢,尿中大量泡沫。初治以健脾益肾固精、理气祛风通络,患者水肿明显减轻,尿蛋白亦有所下降,继而由皮肤瘙痒逐渐出现大面积皮疹,为伏风经过益气祛风通络治疗之后,发于体表,征于有形,因皮疹色暗,《外科症治全生集·阴症门》“夫色之不明而散漫者,乃气血两虚也”[17],可知此属阴证,故虽以凉血祛风之剂亦不能尽透伏风,终以阳和汤治疗,阴中求阳,补肾温阳通络,则伏邪尽达于表,皮疹脱落,脾之运化、肾之气化恢复,清升浊降,水肿消而尿中泡沫几无。
6 总结
膜性肾病病程漫长、病机虚实夹杂,风邪侵袭是其发生的始动因素,三阴不足是风邪内伏、病情迁延的基本前提,伏风与湿浊瘀血等病理产物胶结是病情进展的关键因素,少阳之气调达、络脉通畅是伏风外达、疾病痊愈的重要条件。在治疗过程中,当谨守药到病所、托邪外出、顾护正气之原则,随证施治,以调畅气机、祛风通络贯穿治疗全程。与此同时,开展高质量循证医学研究及基础研究,有助于验证从“风邪内伏”治疗本病的独到疗效,并进一步揭示中医药手段治疗本病的潜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