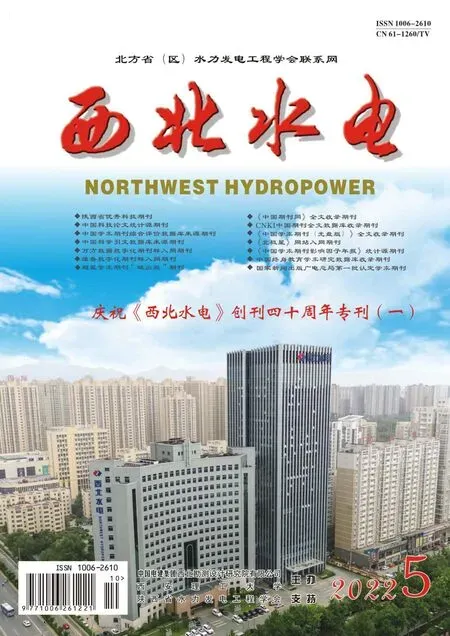西咸新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管子隆,刘 园,强敏敏,张星辰
(1.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 710065;2. 陕西省水生态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安 710065;3. 中国电建水环境治理研究(实验)中心,西安 710065;4.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西安 710065)
0 前 言
土地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组成的复杂系统[1]。土地不仅是人类开展生产生活的场所,同样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基础,有效利用土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2]。而城市化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对当地和全球的自然环境都有负面影响[3-4],因此也一直是学术讨论的重要课题。随着以牺牲自然覆盖为代价的建成区扩张,城市化被认为是“导致不可逆转的景观变化的最剧烈的土地利用变化形式”[5]。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国家,中国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剧烈,其中以建设用地面积急剧增加最为显著,导致大量农田、林地、果园、草地和水域等优质生态用地被占用[6]。新建城区作为我国现阶段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是在新时期发展背景下对区域发展的重新定位。新建城区的不断扩张,必定会带来土地利用的变化,而土地利用作为人与自然联系最为紧密的纽带,其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局部气候及社会生产生活带来冲击,甚至引起更大范围的环境变化[7-8]。土地利用变化日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全球变化的重要课题之一,国内外研究人员从区域差异[9]、尺度效应[10]以及情景背景[11-12]等角度对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进行了专项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下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响应也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13-14]。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应考虑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而如何平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仍然是区域和国家发展中关注的焦点。前期土地利用规划主要注重经济效益,导致生态系统保护压力加大,土地利用效率低下[15]。我国西部地区天然气候条件和生态本底条件较差,用地类型复杂,经济发展和用地类型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城市的全面兴起和发展,土地利用随之发生剧烈变化[16],特别是新建城区的不断扩张导致的建设用地的增加。
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新建城区的代表,西咸新区成立于2014年1月6日,是由国务院发布国函〔2014〕2号文件正式批准成立的我国第七个国家级新区。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和咸阳市之间的区域内,土地面积达到882 km2。随着国家政策对区域发展的引导,新区城镇化在快速推进,随之而来的是土地资源的高强度开发利用,研究人员也针对新建城区影响下土地利用转变、影响因素和环境效应等问题开展了研究[17-18],但就土地利用和区域经济的耦合关系研究还不多。因此,在明晰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的耦合制约关系,对区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同时可为其他新建城区的建设提供决策建议。
本文以新建城区西咸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新区成立前后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情况,分析区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特征和时空变化趋势,选取指标定量评价土地利用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的耦合关系,研究成果为分析新建城区土地利用的演变规律,促进区域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1 研究区域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西咸新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和咸阳市建成区之间(E108°31′47"~108°58′19",N34°10′15"~34°33′16"之间),是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西咸新区规划面积为882 km2,现有户籍人口103万人。西咸新区内根据行政区域细分为空港新城、沣东新城、秦汉新城、沣西新城、泾河新城(见图1)。2018年西咸新区生产总值381.94亿元,同比增长13.3%,增速在陕西省各地市中稳居第一。
西咸新区平均海拔约440 m,地貌有径河冲积平原、渭河冲积平原、二级滩、黄土台塬等。新区属半湿润气候,区内有隶属黄河水系的渭河,泾河、涝河、沣河、新河、沙河、皂河7条河流穿过,区内河流覆盖总长度约为118.97 km。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32.0 mm,多年平均气温12 ℃左右。
1.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土地利用数据根据新区成立时间,分别选取了新区成立前的2010年和成立后的2015、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数据选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resdc.cn),数据在Landsat遥感影像数据基础上,通过人工目视解译得到,分辨率为30m。结合研究区域实际情况在原有的分类基础上将研究区内用地类型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和水域。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于西咸新区统计局。
1.3 土地利用变化率
土地利用面积变化率是对一定时期内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一个具象性表达,它能够反映研究区的一个变化趋势,其中又可细分为相对变化率和净变化速度[19]。相对变化率是较研究区内初期的变化而言,净变化速度则是对研究区年均变化速度的一种表达。根据分析研究区内的面积变化率、相对变化率和净变化率,从而得到一个多纬度的系统分析结果。
(1)
(2)
公式(1)~(2)中:Nc为面积的相对变化率;Rs为净变化速度;Ua、Ub为研究期始末时间点的面积,km2;T为时间段,a。此处涉及的变化面积,均不包含各类型的相互转入与转出。

图1 西咸新区位置及区划范围
1.4 土地综合利用程度
土地综合利用程度反映了某区域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土地利用强度,其包含了自然环境和人类生产生活等活动对土地利用产生的综合影响。本文参考Zhuang等[20]定义的土地综合利用程度指数,包含了4个等级,同时对每个级别赋值相应的指数,具体见表1。

表1 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表
基于各土地利用类型分级指数表及面积,通过计算土地综合利用程度来评价不同阶段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程度。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3)
公式(3)中:L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Ai为i级的分级指数;Ci为i级指数对应用地类型面积百分比;n为总的分级数。
由于未利用地本身存在天然条件不适宜开发等因素,其对区域发展的体现程度较低,因此,为消除这一影响,在计算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指数时,增加了一种情景,即排除未利用地面积作为调整后的指数。
2 结 果
2.1 土地利用变化
不同时期西咸新区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如图2所示,统计不同时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及所占比例见表2。由图2可知,3个时期西咸新区土地利用类型当中,耕地面积所占比例最高,是该区域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建设用地次之,未利用土地面积最小;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由大到小为:耕地>建设用地>草地>水域>林地>未利用地。分别计算比例可知,2010、2015年和2018年耕地面积所占比例分别达到72.57%、67.38%和65.56%,建设用地面积所占比例分别为20.64%、25.90%和28.21%,而未利用地则仅为1.16%、1.32%和1.13%。

表2 不同时期西咸新区土地利用格局

图2 2010—2018年西咸新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分布
由表2同样可知,自2010年起,西咸新区耕地、林地和水域面积均逐年减少,其中耕地的减少幅度最大;建设用地面积呈明显的增加趋势;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则存在波动变化。计算不同时期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率见表3,2010—2015年耕地面积减少最明显,达45.65 km2,林地次之,草地面积减少最少,仅为0.29 km2。消除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基数的影响,由相对变化率和净变化速度可知,林地面积的相对变化率和净变化速度最大,分别为-8.55%和-1.77%。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增加,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最多,为46.27 km2,其相对变化率和净变化速度同样最大,分别为25.48%和4.64%。2015—2018年耕地、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仍同前一阶段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则出现和前一阶段相反的变化趋势,草地面积由减少变为增加,未利用地面积则由增加变为减少。与2010—2015年相比,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的净变化速度均有所增加,其中,草地变化最大,为前一时期的6.4倍,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变化速度均有所降低。纵观整个研究阶段,耕地、林地和水域面积减少,建设用地面积逐年增加,草地面积总体有所增加,未利用地面积先增加后减少,整体有所减少;净变化速度由大到小排序为:建设用地、林地、耕地、水域、草地和未利用地(见图3)。

表3 2010—2018年西咸新区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2.2 土地利用程度
设置调整前(考虑未利用地)和调整后(不考虑未利用地)两种情景进行土地利用程度分析,分别计算两种情景下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结果见表4。3个时期区域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均在320左右,远高于苏明伟等[21]计算的陕西省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2010年为226.57,2018年为232.25),表明该区域土地利用程度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

表4 西咸新区土地利用不同时期程度综合指数
调整前后西咸新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均随时间而呈增长趋势,结合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变化分析可知,虽然耕地和林地面积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的减小,但是建设用地面积的急剧增加使得区域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整体呈现增长。对比调整前后两种情景,区域整体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均有小幅度增加。

图3 不同时期西咸新区土地利用净变化速度

图4 西咸新区2010—2018年土地利用综合程度空间
基于ArcGIS10.2对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见图4)。由图可知,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较低(小于200)的区域面积较少,主要分布在流经境内的渭河和泾河附近的区域;指数在200~300的面积分布最广;土地利用程度较高(大于300)的区域在零散分布的基础上又存在几个集中的区域,分别为新区北部泾河新城的西北部、空港新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附近、新区东南部沣东新城大部,其中沣东新城土地利用程度高的面积最大,其主要原因为沣东新城属于西咸新区最靠近西安市主城区的区域,其城市建设和土地利用变化受西安市影响较大,土地利用程度普遍较高。从时间角度看,土地利用程度高的几个集中区域随着时间推进在不断扩张。由于新区内5个新城的产业引导政策略有不同,导致每个新城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存在一定差异。在同一区域内,地况基本相同情况下,政策的导向同样对土地利用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3 土地利用效益
选择单位面积GDP为评价指标,定量评价不同时期研究区土地利用效益。为真实体现区域经济变化,GDP均转化为2010年可比价。同前节一样分为调整前和调整后两种情景分析。随着西咸新区的建成,区域土地利用效益增长明显(见表5)。计算增长率(见表6)可知,整个研究阶段(201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效益增长率最高,增长一倍以上,而2015—2018年土地利用效益的增长率仅为26%左右,远低于2010—2015年的70%以上。

表5 西咸新区土地利用效益

表6 西咸新区土地利用效益变化率
3 讨 论
3.1 土地利用程度与区域发展相互关系
为定量分析区域土地利用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直接的关系,选取单位面积GDP来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指数(建设用地在区域总面积中所占比例)来表示城市化水平,土地综合利用程度指数来表示区域土地利用程度。同样分为调整前(区域总面积)和调整后(剔除未利用地面积)两种情景,分别计算两种情景下对应时期西咸新区各指标(见图5)。由图5可知,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同空间城市化指数、单位面积GDP均呈现出同增同减的关系,随着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增加,西咸新区的空间城市化指数和单位面积GDP均呈上升趋势。由于区域内未利用土地所占比例较小,因此,调整前后土地利用程度与区域发展的内在耦合关系未发生明显变化。2014年西咸新区的正式成立,使得城市化进程加速,伴随着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的增加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图5 西咸新区土地利用程度与区域发展关系
2010年在城区未建设阶段,区域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增长缓慢。2010—2015年为新城区建设伊始阶段,扩张性增长较为突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也大幅度提升。由于城区新建时期,政府引导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投入力度增加,但实施中很多政策、制度建设及落实还不够完善,发生了建筑用地面积增大过快、空间城市化指数增长过快等现象。2015—2018年期间,经过几年快速发展,政府对区域发展定位及运行方式进行适当调整,由大力度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转为创新城市发展方式,注重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调整产业结构,以创新为动力促进产业升级。因此,建设用地增长变缓,但能保持区域GDP持续增长,逐步开始走上又快又好发展的道路。
3.2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土地利用受自然和人类活动共同影响,而人类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加之城市发展带来的活动强度提升,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愈发强烈。主要驱动因素如下:
(1) 人口变化是土地利用变化最活跃的影响因子,人口的增长必然伴随着居民建筑和城镇用地的扩张,西咸新区成立前的2010年,人口为77.95万人,成立后的2015年和2018年分别增长至91.50万和102.32万,增长率分别为17.38%和31.26%;结合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指数分析,两者存在很强的线性正相关,R2达到0.99,表明人口增长是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驱动因素之一。
(2) 西咸新区位于关中经济核心区,是新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承担着“共建大西安、引领大关中、辐射大西北”的时代重任。因此,西咸新区的发展必然会伴随着产业集聚、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加速等活动[22],这些将导致区域土地利用的急剧变化,最明显的特点即建设用地面积在3个时期出现连续增加。根据《西咸新区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年)》,2030年新区城市建设用地将超过272 km2,城镇建设空间规划总计达到344 km2,城镇建设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将持续贯穿新区的发展过程。
(3) 西咸新区作为现代化新区,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融入了更多的生态和景观措施,如海绵城市的建设中采用的生物滞留池等LID设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区域内水域和草地的面积[23]。
4 结 论
基于西咸新区建成前后的2010—2018年三期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数据,探析新区土地利用动态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得出以下结论:
(1) 耕地和建设用地是西咸新区最主要的两种土地利用类型,两者面积在流域总面积占比在90%以上。2010—2018年区域耕地、林地和水域面积连续减少,其中耕地面积减少最明显,所占比例由72.57%下降到65.56%;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所占比例由20.64%增加到28.21%。土地利用变化与新区建成发展过程基本吻合。新建城区经历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该过程中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的扩张应做好平衡。
(2) 研究期内西咸新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均大于300,普遍较高,且随时间逐渐增大,2010—2018年增长了2.60%。空间上新区东南部土地利用程度较高,西北部略低。地理位置带来的大城市辐射效应的差异以及政策导向是土地利用程度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3) 2010—2018年西咸新区土地利用效益连续增长,增长超过114 %,土地利用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既能相互表征又有相互制约关系。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为政策性引导的人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