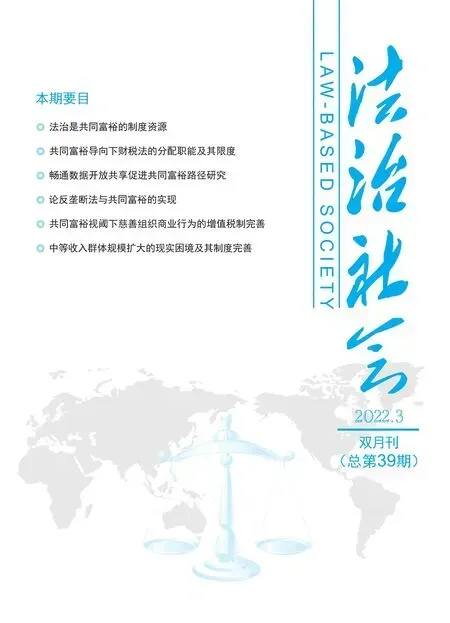共同富裕与法治
——宪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条款的融贯解释
姜秉曦
内容提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对它的法治保障应以 《宪法》 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为宪法基础。 不过, “社会主义” 的共同富裕本质与 “法治国家” 的个人自由底色共同塑造了这一宪法概念的内在张力, 对于两者紧张程度的不同理解或将对我国共同富裕法治建设的基本方向造成根本影响。 为此, 通过借鉴德国公法学说, 本文拟通过融贯解释, 在自由与平等的对立统一中调适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范内涵。 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指导, 我国的共同富裕法治建设应以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安全保障为前提, 以坚持市场经济体制、 解放生产力为物质基础, 以形式法治为制度保障, 以“原则模式” 为实现方式, 遵循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 在自由与富裕的基础上为实现社会平衡、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系统、 全面的法治保障。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 要求到2035 年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相应的法治保障不可或缺。正如李林教授所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追求。”①李林: 《加强新时代人民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 载 《民主与法制周刊》 2022 年第1 期。不过, 在具体推动共同富裕法治保障的制度建构之前, 尚有一个宪法层面的元问题亟待澄清, 即应当如何看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宪法》) 第五条第一款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内在张力。 在当前的宪法秩序中,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成了指导我国共同富裕法治建设的宪法基础, 对于其中“社会主义” 与“法治国家” 之间是否存在、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紧张关系的不同回答, 或将影响我国共同富裕法治建设的根本方向。
有鉴于此, 本文拟从宪法文本出发, 借助教义学作业, 首先阐明“社会主义” 的共同富裕本质与“法治国家” 的个人自由底色共同塑造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张力; 其次, 通过借鉴德国学说, 进一步论证两者在宪法规范体系内相互融贯的可能性; 最后, 立足于两者的对立统一, 明确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下, 我国共同富裕法治建设的总体要求与根本方向。
一、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体两面
在现行宪法的规范体系中, 《宪法》 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构成了探讨共同富裕法治保障的重要前提。 从文义结构上看, 该语词由“社会主义” 与“法治国家” 两项要素构成, 下文将分别对其展开规范分析, 以厘清其各自的规范内涵, 进而探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概念是否存在内在张力。
(一) 社会主义的规范内涵
“社会主义” 是我国宪法的根本内容, 它在现行宪法文本中出现了50 次之多, 分别被用来修饰“国家” “市场经济” “民主” “法治国家” 等内容, 与我国的发展道路、 指导理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政策和制度设计息息相关。 鉴于此, 当前学界多从“根本属性” 的角度解释“社会主义” 的宪法内涵, 认为“宪法文本中的‘社会主义’ 主要宣示国家制度的性质、 国家价值观以及国家发展方向”。②韩大元: 《中国宪法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规范结构》, 载 《中国法学》 2019 年第2 期。典型如, 马工程《宪法学》 教材所代表的学界通说, 就以《宪法》 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为核心将“社会主义” 解释为了国家性质。③参见 《宪法学》 编写组: 《宪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 第110 页。然而, 上述解释方案“只是在价值论维度上表达社会主义之于宪法的高度重要性, 或者说根本性”, 未能从规范论维度揭示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质与规范内涵。④张翔: 《“共同富裕” 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 载 《法律科学》 2021 年第6 期。
基于规范论的立场, 宪法规范根据自身特征与适用方式的不同, 可在性质上被区分为宪法规则与宪法原则。 其中, 宪法规则是指由假定、 行为和处理三部分构成, 须以“全有或全无” 的方式被适用的 “确定性命令”; 宪法原则是指宪法规范中能够作为宪法规则的来源和基础, 并应 “在法律上与事实上可能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被实现” 的“最佳化命令”。⑤参见雷磊: 《法律体系、 法律方法与法治》,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第45-51 页; 周尚君主编: 《法理学入门笔记》, 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 第73-76 页。通过“原则—规则” 二分的一般法理论考察, 现行宪法关于“社会主义” 的表述集中分布于“序言” 与“总纲” 两部分, 内容上主要涉及国家历史、 基本制度与基本国策, 在性质上属于最佳化命令, 理应划入宪法原则的范畴。 不仅如此, “社会主义” 在宪法正文的规范表达中被首先置于 《宪法》 第一条, 用以宣示宪法所调整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 在宪法规范体系中居于根本地位, 应被进一步解释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⑥关于社会主义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详细论证, 参见前引④, 张翔文。而作为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原则构成了宪法秩序的“内在统一性与评价一贯性的基础”,⑦前引⑤, 雷磊书, 第45 页。对其他社会主义规范发挥着价值贯彻和规范诫命的作用。 其中, 《宪法》 第五条第一款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便在社会主义原则的辐射范围之内, 受到后者的价值形塑。 换言之, 现行宪法中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社会主义” 的解释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 首先, 从文义上看, 现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一词并非我国所固有, 而是一个德国概念, 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该学说的提出旨在改变十九世纪下半叶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愈发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日益尖锐的阶级对立, 希望通过建立一个能够适度干预社会经济、 保障公平分配的国家, 以实现社会平衡, 从而确保实质的个人自由和法律平等。⑧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Entstehung und Wandel des Rechtsstaatsbegriffs, in: ders., Staat, Gesellschaft, Freiheit, Suhrkamp, 2.Aufl., 2016, S.76-77.德国社会法学家察赫 (Hans Zacher) 教授曾就社会主义的词源进行考察, 指出它由 “社会” 词根“social/sozial” 发展而来, 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 代表了对不合理的不平等生活条件的批判, 以及将这种不平等向 “更平等的” 方向的修正。⑨参见[德] 汉斯·察赫: 《福利社会的欧洲设计: 察赫社会法文集》, 刘冬梅、 杨一凡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第17 页。在这个意义上, 宪法所规定的 “社会主义” 不宜再仅仅被视为法价值论维度的“根本性” 宣示, 或法伦理学意义上的“合目的性” 表征, 而应被解释为一种规范性概念。 究其原旨, 社会主义原则包含了对社会经济强者的经济自由权的积极限制, 以及对社会经济弱者的“社会权” 的保障, 应当从维护社会正义、 扶助社会弱者, 实现所有人的社会性共存的角度界定其规范内涵。⑩参见[日] 杉原泰雄: 《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 吕昶、 渠涛译, 肖贤富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 第114 页。由此回到现行宪法的规范语境, 随着邓小平同志在1992 年的 “南方谈话” 中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地阐释为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⑪《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第373 页。现行宪法以“共同富裕” 为载体, 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核即社会平衡理念。⑫参见前引④, 张翔文。加之, 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并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促使国家工作重心转向解决发展过程中不平衡、 不均衡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 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目的论解释显然也指向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平衡理念。
综合上述分析,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 系社会主义原则在法治领域的投射, 其规范内涵包括推动社会平衡、 促进共同富裕, 以实现人的有尊严的生活。
(二) 法治国家的规范内涵
在现行宪法中, 法治国家一词仅规定于《宪法》 第五条第一款,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本条款源于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 并于1999 年通过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完成入宪, 代表了 “宪法中国家形象的建构目标”。⑬韩大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贡献》,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8 年第5 期。根据 “规则—原则” 的二分, 法治国家条款在性质与体系上共同构成了对本国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基本原则——即法治国家原则。⑭详细分析参见姜秉曦: 《中国宪法上的法治国家规范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2021 届博士学位论文。
所谓“法治国家”, 顾名思义, 即“构筑在法律基础之上的国家”。⑮张志铭: 《中国法治实践的法理展开》, 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 第214 页。它与社会主义一样, 也不是传统汉语词汇, 而是译自德国国家法传统中的 “Rechtsstaat”, 属于典型的德语造词 (deutsche Wortprägung)。⑯Vgl.Klaus Stern.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Bd.I, C.H.Beck, 1.Aufl., 1977, S.602; Vgl.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Fn.8), S.66.在德国, 法治国家一词诞生于十八世纪末、 十九世纪初, 是康德、 洪堡与早期费希特等人的自由主义国家学说的产物。 在他们看来, 国家本身就是人类为了保障自由而理性选择的结果,是法之下多数人的结合, 为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去维持法。⑰参见[德] 康德: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 沈叔平译, 林荣远校, 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 第144、 146 页;[德] 威廉·冯·洪堡: 《论国家的作用》, 林荣远、 冯兴元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第36 页以下; [德] 费希特:《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 载梁志学主编: 《费希特著作选集》 (第2 卷), 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 第412、 432页。在此基础上, 经过普拉西杜斯(Placidus) 等学者的学术积累, 德国公法学巨擘莫尔 (Robert von Mohl) 最终完成了法治国家的体系化建构, 并使之成为学界公认的公法概念。⑱Vgl.v.Mangolds/Klein/Stark,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2, C.H.Beck, 7.Aufl., 2018, S.103.根据莫尔的主张, 法治国家代表了一种国家类型(Staatsgattung), 亦即根据不同国家的本质与生活目的所归纳形成的有关国家属性的描述。⑲Vgl.Robertvon Mohl, Das staatsrecht des kǒnigreiches Württemberg, Bd.1, Tübingen, 1829, S.6f.在这个意义上, 法治国家是与神权国家、 专制国家相对立的概念, 它以启蒙哲学的智识成果为依托。 一方面, 它摆脱了神权国家对于信仰的狂热与理性的压制, 将个人在世俗中的自由生活作为国家秩序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另一方面, 它摆脱了专制国家以君主意志为转移的特征, 将客观法而非专断意志作为国家目的的基本实现途径。 综合以上两方面, 施米特(Carl Schmitt) 从实现公民自由的视角进一步强调, “一切无条件尊重现行客观法和现有主体权利的国家” 均可被称为法治国家。⑳Carl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11 Aufl., Duncker & Humblot, 2017, S.129.由此可见, 法治国家的概念原旨即通过公权力的依法律行使, 维护个人的自由与财产, 进而推动“个人主体性的自我实现” (Selbsterfüllung der individuellen Subjektivität)。㉑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Fn.8), S.68.高田敏教授曾就此指出, 法治国家本质上是以追求自由为目的的国家。㉒Takada Bin, Rechtsstaat und Rechtsstaatsdenken im japanisch-deutschen Vergleich, Mohr Siebeck, 2019, S.76.
1997 年, 党的十五大报告初次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基本方略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前述法治国家的自由底色。 报告指出, 坚持本方略是“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㉓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载 《求是》 1997 年第18 期。显而易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提出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重要背景。 鉴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权利经济, 以权利本位、 契约自由为精神意涵, 并在根本上指涉自由、 平等、 人权等人文主义的基质,㉔参见张文显: 《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论略》, 载 《中国法学》 1994 年第6 期。因此, 在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的联结中, 法治建设被赋予了维护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 保障市场主体财产权的重要使命, 以此来奠定市场经济的前提与基础。㉕参见胡锦光: 《市场经济与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载 《法学家》 1993 年第3 期。建基于此, 法治国家建设在价值上无疑蕴含着浓厚的自由属性。 这一点在1999 年宪法修改时同样得到了说明。 在《宪法修正案(草案) 的说明》 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曾强调: “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写进宪法,对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 具有重要的意义。”㉖田纪云: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草案) 的说明——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 (三)》,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 第1082 页。对此, 有学者指出, 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市场经济 “本质里潜藏了对个体所享有的营业自由与财产权之保护”, 具有 “法治下的经济自由应予平等保障” 的价值意涵, 构成了国家机构应当尊重的上位原则。㉗潘昀: 《论宪法上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围绕宪法文本的规范分析》, 载 《政治与法律》 2015 年第5 期。2004 年 “人权条款” 的入宪与“私有财产权” 的修改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一意义脉络中, 《宪法》 文本中的“法治国家”通过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形塑, 确立了自身的个人自由导向。
有鉴于此,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法治国家” 应在法治国家原则的辐射作用下, 被解释为通过法秩序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 以实现保障个人自由、 财产与安全的国家目的。
(三) 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的紧张关系
在现行宪法中,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由社会主义原则与法治国家原则共同作用所确立的国家目标。 随着其中“社会主义” 与“法治国家” 规范内涵的逐渐明晰, 这一概念本身的内在张力亦愈发显现。
具体而言,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 社会主义的规范语境以社会平衡理念为内核, 以共同富裕为本质, 指涉国家的公共性与人的社会性, 要求通过国家干预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合理差别, 从而维系人的社会性共存, 实现人的有尊严生活。 与之相对, 法治国家的规范语境则以个人的主体性为内核, 以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安全保障为底色, 从自由主义的视角着重强调了对于国家权力的防范, 进而推动个体人格的自由发展。 故此,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范内部着实难以天然地和谐共存: 一方面, 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平衡与共同富裕并非免费, 而须以限制社会中部分个体, 尤其是经济强者的自由与财产为代价,㉘参见聂鑫: 《“刚柔相济”: 近代中国制宪史上的社会权规定》, 载 《政法论坛》 2016 年第4 期。势必将与法治国家对于个人消极自由的关注相冲突; 另一方面,法治国家则旨在通过法秩序建构、 限制与规范国家权力运行, 并为社会建立稳定的规范预期, 以避免权力滥用、 保障个人自由,㉙参见李忠夏: 《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 载 《法学研究》 2017 年第2 期。又难免与社会主义对于强化国家权力以积极干预社会的主张产生抵牾。 综合而言, 由于“社会公共性” 与“个人主体性”、 防止“个人自由” 滥用与防止“国家权力”滥用, 以及个人的“实质自由” 与“形式自由” 保障等方面的紧张关系, 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在现行宪法中的确存在着紧张关系, 在本质上直指“平等与自由” “社会与市场” 乃至“公与私” 的矛盾。
二、 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的融贯性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客观存在内在张力的背景下,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之间的紧张程度就成为了我国推动共同富裕法治保障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比较法的角度梳理, 二战后, 德国公法学曾就社会国原则与法治国原则能否相容的问题进行了长期争论。 根据两者在宪法秩序中融贯性的程度差异, 学界最终形成了三种具代表性的学说, 并分别对应三条不同的社会国建设路径。 下文将首先对德国学说展开学术梳理, 并以此为借鉴, 进一步分析我国宪法秩序下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之间的融贯性问题。
(一) 社会国与法治国之融贯性的学术梳理
二战后, 为了弭平战争给德国的经济社会所带来的重创, 扶助社会弱者、 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成为战后初期德国的重要任务。㉚参见张志铭、 李若兰: 《迈向社会法治国: 德国学说及启示》,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5 年第1 期。在此背景下, 1949 年通过的 《德国基本法》 在德国宪法史上首次将 “社会国” 作为宪法原则予以明文规定。 《德国基本法》 第20 条第1 款规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 社会的联邦国家”。 而后, 第28 条第1 款进一步强调: “各州的合宪法秩序必须与基本法意义上的共和国、 民主以及社会法治国原则相符”。 社会国与共和国、 民主国、 联邦国、 法治国一起成为德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并形成了“社会法治国” (sozialer Rechtsstaat) 的提法。然而, 社会法治国甫一入宪, 便因其内部紧张关系而引起了剧烈争议, 很快成为战后困扰德国宪法学的最核心难题。㉛关于相关争论的详细梳理可参见前引㉚, 张志铭、 李若兰文; 李哲罕: 《社会国还是社会法治国? ——以当代德国法治国理论为论域》, 载 《浙江学刊》 2020 年第3 期。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学说莫过于分处争论谱系两端的根本否定说与完全融贯说,以及代表当前通说的折中说。
1.根本否定说
根本否定说由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 教授提出, 他基于自身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 从根本上否认社会国原则与法治国原则之间相互妥协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 法治国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它的核心在于“保证自由的法律技术手段体系” (System rechtslicher Kunstgriffe zur Gewahrleistunggesetzlicher Freiheit),㉜Ernst Forsthoff, Die Umbildung des Verfassungsgesetzes, In: H.Barion, E.Forsthoff, W.Weber (hrsg.), Rechtsstaat im Wandel,Duncker & Humblot, 1959, S.61.具有极强的规范性。 而社会国理念局限于国家为公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存照顾, 属于事实层面的内容, 其内涵始终处于变动之中, 缺乏规范性。 因此, 任何试图在宪法层面调和社会国与法治国的尝试, 很可能反过来突破法治国固有的规范结构, 从而使国家陷入危险的境地, 甚至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死灰复燃。㉝VVDStRL 12 (1953), S.14ff.根据福氏的观点, 法治国与社会国应分置于宪法与行政法两个层面, 其中, 社会国仅处于行政法层面, 难以被置于宪法结构之中, 其建构须更多借助行政权的力量, 通过课予国家生存照顾与给付责任等方式予以恰当实现。
2.完全融贯说
完全融贯说则是阿本德罗特(Abendroth) 教授的基本观点。 他的立场偏向于自由民主主义, 认为社会国原则与法治国原则在战后的宪法秩序中可以完全融贯。 他强调, 根据战后德国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 为了重新构建社会秩序与经济基础, 在传统的自由保障之外, 国家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任务。 为此, 德国必须放弃自由法治观而用新的视角看待法律制度, 不再将基本法上的部分自由权视为现存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考虑重点, 而应重新认识基本权利视野下的社会分享权 (soziales Teilhaberecht)。㉞VVDStRL 12 (1953), S.85ff.换言之, 阿氏从作为基本权利的社会权的角度, 为社会国原则注入了规范内容, 确立了实现社会保障的 “权利模式”, 并在此基础上证立了社会国原则与法治国原则之间的完全融贯性。 根据他的观点, 社会国的建构显然应当在宪法结构内, 通过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实现。
3.折中说
根本否定说与完全融贯说分别代表了对待社会国原则与法治国原则紧张关系的两种极端观点,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 却也有各自的片面性。 具体而言, 根本否定说没有意识到现代工业社会对于宪法秩序的根本性改变。 以1918 年《苏俄宪法》 与1919 年《魏玛宪法》 为界碑, 现代宪法已经被深深地烙上了社会主义或社会国家的印记。 与十九世纪相比, 当今时代对于自由的保障已无法仅停留于消极防御国家之上, 而开始更多要求国家在更广领域内发挥功能。 因为, 对失业者而言, 职业自由只能是一句空话, 而财产权的保护、 居住自由的保护也仅针对有产者与有居所的人才有现实意义。㉟Vgl.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C.F.Müller, 20 Aufl., 1999, S.94-95.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国原则自有其规范价值, 不能单凭内涵不明确就否定其宪法地位。 不仅如此, 由于根本否定说的观点排除了对于社会国建设的合宪性控制, 反而可能导致“国家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干预摆脱民主和法治的约束”,㊱前引㉛, 李哲罕文。并使法治国原则陷入危险境地。 与之相对, 完全融贯说则没有意识到社会权的特殊性。 相较于传统的消极自由, 社会权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利结构。 “当它们被形成、 尊重与保障时, 并不会由此就成为现实, 因为其所包含的社会性内容需要国家通过作为的方式来实现”, “而国家为了实现这些社会性内容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有代价的, 常常会引起对于他人自由权的妨碍或侵犯”。 因此, 正如黑塞所言, 社会权难以作为一种直接的、 可以获得司法保障的基本权利而被证立。㊲Vgl.Hesse (Fn.35), S.91.如果宪法规定了这些基本权利, 而国家难以负担实现它们的对价, 则必将损及宪法权威。
于是, 在调和两种学说的基础上, 萧勒 (Ulrich Scheuner) 教授提出了折中说。 该学说一方面承认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社会国理念对于法治国的重塑, 要求在宪法秩序内承认社会国的规范属性与原则地位; 另一方面, 强调该种重塑仅限于内容层面, 不得在形式上突破法治国的传统内涵。 为此, 萧勒认为应当将社会国原则确立为宪法中的国家目标与方针条款, 使之构成对立法者的宪法委托与实质拘束, 要求在具体立法过程中实现“对一般平等的强调, 对社会弱者的救助, 对社会阶层裂痕的衡平”。㊳Ulrich Scheuner, Die neue Entwicklung des Rechtsstaats in Deutschland, in: Restschrift zum hundertjähriger Bestehen des Deutschen Juristentags, Bd.2, Tübingen, 1960, S.506.这一解释方案代表了社会保障的 “原则模式”, 既赋予了社会国以规范性, 避免其脱离宪法秩序的控制, 又维护了法治国的自由传统, 避免社会权对个人自由的过度挤压, 使“社会国下的平等” 与“法治国下的自由” 受到同步保障,㊴VVDStRL, 11 (1951), S.154.从而得到了德国学界的广泛认可, 遂成为通说。
(二) 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之融贯性的规范分析
社会法治国原则在德国宪法中的发展变迁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同样面对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 国内学界通过对现行宪法的规范分析, 也愈发倾向于折中说。
首先, 从 “共同富裕” 的本质切入, 现行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原则虽以社会平衡为稳定内核, 但此处的平衡并非一味追求限制经济强者和扶助经济弱者的 “平均主义”, 而是代表了一种以物质条件极大发展为前提的高水平共富观。 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主张的那样, 共同富裕首先是全民共同致富, 是解放和发展生产,㊵前引⑪,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第142 页。为此应当 “承认全体中国人民都有追求富裕的权利, 鼓励人民创造财富, 以提升社会生产力”。㊶前引④, 张翔文。依循这一意义脉络, 则当前语境下的社会主义不仅具有规范性, 而且兼具公与私两种规范面向。㊷李忠夏教授即认为现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具有 “公私二元” 的规范结构。 参见李忠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宪法结构分析》, 载 《政法论坛》 2018 年第5 期。它在追求社会平衡的过程中, 并不否认保障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必要性, 甚至将社会的自由和财富作为自身建构的物质基础。㊸参见前引⑨, 汉斯·察赫书, 第40页。建基于此, 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之间至少在融贯可能性上得到了肯定性论证, 根本否定说应当被排除。
其次, 从社会主义原则的实现方式上来看, 我国在1982 年修宪时继承了1954 年宪法的规定模式, 在基本权利章中大量规定劳动权、 受教育权、 休息权、 物质帮助权等社会权, 旨在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中实现社会平衡。 就此而言, 现行宪法似乎采纳了完全融贯说的观点。 不过, 随着2004 年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的通过, 这一认知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该条修正案在《宪法》 第十四条中增加一款, 作为第四款, 规定: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文义方面, 通过本条款中“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的明确规定, 修宪者表明, 他们已经意识到实现社会平衡的物质前提性, 不宜为之设定过高标准, 而应量力而行, 否则或将影响经济运行, 导致平均主义。而在体系方面, 本条款位于《宪法》 总纲, 着重强调了社会保障的制度与政策属性, 以削弱宪法中社会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为学界进一步在“原则模式” 下推动社会权的“方针条款化” 奠定了基础。㊹参见姜峰: 《权利宪法化的隐忧——以社会权为中心的思考》, 载 《清华法学》 2010 年第5 期; 参见王堃: 《社会福利保障的宪法路径选择》,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 年第4 期。综合以上两个方面, 现行宪法进一步排除了完全融贯说的观点, 总体上在折中说的范围内处理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的融贯性问题。
最后, 根据折中说的观点, 在现行宪法中, 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呈现为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分别代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体两面。 其中, 法治国家代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自由面向,它是基础、 是载体、 是形式, 一方面从富裕的维度为推动社会主义、 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 由此指明我国所建设的是一种高水平的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也为后者划定了制度与形式, 要求所有关于共同富裕的建构必须在宪法秩序的辐射范围内。 与之相应, 社会主义则代表了平等面向,它是价值、 是内容、 是实质, 从共同的维度, 确立了社会平衡在法治国家建构中的价值基础与核心内容的地位, 以适度纠正法治国家的自由主义视角, 维系人与人的社会性共存。㊺参见前引㉙, 李忠夏文。
三、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导下共同富裕的法治建设
通过前文的梳理, 本文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张力, 并尝试借鉴折中说予以调适, 使之在对立统一中呈现为兼具平等与自由双重面向的国家目标规范。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下, 我国共同富裕的法治建设应当从以下五方面展开:
第一, 在前提方面, 应当明确个人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主体责任, 通过完善对于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安全保障, 为个人自主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提供有利条件, 以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推动共同富裕向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㊻习近平: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载 《求是》 2021 年第20 期。为此, 国家应 “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不断把‘蛋糕’ 做大”。㊼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016 年1 月18 日)》, 载 《人民日报》 2016 年5 月10 日第2 版。
第二, 在物质基础方面, 应当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将市场自由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 通过竞争机制 “让物品生产、 提供与分配的一般性生活过程” 持续运转, 不断推动技术与经济进步, 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从而为更充分、 合理的社会再分配奠定物质基础。 作为反例, 察赫曾经考察了东欧社会主义福利国家, 指出它们的失败并非由于其特殊的福利社会制度, 而是由于缺乏自由和富裕。㊽参见朱民等主编: 《社会市场经济: 兼容个人、 市场、 社会和国家》, 孙艳等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版, 第171 页以下;前引⑨, 汉斯·察赫书, 第40 页。
第三, 在制度保障方面,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未在形式上突破法治国家在防御国家权力方面的传统内涵, 法治国家原则要求社会主义所课予国家的任何干预、 给付、 分配等任务与责任, 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 并只能在宪法秩序所授权的范围内活动。
第四, 在实现方式方面, 共同富裕因其深受经济水平与社会条件的制约, 应更多作为国家的宪法目标, 通过“原则模式” 下的国家保护义务, 在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各项制度性保障中具体实现, 以避免 “权利模式” 下可能导致的社会权的无限制扩张及其对国家经济的巨大负担。㊾参见前引㊹, 王堃文。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指出: 相应的民生保障应以力所能及为原则, “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重点是加强基础性、 普惠性、 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 例如全面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事业。 “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 财力更雄厚了, 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 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 养懒汉的陷阱。”㊿前引㊻, 习近平文。质言之, 一种涵盖了广泛国家救济, 试图将共同体彻底转换为福利与保障型国家的愿望不符合现行宪法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期待。
第五, 鉴于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之间的对立统一,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下, 我国的共同富裕建设意味着一种向“更平等靠拢” 的历史过程, 势必将会经历从低级到高级、 从不均衡到均衡的复杂脉络, 即使到了较高水平, 仍会存在差别。参见前引㊻, 习近平文。因为绝对的平等标准并不存在, “即便在理想状况下, ‘平等’ 亦可能只不过是对各种差别以平等为取向的整合”。参见前引⑨, 汉斯·察赫书, 第23 页。因此, 我国在推进共同富裕法治建设时, 应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 必须立足国情、 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 既不能裹足不前、 铢施两较, 也不能好高骛远、 寅吃卯粮。前引㊼, 习近平文。
结语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张力塑造了共同富裕独特的法治保障路径, 既不能只看到自由、 富裕而忽视了平等、 共同, 走向两极分化、 阶层固化的极端; 也不能片面强调平等、 共同而摒弃了自由、 富裕, 走向否定市场与竞争、 扼杀社会活力的极端。 我国共同富裕的法治建设应当植根于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的对立统一, 在自由与富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平衡与公平正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性共存。